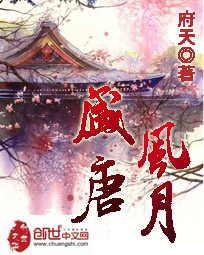盛唐风月-第39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段秀实见两人皆是面色大变;正要解释;不远处一个童子就带着十余随从过来了。
面对这情景;段行琛索性不问儿子了。他也顾不得刚刚还头昏眼花险些栽倒;快步迎上前去后就直截了当地问道:“小郎君怎会来此?大帅呢?”
“阿爷正在鄯州。”杜广元先给段行琛施礼;他不认识其身边的韦伯阳;但看衣冠认人;这点他还是会的;于是像模像样也给韦伯阳行了个礼;这才接下来给二人解释道;“因为姑父和姑母近日就要和宇文师兄送亲一行同来鄯州;必定路过秦州。而秦州如今连震;阿爷和阿娘都担心路上不太平;所以就让我来迎一迎。而秀实阿兄要回陇州探视家人;顺道探望段判官;就一起来了;同行的还有杜二郎。”
杜士仪并没有来;儿子杜广元也不是到秦州凑热闹的;而是来迎接师兄宇文审送亲到鄯州的这一行人;以及其姑父姑母崔俭玄和杜十三娘。得知其中内情;段行琛松了一口气;韦伯阳也恍然大悟。崔俭玄授鄯城令;看似在仕途上并未再进一步;可一连两任都为一地主官;而且是直面外地的县令;在仕途上可谓是扎扎实实的资历;所以他倒很佩服杜士仪和崔俭玄这一对郎舅的胆色。所以;他见杜广元小大人似的一本正经;便笑着逗了一句。
“杜小郎君年方几何;便担此重任;不怕路上遇到艰险吗?”
“我虽年只七岁;可也当为爷娘分忧。”杜广元答了一句;旋即就有些狐疑地端详着韦伯阳道;“阁下已经知道我是谁了;缘何却不告来历?”
竟然被小孩子给鄙视了
韦伯阳又好气又好笑;可还不能完全把对方当成小孩子。毕竟;杜广元能够代表杜士仪到这里来;也就是其父代理人的身份;他总得给予相应的尊重。于是;当他自报家门后;就只见小家伙圆瞪眼睛看着自己;继而又再次唱了个大喏。
“原来是户部韦员外;刚刚是我失礼了我是不放心秀实阿兄;这才特意从上邦县改道来敬亲川来看看;不好多做停留。”
解释过后;他又一拱手;就到段秀实身前低声说道:“秀实阿兄;为免和姑父姑母还有宇文师兄他们错过;我得赶紧走了。你回陇州一路上小心些;记得把我的礼物捎带给伯母和两位阿兄。我要是再不走;否则回头阿爷阿娘知道我给段判官和韦员外添乱;又得骂我了”
他这低声在旁边两个大人听来;全都又好气又好笑;可等到杜广元又过来见礼之后告辞;段行琛想到杜广元还记得给自己的妻儿准备礼物;难免心有所感;坚持要送一程;却被杜广元死活拦住:“段判官;你千万别忙。看你都瘦成这样子了;这些天一定操劳得很;还是顾着大事要紧。我身边的人足够多了;杜二郎还在上邦县废墟那边等呢。我告辞了;还请二位保重。”
杜广元来得快去得更快;韦伯阳都来不及和这小家伙再说两句话。而等他问过段秀实之后;这才知道杜广元口中的杜二郎;并非京兆杜氏的其他族人;而是来自襄阳杜氏的杜甫杜子美;杜士仪虽未曾辟署为判官;却对其才学赞不绝口。尽管他从前和杜士仪并未有多少交情;可从裴耀卿口中;从萧嵩口中;如今又从段行琛身上;都发现杜士仪年纪轻轻至此高位;知人善任确有不凡之处;当即暗暗将杜甫之名记在了心里。
而杜甫之所以没有和段秀实杜广元同行;一则是因为原本的上邦县城正当从长安到鄯州的官道;二则是因为他和杜广元段秀实进入秦州之后;还曾经遇到过一家想要迁居渭州的难民;因为缺医少药以及于粮不足被困在了路上。别说两个小家伙都被父母教导得颇为热心肠;杜甫自己也是难以坐视的。在他们的劝解下;那一家人最终还是决定回到故土来;他少不得负责安置。
尽管州治要移到成纪县的敬亲川;但上邦县也一样是要重建的;如今新城的选址虽晚于成纪县;但也已经有官兵在四处查看此次地震之后变动后的山河地理;预备选址建城。临时安居点在鄯州调派的五百兵马;以及渭州成州调派人手相助之后;已经有了些小小的气象;就连那一片废墟之中也有专人戴着口罩负责清运尸体下葬;防治疫病的几个大夫带着几个学徒;成天在大锅里煎药供人饮服。杜甫只呆了几天;这其中的开销就让他不禁为之蹙眉。
尽管陇右节度因为麾下兵马多;每年朝廷拨付的军费数额巨大;可也不能全部填在秦州;否则;边境的各军可是安抚不下去的
只不过;这样的问题;杜甫就算再怎么心中忧虑;也不可能对杜广元说。这一路上;原本杜广元是按照杜士仪的吩咐;称他为杜二叔的;他却坚称如此会让人觉得他和杜士仪乃亲族;再加上自己年岁不大;死活让杜广元把这个叔字改成了兄字。而杜广元呢;想到段秀实十几岁;杜甫二十几岁;外人面前有礼地称一声杜二郎;人后就高高兴兴一口一个子美阿兄;也一定拗着杜甫人后叫他名字;一来二去;杜甫便仿佛多了个幼弟似的。
当他和杜广元会合之后;得知段行琛和洛阳来的仓部员外郎韦伯阳仿佛关系不错;他就舒了一口气:“对了;广元;萧丞相还未归去洛阳;仍在官驿;大帅昔日是他下属;你是否要去见他一见?”
杜广元从前也见过萧嵩两回;出身世家如今又贵盛一时的萧家那景象;他一直印象深刻。只想了一想;他便立刻答应了下来。果不其然;到官驿门前去通报之后;须臾就有从者来请;就连陪同前来的杜甫亦是得以入见。
杜甫不比李白王之涣和孟浩然之前得了杜士仪扬名;贺知章四处传颂引荐;曾经见过不少权贵;他还是第一次拜见退职宰相这样的人物;难免有些紧张。而比起极具个性的李白三人;他的性格要内敛许多;所以萧嵩对他的第一印象竟是很不错。
而萧嵩对于自己欣赏的人;素来就毫不吝惜善意:“人皆以为君礼年少而居高位;却并没有看到他这多年一任一任;脚踏实地的政绩。而他简拔之文武;如今许多已经独当一面;知人善任可见一斑。子美既然相从君礼;虽不入幕;却一定会有大收获。令祖父当年曾经文盖群豪;名噪天下;假以时日;你他日能继承乃祖衣钵也未必可知;不要辜负了君礼的信赖”
得到这样的期许;杜甫只觉得后背心微微发热;赶紧谢过了。而杜广元在起头相见时叫了一声萧大父之后;就一直乖乖侍立在一边不说话;这会儿见到萧嵩招手方才上前去;笑嘻嘻地应着萧嵩提问说着父母的近况。等他说到是来接姑父姑母以及宇文审送亲那一行的时候;萧嵩突然若有所思地挑了挑眉。
“记得你阿爷去岁巡视赤岭;而后消息外泄;以至于吐蕃犯境的时候;曾经射出过一支司马宗主特制的响箭?那之后玉真贵主奉司马宗主入宫;费了百般唇舌方才说清楚了那不是什么神迹;而是炼丹所造成的会爆炸的废料;司马宗主兴之所至;所以想给你阿爷试试;谁料就闹出了那么一场风波。倘若不是之前据说有神仙术的张果已经被桓州刺史韦济给荐了上京;恐怕陛下还会继续冲着司马宗主穷追猛打下去。纵使至尊;就没有不好长生的。”
倘若杜士仪在此;一定会暗叹司马承祯还真是每次都会沾惹上这种玄妙的官司;可杜广元就不会考虑这么多了。他假装听不懂;眨巴着眼睛继续装可爱;心里却在想;阿娘因为阿爷的要求;找了两个游方道士在鄯州测试什么炼丹废料的爆炸性问题;却没想到京城那位司马宗主遭了秧;回头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阿爷阿娘才行。
萧嵩如今不大理会官场上的事;此次到秦州更是几乎没见什么官员;段行琛也好;杜广元杜甫也好;还都是因为杜士仪的关系。即便如此;他也没有留人谈话很长时间;最后只让杜广元代向杜士仪传一句话。
“日后我就是富贵闲人;他日君礼回京之际;若想下棋钓鱼娱乐尽管来;国事免谈。”
当杜广元终于等到了崔俭玄一行人之后;他立刻对自己在云州和怀远停留期间;一贯很喜欢的姑父和姑姑说出了萧嵩转告的这一句话;而崔俭玄想了一想;就大大咧咧地笑道:“萧丞相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那会儿和裴光庭争得如火如荼之际;他豪气万丈;哪里像现在这样想得开?”
杜十三娘素来心思细腻;却忍不住生出了一个念头。萧嵩这是表示;自己将就此不涉政事;安心养老;恐怕再也帮不上兄长什么忙了?
不论怎么想;夫妻两人对于秦州这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全都心里沉甸甸的。可崔俭玄刚刚拜领了鄯城令一职;不便停留;宇文审也正在紧赶着把妹妹送到湟水;所以;一行人会合之后;便立刻折返回程。尽管官道已经勉强打通;可因为一路上常有陆路转运过来的车辆;他们这一程实在难能走快。倘若不是崔俭玄的到任期限因为这一场地震而得以延期;早就不得不丢下其他人先行奔赴上任了。
这一路又走了十几天;这一日午后申末之后;一行人方才终于抵达了湟水城下。眼见得前头一袭新郎官衣袍的张兴驰马前来;崔俭玄不禁冲着身旁的宇文审笑道:“文申;你妹妹和奇骏还真是好事多磨;我这次总算赶上喝一杯喜酒了”
尽管是兄妹郎舅多年未见;可杜士仪就算再思念崔俭玄和杜十三娘;他如今身为陇右节度;边防本就要紧;又因为秦州之事忙得不可开交;不能亲自到城外来迎接;正好迎亲的张兴就全权代表了。他先是见过了送亲的大舅哥;然后到了崔俭玄面前转致了杜士仪的话;这才到马车前头。还没说话;就只见里头的杜广元探出了脑袋。他着实没想到一贯讨厌马车的杜广元竟然会情愿窝在车厢里;微微一愣便笑了起来。
“小郎君难得这么听话啊”
“嘘;姑姑一路劳累;好容易睡着了;别吵醒她”杜广元把手放在嘴唇上示意张兴轻声;这才眨巴着眼睛说道;“别说得我仿佛只会闯祸;就连萧丞相也夸我大有阿爷之风呢时候不早啦;赶紧进城去见阿爷阿娘吧”
第七百七十九章 郎舅之志
古往今来;婚姻大事就少有如张兴这样自己两手一伸啥都不于的。
他父母双亡;兄弟姊妹皆无;而要迎娶的新娘又远在两千里之外的长安;所以迎亲之事;杜士仪和王容不但从六礼到房宅家具全部包办;就连迎亲大事;也替他请了崔俭玄帮忙。于是;他在湟水城外接着了送亲的大舅哥一行;众人竟是先周顾着他的亲事;最终将新人迎到了鄯州都督府后街的一处三进院子;早就在此等候的杜士仪和王容充了一回男方家长;宇文审这个送亲的充了女方家长;什么却扇障车之类全都弃之不用;竟是须臾就礼成了
杜十三娘适才在路上昏昏沉沉小睡了一会儿;眼下精神奕奕地和王容在后头寝堂招待今日前来赴宴的各家夫人们。而新郎官张兴饮过合卺酒之后;在前头豪爽地应付了众多劝酒的宾客之后;见主宾杜士仪冲着自己招了招手;他赶紧举杯四下一敬酒讨饶道:“今日是我的大好日子;还请各位放我一马;否则醉醺醺的;不但应付不了大帅垂询;而且届时倒头就睡;那丑就要出大了再者我舅兄文申在此;诸位还请容让我这一杯酒;权当是都敬过了”
张兴是陇右节度掌书记;此次婚礼办得并不算极其隆重;出席者除却陇右节度使府和鄯州都督府的一应官员之外;便只有郭建王忠嗣等临洮军中的将领;余者都未惊动。一来是因为他不希望大张旗鼓;二来也是如今秦州骤然遭灾的缘故。故而刚刚别人起哄多灌了他几杯;如今他把杜士仪和宇文审给掣了出来;众人也就不好继续一味强逼了。录事参军唐明代表众人狠狠灌了他最后一大杯;这才放了他回主席。
杜士仪见张兴一面擦汗一面坐下;便笑着说道:“从今往后;你就是有家室的人了;不能再如从前那般恣意;否则文申的性子你是知道的。良宵苦短;我给你三天假;多了没有;你在家中多多陪陪你这娘子;但三日之后;你可给我打起精神来”
张兴本还想推辞;可看到之前还一副长辈样子的崔俭玄冲着自己挤眉弄眼;而宇文审亦是满脸赞同;他只得答应了下来。等到杜士仪默许了他这新郎官第一个逃席;长舒一口气的他出了喧嚣的正堂;各家夫人云集的寝堂;最终来到了内寝门口时;心里竟生出了几分说不出的不可思议。
他一个出身寒门;上溯十几代也没有出仕过的无名之辈;如今竟是迎娶了宇文融之女为妻?
呆立了好一会儿;他方才打起精神上前叩门;未几;大门为人拉开;出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刚刚从寝堂悄然退出来看宇文沫的杜十三娘。许是猜到杜士仪会让张兴先行逃席来此;她微微一笑后便让开路道:“她辞母长途跋涉远嫁;心里难免惶惑。张郎可要好好相待你家娘子。”
“是是;多谢夫人一路陪伴辛苦。”
张兴赶紧长揖谢过;等到杜十三娘出了门来;他闪身进去关上了门;却只见偌大的屋子里;除了新婚妻子及其身边的一个侍婢一个媪妇之外;再不见其他人。大红蜜烛跳动的火光照在那张艳若桃李却带着几分羞涩的脸上;他看着看着;更是生出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犹如提线木偶似的被人摆弄着又是一些繁文缛节;直到侍婢和媪妇含笑退下了;他方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张……郎。”尽管之前喝合卺酒的时候;宇文沫曾经叫出过这样的称呼;可此时此刻;她却不禁更加紧张了。因为之前父亲被黜;而后又死在流放途中;她的婚事耽误了多年;当年宇文氏一族中和她年纪相仿的族姊妹;如今不少都已经膝下有儿女了。婚事定下之前;她曾经死活说动了兄长;悄悄看过张兴一眼;只觉得人虽又黑又壮;年纪也大了些;却仍是英姿勃发一表人才;最终便默许了。
张兴这会儿比自己的新婚妻子还要更紧张些。他年过三十而孤家寡人;虽还不至于不知女人滋味;可正如杜士仪所言;娶得贵妻的心情总是截然不同的。在宇文沫一声张郎过后;以往最是能言善辩的他张了张口;最终迸出了一句话来:“能得娘子为妻;兴之大幸”
如今已经是三月末了;夜空中的一轮残月在群星的包围下;显得黯淡无光。席散之际;杜士仪王容和崔俭玄杜十三娘两对夫妻回鄯州都督府时;杜士仪忍不住打趣道:“我打赌;奇骏今晚这新婚之夜;必定是嘴笨口拙;大异于往日从容风度。”
“平生第一回嘛;在所难免;再说一回生两回熟……哎哟”崔俭玄喝多了几杯;口无遮拦地说笑了两句;突然感到腰中一阵剧痛;惊呼了一声后方才看到旁边满脸怒容的妻子。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他赶紧咳嗽两声;随即讨好地对杜十三娘说道;“十三娘;一路车马劳顿;你又跟着嫂子忙了这么久;实在是辛苦了;等回去了早点休息……”
王容见崔俭玄越说越是小声;在那哄着杜十三娘的样子;一时忍俊不禁;悄悄拉了拉杜士仪的手道:“崔十一郎还真是老样子一点儿都没变。”
“他呀;就得十三娘这样的媳妇才能管住他;所以如今赵国夫人别提多省心了”杜士仪见杜十三娘故意板着脸的样子;忍不住想起了从前的情景;嘴角露出了微微笑容;“只是;真的很久没见到他们了;眼下看到这样子只觉得亲切。只可惜他们顶多就能在鄯州都督府停留一两日;就要启程赶往鄯城。”
“你就别贪心了;能够让你们郎舅俩在同地为官;这已经是少有的。”王容看着如今年岁渐长;却越发显得珠圆玉润的杜十三娘;忍不住想到自己如今也是子女双全;心里自是又熨帖;又安心;见杜士仪不以为然;她知道杜士仪又要拿出张嘉贞兄弟邻州为官;张说和张均父子同在中书省的旧事来;当即也就不继续这个话题了;而是话锋一转道;“今夜你们郎舅俩难免要长谈;我就不等你了;我和十三娘同室而居;姑嫂说些悄悄话”
妻子竟然名正言顺赶了自己去和崔俭玄同宿;而要留下小姑子说话;杜士仪登时无言以对。于是;等回到镇羌斋之后;见崔俭玄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满脸的新奇;他顿时没好气地说道:“你这一来;我就被幼娘赶来睡书房了”
“十三娘这回是有了嫂子忘了夫君也忘了阿兄;我总算心气平了些。”
崔俭玄却很得意;委实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之后;他方才笑眯眯地说道:“要不是你出为陇右节度;我还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当官的好;这下总算不用想了。哎;我倒是想一直留在云州;可王子羽和老郭既然一正一副杵在那儿;其他人要是始终不挪窝;恐怕朝中有些人都要急眼了。就连固安公主;都有人觉得她长住云州不是个事;说是李鲁苏既然都到长安定居了;她也不妨回来;横竖李鲁苏已经不是奚王了……”
这些论调杜士仪并非第一次听说;可崔俭玄此前一任怀远令四年;对于云州的情况可以说如数家珍;此刻一一说来自是滔滔不绝。等到告一段落后;他便叹了口气说:“你要是河东节度就好了;那时候外人可就别想从云州插进手去。”
“我一任云州长史;一任代州长史兼河东节度副使;若是想继续留在河东不走;你以为别人肯答应?只要云州的根基打严实了;外人就算到任也不能为所欲为。更何况;我在陇右站稳脚跟;异日未必不可能重图河东。”在崔俭玄面前;杜士仪毫不遮掩自己的目的;见妹夫对自己竖起了大拇指;他方才上前在其对面坐下;郑重其事地说道;“鄯城令绝不易为;我去岁年底巡视鄯城时;曾经……”
将自己将那赵庆久就地正法;甚至还引来好一阵喧然大哗;苗延嗣更是上书参了他一本的事原原本本道来;杜士仪见崔俭玄果然攒眉沉思了起来;他就说道:“治理一县;不比打仗轻易。不止是鄯城;其他各州县也往往是县令轮轴换;而胥吏却多数雷打不动就是这些人。他们上下勾结;把持政务;往往是将县令甚至县丞主簿县尉全都蒙在鼓里;让主官不但一事无成;有时候还要给他们背黑锅。尽管鄯城那些胥吏已经被我狠狠杀了一回威风;但因为牵涉到郭知礼;我借此清洗了一回军中;但很可能会有人因此对你心怀衔恨;挟私报复;你要小心。”
“我可不是那等软弱的人。”崔俭玄露出了雪白的牙齿;嘿然一笑后就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阿娘和阿兄对我此来鄯州;嘴上说放心;其实心里都是一万个不放心。阿爷当初把赤毕以及跟随他很久的几个人给了你;但崔家不是只有这些人。既然只有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出外任;阿娘和阿兄就把这些人都给我了。当初能够敢跟着伯父和阿爷诛二张;杀阿韦的人;多年寂寞之后能否宝刀不老;就看这一次了而且;我在怀远也没白呆。”
崔俭玄指了指外头;似笑非笑地说:“虽说我不如你这陇右节度能够辟署幕府官;但我可以招募幕佐在怀远的时候;我和王子羽他们很是在那些前来游历的久试不第士子当中简拔出了几个人才。尽管他们对于民政未必熟悉十分;可用来监察胥吏;却是再好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