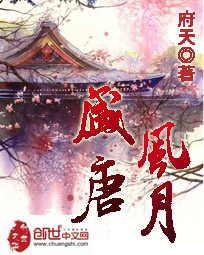盛唐风月-第46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嚷。
“看样子;我们此来兴许无甚必要;阎宽阎将军果是沉稳老将;已然控制了局势。”
口中如此说;来圣严心里却不禁思量了起来。而阿兹勒谨记着杜士仪对自己的承诺;悄悄到旁边拉了个路人询问了两句;等听完对方透露的消息;他不禁愣在了那儿。倘若那是真的;当初即便他不跟着杜广元去灵州;而是留在这里;兴许也能够遇到一个人生中极其重要的机会。可是;那是真的吗?之前杜士仪派遣他跟着来圣严回中受降城时;为何一字一句都不曾提起过?
来圣严一直都没有忽视过杜士仪让自己带上的胡儿阿兹勒;见他悄然去找路人打探;等人回来的时候;他便笑问道:“问到了什么?”
阿兹勒刚刚建功心切;没有请示也没有得到吩咐就自去了;没想到来圣严竟然一直都注意着自己;不禁有些尴尬。他将打探到的布告之事一说;就只见来圣严面露惊讶;而姚晔窦钟以及一应从者牙兵亦是满脸茫然。于是;他不禁小心翼翼地探问道:“敢问;所谓建文武百工诸学的事情;是真的?”
至少杜士仪从来没对他提过这段秀实好大的胆子
来圣严心中闪过这念头;面上却不动声色地说道:“既然已经昭告中受降城上下军民百姓;自然是真的。阿兹勒;你带路;我们到布告的地方去看看。”
从贴出布告;设专人答疑解惑;这已经是第六天了。可是;通衢大道的各大布告张贴处;就不曾断过带着儿孙前来咨询的人。在中受降城中军民百姓看来;一贯高高在上的官府中人;如今却能够坐在那儿耐心地回答问题;虽然每人只限一问;却足以⊥人心满意足了。而那位主持此事的段郎君;奔走于各处;每一现身就会引来众多人一拥而上。
这一次;来圣严等人便是一眼就看到了应接不暇的段秀实。
“这位老丈;你从军多年;如今儿子又在军中;你的孙儿不但符合要求;而且还可以优先录取……”
“不不不;没有贫富高下之分分班。只会根据从前认字与否;从启蒙班一直到初级高级;这位娘子要担心的;是能否让孩子每旬都有相应的时间去就读。”
“汉民胡户并无分别;既然登籍;就都是大唐子民;怎会区别对待?”
段秀实这些天来连轴转;白天应付军民百姓;晚上还要为自己的主意完善所有的细目规定;不断补充写成条陈命人送信给杜士仪;不但人消瘦了一圈;喉咙也早就有些嘶哑了;但他还是不厌其烦地细心讲解。当一旁有人递上来一杯水的时候;他感激地笑了笑;接过来举到嘴边正要喝下;他突然听到不知哪儿嚷嚷了一声。
“段郎君就不怕水里有毒?”
段秀实一愣抬头;见说话的那人已经不知所踪;而一旁那递水给自己的少年显然听到了那句话;脸上露出了极其愤怒的表情;他便笑了起来:“中受降城中;有的是心肠纯良的父老;有的是血气方刚的将卒;没有那么多心怀叵测之徒这位小弟;谢谢你”
见段秀实毫不犹豫就咕嘟咕嘟把那杯水全都喝完了;随即方才还了那个粗瓷杯子;排队咨询的人群中不禁有人叫了一声好。这一声叫好起头;一时此起彼伏全都是叫好声。而面对这样的认同和夸赞;段秀实深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对四面八方拱了拱手道:“诸位乡亲父老;我本是受命而来;做的事情也都是自己分内之事;当不起大家的称赞。我到中受降城才一个多月;可杜大帅上任朔方;却已经眼看就快要三年了”
他微微一顿;即便喉咙仍然有些于涩;但他还是奋力提高了声音:“杜大帅到任朔方之后;赦还了宥州胡户;防止了胡户;又以康将军为朔方节度右厢兵马使;坐镇宥州抚胡;即便当初煽风点火以及骚乱的胡人;也只是本人流岭南恶处;不罪及家眷亲人。所以;那些说什么登籍人户;是为了防范蕃军胡人;无非是自己凭空想出来的胡言乱语朔方三受降城的屯田;是为了防御突厥南侵;为了保家卫国;所以此次登籍;杜大帅已奏明陛下;不增租调。”
这倒不是段秀实自作主张;而是他行前杜士仪特意交待过的。之前他一直隐忍不言;却在连日以来中受降城民心渐定的时候说出来;自然而然就有了相当的信服力。一时间;原本在排队咨询的人渐渐聚拢了来;很快竟是里三层外三层。
而在人群最外端;看热闹的来圣严赞赏地看了一眼阿兹勒;颔首笑道:“你那句质疑水中有毒的话时机不错。好了;段郎君得大帅教导多年;如今又抛出了这样一个杀手锏;不用担心他了;我们走。”
安北都护府中;当心腹从者进来报说;来圣严一行已经轻车简从到了朔方;阎宽不禁暗叹了一声来得好快。当年信安王李炜还是朔方节度使时;他便镇守中受降城;和来圣严打过不止一次交道;对这位节度判官知之甚深;此刻却没有亲自迎出去。
若要摆排场;来圣严何必这样隐匿行踪?
一文一武两人的见面并没有多少寒暄;落座之后;来圣严简要介绍了窦钟和姚晔;却略过阿兹勒不提;随即便直截了当地说道:“我刚刚入城;远远看到段郎君行事;着实抓住了人心向背。所以;我如今并不担心中受降城中再有骚乱;然则此前之事不可不严查。听说阎将军已经把骚乱的胡人各自加以责罚;都放走了?不知道可曾顺藤摸瓜;抓到线索?”
“来判官还是和从前一样;虽初来乍到;却明察秋毫。”阎宽笑了笑后;便露出了森然杀气;“那些宵小之辈百般遮掩;可怎瞒得过我的利眼?若非我打算撒大网捕大鱼;眼下这些人一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不过;眼见如今城中军民不少都被段郎君的宣言打动;他们渐渐又有蠢蠢欲动。是要连根拔起;还是先行收网;来判官发句话吧。”
“那就收网。”来圣严想也不想地迸出了四个字;见阎宽露出了了然的笑容;他见侍立身侧的姚晔和窦钟全都不明所以;他便不吝解说道;“倘若段郎君的登籍能够顺利进行;那么;纵使有漏网之鱼;很快也会露出马脚来”
“好;那就依来判官”阎宽倏然起身;正要传令下去时;却只见来圣严也站了起来。
“若捕拿到一应人犯审讯的时候;请阎将军带上我这个从者。”来圣严指了指阿兹勒;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杜大帅特意让我带上的人。”
即便阎宽有些不明所以;但只是如此一个小小的要求;他自然不会拒绝。等到唤了一个亲兵进来;他先是下了令;继而就把阿兹勒交给了对方。
从这一天黄昏时开始;连日以来再未出动过的安北都护府长史阎宽亲兵;突然再次纵马驰骋于中受降城街头。然而;这次突然行动来得快;收得更快;甚至人们还未来得及做出多少反应;大街上那一队队兵马便倏然收回;再无痕迹。
一夜宵禁之后;在此前段秀实命人贴满全城的布告旁边;又贴出了安北都护府的布告;却是昭告全城上下军民百姓;道是已经抓住了之前散布谣言的首犯从犯数人;将由朔方节度判官来圣严亲自审问。
直到这一刻;中受降城上下军民方才吃了一惊——那样一位大人物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驾临了?
第九百二十章 教化洗脑,胡儿有智
连日以来;段秀实几乎是一日一书;将自己在现场为中受降城军民答疑解惑时想出来的增补条陈;用快马急送灵州都督府杜士仪面前。、
自从得知段秀实竟然在登籍人户出现骚动后;想出了那样一个办法游说上下军民;杜士仪虽赞赏于他的急智;可也恼怒于他的大胆。但平心而论;倘若不是他多次对段秀实熏陶学校和教化的重要性;甚至举出过陈宝儿管理云州培英堂的例子;段秀实也不会在那种时候想出那样先斩后奏的主意来。所以;他已经决定;倘若段秀实归来之后;功过自要分别奖惩;可他将就此顺势在整个朔方推行这样的义学制度。
和嵩山卢氏草堂以及云州培英堂的模式不同;这一次;他打算利用后世英国主日学校的那种模式;每个适龄的孩子每旬上两天课。如此贫苦之家不至于少了劳力;学校的老师也不至于缺口太大。至于教授百工及农艺的学校;则是采取和传统学徒制结合的双轨制。
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还有另外一样东西需要进入议事日程。
这天黄昏;当他回到妻子的正寝门前时;就只听里头王容正在教导杜幼麟背诗。他这个幼子如今是四周岁有余;但若按照约定俗成的算法;过了年就已经六岁;也到了该启蒙的时节。和杜广元不同;杜幼麟的性子更加安静一些;当初甫一认字不多时便已数百个;如今何止能够背诵七言绝句;甚至已经开始背班超的两都赋。此时此刻;听到那清亮的童声正背诵到“国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业”;眼看一首西都赋竟是快背完了;他不禁站在门口暂未出声。
等听到最后那一句“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遍举也”;他这才欣然打起帘子进门:“竟是如此流利;你阿兄当初不能及也”
“阿爷。”杜幼麟连忙站起身来;上前规规矩矩行了礼;和杜广元的大大咧咧截然不同。可是;听到父亲赞扬自己胜过阿兄;小家伙却还立刻摇了摇头说;“阿兄天赋比我好;只是坐不住;阿爷不要怪他。”
杜士仪不禁莞尔;摸了摸杜幼麟的脑袋;见秋娘连忙上来拉着人出去了;他方才来到了王容面前:“我早起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已经不止一根白发;一晃连这孩子都已经快要六岁了;真是时光匆匆。”
“你就是操心的事情多;所以白头发长得快”遥想自己当初和杜士仪初次于上元灯节相见;据此已经快要二十年了;王容也同样颇有感伤;口中却不肯继续这个话题;“算算日子;再过几日我就得带着广元启程回长安;幼麟的课业就得你亲自过问督促了。孩子还小;习惯得从小养成……”
听到王容说起回京看杜仙蕙的事情;随即又絮絮叨叨嘱咐幼子的课业;杜士仪先是觉得一阵好笑;当年叱咤风云掌管金钱无数的女子;如今仿佛泯灭在了相夫教子之中;可渐渐地;他就感觉到了一股说不出的温暖。能够让一个不平凡的女人洗手作羹汤;相夫育儿忙;何尝不是男人最大的幸福?所以;他直到王容把话说完;这才笑出了声来。
“是;夫人;你就尽管放心地去看蕙娘吧;我不会让你回来时看到一个荒怠贪玩的幼麟。不过;她们很有可能不在玉真观;而是避到王屋山阳台观去了;你也许得多跑一个地方。另外就是;你这次回长安;顺便帮我再做一件事。
王容本有些微嗔;听到末了一句时方才丢开了;却是认真地问道:“什么事?”
“秀实在中受降城掀起的那一场风波;你应该知道了。识文断字的师长虽然困难;但随着少伯和仲高的诗集在关内道传播开来;已经渐渐有士人慕名而来。但光是有人还不行;既然要识文断字;那就需要笔墨纸砚;而更重要的是;需要书。之前我在云州代州;先后印云州集;代州集;那时候用的是雕版;佛寺如今多用此来印佛经;但现在;我不在乎印书的质量;而要降低成本;增加数量;所以要换一种方法。”
他拉着妻子到一旁的书案旁;展开了手中的一卷图纸;略一解说后;就只见王容眼睛一亮;随即欣然点头;他便知道;妻子已经明白了此中利害。
“泥活字成本低廉;不用雇人不断手抄雕版;刻好一套后便能管用很久;至于合适的胶泥;我早年曾经对赤毕提过;虽说这些年他常常身负要务;但他做事一向滴水不漏;说不定已经有进展。即便暂时没有合适的胶泥;用木活字也不是不能暂且凑合。”说到这里;杜士仪顿了一顿;又继续说道;“活字印书;比雕版印书成本低廉;但同样需要识字的排字工人;但如果朔方之地能够在教化百姓上下足功夫;日后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
想到杜士仪早年便曾有过这样的思量;却隐忍多年;直至如今方才拿出来;王容不禁心生敬服。于是;当杜士仪再三告诫;活字之事一定要找看似最不相关的人;将这一条线**出去;她立刻毫不打折扣地答应了。
“另外;你给我带一部书到长安去;把我亲笔写的这一部书找个书法一流的人抄个几十份;从政事堂那两位相国;到贺礼部、徐学士以及诸位饱学文士;都不妨送上一份。总而言之;告诉长安上下;这是我为朔方义学预备蒙童教案。”
既然段秀实起了个头;那他就顺水推舟;把三字经这种最适合蒙童的启蒙教材改编一下给推出去。若能让朔方上下多出几百上千个识文断字的童子;十年之后就会收获一批俊杰更重要的是;这也许可以成为遥远的漠北;罗盈和岳五娘拿来教导胡汉幼童的教材。洗脑……不;应该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尽管杜广元还对自己靠拳头招揽回来的胡儿念念不忘;可他也同样想念许久不见的妹妹;只能带着两难的情绪跟着王容踏上了回长安过年的旅程。如今天寒;日行八十里;路上至少得走上大半个月。
而杜士仪送走了王容和杜广元母子之后;来自中受降城;阎宽和来圣严联合署名的奏报终于送了回来。之前胡乱的主犯和从犯已经一网打尽;在讯问之后供述出;却是受突厥登利可汗指使;潜入中受降城为细作;因见登籍;唯恐暴露;故而挑唆胡人蕃军作乱。
尽管上头写得清清楚楚;每一个被抓的细作供述了什么;全都单独罗列了出来;以作比对;可杜士仪看着看着;仍然觉得不无蹊跷。等翻到最末尾的夹片;他看了心中一动;抬头瞥了一眼亲自驰马送回来这份奏报的阿兹勒;突然开口问道:“我让你此行随侍来判官;你都做了些什么?”
阿兹勒在中受降城便几乎是日夜观摩审问犯人;这一路紧赶慢赶;早已经疲惫不堪。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力争脊背挺得笔直。此刻杜士仪一问;他便大声说道:“来判官发令;阎将军抓人;我正在场;而后则跟着阎将军部属捕拿主从犯人;审问的时候我也都在场。”
“哦?”对于来圣严如此能够体察自己的心意;杜士仪早已不意外了;“来判官这奏报;你可知道写了些什么?
“应该是说;那些主从人犯都是突厥细作;是登利可汗支使他们如此做的?”阿兹勒毕竟亲历了七八个犯人的审讯过程;即便不认字的他即便看了也不知道来圣严究竟写了什么;但他还是能够猜出来。见杜士仪果然微微颔首;他在迟疑了片刻之后;最终开口说道;“大帅;来判官乃是节度判官;阎将军是中受降城主将;我原本不该质疑他们;但我旁观了所有犯人的审问过程;实在觉得有些不对劲。”
杜士仪本来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但阿兹勒的回答引起了他的兴趣:“哦?你说。”
“不瞒大帅说;我原本并不是孤儿;我的阿父曾经是突厥牙帐的侍卫;阿娘是一位小王妃的侍女。因为梅禄啜毒杀毗伽可汗的缘故;我的阿爷受到牵连被处死;阿娘带着我四处逃亡;最终病死在了路上。我小时候;曾经见过还是王子的登利可汗;不能说了解;却也知道他几分。”
看到杜士仪神色纹丝不动;阿兹勒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否能够打动杜士仪;可已经开头就不能停下;他只能鼓起勇气说:“登利可汗这个人;自大狂妄;从小就对一母同胞的兄长并不尊敬;所以伊然可汗被杀的时候;曾经有传言说是他派人下的手。他这样的人;如果真的对朔方有图谋;应该不会用这样细腻的阴谋;他自己不是这样的性格;他的母亲是暾欲谷国师的女儿;但却没有继承国师的多少智慧;而他身边也应该没有这样的人。”
“然后呢?”
杜士仪仍然只是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阿兹勒顿时就更不确定了。于是;他的声音不由自主放得更低了:“那些犯人受审的时候我都在场;在严刑拷打之下;好几个人都是轻而易举地供述了出来;但对于怎么知道所领的是可汗王命;却都说是那个主犯告诉他们的。可那个主犯熬刑数轮后;却突然咬掉了舌头。虽说救回来了;因为不通汉语;却再也问不出别的。而且;我听说此人当初在被抓的时候;曾经差点自尽。如今的突厥牙帐;怎会把这样刚硬的人派到中受降城来;主持这种根本不确定的事?”
第九百二十一章 传首问罪
来圣严和阎宽在奏报上如实转述了那些主从犯人的供述;而在夹片上;却各自陈述了自己的判断。尽管不像是阿兹勒那样曾经在突厥牙帐生活过;而且见过登利可汗;但两人一文一武;阅历经验无不丰富;隐隐之中由从犯的脓包和主犯的决绝;已然觉察出了某些端倪。
故而;来圣严的判断是;突厥牙帐内部争权;新任的左杀判阙特勒和右杀伊勒啜试图以此栽赃登利可汗;这种可能性极大。而阎宽的判断则更为大胆;他指出;很有可能是这些年来因为毗伽可汗和阙特勤兄弟再振汗国;收拢各部;那些因为强势而不得不附庸其下的部落眼见突厥内乱;不甘继续受其压榨;因此方才想出了这样一条计策;为的是让大唐继问罪突厥不朝觐圣寿之后;进一步断绝和突厥的往来;从而让孤立的突厥狗急跳墙;自取灭亡。
所以;杜士仪看着面色不安的阿兹勒;不禁有些赞赏这个胡儿;而他更加满意的;是镇守中受降城的主将阎宽。
阎宽此人作为安北都护府长史坐镇中受降城;老成持重;行事最为谨慎;拂云祠那个地方聚居了那么多胡儿;怎会置之不理?那些蕃僧汉僧之中;早就被掺了一些沙子进去;对这些胡儿一再甄别;确定并无问题之后;这才对他上书提及此事。毕竟;作为突厥人心目中的神祠;即便那些胡儿都是因为年少而托庇其中;可日后长大了该何去何从?
“虽只是揣测居多;但只是旁听就能想到这么深远;着实不错。”杜士仪微微颔首;随即开口说道;“你此去中受降城之前;我曾经承诺于你;如若此行有成;那就赐你杜姓。如今还未足证你的揣测;可你的用心和仔细;我却已经看到了。我暂时没有别的事吩咐你;先回去和其他人团聚吧。对了;广元如今上长安去了;我在你那些同伴中挑了两人相从。”
即便杜士仪的言下之意是说暂时不能赐他杜姓;但阿兹勒得到了肯定;心中仍然极其兴奋。他恭恭敬敬行过礼后出了门;等回到了自己这几十个人的居处;他就发现;自己一来一回不过大半个月;可这个小院子已经变了样子。小小的院子里整整齐齐地晾晒着衣服;每一间房的门口都贴着标签;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图样代表每一个人。而平日里这些胡儿聚在一起;最喜欢吵吵嚷嚷说话;眼下却没有喧哗之声。
好奇的他走到其中一间房前;从门缝里往里头一看;发现里头六个女孩子正在一个婢女的指导下做针线。以往一如男子那样大大咧咧的她们;如今那坚毅的脸上写满了专注;而那个婢女看了一圈后;最终开口说道:“夫人说过;女子不逊男儿;但若是极刚却不知柔;未必就是好事。听说你们之前在拂云祠的时候;缝补衣裳并不常做;针脚功夫实在过不去;这才让你们学一学。如今你们不用过了这顿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