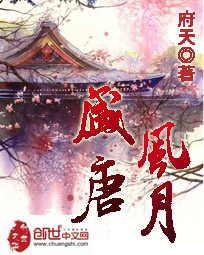ʢ�Ʒ���-��9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ǴҴҸϵ�����ʱ����ֻ�����ſ��Ѿ��ۼ��˺�Щ����������֪���˶�ʿ�Ǽ�״ͷ�ǿƵ���Ϣ���ɵ�������������Ц˫�ֳ������ǽ����ӣ�һʱ����Χ�㴫��������������·���״Ԫ�ɳ����Լ�һ�㡣
������״Ԫ�ɼڵǿƣ���ri���������ԣ���������Ԥ������
������������������ܹ�������ʡ������ʷ�ģ�ȴ������λ��Ȩ���ĸ��֣���ʿ�Ǽ��乧������Ȼ�ٲ���������л���ȵ��������ߣ��������������۵�Ŀ���й��˹��֣���������Ժ�ӣ������й����ͷ�������Ž����ӡ�ֻ��������һ�ų������������������Ļƻ����ӣ�������д�Լ������������������ᡢ�������䣬Ȼ�������Σ��·��������������Ỵ�Ĺ�ְ�ͻ�Ѻ������ͷ��Ӳ���ϣ�Ҳд���Լ����������������˽���Ҳ�ǰ�����Ϊ�����ӵ�������
�����ֽ���ݸ��˶�ʮ�����n4��Ѿͷ��������Ƶ����������У���������Ц��ȴ������ӯ����������Ƭ�̱㿴�Ŷ�ʿ��������ʮ���֣��һ���һ����Ҫ�����æ������ľ�լ�����ܷ��Ҷ��������̣��������������
���ɾ��������ˣ���������ſ���ֹ������ʿ��ҡ��ҡ�֣���ֻ�����ָж������Σ�ֻ��ګګ˵����������ô�С�������ô�С�����
�����������С����һ������֣�Ҳֵ����ˣ���
����ʿ����Ӧ��ˬ�죬��ʿ�dz�������һ�����������������û���ü��ص��Լ���������пտյ�������ի������ֻ���������ִ�������İ�����������ɾ�����ʮ������ʮ����һ��������������λ��˵��ǧ������������������������Ԫ������
���������ֶ�ʿ�Dz�����������������һ���������ˣ���������ά�����ƾ�һ�����ˣ���ʿ�ǵ�ʱϲ�����⡣��������ƽ������լ��ֻ���˸��ľ��ƹ��µ������ֵܺ����е��ż��Լ���Щ����ľ����ȵ�ͬ�����ţ������û���ü�֪ͨ��û�뵽�û����ڣ������ֵܾ͵����ˣ�
��һ�پ�ʮ�¡�ǧ����ȡ��֪���ѵ�
����ǰ�ֺ��õĸ�֣����赲����ͷ·�ϵ����ӣ���������֮������jil����֮ʢ����Ȼ�����鴫����
���Ƹ����ֳ�һ̤��լ�ӣ���ǰԺ��ӳһƬ���֣�˳��һ������С�����ڣ������һ�����������ã���������������һ�䡣�������������䣬��ֻ��ǰͷ������һ��Ц����������ʳ���⣬���ɾ�������ʮ�����Ǹ����ˣ���Ȼ������һƬ���ֶ�������ϲ������ȴ���������ֵ�������Ȥ�ˣ����������ri������chun��ȴ�ǿ��Ժúô�����һ������
��ʹ��ά�ŷ𣬴˿�Ҳ����Ц��������������ʮ���ɣ����⻰Ҫ�DZ�������Щ���������ֶʣ�����мӵ��������ˣ���Ȼ��ʧ��������
��ʿ����ʱ��Ÿմ�ǰ��֮��ת�˳���������һ̯�֣����������£��������ν��ײ裬��һ����ҪǮ��������ʮ������̾�мӵ�����լԺ�������ǵ����dz��䶯�����Ĺ�˾��Ф����Ǯ���ɣ���ƾ��֮����Ҳû��ô��������ɣ�Ҫ��绨ѩ�£��ȵ��п�Щ�����������ʵ��֪��ڣ���ʳ���֪���裡��
�⻰�����ֵ�����ֻ�Ǿ����ֺ����ֺ�Ц��Ȼ�������������������������������Ԫ����˵��ȴ��ͬʱ����һ�������������֪����ʿ��xing�Ӻ���Щֻ֪������ʫ������ʿ��ͬ����������֮����ͬʱ��Ҳ��������ôǮ��������Ԫ������Խ�ri֮�и����˼��ְ��ա�����ʿ�ǽ����DZ����������������˵���������֣���ʮ���ɼ�Ȼ����������������������ס�����������Ҳ������ҹ̸�����ؼ��Ÿϻ�ȥ����Σ���
��Ȼ������������������λ�����ľ��̣���ά֪����ʿ�Dz�������������ˣ��������Ǽ����������������֮ǰ�سDZ��Ͳ����ˣ�������ˬ���Ӧ�ˡ������ƻ�Ҫ�پ��������ַ�������п�����ʿ�ǾͰѺ�ͷ�Ķ�ʿ������������Ц�Ž�˵���DZ�լ��Ӫ���ܼ࣬��������ʲô���ܱ��ʶ�ʿ����˳˳�������������ֶ���ȥ�����ֵܶ����洦�䡣�ȵ��˾�ֱȥ�ˣ������Ű�����������Ԫ���뵽����ի��ʾ�������������Ц��������λĪ����Լ�õģ���ri��ô��һͬ��������
��Ԫ��������¹ڻ������ҵ�������ǻ�����ȶ�ʿ�Ǹ����ȣ�Ȼ�������������㸻�׳�����������������������ʿ��֮����ȥ���������������ǰ����о�ֹ����ʿ֮�����������б���¶�����ֹ��к��ӵĺ�ˬ��
�������������ȿ��ڣ����Ϳ��ż�ɽ��˵������״Ԫ�ɽ���ڵǿƣ��������˲�֪���˲������Ҽ���Ҳ��������ȸ��ǰ���˸����֣����ȴ��������ҭ�˸�ûȤ��״Ԫ�ɻ���ʶ�飬��ʶ���⣬���ƺ�ī���˶����ǧ�����ܷ���һʱ���ҵ�Ȼ�����ǧ���������⣡��
�����Ʋ�����Ԫ���Ⱪ�������ɴ˿�����˵����֣�ȴֱˬ�úܣ���������������һ�������Ͼ�������ʿ�ǵ���Щ����ͷ���ųƶ���ī�ĸ���ī������ȴ���������˵�֮�⣬����ǧ����רӪ��������������һ���⣬����ֻ����Σ�����ȴ����ʧ����
���ǣ�������jing��Ц�ݿ����˵�������������׳�������Ȼ����������ɾ��Դ�һ�ټ�״ͷ�ǿ�֮��ǧ�������۶���Ͷ���īÿri����Ӧ���䶼˵���ɾ����Եǿƣ�ȫ����ⲻ����ī֭�������ټ��Ϻ�Щ��Ұ������֣�ÿri���߲������ҽ�ri����ֻ������ѯ����������ͷ����
����ʯ�ѵã���Ʒ���Ƹ��ѵá�����ķ��ı�֮��������������ʮ�꣬��jing������࣬����ʯ������jing��ϸ����ī�����dz���ֻ������ɽ��������ȴ��������������ʿ�Ǽ��������·���Щʧ��������Ц��˵����������ǧ����Ҳ��������ЩС���⣬��ri��������ʲô�ö�������Ҫ������������������
�����⻰������������ˬ��ش�Ӧ������������ǰ���ʮ�����Ҫ���ڽ���֮ǰΪ��ʿ�Ǻݺ����ƣ���������ƣ���������������Ǯ�����������ʹʹ��죬���������ٴε���֮��˵�˼����л�����������Ԫ��ʼ��û�ٿ��ڣ��·��ǵ����Լ����֮��˵����˼�����ã����ջ��Ǹ��˴ǡ��������ϳ�֮�ʣ���������ͻȻ������λ�����������ƺ��и���δ���˵���Ů��
��Ԫ����������˳�������ɣ�������������ḻ�����£���������¹ڻ���������������Ͷż����ף����÷���ȫ���ٲ��˼��̵�������
������һ�ߣ���Ԫ���������ں��غ�ȻЦ���������������ӣ��·��Ǿ�������һ�ߣ��ұ�Ҫ������״Ԫ������һ�㣡��ǰ��ȸ���Ǽ�������Ϲ���£���ʹ����Ԫ��ȷʵ������Ҳ��������Ҫ�и�״Ԫ�ɵ�Ů����һʱ��ҫ��ri���������˭֪������
��ʿ��Ҳ����˼��������˼�»ؾ���Ԫ���Ҵ���ʱ�Ļ�������Ԫ�����ֱ���˵��������Ǿ��������Ϊ�����ǿɰ��������ʵ�������֪����������Ϊ���£���
���ܼ�����Ԫ��һ����ˣ���������ң�����״Ԫ���IJ���˫�����Ը�����������ֻ��Ѹ�һƪ����Ϊ���ͣ�������״Ԫ�����ⷮ����լ�ӣ�������ri������լԺ���Ҷ��������������ȣ�����������õģ���
��������Ԫ������ʿ�Ƕ�ʱ��ȻʧЦ�����ֵ������ɱ�������ͨ�ģ�Ȼ����������Ԫ�������������ټ���֮ǰ���£������������ֹ�����ʱ�˿̣��뵽��������ȷʵ���������ϡ���ı����ȴҡͷ˵�������������������������ҳ�ԭ�������ȣ�������ĺã�����������һƪ�������١�
���ã�״Ԫ�ɿ��˿�����Ǵ�Ӧ���£���ͷ�������˵����㣬�ҾͲ�߶���ˣ�����Ԫ����������վֱ���Ӻ����ֶ����˶�ʿ�Ǻ�һ�������Ź��ָ�ǡ����˶�լ���ţ����̲�ס�ֻ�ͷ������������һ�µ�լԺ�������Լ���ǰ���꿪ʼ��������ƶ�����ӣ�ȴ����û��˵�����ʿ����㣬�ܹ�ƾ��һ��֮�����ѷ����Ѿ��ҵ��������ͥŤת���������������֮�ơ�
������ᣬ����ֻ��һ�����б���һֻ��˹è������ȥ�귽ʮ�壬�������ĵĺ�����Ů���۾������ؿ�������ȴ�Ǻ�����ʵ�������ү����λ״Ԫ�ɼ����ˣ���
���ǰ��������ˡ�����Ԫ�����ǵذ��˰�Ů���Ǽ���漴̾��һ���������������һ��벻����Ļ���ǿ��һ�ԣ��������������ƣ����������Ķ�������������������ĶԴ���������Ƕ���Ͷ���ī������ʱ��ȴ��ֲ��������������ұ㲻���������ˣ������˵�öԣ�����Ů���ҿ����ܲ��𣬽�������һ�ɻ��ڴȴҲ��ͬ�dz�����ū����ë��һ�������Ӵ�һ����������������������ί������
������˵�ˣ��ǰ�ү������˵���Ķ����ǵ�������һ��״Ԫ��Ů���������������ۿ�����������Ц�Ÿ������������ѣ��о�����������ת�����������������۾�������˵��������үҲ�����룬����û���ң�˭�����ˣ���
����ѽ��ѽ�������������Dz����ã������ܲ����ڼ���һ���ӣ��ҿ��Ƕ�ʮ���ɣ������һ���˲ŵĺ��ж�����
������������˼������������һ����������ɨ��һ���Ǵ����������ʵľ��£���Ԫ������ҡ��ҡͷ�������������Լ������������ľ��ӣ�������Ȼҡ��ҡͷ���̼�֮�жౡ���ˣ���Щ��ji�ŵ���ʿ�ӻ����Dz�ࣿ
����ү�����ǰ�����ң���ʮ������Ϊ�����������ӵܣ��ɼ�Ȼ�ҵ����䣬Ҳһ�ȴ������ɲž��Ĵ��ԣ���������������������ֳ������裬Ҳ�����н��죡�������һ����ȡ��ͷ״ͷ������������˻����Dz����ˣ�����ȴһ·�����ն�������˹���������һ���˲��ĸ��֣�������˵���м�������
��Ԫ����Ů��˵���⻰������������ȥ���˱�����ʱ��Ц��һ�������������Ի�����ЩǮ���������ö�Ů���ֶ��飬����������������������ɹ����Ψ�����Ů�����Ǵ�����ͨ�������������Ǹ�������������̾���ѣ�
������˵����Ԫ����������������������
����ʿ��ϸ˵����ԭί����ά��ʱ������˼���˵�ͷ����ȷʵ������ƽ���������������������������������Գ�ȥ�ⲻ�����������Ҳ��ȱ��ЩǮ����������ǰ������дһƪ����ʢ�ޣ���ʱ�������̸�ˡ���Ԫ����Ϊ�̼֣�����ȴ������壬���������Ե����������
����ȴ����Ԫ����������Ϊ����Ů���������û��˼��ֱ���ֳ��ֺ�����ʶ�ʿ�ǽ�����ʥ�������ţ��Լ������ټ������Σ�����������������������������ʿ�Ǿ�Ȼ����¡����������¬���ɽһ��ʱ������ֱ�Ծܾ����������̲�ס�ˡ�
����ʮ���ɣ������Ҳ̫���ˣ���һ��������ܾ�������ŭ�������¿�״Ԫ�ټ���ʥ����ҫ���ɾͱ�������ˣ�
�⻰��˼��Ҳ����˵������ʿ�����Ѿ�����λ���߶��������������ڶ��䶼�����ϼ룺����ʹ�����ʹ����ʱ��ֻ�Ǿ���ʥ�����������������Ի���ȥ��һ�ġ����ʥ�˹�Ȼ��Ϊ��������ri�������������������
����Ȼ����ȥ������������ʥ�˾�����˵����������������е�һƴ����
�������ֹ�������һֱ����Ϊ����¡�����Լ�ȥ���έZ�Ķ�ʿ�ǻ�Ȼ����Ȼ�����뵽����������έZ��ͬʱȴ־���������ż��꣬������������������֮̾������һ˿�˸У��ܿ������ά�Ღ�����ҵ������л��������С�Ϧ��֮�У��������������������ֻ�������������ĽԾ�����Щ���˵�������֪������ȫ������������һ�����ˣ�ȴֻ��һ��ͻأ����������̧ͷһ�����������ƻ��к��ˣ�
������������Խ��Խjingտ�ˣ���
����ʮ���ɣ��������ԣ���ҪС��Щ���������һ���࣬������ټ������˳���Ҫְ�����У���������Ϊ��������Ա���ɵ���Ա�ξ�����ι��Ծ��������֡����纬Һ�ĸ��������ã����dz������������ˣ�һԾ��������ʡ����֮��ǰ����ͬri�������ҹ��ʮ����������լ��ҹ�磬����ʱ�õ��������Ϣ������������Ѷ��˵�����������֮�������¸������ο��������ˣ����������������ڼ����㲻��ȥ�����ˡ���
��һ�پ�ʮһ����������
��������������ȴ�����٣�������Ƕ�����ʿ�Ǹ����ò�����ȥ�������䲻��������ʥ�⣬ȴ��������Ƣ�����꣬��һ����������ܼɣ��鷳�ʹ��ˣ���������ȴ�ǧ������������������һ�ߺ��ɹģ�������˹�ȥ���ٸ��ˡ��ɹ��̡�һƪ����Ȼ����λ�ʵ�������Ϊ���⡣���ȵ����լ�г�����������ʱ��ȥ�˸��˷�����۵����湫������ѭ����л֮������ֱ��˵��������ri������ȴ��һ����Ҫ�����ʹ�����
���ܸ���ʿ��ͼ����ë��֮������û�гɹ��������湫���Ѿ�������������Ϣ�����飬��ʿ���ֲ����������¼�״ͷ������������Ȼ�õúܣ��˿̱����Ϸ�ʵ�˵��������ȡ��ͷ״ͷ�Ķ��ɾ���������Ҫ�����������֮��ô����
��ǰʱ����ʡ���ù��ð����࣬���������������Щ�ɼ�����
���湫������ʿ�Ǿ��Լ����£��������Ȼ������ͷ������㴫�ԡ���Ȼ��Ҫ���Ĵ����ǣ�ԴǬ�����������ӵĿ��ͣ����ʿ��ȥ����覣������ʳ�¯��״Ԫ�ɾ����Ѿ�����������̸�����������������μ��ù��緹���Ÿ����ȥ��Ҳ��֪���ö�������Щ�������ӵɳ������뵽������������Ǻ����ʿ���ܺ������ʲô��ͬ���⣬�������Ȼ���뵽��覵�������ʮ����ǵڣ��վ�����û����������ʳ��ڡ�
�������ʡ��������ף�����������أ��ɰ����ż��겻Ӧ��˲��ǡ���Ŷ���������ˣ����Ÿո������������Ϊ�������ˣ���ȴ�ǹ�������ɾ���������������������ǰ��ЩԹ�ԡ��ż����������Σ����Ⱦټ��������˱��������ú�Ա�ξ���һ��Ǩ�������ˣ�һ��Ǩ����˾Ա���ɣ�����������������Ա�ξ����������Ը���ʹ���ӣ�����δ��û���ܡ������ǵ��ǣ����ż�����έZһ�������������飬ri������ѡ��ʱ�������ĸ���ְ��һ�����ꡭ������ʱ��ɾ�����
�����ԣ���ֻϣ����һ���ܹ�����ƽ�������ڳ�Զ��Σ������������ǡ���
����ʿ�Ǵ�������߳�����ʱ����ų�������һ�������ż��������û��̫��̵ļ����ӡ��Ȼ��������ͱ��˵��������磬��Ӧ���᳤�á���ѡ����֮�䣬���Է����ܶ�仯�ˣ��ż����ڳ����绽���ʱ�䣬��������ʮ������Ϊ�ϼƣ�����������Ѿ��д˴��㣡
��ʿ�Ƽ�����ν֮Ϊ�ǿƣ�����׳��½�ʿ����Ҫ����ȡ�����ٵij�����ȴ����ͨ���������ԡ�ֻ�й��������������Ĺأ������׳�֮�е�ǰ��ʿ��������������˹���֮����һ��������������ѡ���������ͺ��ڹ١���Ȼ����ù������ѡ�������߰��꣬Ҳ�����ټ���ʱ����η�������ؼ������ء�
��ˣ���������Ϊ���������Ź��ԵĽ����������Ϊ��������ѡ��Ȩ�����������½�ʿվ������ʡ��������Ĵ����У�����������Ϣ������ʮ��С�ġ���һ�������������ԵIJ��DZ��ˣ��������ο���Ա����Ա�ξ���������̱���Ϊ����˾��������֮��Ϊ��һ�������Ŀ���Ա���ɻ�������ʱ����ʿ��Ϊ�ף������˶��������ȥ��
Ա�ξ���ǰ�ι���ʷ���������������ף�����ȥ�����������ϣ�������ɨ������һ�ۣ�Ŀ���ڶ�ʿ�Ǻ��纬Һ����ͣ���˺�һ������������ѵ�������䣬������ת�����ݣ�������ʿ�ǵ�һ�����������ӣ���Ա�ξ���ϥ�����鰸֮�����ٴ�����֮��ֱ���������㷢��Ա�ξ������Լ���Ŀ���У��·��м�����ı��顣֪�����湫��Ӧ��ȷʵ����к�������·������Ƶ�ͦ����������s���쳣���ݡ�
����֮ǰû�������ټ��մ����ƣ��������湫���Ļػ���Ա�ξ�����Ͷ�ż������ã�˳��Ҳ������ͬ������ż���������������һ�����飬�����������Ȼ��Ȩ����������ǣ����湫������к���ζ�������������������ĸ�����������������Ρ���ʱ�˿̣�����һ�Ա�¼����ʷ�������Զ����϶����������ϣ����������Լ�����ģ�����Ȼ������������ҭ�ûš���������һ���ɨ��һ�۶�ʿ�ǽ���������һҳ�֣�����Ȼ�Ǽ����ͦƯ���İ˷��飬�����ս�Ӳ�ض��˶��°͡�
�����ϣ���
�������ߵ���ʿ���������£�������һ���������룬Ա�ξ�ʼ���IJ����ɣ����ջ��Ǿ������������������ȿ�����ʿ�Ǿ���������Σ���������ȥ���Ǿ߸�����������£���Ϊ��������õ�ʱ����Ĵ�ŭ����λ��������ǰ�ܵó�����湫���������º��й�������ã�����λ�����������˺�ĸ���ȥ�����¡��뵽�������ʱ��Ȼ����������һһ����ǰ�����������һָ��ͷ���⣬����ʷ���˳�ȥ��
�����ԡ��������ʮ������ʿ��һ����ƽ��ͨ�����ȵ������鷳������������Ŀ���£��������ڴ�ǰʡ�Ե�����ʡ��������riĺ֮ǰ������ʱ��һʱ������������ü��˼����ν���У��������龰���дʣ������ǿ���Ϥ�ɷ����Ȼ����Щ�����������д������Ѿ��������У�����˵�������ذ�빳��⣬������˵ȡ�Ծ�����Ŀ������˵�DZ�����ѧ����������һƪ�������¶��ѡ�������ˣ���������ɷ��ߣ������������ﶼ�����жϡ�
��ri���⣬һΪ�����丸�����DZ�Ӧ�����ܵĸ�һ���������˾������Խ����Ϊ����ð������Ϊ�������乫������˾��������Υ�ɣ������ҳ�����էһ�����dz�ԣ�����ȴ���������Ƕ����������Ƿ���Ϥ��������Ϧ����ֻ����ʮ����������ʱ����˼��ʱ���ܱʼ��飬������������y����������ة¬��Ը��ʱ������������ɨ��һ�ۣ�����֮���ֶ��������ۣ�ȴ���ִ�ǰ�������Ķ�ʿ�Ǿ��Dz����ˡ����������ǽ���Թ٣��ɽ�ʿ�Ƶ�����ȴ�������Զ������ģ��˿̲������´��ɣ����ֱ�����˼ೡ��һ������ʷ��
��״ͷ��ʮ������ô�����ˣ���
�����������ɣ���ʮ���ɽ������ˡ���
����ô�죡��
������y����һ������Ա�ξ��ӵ���ʿ�ǽ������������У�������ͬ�����һ�����������м���һ�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