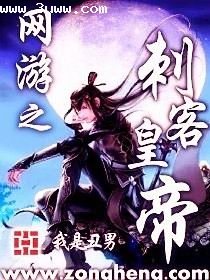刺客无名 by 夜雪猫猫-第2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紧蹙,却只闷哼了一声。做完这些,她已全然脱力,但仍旧死死咬着唇,不让自己痛晕过去。
她轻声道:“替我把毒吸出来。快!”本是求人之事,却听不出一丝哀求之意。
原清泽心知要是不照做,她就只有死路一条。虽仍不耻她所作所为,但对她方才拔箭之举亦心生敬佩。于是顾不得男女之防,俯身替她吸毒。她见他动作,终是松了一口气,随即便昏死过去。
足足吸出十几口毒,嘴唇都麻木了,才见到血色逐渐从浓黑转向殷红。他这才想起来,自己这个吸毒人也有中毒的可能,却管不了那么许多。给她上了蜀山特制的金创药,草草包扎了下,便出门去寻大夫。
一时根本找不到江湖上有名的解毒圣手,加上风露寺地处偏僻,他只能在附近小镇上寻了个代夫,替她熬了些普通的解毒药。
无奈她昏迷中如何都不肯喝药,强行撬开牙关灌下去,却咽不下。他看着墨色药汁从她鲜妍不复的嘴角缓缓流出来,一闭眼,一狠心,用嘴含着一口一口喂她。将一碗药灌下去,方才松了一口气。
当晚,他却怎么都睡不着,索性起来点灯,怔怔地看着她的睡颜,守了她一整夜。
好在她武功底子好,第二天就醒了过来。
她醒来时脸色依旧苍白如纸。一开口就要水喝,声音低而嘶哑,像风过树梢,沙里柔着脆。他只觉那一把细沙撒在自己心上,磨得他又疼又痒,却顾不得细细思量,忙扶她起来,喂她喝水。
唐仪的伤一日日好了起来,渐渐能够行动自如,只把原清泽的屋子当作了自己的地方,没有半点不自在,颇有占山为王的意味。原清泽自然也不会主动提出要她走。
谁知,她却是个得寸进尺之人,一会儿说要吃寺中素斋,一会要换干净衣裳。他冷颜相待,她也不恼,只说既然将她救活就有义务照顾她,直到她伤好。
原清泽百思不解,唐仪如此一个冰雪之人,为何会转眼间如此无赖。便是无赖了,态度却仍旧一派冷硬。更不明白,为什么明知她胡闹,却半点奈何不得。
一日,她要他去买苏记的东坡肉。原清泽提了油纸包回来,她已经去别处买了酒。却只着中衣斜倚在榻上,红烛之下,一双眼睛如同润了水泽,嘴角一抹笑,勾魂摄魄,素臂一揽,邀他同坐。
他无奈坐下,道:“你的伤刚好,不宜饮酒。”
她却理也不理,兀自倒了一杯酒,道:“我要走了,这是践行酒。你也不喝么?”
他顿时心中一空,不由自主便举起酒杯,与她对饮。不知不觉数杯下肚,皮肤寸寸灼烫,心中慢慢燃起一把火,终至燎原。她轻轻靠过去,将头枕在他臂上,眉心殷红烧得他神思绷断,理智顷刻如沸水蒸腾消弭。
罗带轻分,香囊暗解,销1魂当此际……
次日,原清泽醒来,一时浑浑噩噩,不知身在何处。待神智清明,却发现已不见她,身旁锦衾已冷,只余一缕残香。
他深恨她下药,坏他清修道体,更恨自己把持不住。却仍是免不了担心她,便急急出去寻。
皇天不负苦心人,她当真未曾走远。见她在酒楼喝酒,原清泽却不敢现身,跟了她一路。
待快要出镇子了,她忽然回头冷道:“你救了我一命。我已用身子报答过。你还待怎样。”
一晌贪欢,原来只是报答。他只觉得心中一阵巨痛,说不出半句话来。心道:要怎样,我却当真不知。
她见他不走,冷笑道:“我这一生,有过无数男人,多你一个不多。想跟便跟来吧。”
原清泽少年心性,何曾受过如此折辱,终是扭头走了。
不料,当晚投宿客栈的时候他便听到一则消息。唐仪重伤那晚原是去赴了与“暖阳真人”之约。此人以修道为名练邪功,污了无数女弟子清白。她一人一剑,灭了对方上下百余高手,是以才弄得遍体鳞伤。
寻常侠客斩妖除魔,自是天经地义,何况淫邪之人,人人得而诛之。而唐仪做出这番举动,原清泽却委实不解。
他终是忍不住,再次寻到她。原不过想问她一句,为何不顾性命也要杀了“暖阳真人”。谁知一开口却道:“你能不能只要我一个男人?”话刚出口,他自己都惊呆了。
本以为她会冷嘲热讽,谁知唐仪听了,半晌没有说话,眼泪却似檐下雨滴,滚滚而落。她悠悠转过身去,低声道:“你当真要我这个残破之人?”
原清泽见她双肩止不住轻耸,只想揽她入怀,自然信誓旦旦斩钉截铁回答说:“是”。
只是事后他才明白,这一声答应得委实太过轻率。
天意弄人
如果说这上半个故事是一首凄婉艳丽的词,那下半段就是白骨森森的现实与绝望。
人都道少年不识愁滋味,何况初沾一个情字。
原清泽和唐仪在一起,初时如同进了蜜罐一般。他将自己寻找琅琊杖的初衷深深埋入心底。但其实那就像已经落地的种子,即使碰到一时干旱,只要有一场雨,便会生根发芽。
二人找了一处山水秀丽之所,过起了男耕女织与世无争的生活。
只是,与师傅约定回蜀山的日子越来越近,原清泽一日比一日不安,一日比一日烦躁。
唐仪自然看出来了,问他是否有心事。
他只愿此刻平静拖得一时算一时,只说没有。
唐仪便提出去镇上赶集。
二人像寻常夫妻一般,走在街上。她兴致很高,越发小孩心性,看到各种小玩意儿都想买。
原清泽原是道士,本就没什么积蓄,何况下山日子不短,都已花得差不多了。几次之后,她看出了他的窘迫。于是直接拉着他去买发带。
不过是普通红绡,她却极开心,立刻让他替她系上。他却觉得在人来人往的街上,未免太过张扬。
唐仪见他迟疑,说翻脸就翻脸,转身便走。
原清泽在后面追了很久,直直追出了集市,来到人烟稀少处。其实以她的轻功,若真想甩了原清泽,他是怎么都追不上的。
原清泽不会哄人,只能拉过她,抚着她的青丝,给她系上发带。如缎的墨发上一缕鲜红似情丝逶迤,只不过发带再长终究也有尽头。
唐仪也真是任性,立刻就春风化雨,直说要去酒楼庆祝。见她回转,原清泽松了一口气,便忘了问她庆祝什么。
到了镇上唯一的酒楼,才刚坐定,便有两个作读书人打扮的公子哥上前与唐仪搭讪。起初唐仪充耳不闻,神情一派漠然,像是根本不认得他们。
其中一个见她如此,便不耐烦道:“装什么假正经,那天晚上不是伺候得我们兄弟两个挺乐么。”
另一个打量了原清泽几眼,立刻帮腔道:“莫不是因为有了新欢吧。倒是长得挺标致,是你养的小白脸吧。你们俩可以一起来,小爷我多一个人服侍,更尽兴……”
二人一搭一唱说得越来越不堪。原清泽自是听出来了,他们曾经都是她的入幕之宾,待二人扯到他自己身上,顿觉脸上被两个肮脏蠢物当众连扇数个耳光,**辣地疼。
唐仪面上血色缓缓退尽。起先她一直强忍着未曾动作,待二人言语辱及原清泽,一直被她死死捏住的剑,忽然出鞘,一剑一人,不过两个眨眼的功夫,就刺穿了二人的心窝。镇上的乡民何时见过这等阵势,立刻四散奔逃,一片哗然。
饭自然是吃不成了。
原清泽拽着她出了酒楼一路疾行。心中却怪她出手太狠毒。便道:“你也太嗜杀成性了,连自己曾经的枕边人也能下得去手。不知姑娘何时也将我弃如敝履?”
她怔怔看着他,过了半晌,才冷冷吐出两个字来:“现在”。说完转身就走。
原清泽自然不肯去追。却一个人在原地站到黄昏,直到他的影子都淡了,才独自回到二人一起搭建的茅屋,却不见唐仪踪影。
他等了足足十天,也不见她回来,心中不免懊悔。
第十一天的晚上,她手执酒壶,艳红身姿卷着风雪而入。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邀他同饮。酒过三巡,她忽然靠过去。
原清泽知她心思,心中怒极,便一把将她推开,厉声道:“你自己不自爱就算了,当我是什么人!”
她忽然脸上媚色尽收,凄然笑道:“我早知你终有一天也会瞧不起我。”一顿,她又低低道:“原以为你跟他们不同。是我痴了。”这一句却像是自言自语。
他心中大痛,问道:“到底为何要如此糟蹋自己?”
唐仪忽然猛地灌了一口酒,因灌得太急,呛了喉,不停地咳嗽,一时眼泪疾奔,混着酒水,沿着她下巴的清冷弧线滴下来,落到他的衣襟上,淡淡化开。良久才嘶声凄道:“我便是这样人,没了男人会死!”艳色无双的脸上却满是自厌与自鄙。
他见她如此自苦,心中一软,反道:“我知道你定是有苦衷的。”
她听了,整个人都一震,凄声道:“身为女子,有谁又生来就愿意一双玉臂千人枕呢。”
原清泽听了却越发糊涂。心道:这世上操皮肉生意的女子大多都是为生计所迫。她的父母虽离家的离家,叛出师门的叛出师门,却都是人中龙凤。当不至于让她这样吃苦,受委屈。
唐仪悲泣道:“你可知,这世上有一种极霸道的淫*药叫‘销1魂香’,至今都治无可治。只有不断地找男人做那事,才能活下去。哈,你当我喜(…提供下载)欢那些男人么,我每次到了发作的时候,便去酒坊买醉,只要醉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只求不记得他们。只因每记得一个人,我便厌恶自己一分。却下不了狠心去死。若是爹娘早早在地下看到我,不知会怎样伤心。”
原清泽听了,心魂剧震,这才明了她每次饮下的不是琼浆玉液,而是自毁铸就的血泪。
半晌,他才颤抖着唇,轻问:“是不是那个‘暖阳真人’害的你?”
不料,唐仪却摇头道:“我不过是不耻他所为,一时兴起练练手罢了。”
“那到底是谁下的毒?”
“你别问了。我是不会说的。我本是污浊不堪之人,原不配你的怜惜。”
一行清泪倏忽滑落,却道己身污浊不堪怜。
一瞬间,他只觉得自己的心被她掏空成一只盛雪的瓷杯,承了她的泪,痛彻心肺地冷。
只是这世上的爱情,光靠怜惜是远远不够的。现实永远屹立如山,叫一干有情人无可跨越。
有时候,表面上的伤口是结好了,谁知,却腐了内里的骨肉。
二人还像往常那般形影不离,甚至更亲密无间。
情人之间朝夕相处的日子总嫌不够长。不知不觉冬天已经过去,万物迎春。唐仪提议去集市买些布匹裁春装。原清泽却显得意兴阑珊,只是终究拗不过她,便一同去了。
许是经过了漫长的冬季,春寒虽然尚且料峭,出来赶集的人们却很热情,不大的集市上摩肩接踵。唐仪本就风姿无双,原清泽气质清华,二人走在这乡村小地,自然引人注目得很。
每当有男人的目光投注在唐仪脸上,原清泽牵着她的手便下意识地松一松,直到有个男子盯着唐仪瞧,眼神十分露骨。人群中,本来相握的两人,终被冲散。
原清泽呆呆地立在人来人往中,睁睁看着那一抹为寻他而四处奔忙的红色身影,那紧蹙的眉、茫然的眼,如同一只裂了缝的细瓷杯,知晓自己命运的惶急绝望。他的腿却像扎了根似的,不能向她移动半步,喉中如同堵了铅块,不能吐出半个音节。
直到傍晚集市散了,唐仪才寻到他,一时笑看如春花初绽,原清泽勉强回以一笑,二人相携归去。
只有他知道,那只手,是他主动放开的。他自然绝非故意,而有些事恰恰就坏在不由自主。
与师傅商量好的历练期限早已过去,原清泽迟迟未归,不免忧心忡忡。有道是怕什么来什么,一日,师傅终于下山找到了他。
琅琊杖本就是原清泽的一块心病。他觉得愧对师门,更愧对恩师,犹豫再三,终于决定先跟师傅回蜀山。他不断说服自己,或许交出琅琊杖,就能换得自由身。
严刑逼供或许会很难,因为武林中多的是死士,但套枕边人的话却往往易如反掌,尤其当她爱着你的时候。
原清泽顺利地拿到了琅琊杖,随师傅回到了蜀山。
“无奈,造化弄人。这一去却是有去无回。师傅将我禁足,让我悔过。她终是找上了蜀山,大闹一场。蜀山弟子发现她居然也会使蜀山剑法,且招招料敌机先,便越发拼了命围攻。本来凭她的武功,要全身而退并不难。谁知,师傅却越众而出,对她说,我对她的情意全是假的,这一切不过是个局,为的就是骗取琅琊杖。她听了非但不退,居然拼了自己性命不要,只身硬闯藏宝楼,将琅琊杖重新抢到了手。看守藏宝楼的弟子都是蜀山一等一的剑术高手,她终究因为寡不敌众,身受多处重创。却犹自苦苦支撑,以毁去琅琊杖为挟,定要见我一面。师傅无法,只得放我出去见她。她听了我亲述事情的始末,不再信我有半分真情,竟然手持琅琊杖,跳下蜀山绝壁云烟。我当时心胆俱裂,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身如飞仙,衣袂飘散。出了这样的事,我成了蜀山出家弟子中的罪人,被逐出师门。那时候我已心无留恋,只想着能寻回她的尸身,便发了疯一般漫山搜索,如此这般,寻了几十年,却一无所获。”
原清泽一辈子忘不了当日金顶之上,唐仪一身染血红袍翻飞如折翅艳蝶,面上如未经烧制的白瓷胎,染着一层浅灰,一声凄厉大笑,道:“原清泽,我唐仪一生过尽千帆,却独独将一腔真情错付予你。我本污浊之人,自问不配与你结发,所以我只求你亲手给我系上发带,就肯无名无份地跟着你。谁知却落得今日下场!算我唐仪有眼无珠。不就是为了一柄琅琊杖么,我偏偏叫你得不到!”说完,她义无反顾,纵身跃下仙台。他却连她一片衣角都握不住,只记得她面上决绝凄凉,泪珠四散。
其实,大多时候,所谓天意弄人,不过是各人自找各人的借口,算在老天头上,不过是一场事后的自我救赎。原清泽当时并未追随唐仪纵身而下,而是事后寻找她的尸骨,一寻就是几十年。与其说他的爱深刻入骨以至毕生难忘,不如说他在苦苦寻觅一场良心的安置。不是所有的爱都能誓死相随。爱情往往是一座只开一季的花园,当这满园盛景轰轰烈烈地过去,当一切凋零颓败归于沉寂,置身其中的赏花人才发现,原来自己始终只是旁观的看客,纵然这满庭繁华就此烙印于心,如同一场梦从此跟随余下的人生,那终究不过是梦。
倾谈
仙翁说到此处,不禁老泪纵横。
莫熙却寻思着,原来唐门跟蜀山这一南一北两大蜀中霸主结怨,都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唐仪虽然身中淫*毒,但她当初为何要采取这种捡到篮里都是菜的方式呢,就算那毒邪门得厉害,一个男人满足不了,搞NP就是了。这种固定会员制,既可以保证数量,又可以保证质量,不是比她随机撒网要安全有效得多么。而且这姑娘也太想不开了吧,不过是一个负心汉,那么多男人都应付过来了,为了仙翁毁了千年道行不说,最后还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委实可惜。还有,古代不是男权社会么,怎么唐家的姑娘拐了蜀山弟子,生出来的孩子却姓唐呢。不知唐仪的爹娘是何方神圣,思想挺前卫啊。
唐欢待仙翁情绪平复了些,才问道:“当年唐仪前辈既然跳下蜀山,兴许尸骨无存。前辈又怎知她葬在唐门后山呢。”
仙翁道:“不瞒唐掌门说。有道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老夫当年遍寻不着她的尸身,曾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想着她武功高绝,兴许还活着。便厚颜来到唐门求见。当年也是贵派的大总管唐德接待的我,他说唐仪已死,后山墓园里就有她的碑。只是老夫一直不得亲见,深以为憾。还望唐掌门替我了却这个多年夙愿。”
唐欢颔首道:“那是自然。”
沐风亭忽道:“前辈是否知晓那销1魂香的来历?还有唐仪前辈是如何染上这等霸道淫毒的?”
仙翁摇摇头道:“我自然是问过她的,无奈她怎么都不肯吐露半分。我不想再触及她的伤心事,也就罢了。”
莫熙心道:这就怪了,唐仪既然能把中毒和她过往所有的不堪,都毫无保留地对原清泽吐露,为何独独不坦白是谁下的毒呢。其中必然另有隐情。莫非对方是一个极厉害的人物,凭唐仪的武功都奈何不得?她怕原清泽一时义愤,为了替她报仇白白送死?再者,如果说“销1魂香”霸道至极,唐仪身在唐门都束手无策,倒也说得通。但原清泽救治唐仪箭伤的时候,不过随便找了一个山野郎中,那毒伤就被治愈,可见只是一般毒药。唐仪身为唐门中人,为何却连这等解毒手段都没有?
次日,唐欢便信守诺言,带仙翁去后山拜祭了唐仪。莫熙跟沐风亭二人不便进入后山禁地,就静待二人出来,在墓园门口与仙翁就地作别。
莫熙回到住处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唐欢就带着药箱来了。
照例按部就班,开始按摩、温洗、敷药的治疗过程。
拆开纱布,手腕的红肿已消下去不少。莫熙稍微试着转了转,好像疼痛也大大缓解,她笑嘻嘻地道:“你这半个神医,都成专治跌打损伤的江湖郎中了,实在屈才。”
唐欢本专注地替她揉着手腕,闻言低低道:“欢只愿姑娘此生无灾无病,一生顺遂。”一顿,他停下手上的动作,握着她的手轻轻放在自己膝上,抬头凝视着她的眼睛,道:“我也知人生无常,不能事事如意。只盼你今生今世所有伤疼,我都能治好。”
他不待莫熙回答,便问道:“这伤是怎么得的,还没告诉我呢。”一边又低头专注手上动作,不再看她。
莫熙也不瞒他,开始简单叙述事情的始末。
待唐欢听到她经历雪崩的惊心动魄,心中一颤,暗道:万幸,她此刻仍是好端端的在我面前。心中这么想,手不知不觉便握得紧了。
莫熙轻道:“疼。”却也没把手挣开。
唐欢这才回过神来,忙松开她,向她的手急急看去,道:“对不住,方才一时听住了。”
那一声疼,尾音稍长,听在唐欢耳中不免带着一丝撒娇抱怨的意味。他立刻又欢喜起来,唇边带笑,轻道:“弄疼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