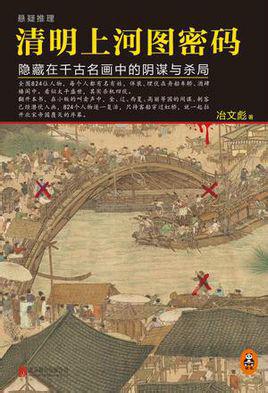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11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别的没打听到什么。
但另外有件事在小海心里结了个大疙瘩。
就是那只青铜宝鼎。
她清楚记得母亲去世前,家中锁钱的柜子里有一只和夏东屹家里那只很像也许可能是一模一样的宝鼎,而母亲自知死期将至时,曾让小海把酒爷叫到家里面来,两个人说了大概半个钟头的话,小海亲眼看见酒爷走的时候手里拿着个蓝色的包袱。
那时候她小,对很多事情都还懵懂,压根没多想,也没地方多想。
但现在想起来,就不太那么对劲了。
244、老懒看见鬼了()
那年小海母亲去世后,葬礼是酒爷主持的,要不是有他镇场,肯定乱得一塌糊涂,小海很记这份恩情。
再过了几个月,小海终于渐渐接受自己变成了孤儿这件事以后,便仔细把家里翻找了一遍,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指引她把父亲找回来,但除那张写了陈家坞和北排沟两个地址的纸条以外,别的什么都没找到,那只她曾经看见过的青铜宝鼎也彻底不见。
当然那时候她没在意,觉得可能是被哪个亲戚拿走了,后来这许多年里也都没在意甚至已经忘掉,直到白亚丰在夏东屹家里拍到只一模一样的,才突然把她十几岁时候的记忆给唤醒了。
这些日子里小海想来想去,觉得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因为她当时年纪太小,母亲怕她吃闷亏,所以临终前将她连同家里要紧的东西都一起托负给酒爷照看和保管。
想到这一层,当年酒爷从他家里走出时手里拿着一只蓝色包袱的画面,也渐渐清晰起来了。
所以这趟回去见到酒爷,小海就问他了,当然措词很小心,只问他给她母亲办丧事时有没有用到过一只老旧的青铜香炉类的东西。
酒爷回答说没有。
小海再问他有没有在哪里看见过这样的东西时,酒爷还是回答说没有。
小海跟我说酒爷当时神情慌张眼神闪烁明摆着就是撒谎,却又不敢逼问太紧。
我知道这些年里她基本是靠着酒爷的照顾和撑腰才熬过来的,特别是那几间房子,如果没有酒爷主持公道,早被亲戚霸占去了。我怕她因这件事而失去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里难得拥有的一点温暖和亲情,实在过于残忍,就安慰她先不要着急,肯定是哪里出错了。
她冷冰冰地说:“确实可能有哪里出错了,但酒爷说谎和有所隐瞒这两点肯定不会错。”
我见她脸色不好看,也不敢多劝,只好默不作声。她过了好一会才说她能想到的最大可能性是她母亲把青铜宝鼎交给酒爷保管,嘱他等她丈夫回来或者女儿长大以后转交,但酒爷却把东西昧下了。
我因为没有跟他们一起去花桥镇,不知道酒爷在被追问那件东西的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表语和语气,所以不好作推测更不好下结论,只能默默不作声,心里凄凄然。
小海表面上看上去平静,实际心里憋着股劲,我知道她迟早还是会回去问个明白的。
也该她问个明白,没谁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就被欺负,东西见没见过,昧没昧下,怎么的也该有个明确交待。
我叫老懒接着找周长寿和夏东屹,但给白亚丰布置了别的任务,叫他想办法把他爸爸以前那个叫陶玺的搭档找出来,找不到人也得找到点线索。他查陆瑶琳和画的事情正查在兴头上,突然被指派别的任务,有点嘟嘴,被小海狠斜一眼立马老实。我悄悄跟小海说夏东屹的画大有乾坤,亚丰脑子太简单,一根筋查很容易惹上麻烦,叫她看着他点。
这里前后差不多两个半月的时间,我和代芙蓉都住在城西黎绪提供的那套房子里,因为就在城市边缘,比我自己的房子近很多,来去能省不少时间,所以就一直没回自己家。小海则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白亚丰家里,因为老爷子的情况不太好,时不时会有低烧,而且还长了褥疮,她和保姆两个人轮流照顾,偶尔的时候会到我们这边来串串门,帮我们洗洗衣服搞搞卫生什么的,用她自己的话说,“得对得起你给的工资”。
但老懒一直不知道我住在别人家,我们都没告诉他,也不是故意不告诉,而是压根没觉得有必要告诉,所以有天晚上,我在城西的住处正跟黎绪头碰头研究夏东屹那些画时,老懒开车到我乡下的家里去找我了,他把车停在离大门五米远的一棵树下,没下车去按门铃,而是打电话给我,特严肃地问我有没有在家。我回答说我在朋友家。他说那你自己家呢,没人在吗?我说没人啊,小海在亚丰家呢。
老懒的语气太严肃,情绪里有紧崩的感觉,我直觉不好,心里咯噔一下,刷地站起身,口音都跑偏了:“咋的,家里有人?!”
那边很镇定地嗯了一声。
我脑子里划过道闪电,血液都沸腾了。等了这么久,那个几次三番闯进我家的女飞贼终于又出现了,而且正好被老懒发现!
我马上给黎绪使了个眼色,她聪明得很,立刻明白情况,风一样旋起身把桌上的东西都收拾好,又转身去拿钥匙和包。
我叫老懒给我盯紧,如果家里面的人准备逃,就动手,如果那人一直呆在房子里不出来,就在外面盯着等我们到,千万别打草惊蛇。
他应了一声。
我又放低声音嘱他把枪上膛,但只能作自卫用,不能轻易开枪,万不得己的情况,宁肯给对方条生路也不能伤了她。
说着话,我和黎绪也出门了,蹦着跳着下楼,把车飚到一百码,连闯两个红灯,一边飞着车一边叫黎绪用我的手机给白亚丰发短信,叫他想办法跟交通部那边联系把我闯红灯和超速的记录都消掉。他收到以后回了句骂人的话过来:“你当交通部是我家开的啊什么事都摆得平?”
我一路上想得挺美,以为只要我们赶到的时候那女飞贼还在家里,就一定能把她抓住。凭我们三个的身手,哪怕她长了翅膀也逃不脱,这次,铁板钉钉是要跟那女飞贼面对面聊聊,问问她的来路和目的了。
可人世间的事,有时真不能想得太美满,否则一失望就容易失态,容易气急败坏。
老懒居然没能把人给我看住!
我当时真是气极了,连踹他三脚,要不是黎绪拦着挡着骂着,我真有可能会把他踹死。后来反省这天自己的行为,觉得真不是人,恨不得拿块豆腐把自己撞死算了,可老懒倒还安慰我,说是不明不白的事情接二连三来,心里憋屈,有个由头发泄出来是好事。我问他当时为什么不躲,他很暖地笑笑,笑得有点坏,说女人的德行都一样,我越躲你肯定越气,我不躲你倒可能会不忍心,何况当时还有个拦架的。
说起来这天晚上的事情真不是老懒的错。
他车子开到离我家大概二十来米远的地方,隐隐看到二楼书房的阳台那里有一点摇曳的光,心里觉得奇怪,就把车停在路边观望了一会,几秒钟以后那光开始移动然后不见了,过了两分钟左右突然在三楼的窗边出现,光是摇曳的,他到这时候才明白应该是有人拿着蜡烛在屋子里走动,就没多想,以为是跳闸或者停电,我或者小海在里面检查,就又把车子往前开了几米,停到大门斜对面的树底下以后,突然回过点味来,觉出不对头。
因为老懒知道我和小海是那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做意外防备的人,碰上停电,手边肯定马上能捞到电筒类的照明设备,点根蜡烛乱晃悠的情况完全不符合我们的风格,所以他才没直接下车按铃,而是先打电话给我。
之后,他就按我嘱咐的坐在车里等,但时间太久了,而且因为车子停得离围墙太近,视线受阻,看不见里面到底还有没有光,不确定里面的人是不是跳北边的窗逃跑了,可又不敢把车倒回去几米,怕发车的声音反倒把里面的人惊跑。就这么焦急等了二十来分钟,实在等不住了,便偷摸着下车,翻墙进院,蹑手蹑脚摸到一楼客厅北边的窗户底下。
他对自己的身手很有把握,否则绝不会这么干。
可惜他低估了对方的能耐。
后来他说他怀疑其实在他看见二楼书房那点蜡烛光时,擎蜡烛的人恐怕就已经发现他了,只是不确定那辆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才没马上逃走,而是继续呆在房子里。
老懒摸到北边墙根底下时发现窗帘没拉紧,里面有忽明忽暗忽蓝忽红的光透出来,是电视机,声音开得很轻,不仔细听几乎听不见。也就是说里面那人非但没跑,还没心没肺坐客厅里看电视呢。老懒一时大意加上好奇心太重,就抬起身子把脸贴近玻璃往里面看。
然后就看到了
老懒说他这一辈子,恐怖的事经历过不少,恐怖的人也见过不少,但当时往里看的那眼,还是没能禁住吓,感觉大冬天里兜头一桶冷水把整个人都冻成了冰柱,从里到外的凉,骨髓里都冒冷气。
他说他看见鬼了。
一只女鬼。
他说那只鬼就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里,大概早就知道北边窗跟底下有人,所以老懒往里看的时候,她就是斜着身子面向着窗户的,一身黑衣,长发披面,头发缝里露出一只眼睛,定定地瞪着他看,电视银幕的光变换着颜色一片一片打在她身上,活活就是个午夜凶铃。
我想象当时的画面,背上一层冷汗。
245、目的不明的女飞贼()
我想象当时的画面,老懒和那女飞贼,两个人,一个在窗里一个在窗外,你瞪我我瞪你互相瞪了十几秒钟,况且又是那样的光线、那样恐怖的气氛,老懒没被吓瘫真算他胆大。
互瞪十几秒之后,女鬼的身体一动,电视突然关掉,房子里压根没开灯,瞬间一片漆黑,老懒猝不及防,怔了会才拔腿往前门追,但已经来不及了,大门敞开着,还在微微地移动,女鬼早就跑没影了。
老懒说那半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除了前门被打开的声音之外,他没有听见别的任何声音。
也就是说,没听见脚步声。
我在脑子里把老懒描述的情节过了一边,越发觉得寒意凛凛,但很快就清醒过来,心想肯定是女飞贼捕捉到窗户外面的动静以后,故意把自己弄成那副鬼样吓唬人。
但黎绪好像不这样认为。
她的神情特别凝重,问了老懒很多问题:女鬼身上的衣服什么款式,是衣服还是袍子;身材是胖还是瘦;大概有多高;头发有多长;眼睛是什么样子的
特别是眼睛这部分,她着重问了好几遍:你跟她对视过的对吧?那就是说看清楚她的眼睛了对吧?她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有明显不正常的地方吗?你就不能再仔细想想吗!
一个问题追着一个问题。
我刚平静些下来,黎绪倒是有点抓狂了,一声比一声响,步步紧逼着问,凶神恶煞的样子。
老懒只会摇头:“没看清楚,真的没看清楚,衣服是黑色的,长袖,但没看清到底是衣服还是袍子。头发很长,但也不是特别长,应该和妮儿的差不多吧,或者比妮儿短一点?我真没看清楚嘛。眼睛眼睛没什么特别的吧,她的头发把眼睛遮住了,只能看见一点点,而且当时电视机的光闪来闪去。喂,喂喂喂喂喂,你饶了我好不好。”
黎绪不饶,差不多把整张脸都贴到老懒脸上去,而且看上去比之前更凶,我不得不把她拉扯开点,免得老懒憋气把自己憋死。
我问黎绪是不是知道闯进我家里的人是谁。
她没回答,不轻不重推了我一把,我一屁股坐进沙发里,就是不久之前女飞贼坐过的位置上。
我闻到一缕奇异的、隐约的香味,有一点苦,还有一点甜,就是之前几次在空气里闻到过的那种药草味,那个女飞贼留下的痕迹。
从进门以后,我的嗅觉就一直被黎绪身上那股多种香水味混合的冲鼻味道影响着,压根没注意闻屋子里的空气,这会突然捕捉到一缕,立刻激起之前所有关于气味的细节和联想,马上挥手叫黎绪走开点。
黎绪看我吸着鼻子仔细嗅,很识趣地几步就退到了门外,瞪着两只眼睛等我嗅出个结果。
我嗅了一阵,不会错,就是之前每次女飞贼来过以后我都能闻见的味道,有点甜,有点苦,是药香,很隐秘。我喊黎绪进来,把这味道形容给她听,她的脸色瞬间比之前更白。
我心下有了数,问她:“你肯定知道是谁,对不对?”
她狠力咬了咬嘴唇,像是想把自己从梦里咬醒过来似的,一字一顿说:“如果是我以为的那个人,那老懒真的是见了鬼了!”
我恍了一会才明白她的意思,她是说她觉得可能的那个人早就已经死了,如果真是她的话,只可能以鬼的形式。
不,不对。
我提醒黎绪,就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死而复生好像已经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可能那人死前,有人把她的灵魂复制了一份,死后又把她复活了过来。也可能她现在身体里面的根本就是别人的灵魂。在这个连灵魂都可以移植的年代里已经没有什么样的可能是不可能的了。
我说得飞快,差点把自己的脑子绕晕。
黎绪听够了,不耐烦地举起一只手说:“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懂你的意思了。”
她说:“你等等,我得打个电话。”
黎绪说着话的时候已经从口袋里掏出那部老掉牙的诺基亚了,开机,长按数字健1,然后走到院子里去讲电话,没多大会回来了,跟我说肯定老懒刚才那番描述在她脑子里形成了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让她以为是那个人。说完以后一屁股坐到老懒旁边,抓着他的手,很认真地盯着他说:“你想想,你再仔细想想,你看见的那只女鬼,眼睛正常吗?”
老懒真的很不习惯这么近距离地跟一个女人对视,下意识地又开始憋气,并且微微把脸往后仰,摇着头说:“我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黎绪想了想,拧住眉头,更用力地捏他的手,一字一顿问:“她的眼睛,有眼白部分吗?”
我看见老懒的神情里飞快地掠过一丝震惊,但黎绪却忽略了,她现在只关心女飞贼到底是不是她以为的那个人。
老懒很笃定地回答她:“有,有眼白部分。”
黎绪松开紧抓着老懒的手,长长长长吐出一口气,冲我疲倦地笑笑,说:“妈的,我就想嘛,世界上有再多离奇事,也不能完全没个谱吧。得了,进你家来的人,不是我以为的那个,搞不好只是个普通的贼。你还是赶紧看看家里少了什么贵重东西没有。”
我当然知道不会有什么东西丢失,但还是听她的话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结论是没丢贵重物品。
当然,也没像上次那样再多出什么诡异的东西。
二楼阳台门上的锁从外面被粗鲁拙劣地捅坏了,女鬼就是从那儿进来的。
我盯着那被捅得很不像样的锁,心里真的特别难受,因为这说明了一个之前就想到的问题。
女飞贼前几次进来,这锁没有被撬的痕迹,小海说是锁芯被溜坏了,很高明的手段,而且坏掉有点时间了。所以我们就想,这锁不是女飞贼弄坏的,而是前面有谁溜锁进来过,女飞贼只是碰巧利用到这点,但只是推测,不能确定,现在百分百确定了。前些日子小海把锁芯换掉,女飞贼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进来,只能蛮力撬锁。
而且显然,在我和小海都不在家的这些日子,那女飞贼完全把我的房子当成自己家了,在里面住了起码有一个星期。冰箱里所有能吃的全吃空了,连橱柜里的干货,挂面、方便面、腊肉和脱水蔬菜什么的都少了一半多。
我检查厨房的时候目瞪口呆,马上又颠着脚跑上楼比刚才更用心地检查了一遍其它物件,可以相信那女飞贼上过楼,但没怎么在楼上多逗留,也没翻动过什么东西。
可以看得出这一个多礼拜也可能更久的时间里,女飞贼的吃喝拉撒基本都在一楼,除了厨房里的设备和客厅里的电视机以外,别的好像都没动过。而且卫生搞得特别干净,用过的碗洗净擦干排在橱里,不锈钢水槽擦得锃亮,垃圾都已经处理掉,桶里换上了新的垃圾袋。
她用在我家里生活的方式向我们呈现了她的某些品质:有礼貌、懂事、爱干净,不希望给别人添麻烦。
我仔细品味了一会,越发肯定了之前有过的判断:这人几次三番闯进我家并没有恶意,可能真的像她写在纸条上的那样,只是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问问苏墨森。
我甚至觉得,这应该是个很善良的人。
黎绪见我在厨房里发很长时间的呆,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厨房和其它地方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她张着嘴笑,脏话不自觉地又从喉咙里往外滚:“妈的,这哪是贼,分明就是你家亲戚啊。”
她笑完以后马上正色问我要不要找个鉴证科的人帮忙采集指纹和dna,我摇头说不用,我自己来。
我走到楼上取采指纹的工具,虽然之前采集过一次,但放心起见,还是再弄一次比较好,以防万一不是同个人的情况。
我做事很谨慎,尽可能避免差错,何况在这种事情上,一丁点差错都可能造成很不同的局面,必须得小心。
老懒帮我一起扫指纹粉,黎绪交抱着双臂在旁边看了一阵,觉得无聊,走开去参观起我的房子来,啧啧啧地叹,说:“瞧你这地方,比我住那破屋子好不知道多少倍,居然非得在我那赖这么久,有没有毛病。”
我没好气地说:“之前是避难,之后是图个方便。”
她没接茬,问我介不介意她上楼去看看。我刚想说随便,她的脚步已经踩在楼梯上了。
黎绪在楼上呆了二十多分钟,我想她肯定是在研究二楼书房墙上那些案件信息。她回客厅以后,我和老懒也已经做完最简单的取证工作了,我把这次套取的指纹膜和刚进门时搁在茶几上的那只水杯以及几个月前弄的那些都放好,说明天交给王东升,让他帮忙看看能不能找出匹配的资料。
我觉得这么玩游戏也不是事情,总得往前迈一步,看看能不能有进展,既然对方死活不肯露面,只好我主动一点。
然后我问了黎绪一件事。
我问她这个几次三番闯进我家里的女飞贼,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