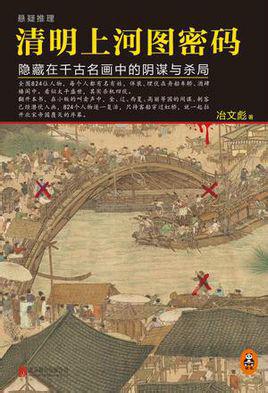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ƴͼ��-��179��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
�����������Ա����ö�ƽ���һ����
���������ҹ���������ܿ�����н����������Ͱ�ϸɵȿ϶��Ȳ�ס����˯�Ļ���û����ʱ�����˯�ˣ����Ըɴ��϶�¥�鷿�������ϵȡ�
��������ֻ�����ͷ����ƽ�ʹ�绰�����ˣ���������˵����ǽ�����ˣ�������ǽ����ǽ�涼�ʿ��ˣ�û�κβ��Ծ��Ķ�����
������������Ȼ���ǵ�������������ԣ������Ǵ�ʧ���������Һܲ����ģ���������ȷ�ϡ�
����������ȷ�����߰˱飬�Ͳ���䷢�ġ�
������������Ȼ��������Ĭ�����°ѳ��������������һ�飬��ҽԺ�������ɨ��������������ǰ�Դ��ϰ��������ң���Ȼ���Ҫ���������������ᵼ�º����������صĺ���֢���ټ��϶�ƽ˵�ģ��⼸���ﳣ���������Ͻ����������ı��֡���Ӧ����Խ��ԽѸ�͵�����������Կ϶���������Ҳ������ij�֡��컯�����������ظ����õ��컯��
�������������������ΰ������������Ϣû�����ټ���������ʾ�¼���ص�Ĺ������Щ�����ޱȵĺ�ɫʯ�ס��Թ�ǽ����̨�ȵȵȵȣ�Ψһ�Ŀ��ܾ��������ڳ�����֪����������°���ΰ���������ڳ������о������������������˵�����ͬʱ�ƻ������ĺ��������������������ϡ�
������������ΰ�������������ֶ������ٵĻ������岻���ã�������ʹ��Ҳ��Ч���������п��ܾ���Ū�����ҵ�����ǽ���������ֻҪ�������Ǽ�������˯���ͻ�������ܵ�������
�����������dz����ҵ�ǽ��û�����⡣
���������ǻ�����������������ܰ����ֶ���������
���������������ֻ��߳������䣬�ߵ�¥�ϣ��ߵ��Լ������ſڣ���������ָ鵽�Ű��ϣ�����һ�������˽�ȥ��
��������С����û��Ϣ�ظ�����������¥��
���������Դ�����������ΰ˵����Щ�����뵽���������ܳ�����������Ҿ����ҵķ�����Ҳһ�������ֻ������˺����Ե��·���Ŀ���Դ��뵽�����ҵ��������û�ù���Ҳ��û���������ң�Ҳ����������ȥ˯����������С������Ϊ������Ū���ҵĴ���Ǻ���Ҽ��䡣
�������������Ҵ���ȴ�Ҷ��ѳ¼����¼�ȫ���˽�����Ժ���һ���ְ������X��ǽ���ÿ����ģ������ڣ��ƺ�Ҫ���¿���һ�¡���Ȼ�����ſӺ��������˺ͿӺ��ҵ��˿϶�����ͬһ����������Ӧ�ò�࣬�϶��ǰ��ж��Ŀ������һ���ȷ����־�����Ч�ĵط���
����������վ�������ſڿ��������ޱ���Ϥ��һ�У��ҵĴ����ҵ���ױ̨���ҵ���������ܻ���һ����¹�
�����������ǵ����ܰ���Щ���˵Ķ������������أ��컨���𣿻����ǵذ��£�����̫���˰ɡ���īɭ�Ļ�����У�����������������ģ��������ʲô�϶�û���⡣���������̫��ͬ�ˣ���������ֻ�ܲ�������İ취��ǽ���Ѿ���������Ȳ��ü��ķ�������ô���ܻ����컨���ذ��ﶯ�ֽţ�
����������ͻȻ������īɭ�����������ô��ط���������ÿһ�����Ӷ������Լ���ģ�Ҳ����Ļ�����ġ����ܳ�ס���Ƕ�ס����õļ����Ҿ��������Լ��ð죬�ٻ��ط�ʱ�ȴ����Ҿߣ������������˷���
������������ô������Ϊ�˲����ºۼ���
�����������ԣ���������ߵ���������ӱ���Ӧ��û�����⣬�����ڼҾ��ϡ�
����������վ���űߣ������ӿ���һȦ��Ȼ���۾�ˢ�ض�ס�˴�����Ҳ�ƶ����ˡ�
���������ԣ��Ǵ���
������������һ���ڴ��ϡ�
����������ʱ����Ҳ�����ˣ���������ô���¡�˯��С�����������������������Ҳ�����߳�������Ŀ�����ĵġ�
����������ƽ���ڵ绰�Ƕ˵��ҵ�ָʾ��
����������ҧ���г�ָʾ��ȥ������������
367��������Ķ���������
�����ָʾһ��أ��DZ߶�ƽ��ž�ذѵ绰�Ҷϲ����Ĵ�ȥ�ˣ��������С��ɲʱ��������˵ʲô��Ҳ���̳�����ǰѴӲ������ľɶ̵�����ҵ��������Ҳ���ʣ���Ҳ�����ң����İѱ��Ӵ���ʲô�ij�����������һ�ӣ�¶��ϯ��˼���棬һ������ȥ�����Ƽ��˵����������ű���ϡ�ﻩ����������������������ֺݡ�
���������������������ҵļ��Ȼ���߽�ȥ��С����æ��
���������ұ������ſ�ֻ�����������ҿ�����������ô�����ʱ����ҵ�������ʲô������������������IJ�������Ρ�
��������¥��������������������������������������Ȼ�������Ŷ�¥¥�ݵķ�������̽��ιιι�غ������ҳ�ʲô���ˡ�
���������������˵����û�£��㰲�ݵ���������������
����������Ŷ��һ�������Դ�����ȥ�ˡ�
���������ֻ��죬��ƽ������ģ����Ǵ��������Ҽ����ܿ������DZ��������Ź���վ��һ�䱻���ϡ���õķ���������ӡ�
����������˵�����������ˣ�����Ҳ�����ˣ�û�����⡣
������������ɫˢ�ر�ף������ź��˼������������ȵ�ǽ�ڣ�˵��������������ô���ܣ�
����������ô���ܣ�
���������Ѳ����Ҳ´��ˣ�
���������Ѳ������Dz����������ܻ��г������������⣬�������ֽС�������Ŀ���һ���ϵ��û�У�
�������������£����������������˵Ķ���ͻȻͣס�ˣ�Ҳû��˵�����żž����е���졣
���������ҽж�ƽ��ҵ绰��Ȼ����������ܣ��մܵ��ſڣ�����ͻȻ�˹���һ�ѽ�����ס���ú���ܳ��������ɵ�����˵����֪��������ͺã����ˡ���
��������������һ�������������������浽����ʲô��
�������������ش𣬻������Ű��������ƣ��ܲ�ס����������������һ���������Ѿ��ڴ����ˣ���ɫϯ��˼������������ã�¶���������͵��ɲ㣬էһ�ۿ�ȥ����ûʲô���⣬Ҫ�յ��ܽ��ĵط������ܿ����������������һЩ��ɫ�Ķ�����һ�ſŵġ�ԲԲ�ġ������������ڵ������棬�����е�����ƽ��ϲ���ȵ������̲���������飬���ŵ��������ʪ�ģ�����ϸ����һ��һ�ŷ·��ڶ������ں���һ����
����������û��ס���۵�����һ�ء�
���������������ҷ���¥����������������չ��ң�Ȼ���Լ���¥ȥ��С��������Щ�������������ҵ��ֻ������ˣ�������ָ����ƽ���������Ѵ���ף��ٿ���������û�мв�ʲô�ġ�
����������ƽȫ�����������DZ����ʲô��û�ҵ���
�������������������Ժ�ͻȻ�������������������ӣ���ͷ��ȫ���������
�����������Ǻܿ죬��������ˡ�
���������绰�Ƕ˵Ķ�ƽ�ѳ������ϵı���һ����ɫ��ĩ��ɵ����춼�ǡ�
���������������ж������̱ܵ�����������֧Ԯ��
���������������ŵ绰����¥��������û��ʲô�뷨���һ������ţ����Դ����Ǹղſ����Ļ���ѹ��˵���˻��������˴����ġ�
�����������������������һ�����ڵ�ԭί����ͷ�����룬����ֻ��ƿڳ���ƽ�����ȥ������ģ����Ƕ��dz�ʺ�İ�����
���������DZ�һ���Ĭ��
������������ѹסƢ�������������������궼û����һ�������𣿡�
����������ƽ˵������֪������
���������������ʣ����������ﶬ����һ�������𣿡�
����������ƽ���Dz�֪����
���������������ʣ����⼸�꣬��˭�ڰﳣ������������
����������ض�ƽ����֪������Ҳ������������˼�ˣ������ش𣺡��ӵ㹤����
��������Ȼ������˵�������������ˣ���Ȼ�������������������Լ���һ����ȭͷ��ǽһ������������Աߵ�˭���ſ����˵���������˭Ҳ�������棬Ȼ���Լ�����������¥���ܣ�������˵���ӵ㹤һ������һ�Σ�����������������ɨ�����ӣ�֮ǰ����ǽ��ʱ�������������������ˡ�
���������������˾�����ѵ绰�ҵ���
�������������DZߵ�������Ҳ�ﲻ��æ��ֻ�ܵ���Ϣ���ο����������һ�����̯�ӡ�
��������������¥�ϰ��ҵĶ����ﱻ���ı�Ҳ������������������û��ĩҲû��Ķ��������վ�������Ҫ�ˣ��ͺ�С��һ��������������ļ���ʲô��ȫ��һ���Զ��ᵽ����ȥ��һֱ�ᵽ����к���ǧ����Զ�������룬�������ͼ���ѻ����ˡ�������Χ������ûʲô���̣�����ũ�壬����ո�֮������龭���У�����û����ע�⡣
����������������Щ�µ�ʱ����һֱ�����ڿ���ɳ������Ų��ʣ�����������һ�ۡ�����˵������ô��Ӧ���������ǰѴ�����Ķ���Ū�����װ�ã��Ա��պ���һ��Ҫ���������ʱ�������������ã�����һ���������������һ�ѣ�ͷƤ�Ϳ�ʼ���飬����˵�����ڣ�ֻ���������յ���һ�˰��ˡ�
������������ᵽԺ���ʱ��������ȥ����һ�ۣ�����üͷ�������Ҽ�����ɳ���↑ʼ���̡�
������������һ�����̳鵽һ���ʱ����Ҳ��֪���ĸ����ԣ�ͻȻ���ֶ�������Լ�����������������һ�ڣ�Ǻ����ð���ǡ������������ȥ��˵���������Ͳ�ҪϹˣ�ᣬ�ֲ���ʲô�����⡣��
���������������������ƣ��е���֣�����һ�ۣ�����������ô�����ˡ����϶���Ϊ��ѧ�����̵ľٶ�������ʯ�ᣬʯ�����ǰ����ѹ���ر��Ҳ�������dz������̡�
���������ִ�Ĭ�����˼����ӣ�����ͻȻ������ûͷû��Ц��һ�����ý�ֺͷ����ҵ��ȣ���������������˵���¡���
��������������������֪��������ʲô�����£����Բ���ʲô��Ӧ��
������������������û�з�Ӧ���Թ��Ծ�˵�ˣ�����С��ʱ����һ�꣬���껹�������ʱ��ɣ��Dz�̫���ˣ������������ȥ���£���ס��һ��ũ��������������Ҳ���ܲ��ǣ�̫С�������¡������˰ɣ���С�Ը�Ź֣�ʮ�������ӣ�Ҳ��֪��ô�ľ��ǻ��˼ҵ�С���Ӵ��������������������������ֱ�Ӱ��������˹�ȥ��������ʱ����Χ������ģ�һ���һ��������û�У����Ż��ˣ��Ϳް��а��ְ���û�������ҵ���ײײ������������������ö���ֵĶ�������������Ӳ�ģ���ʪ���иɵģ�С����Ҳ�����������ģ��ҵ�ʱ�������Dz��DZ�ʲô�����̵��������ˡ���
���������Ҵ����ؿ�������
����������������Ц��˵������ʵҲûʲô�������ǰ����������ϵ���ũ�����������õ�Сé�������һҹ����
�����������������ֻ����ž������ֹµ������������Ķ��������ˣ���һ��������ĺ��ӣ����Ǹ�Ů���ӣ���ĸ����ô���Բпᵽ�����ĵز���
����������������Ц���ƺ����Ѿ���ȫ�ͻ��˵����ӣ�˵������ʵ�ɣ������������������ˣ�ֻ�������е�ӡ���ر�һ����ڵĻ�����ͻ���źͿ־壬Ҫƴ�����Ų��ܲ���г��������Ǻ����¼��밸���������ǹ�����ͳһ����ǿ���Ե�������Ԥ��������ҽ�������²�ͻȻ������Сʱ���й���ô�����ҵ��£������Ҿ�������ѧ����ر����档��
��������������������������������ۡ�
�����������������������ꡣ
����������˵�����ޣ���ô���ޣ������ˣ�������������
��������������������Ȼ�������������������˰���ˣ���Ϊʲô��ƴ����Ҫȥ�ȣ���
����������˵�����٣���Ϊ�������谡���Ҳ����Ҿͳ���ʮ������治�������ˣ��Ժ��м�ʮ���أ�������ҿɱ����𡣡�
����������˵����������ô���ȷ������װ��Լ��������ȥ����
���������������ѵ�Ц��˵���������ã���������ɥ�ˣ��ҾͲ�Ƿ���ˣ��±��ӻ����裬���ҵĺ�����ȥ����
���������������̣�û��ס������һ�ᣬ��������µ���������������Ҳ����ᣬ����������Ц��˵�������ƨ�����ֲ������衣��
����������˵������Ҳ��������С��û�裬���涼û��������
���������������룬��ο�ң�����������ֻҪ����Ҳ��������Щ���߰����������Ǿͳ����ܰ����ҳ�������ʱ�����Ǻ����أ��۾��ϣ��������ס�Ҫ���Ǹ������أ��Ͳ�Ҫ���۽�������ң��úù����ӡ���
���������ҵ��������������µ�����ô���������ɾ�������˳�����Ļ����ģ�����Ҫ����С����С��Ҳ������һ������ӡ���
�����������������ˣ����ޣ���������������ˣ����˵����㣿��
�����������۵�Ц��������Ҳ�ǡ���
�������������룬������������������ô�죿������ȳ����Ժ��ֲ������𣿡�
����������������ص�ͷ˵�����ţ�������ˣ����������Ժ���Ҫ���Լ��ܹ������أ��������ؽ����Լ�������ȥ���������������������������һֱ�ܿ�����������˵�ػ��ݻ�����������һ����������ܷ��ġ������������ȥ���أ��ҾͰ������͵�����Ժ��ȥ����ƴ��ƴ�����һ�����ٻ�Ǯ������Ժ�������ϣ������Ϲ���ȥ�ˣ�����Ҳ�������Ҳ�Т˳������������
����������������
368����Ƭ����Ů���������ң�����
��������һ���Һ�������Ϊ����һ��������龰��ͦ�õģ�����Ҳ���С����������Ҳ�ø�������һ�𡣵���Ҫ�����ܸ��Ƿ���Ļ������ٲ����Ҳ�÷���ȥ������������һ�ԣ�����ע���ķ��ޡ����Ժ�Ҳ����ˣ�Ҳ����ʱ��Ͳ�������ס�ˡ���Ȼ˵������������ȼ��ˡ�
��������ͻȻ����е�Զ�ˡ�
�����������Ҳ�֪��Ϊʲô�����뵽�ҽ�������Ҫ���˵�ʱ��������ͻȻð����������������������û���ǰ���ڶ�¥�鷿��������£�Ī���������Ԥ��ͻȻ��ת�����˱��ҡ�
���������һ������ǰ�ǴΣ������ҵ���¥������ʱ˵����Щ���űʵĻ���˵��һ�����ٰ��ij��С�
����������������֪��֪���㽭�и����ٰ��ĵط���
����������˵����֪�����뺼�ݲ�Զ����
������������˼��Щ��㱣�������˵����������ǰȥ�����˵���Ǹ��õط���ɽ��ˮ�����续����
���������������ž�֪����ʲô��˼�ˣ�Ц������˵�������������У�����ģ���Ҫ��ȥ�ٰ�������ߵ���һ�˽ᣬ�Ұ����谲�ٺã�������ȥ����
��������˵�Ż�������Ժ�����ж�������С�������Ҳ���Ĺ��ߣ��������Ŵ���ͱ���ʲô�İ����ۻ��Ȼ��ˣ�һ�������ĺ����·�ʪ�˴�룬ͷ����������ճ�����ϣ��ҵ�����ת���ֳ�ȥ��Ѹ�����䣬Ŀ��б�ӣ�����һ����鶼û�С�����������ȥ��������Ъ�ᣬ��ȥ����æ�ᡣС������һ�ۣ�������ҡҡͷ�������ڼ������ҡ����������ֻ������£������ȵ����ЦЦ˵����������ӣ�ʵ��ʵ�ĺ��ˡ���
�����������������������죬�����ڰ�֮ǰ�������������Щ���Ļ���������������ȥ�ˣ���С��һ����������Ҳ���Ż������������̵�����ȥ��ĬĬȻ�����Ų���˵����
�������������������ˣ����������û��ʲô������ת���ҵ�ע����������ӭͷֱ�����⣬�����ܲ���ȷ����������ֽ�����īɭ���ġ�
����������˵��ȷ����
����������ҧ��ҧ�̵٣��ݺ�����һ�ڣ����Һ�������
�����������������Ǻ�ҧ���гݣ����������Ĺ��������������Ѫ�������⣬��������ʱ��ͻȻһ�������˶�ƽ���ˣ������������Լ��������������ţ��·��Ҳ����Ƶġ�
��������������ĺ��ˡ�
���������Ҳҿ̵�Ц��˵���������ǰ����������������һ������Ļ�������Ҳ��ȫû���ˣ�ֻʣ�º��ˡ���
������������б��������̣�Ư���������ڻ�ɫ�������棬�������۾�˵�����������һ��ɱ���Ļ��ᣬ���µ�ȥ���𣿡�
�����������µ�ȥ����
���������µ�ȥ����
�������������������һ�ᣬ��ɥ�ش����۾�������ҡͷ�����Ҳ�֪������
�������������治֪����
����������ûɱ���ˣ���Ȼ�������������ݹ�ɱ����īɭ������Ҳֻ�����ݣ������µ���ͷ����Ż��ǻ᷸�˵İɡ�
������������ͻȻһ�������������磬��ݺݵ�˵�������Ҿ�����µ�ȥ��ɱ�������ɰɡ���
���������Ҵ�����̧������������֪���⻰�Ǽ�����˼��
����������˵�������ϻ�������������үү����
������������һ����ģ����ܵ��¼��ʹ��������ˣ���������һ������һ��ʮ�ֲ����ѣ���������ǧ���ظ�����˵��īɭ����������үү��ʱ���ҵ����ӻ�û��Ӧ����������Ҳ��ȫ�����Ͻ��ࡣ
���������������е��ջ𣬴��������̫���ܾ����顣������������̣�����¥���ߣ�ͷ����¥�ݲȵ�ɽ�죬һ�����Ҳ��ɸֵ����ӣ�Ȼ���͵�����ǧ���ܾ��������㣬���ԸϽ��ַ����ֽš�
������������û���һ�ᣬ����������¥�����������ҵı�����������ִӱ������ҳ��ҵ�Ǯ������������������īɭ���ҵĺڰ�����Ƭ�������۾�ǰ�棬�������ʣ�����Ƭ�ϵ�������ˣ�����īɭ���ɣ���Ƭ�ϵ����СŮ������������Ů��������ɣ���
���������Ȿ�����Ǻ�ȷ�������飬�Һ���īɭ�ĺ�Ӱ���Ļ��д������DZ����ղ��ǻ�һ˵�������ھ�Ȼ�е㲻ȷ�������ˣ��ӹ���Ƭ����ϸϸ�ؿ�����Ƭ�ϵ���������īɭ���Դ����ˣ���òʲô�Ķ�һģһ����������û���������§�ŵ���Ů���Dz���������Ů�������黹��û������ò���������ôС��СŮ����ü�۶���û��ȫ������
����������ϸ����һ���Ժ����ֿ�ʼȷ���ˣ�������˵������Ȼ��ʮ�����ԣ��������˻�����Ѫ������ĵط��ģ��ο���Ƭ���滹���֡���
���������ҳ����Ƭ�ѱ�������������������С�������ıʼ���үү���������1933��
����������������һ��Ȼ�����ң�������������д���𣿡�
����������˵����Ӧ���ǰɣ����ǵ��ˣ�Сʱ������飬�ļǵ���ô�࣬���Լ��ող�Ҳ˵��Сʱ�������Ҳ���˺ܶ�ô����
�����������������ּ������ˣ�����Ƭ��ת�������ݵ�����Ƥ�ӵ��½��Һúÿ������濴����������ٻش�����Ƭ�ϵ�Ů���Dz����ҡ�
��������������Ƭ�ŵ������۾�̫������ѹ��û���������е�û���������ֶ�����������������������һ������㰡������
���������������⻰Ҳ��ŭ�������Ц��˵�������治���㡣��
���������Ҵ��˴�������ʲô��˼��
����������˵��������������˼����Ƭ�����Ů������Ӧ���������ī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