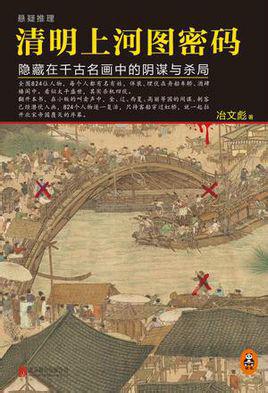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火车站录象的事情就到此为止,然后我跟谭仲夏回三楼会议室,还得接着讨论案件里的疑点。
关于凶手不遵守模式这件事,我耿耿于怀,还有麻醉剂的事情想不通,太想不通。
如果非要说凶手没有强迫症,根本不讲究什么模式,可以,但为什么在“开膛案”中对受害人使用麻醉剂?这桩案子的凶手明摆着胆小懦弱,根本不是个做屠夫的料,他蛮可以选择更简单的方式,比如一把火烧死扔水里溺死。可他宁肯冒着被法医查出麻醉药物成份然后有可能循着成份再找到来源的风险,也要将受害人麻醉以后再施以开膛破肚的酷刑。
到底为什么?
我恍惚间好像明白什么了,有道灵光在脑子里转来转去,我拼命想抓住而且似乎马上就要抓住了,可谭仲夏突然说话,吓我一跳,那道灵光刷一下不见,再要想找它又得从头想一遍。所以很沮丧地阴着眼睛朝他那边看过去,没有好脸色给他。
他也想跟我讨论麻醉剂的事情。
他侧身靠墙站在那里,眼睛看着地面,一只手半握成拳头放在耳朵边,摆出的是一个很文艺青年的便扭姿势。
他把好好的句子拆得零零落落往外吐:“先是、扎了、七刀、都、避开、主动脉,让郁敏、活活流血、死。然后、又是、肌肉、麻醉剂?所以,那个团伙、里面,有个、懂、医、的。”
我实在接受不了谭仲夏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几字一顿的说话方式,皱着眉毛瞪他几眼然后兀自坐下,不理睬。
他也不介意我将他视为空气,仍保持着那样的姿势和说话方式喃喃地重复一遍刚才的话,然后才终于恢复常态走过来问我他刚才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我只微微点了点头,但没有说什么,甚至点头的时候都没有抬起头去直视他的眼睛。
点头是因为我觉得从常规情况看,他的分析是对的,凶手团队里面至少该有一个懂外科知识,应该是与此相关的工作人员,比如医生、护士、麻醉师或者药剂师之类。
但是,这世界上就有些情况是非常规的。
我仔细看过“七刀案”尸体的照片和解剖报告,那七刀是慢慢地、仔细地落刀的,并不是在斗殴的混乱和情急中乱刺,所以,但凡只要是个稍微懂点人体结构和器官分布的人,都可以避开致命部位刺上受害人七刀,未必一定需要懂外科知识。
而麻醉剂这点,据我所知,除现在医院普遍使用的西医麻醉以外,中药里面也有些药物是能致人麻醉的,比如虎蝇草、马惊草、千缠姬等。有的需要吞食才会起效,有的通过注射,而有些甚至只要随呼吸进入体内就能立即起效。当然这些药都在常规之外,普通生活里十分罕见,所以在迹象和证据不是太明确的情况下我也不予多考虑。
只是那天在“开膛案”现场隐隐约约闻见的银贝梗的味道,像哽在我喉咙里面的一根刺,拔也拔不掉。银贝梗和马惊草、虎蝇草这些都是存在于常规之外的东西,所以既然我闻见其中一样的味道,如果现场还存在另外一两样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太震惊。
所以我对谭仲夏的分析,只抱一半的认同。
凶手团伙中可能真的像谭仲夏认为的那样,存在一个懂外科知识的医务工作者。
但也有可能是一位深谙中药,特别是罕见中药药理的人,比如像苏墨森或者陈伯伯那样的人。
在我看来眼下最应该纠结的不是这个,而是模式。
凶手们到底是用什么模式在进行犯罪。
必须弄明白这点,我才能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找凶手,否则只能被困死在这个像是用蜘蛛丝结起来的乱网里。
44、不存在的地名()
谭仲夏又准备说话,大概还是想跟我讨论他刚才的分析,我刷地刺过去一个严厉极的眼神,要他闭嘴。他便闭上嘴,交抱双臂歪坐进椅子里开始睡觉,两条长腿直直地伸在前面。
我重新把四桩案子的卷宗又铺排着看一遍,理出其中的共同点和不合模式的疑点,拼命拼命地想,费尽力气绞尽脑汁,终于给我想到始终隐藏在里面一个不和谐的点:生硬。
这起连环案绝对不像谭仲夏所认为的那样是由几个反社会人格的变态组织成的团伙所进行的什么审判式谋杀,也绝对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凶手没有任何强迫症,习惯随心所欲做事情。
都不是。
凶手不止一个人这点是肯定的,起码有两个以上,也许更多,甚至每桩案子都不是同一个人所为的可能性也很大。现在我不分析个性,只把他们当成一个整体看,这个整体不但讲究模式,而且也许可以说是讲究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所以才会显得如此生硬不和谐。
将每桩案子当成单独的来看,不觉得有多生硬,但连在一起看,问题就多了去了。为什么冒着可能会伤及主动脉或要害的风险非要刺郁敏七刀而不是比较保险的一刀或两刀?为什么冒着可能会被过路人看见的风险非要在枯河滩上将骆波凡活活烧死?为什么明明胆小怯懦不是做屠夫的料却非要选择那么残忍可怕的手段将铁俊开膛破肚?
然后,为什么前面几桩案子似乎已经有了相对比较固定的模式,到了“砸头案”时,却又突破模式,没有让受害人受多大的痛苦,直接一石头砸死了事,虽然后面又砸了很多下,但明摆着是泄愤的举动。
到底是为什么?
我唯一能够想到的理由,是他们根本没得选择。
他们必须这样。
所有这一切,时间、地点、目标人物以及死亡方式,都不是以凶手自己的意愿选择的,而是出于某种客观原因,必须得这样。
有什么样的特殊原因能够迫使凶手遵循这么个不成模式的模式?我想来想去,大概只有一种可能性。
复仇。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复仇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这个发现跟我之前一贯坚持的主张又合并到了一起,不会错的,这个犯罪团伙是复仇者联盟,不会错的。唯有这样才能解释全部我所强烈感受到的愤怒、仇恨以及案件里面想不通的疑点。
我想,很有可能,案件里这四个死者:郁敏、骆波凡、铁俊、王军,曾经都犯下过人命血案,并且就是以捅七刀、火烧、开膛破肚、石头砸头这样的方式杀害过别人,然后现在,那些案件中受害者的亲人突然通过某个渠道集中在了一起,组成复仇者联盟,犯下这四桩命案,他们在用以牙还牙以眼还
等等,好像不对,这四个死者以前真的犯下那样惨无人道的命案过吗?为什么在做背景调查的时候,没有提及到任何一点相关性?是凶手找错复仇的对象了吗?不对,一个找错也就罢了,不可能四个全部找错,而且还错得一点影踪都没有。
或者只是凶手根本不在乎真正的复仇对象是谁,只是随意将仇恨迁怒到另外一个人渣身上?
真的有这种可能吗?
不管怎么样,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立刻从旧案中查找,看看有没有与这四种凶杀方式类似的案件,无论是已经告破的,还是悬而未破的,都得查。如果真的有,就证明我的复仇论断正确,那就从旧案中翻找新线索,再来考虑为什么凶手会把仇复在这四个人身上。
我轰地起身,想喊谭仲夏派人去查,结果他不在。刚刚还歪在墙边的椅子里睡觉的,我走了几分钟神的功夫,溜得没影了。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跟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侠客一样。
我只好找别人,可惜付宇新压根没在局里,刘毅民回是回来了,被困在一楼大厅里跟那个折腾死人的代大记者周旋。
还能找谁?前面倒是走来一个熟人,王东升,可他是鉴证科那边的,不负责这摊子事。
王东升看我东张西望心神不定的样子,笑笑,说:“唉,你这个丫头,二十好几的人了,还不稳重着点,小心将来嫁不出去。”
我心不在焉跟他搭腔,说:“去,我走的是清纯可爱公主路线,等的是骑白马的王子,不用你操那没用的心。”
我没把握好音量,喊得有点响,惹得路过的几个警察窃窃笑,搞得我几乎想不起来刚才着急慌忙到底想干什么。
胡海莲正好从楼上下来,也听见我喊的那些臭不要脸的话,哈哈两声笑,说:“苏姑娘,你这狗血小清新的脸皮可真是越来越厚了,子弹都打不穿。”
我看见她,立马想起自己在急什么,拽她进会议室,叫她赶紧去查近五年里,也可能是近十年里,有没有发生过与眼下四桩案子类似的其它命案。不管是已结案的还是没结案的,只要有,都把卷宗调出来给我。
胡海莲是个极聪明的人,我话刚完,她便明白其中缘由,再不多问,拔腿就按吩咐办事去了。
看着她背影一闪消失不见,我心里挺不得劲的,又有点替她抱屈的意思,明明是个够格升职的人,偏摊不上这样的好命。那个懒得要死现在大概躲到哪个储藏室里睡懒觉的谭仲夏倒是好命,横空就降下来当了副队长。
这种官场职场里的事,真心看不懂,估计是他后台够硬路子够广,否则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接下去我要做的,就是等消息了。
整整等了两天,各方面的消息才到位,却都没什么大用,几乎可以说条条大路都是死路。
胡海莲那边只找到一桩用石块砸头的案件似乎跟现在的案件有点像,但细节完全对不上,而且那件案子的凶手早在三年前案发后不久就抓到了,人证物证都有,凶手也认罪,更加扯不上关系,其它别说是一样的旧案,就是有点相似的都没有。所以我之前的推理可能不成立。
白亚丰是去查“七刀案”死者郁敏生前用的手机号码的,可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说她只有那一个号码,而且十年没有换过。所以只可能是她在到乾州前不久买了一个没有身份登记的新号码,大概是凶手挑唆或要求的,只用那个号码进行联系。反正也差不多是条死路。
第三个回馈虽然跟连环案件没关系,但居然也是一条死路。
小海让我帮忙查一个叫“北排沟”的地方,我先问了刘毅民,他是地地道道的老乾州人,以为他应该知道,结果他听都没听说过,给了我个手机号码说是计算机部门的谁谁谁,叫我跟他联系让他帮忙进户籍档案系统或市政城建方面的系统查查,可能是早些年的老地名也不一定。可查了两天,回信息过来给我,说无此地名。
简直莫名其妙。
我原以为帮小海查个地址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谁知会查无结果,不由糊涂得要命,问小海会不会是她抄错字了。
小海听到“无此地名”的结果,眼底浮上失落,沉默着从包里面小小心心拿出一张用塑胶袋裹得严严实实的旧纸,看大小应该是从以前那种巴掌大牛皮纸封面的小工作笔记软抄本上撕下来的,撕得不齐,边缘很难看,上面确实写了小海跟我讲过的那两个地址,一个是乾州市北排沟,一个是江城市陈家坞。
江城市陈家坞。
陈家坞。
我感觉我拿着纸条的手都颤了,陈家坞,居然是陈家坞。她来乾州的第一天先跟我打听北排沟,我回答说不知道以后,她再跟我打听江城,说她爸爸可能有亲戚在那边。她只说到江城,并没具体提陈家坞三个字。现在看见,心里猛地一跳,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陈伯伯的脸。觉得这个地址,很可能是因为陈伯伯在那里的缘故。
可陈伯伯早就过世了,而陈家坞,也在四年前变成了一条荒村。
我稳住心思,觉得在搞清楚大概状况前,还是先不要把陈家坞的事情告诉小海,免得她着急上火就想马上跑过去看看,何况现在真想和她说我也根本说不清楚,我并不知道四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诡异离奇的事情,导致全村人死的死逃的逃把整个村都荒掉还驻扎进了武警部队。
四年前我去江城找一个姓林的教授请教问题时,恍惚听见有人说陈家坞闹鬼什么的,一是因为陈伯伯已然病逝,陈家坞对我来说不再有什么意义,二是觉得闹鬼这种事情,纯属无稽之谈,所以没留心,直到去年无意间听刘毅民提起。
陈家坞那个村子我知道千真万确存在着,虽然那里出了天大的事,但在地理上的坐标没有消失。
但这个北排沟是什么情况?怎么能连个影子都查不到?
45、死人样的眼睛()
这张写着两个地址的纸旧得泛黄,很有些年头了,我问小海哪里来的。她说是她爸爸藏在家里一张床侧面底部的抽屉里,她无意中找到的。
我听见说是修叔叔藏起来的,心里不由咯登了一下,因为脑子里有这么个潜在的意识,仿佛跟修叔叔有关的一切事物,就应该跟苏墨森有关,而跟苏墨森有关的,就该跟我有关,我费这么大的劲花这么多的时间跟警察打交道,就是为了查自己的身世之谜和身体之谜,现在有个现成的线索搁在眼前,当然不能轻易放过。
所以仔细又把那张纸看了几遍,重新用塑料袋装好交给小海保管,跟她说我会再想办法找人查北排沟这个地方的,可能是很早以前的地名,变来变去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
另外,我又告诉她说等手头这几桩案子一结束,就跟她一起去趟江城,我知道陈家坞在哪。
她眼睛里面冒出一点难得的光,灼灼地望着我,刚才那点失落不见了,脸上泛起些光茫来。
看得出她心里非常高兴,而且饱含感激。
我在心里叹口气,感激我做什么,我也并不是都为你,估计多半的原因还是为了我自己。
一圈转下来,只有刘毅民那边稍微查到点有用的线索。
他带了人拿着“七刀案”死者郁敏的照片在火车站附近打听,老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个在火车站外面马路边摆水果摊的妇人认了出来。
那妇人说几天前,照片上的女人在她的水果摊前站了十多分钟,不停朝候车大厅出口处看,明摆着是等人,很着急的样子,还一直打电话,但好像都没人接的样子。后来她手机响,她接起来,问对方怎么还没出来,说自己在哪个位置等。她接着电话的时候,不停往周围看,是找人,然后就走了,走到前面不远的地方上了一辆车。
妇人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郁敏在电话中告知对方自己所在的位置时说“在一个穿着花棉袄土不拉叽的老太婆的水果摊前”,这话气人,所以妇人记她记得特别清楚,说看她穿那样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货,估计是出来卖的,脸上的粉跟刷大白似的。
信息不会有错,只可惜那妇人不认识车的型号,只知道是辆银色的、能坐好几个人的大车。警察磨了好些时间请她指认,最后大致能确定是辆银色的七座商务车,牌子不明,更别说车牌号了。
不过老妇人说车上应该不止一个人,因为那女人打开的是后面的车门,而且没有直接上车,先跟后座上的什么人说了几句话才上去的。也就是说,车上至少有两个人,一个在前面开车,一个在后面。
当然也许不止两个。
用我的推断还原郁敏生前最后几天的情况,大致应该是这样的:有个什么人以谈什么生意为由接近郁敏,因为那生意违法或者跟法律擦边,所以让她买了个新的未登记号码跟他进行联系,继而两人坐同一班火车但分开行动到了乾州,出火车站以后,那人跟同伙在车上等她,她上了车就等于是掉进了坑,三天以后以尸体的形式出现在一间没人住的出租屋里。
这算是这两天里最有价值的一条线索了,可还是离抓住凶手很远。
我在家呆着也闷,就带小海一起往局里跑了一趟,在大门口碰上白亚丰,挂着张脸嘟嘟嚷嚷嘟嘟嚷嚷不知道在念什么咒,凑近了问,把他吓得跳起来,然后骂:“姓懒的欺负我,你也跟着一块欺负我?!”
我噗一声笑,问他:“哪个姓懒的?”
他张牙舞爪叫:“还能有哪个,就新来的副队长啊,一天到晚睡不醒地睡,有活全派给我去干,自己捡个缝就躲进去睡一会,气死我了。”
他管谭仲夏叫“姓懒的”。
我又噗地一声笑,问他:“姓懒的这会在哪?”
他翻着白眼气哼哼地说:“不是在这里睡着了就是在那里睡着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哪里能睡觉你往哪里找,错不了。”
说完就甩手走了,连背影都是气呼呼的。
我进大厅,看见楼梯那边走过来一群人,领头的一个好像是省厅的领导,赶紧闪身躲到旁边的接警室里。
我不愿意跟上面的官打交道,他们做事讲套路讲规矩,不喜欢我这种社会闲散分子插手刑案,稍微有点什么麻烦都喜欢往我脑袋上扣,之前有桩案子不知怎么的哪里走落风声,嫌犯跑了,上面几个领导就把付宇新叫去一顿批,说肯定是我嘴不严实什么的,好在付宇新当着那边的面嗯嗯嗯全都应承下来,到了我这里笑笑笑笑就过去了,什么都没说,之后有什么事情还跟从前一样找我。
躲了十来分钟出去,付宇新正好送走领导回来,抿着嘴看着我笑,说:“你倒真是机灵,知道躲。”
我听这话不对,脸就有点白,问他是不是出事了。
刚刚看见脸色难看的局领导,又看见脸色难看的付宇新,不用想也知道肯定出状况了。问了一声,果然!
付宇新回答说:“昨天晚上九点多钟,乾州社区网上出现一篇贴子,洋洋洒洒几千字,写最近四桩凶杀案,长篇大论头头是道,很是厉害,上面连夜公关,通宵一个晚上才压下,但影响已经扩散出去,再不赶紧破案,估计会有人跑公安局门口来泼大粪了。”
我挺不高兴地翻两下白眼:“怎么,上面又怪到我头上,说我走漏了消息?”
他笑着摇头,往里面走,我跟在后面。
他说:“你刚才多机灵,躲得那么快,领导没看见你,他们压根不知道你参与侦破了,我嘱大家瞒住的,省得多事。”
我听着就乐起来,说:“你胆子可真大,不怕我真给你捅点什么篓子,你交待不过去?”
他斜过来一眼,说:“你要真敢给我捅篓子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