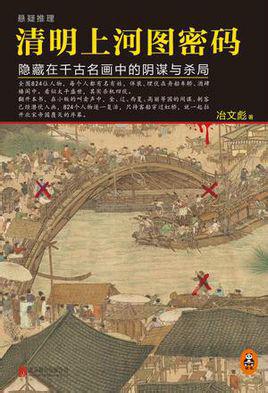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2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黎绪打来的。
她破口就是脏话:“妈的!”
吧完脏话以后她哈哈哈哈哈哈一顿狂笑,说:“我一直看不惯我妈把什么垃圾都收着的恶习,为这事跟她吵了不下几十遍,结果临了临了发现还真不是个坏习惯,至少她还保留着夏小雨那次请假时留下的手机号码。”
我原本还犯迷糊的脑子,一下清醒了。
459、画里的秘密()
黎绪把夏小雨的号码报给我,然后说:“我打过了,关机,说明这个号码应该还在使用中。我给她发了条短信,没说别的,就说了我是谁,让她回电话。我把你的号码也发给她了,万一打我的手机打不通,她至少能找到你,现在特地跟你打个招呼,免得你到时候吃惊。”
我表示很赞同,然后问她在哪。她说还在江城,到目前为止没收获,还得再蹲几天。
听这意思,好像是在跟踪调查什么人。
我问她需不需要帮忙,她说暂时不需要,然后问我这边怎么样。我就把她离开这几天里发生的事,审问周长寿、夏东屹真迹里隐藏的圆圈、把画当鱼饵放出去卖、吴沙帮乔兰香偷了药出来、把乔兰香送到私人医院去等等等等一系列事全都长话短说讲给她听。
她听了半天,呆呆地骂道:“操,我才走开几天,你们就演了这么多,开挂来的吧?!”
我噗地笑出声音,难得一下心情很放松。
然后黎绪又问我代芙蓉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我说他正在查独眼殷三郎跟廖世贵的关系。
她沉默几秒钟,说:“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尽量多照顾着点,代芙蓉现在的年纪正好是最危险的时候,他的家族遗传病随时会爆发,一旦爆发就全身骨头发疼,得生生疼死,可千万别让他孤零零受那种生不如死的苦,能陪着,尽量陪着吧。”
我听着,心里大恸,刚刚因为乔兰香得救而稍微好点起来的心情马上又低落下去,想了一会,说:“要不我还是再去求求殷向北吧,也许他会心软,人心都是肉长的。”
黎绪叹口气说:“算了吧,殷家的规矩比山都重,殷向北是绝对绝对绝对不会参与任何与盗墓有关的事的,如果他授意别人去做,真的盗出血珍珠来给你,就等于暴露殷家的身份了,他不可能为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拿整个家族冒险,换谁都不会。”
我原本想过到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就把代芙蓉送到研究中心去做治疗,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但今天听过吴沙的话,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了,把他送到那里去肯定不如让他死。
所以代芙蓉的命运,好像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比乔兰香都绝望。
黎绪问我现在手头还有没有别的事。
我说:“暂时没有十万火急的。”
她说:“要是腾得出时间来,你就往监狱跑一趟,看看能不能见到陈家坞那个于老棺,既然他多年前跟苏墨森有金钱上的来往,你又是苏墨森的孙女,还跟他有过一面之缘,说不定能从他嘴里问出点什么来。”
我说:“行,我这就打电话叫丁平帮忙安排好,我马上跑一趟,问出什么再跟你联系。”
她嗯了一声,突然笑笑,说:“保重啊,妮儿,故事在往前发展,还没到高潮部分呢你可千万别死在半路上。”
我用力呸她:“呸,闭上你的乌鸦嘴!”
她哈一声怪笑,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赶紧打丁平电话,问他陈家坞那个叫于老棺的现在在哪座监狱,能不能安排我见他一面。
电话那端愣了一下,问我见于老棺做什么。我说有点事情想问问。丁平叹口气说,迟了,他死了。我大吃一惊,本能以为又是什么阴谋或者杀人灭口之类的情节,可丁平说是肝癌,发现得太晚,没熬多久就死了,半年前的事情,因为于老棺本人跟别的这些事情没多大关系,所以之前也没想到应该要告知我一声。他说着,又问我想问于老棺什么。
我怅怅然叹气,说:“没什么,就是四年前陈家坞连环案里面一些事,想了解得充分些,既然死了就算了。”
挂掉丁平的电话以后我抱腿蜷在沙发里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整理一遍,各路信息挤得脑袋发疼,便干脆起身打扫卫生,把家具都擦了一遍,上上下下的地板都拖一遍还打上蜡,累得满头大汗,然后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感觉神清气爽整个世界都干净了不少,才又回到书房开始翻阅资料。
我很有目的地翻阅代芙蓉叔叔留给他那个笔记本的复印件,一页一页一行一行仔细看过去,终于找到了我想找的内容。
第十九页倒数第二行写着一排名字,其中一个,叫沈建庆。
沈建庆。
吴沙在叙述研究中心的人和事时,曾屡次提到b组的负责人沈建庆,我当时就想到这个名字早在我们的调查中出现过了,也清楚在哪里出现过,只是没有作声,也不着急,直到现在才来翻找。
代芙蓉的叔叔代文静把这个名字写在他临终前寄给代芙蓉的那个本子里,除沈建庆以外,本子里零零落落还记录了几十个名字,我起先挺在意的,但因为各方面调查都找不出任何跟这些人身份有关的信息后,就放弃了,没继续留意,谁能想到突然它就蹦出来了。
沈建庆!
所以我想,代文静生前的调查一定进行到了几乎触底的阶段,可惜老天给他的时间太有限,不然,他很有可能掀得起大风浪。
代文静记录下来的这个名字,是研究中心某个权位不低的人物,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本子里其它的名字,也是差不多的意思?也都是研究中心里有权有位的人物?
不能确定,但至少是一个可以进行调查的方向。
我给代芙蓉打了个电话,说我刚闲下来,可以跟他一起调查。他在电话那端温柔地笑笑然后拒绝了,说他一个人可以。我有点严厉,语气很重,问他是不是又在和那些危险的盗墓份子还有文物走私犯打交道。
他说:“你别说得这么吓人嘛,他们人其实都挺好的,只要不触犯他们的利益,都是很讲义气的人,我跟他们本来就没有利益冲突,还舍得花钱,他们不会为难我。”
我语气更厉:“代芙蓉,这世界上有句话叫‘不作就不会死’你听没听过?!”
他突然一声笑,说:“问题是我不作也会死啊。”
一句话把我堵得死死的,都不知道怎么接好了。
然后他跟我说他查到一点独眼殷三郎的事,和他太太有关。
殷三郎太太的身份是清白的,美国留学生,哈佛大学主攻数学,是个天才级别的人物,十四岁就参与几项重要课题,顺风顺水,二十二岁回国时在一次文物拍卖会上认识殷三郎,据说那次拍卖的是战国酒樽,有精美花纹,那女子非常感兴趣,但拍不起,殷三郎拍下送给她,两个人开始交往,两年后结婚,道上的人都不知道那女人的名字,只管她叫殷家三少奶奶,身份隐蔽,为人低调,道上的人都没见过她的样子。
据说她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中大儿子和小女儿由殷三郎夫妇抚养,二儿子暗中过继给殷向北抚养。大约六七年前,三少奶奶突然失踪,殷家黑白两面都花大力气查询其下落,至今不果。有传言说她是遭了绑架,不知道什么人以她的性命为要挟逼殷三郎盗金诀王墓。
这个乔段好耳熟,跟黎淑贞被绑,绑匪逼迫黎绪替他们卖命如出一辙,搞得不好是同一伙人。
代芙蓉还探听到另外一个重要信息,就是金诀王墓可能有个大门,而那个门需要密码才能打开。
我倒吸口气,立刻想到夏东屹那些画,画的数量、顺序、用荧光颜料隐藏在里面的圈,很可能就是金诀王墓墓门的密码。
如果真是这样,有些事情就能解释得通。
夏东屹通过周长寿的嘴对外放出消息,说他的画里藏着三十年代江南殷家埋下的那批宝藏的线索,以此引出了两个疯狂买家,这会那两拨人都正在打老懒手里那幅真迹的主意。
我们分析过,画里真正的线索应该不是导向宝藏,因为寻宝猎人不会花那么大的代价来获取不确定的线索。因此画的价值应该大于宝藏很多很多倍。如果关于金诀王墓所有传说都是真的,那么,似乎可以认定,夏东屹画里的终极秘密就是金诀王墓。
再想他画上的那些内容,湖、大屠杀,还有彩虹瀑布,这些真真切切指的就是1937年以前“娏”机构用来做实验那个叫长生殿的地方,两下一结合,也就是说,长生殿可能就在金诀王墓里面。
这还真是个不得了的猜想!
这么一来,就能解释为什么他们非要找到金诀王墓了。1937年那场大屠杀是始料未及的,里面的人逃得仓促,必然有很多实验数据和成果留在里面,非得回去拿到不可。
了解内情的人只要一看见夏东屹的画,就会明白他画的是什么,再结合周长寿放出去的关于宝藏的传闻,然后稍微对夏东屹做些调查,就会立刻意识到画的价值。
他们企图从夏东屹的画中破解出密码,回到金诀王墓中,也就是曾经研究长生不死和死而复生之术的长生殿中。
太疯狂了。
460、胡海莲的悲伤故事()
代芙蓉说他暂时只查到这么点信息,但还在努力跟进,应该还能再多挖到点什么。
说着,不等我说话,他突然兀自温柔地笑起来,问我这几天怎么样,过得好不好。
我听他的意思是不想再聊那些沉重的话题了,便也笑笑,说:“还行,得到些有价值的线索,感觉上挺顺利,也许要不了多久就能把真相连根拔起。”
他沉默了一会,说:“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说:“别的也挺好,吃什么都香,身体倍棒,偶尔会做个美梦,梦见一个干净完美没有阴谋的新世界。”
那边又突然沉默,好半天才重新开口,用一种怯生生的语气问:“你和老懒还好吗?”
我说:“好啊,挺好的,合作相当愉快,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都不跟我打马虎眼,听话极了。”
他笑笑,说:“嗯,你们好就好。”
然后说告别的话,把电话挂了。
我到他挂断电话才突然醒悟过来他问的不是这个,而是我和老懒的关系,除合作调查之外的关系。
恋爱关系。
可我都不确定,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谈恋爱。
真的,我没谈过恋爱,确实不知道我和老懒现在的关系算不算男女朋友,但我好像确实挺想念他的,有时空闲下来,想想他平常跟我开的那些不大不小的玩笑,就会傻兮兮地笑出来,跟个小孩子似的。
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
我带着奇怪的心情收拾背包,然后出门,开车去医院看白老爷子,正好白亚丰和刘毅民都在,便坐下闲闲聊了几句,听说老爷子的情况又稳定下来以后稍微放下点心,但实际上我们都清楚再怎么样努力救也没多少时间了,我很担心白亚丰到时受不住。
走出病房以后我问刘毅民认不认识很懂网络的人,白客或者黑客都行,但一定要技术够硬的、厉害的。我说我需要这么个人帮忙从网上查点东西,要快,越快越好。
他想来想去,慢慢摇头,说:“没有,局里那几个技术员懂是懂些,但不厉害,有次碰上桩网络犯罪的案件,是移交省厅处理的,但那边网络部门的人我一个都不熟,恐怕问了也不一定愿意帮我。”
我垂下眼睛不说话,心想这方面就只能另外再找办法了,但脑子转得发疼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到底不甘心,表情就有点恨恨的。刘毅民问我怎么个情况这么要紧,我笑笑,说没什么,他就没再问,脸上有担心的表情。
我让小海替换保姆在医院里照看,自己跟刘毅民还有白亚丰去了公安局,进门看见付宇新迎面而来,居然有种久别重逢的美好,忍不住便扬起明亮的笑脸快快乐乐喊了他一声。
他倒还是从前的样子,不特别冷,也不特别热情,只温厚地笑笑,问:“你最近在忙什么?怎么都见不到人?”
我歪着脸笑:“我还能忙什么,颠来颠去瞎忙呗。”
这回他笑出了点坏坏的意思,说:“瞧你春光满面的样子就知道没忙什么好事。”
语气里隐含的又是我谈恋爱的意思。
我突然就想不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个状况,让我和老懒看起来那么像是一对恋人,仔细回想这些日子跟老懒之间的点点滴滴,只觉得他变化很大,以前冷冰冰阴沉沉的,两只眼睛像是死的,给人一种心怀鬼怀的印象,后来变得温柔起来了,时不时还会有笑容。
我想起那天在我家书房里,他莫名其妙走过来抱了我一下,整个姿态看上去蠢蠢的。
嗯,突然觉得,他应该很喜欢我,不然不会有那么莫名其妙的举动,跟个小孩子似的。
付宇新没再说什么,叫上刘毅民一起出勤去了,我和白亚丰正要上楼,接警大厅那边突然跑来个女警察递了份材料给亚丰,说是刚刚从花桥镇派出所传真过来的,正月里那件泥石流白骨案的最新情况,因为是他在负责,所以交给他,让他赶紧看看。
我对那件案子没什么兴趣,就撇开他自己往楼上去,走到二楼晃了一圈看见胡海莲坐在茶水间里发呆,手里捏着个手机,落寞极了,静静坐着,简直像是刚刚从悲伤海里捞出来似的。我心里诧异,慢慢想起这样的情况好像不止一次,她似乎经常会有悲伤的时候。
胡海莲抬了下头,发现我在外面,笑笑,将手机揣回口袋,我真实看见她眼睛里有泪;正硬生生想憋回去。
我最见不得人伤心,赶紧走过去挨她坐下,握着她的手问她出什么事了。她摇摇头,默默擦掉眼泪,说没事。我再问、再问、再问、一再一再地问,几乎要把她问得痛哭出声。
最后,她哽着声音说:“妮儿你别问了,真没事,都过去好几年了,我就是死活放不下。”
看她那样悲伤,我真的不敢再问了,虽然我没经历过,但也能够想象往伤口撒盐应该是很疼的。
胡海莲说完走了,走得踉踉跄跄,几乎摔倒的样子。我实在不放心,想跟着扶她一把,可她不让,硬生生把我推开。
我一个人呆站一会,转身找她的同事打听,问了好几个人才终于有个稍微知道点来由,说胡海莲从前有个未婚夫,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经常跟驴友一起出去登山探险什么的,五年前遭遇山难,当时一队九个人,没有人生还,找到七具尸体,胡海莲未婚夫的尸体没有找到,只找到部分遗物,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死亡可能性很大,可胡海莲一直不接受这个事实,老觉得未婚夫还活着。她从原来的城市调到这里也是因为这件事,在那边没办法正常工作,整个精神状态都不对,什么活不干,只要找她未婚夫。那边局里没办法,给她安排了强制性的精神干预后又强行把她调到这边,总算好了许多,但时不时还是会情绪低沉,经常往未婚夫的手机里打电话。
原来是这么回事。
确实有好多次,我看见她拿着手机给什么人打电话,却又不吱声,原来是打给一个永远不会再接通的手机上。
仔细想想,换我我也一定很不甘心,尸体都没找到,怎么就能说一定是死了呢。可是再往深里想,真的不甘心也不行,看看每年有多少具无人认领的尸体躺在冰冰冷的格子间里,还不算那些了被烧了的。
所以老话总是说,人这一世,很无常。
我正想再找胡海莲聊聊,尽可能安慰安慰她,可突然听见楼梯那里白亚丰扯着嗓子在喊我:“妮儿,妮儿你在哪啊?!”
喊得歇斯底里,把我吓得原地跳了跳,飞也似的冲过去,差点当场把武器拔出来。
白亚丰喊成那样,为的是花桥镇那桩“白骨案”。
白亚丰刚才从接警员手里拿到的那份传真,是花桥镇派出所警察的一份后续调查报告。
报告上说镇中心小学教师周红于五天前失踪,没有向学校请假也没有跟邻居说什么,消息传开以后,苍头村有个村民跑到派出所跟警察说星期二凌晨两点多时,他打牌回家看见竹林后面好像有火光,走过去一看,是有人跪在那里烧纸钱,嘴里还念念有词,说些什么没听清楚。他大喊了一声,那人站起身拔腿就跑,他追上去扯住,用手电一照,就是周红老师,问她干什么,她说那个地方冲出白骨的时候她看见了,后来不停做噩梦,吓得不行,好像被鬼缠上了,就来烧点纸钱送送。那村民当时没多想,信了,周红老师在镇上口啤一直都好,而且说得挺像那么回事,换谁都不会多想什么,就放她走了。
直到镇上传言周红失踪,警察到家里调查以后发现门户完好,没有打斗或被翻动的迹像,看样子不像遇害或者被绑架,应该是自己离开的,那个村民这才联想起星期二凌晨竹林后面烧纸钱的事,就猜测正月里泥石流冲出来那具白骨跟周红老师有关系,市里警察前几天上门调查,把她吓坏了,所以畏罪潜逃,马上跑去告诉警察,这才有了今天这份报告。
我听着,心里隐隐有些不安,觉得哪里很糟糕。
我想起之前有次无意中听付宇新和刘毅民还是谁讨论过这桩案子,说尸体放在下面县公安局的殓房里,还没有做dna鉴定。
农村里这样发现的骸骨有很多种可能性,未必就是命案,也可能是经久失修的荒坟,或者哪户人家病死了人没钱火化草草埋葬了事,所以在办案排序上肯定往后靠,先紧着要紧的办。
何况那具白骨死了有些年头,样本采集上有困难,而且dna又是近几年才兴起的,数据库很不健全,就算能采到脊髓做鉴定,匹配上也会有很大难度,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又不小,所以县里一直拖着没办。
初步验尸报告上写着骸骨为男性,身高一米七八左右,从牙齿的情况判断年龄为四十到四十五岁,骨殖上没有伤痕,颜色也没有异样,死因不明。
461、最糟的一种()
我一边看报告一边把全部和花桥镇有关的信息都捋了一遍,很多人很多事呈爆炸型在脑子里炸开,泥石流、白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