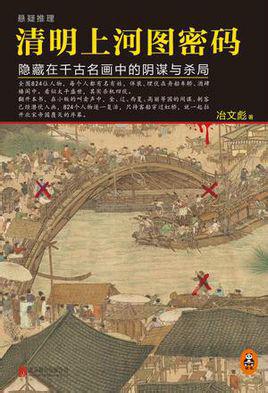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过她有次跟我闲聊时提到过,美国倒真有那么个顶顶厉害的催眠大师,能达到操控一切的地步,现在正被人当成研究对象关在美国某洲一家精神病院的顶级牢房里,用的全是最先进的隔离设备,一丝声音都不能从里面透出来,杜绝他跟外界对话,以防被他催眠。
传说那人用催眠术干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fbi跨境追踪好几年,最后进行缉捕时,还死了好几个警察,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是不是应该联系一下庄静,问问她,关在美国精神病院里那疯子是不是逃出来了,是不是逃到中国大肆犯案来了。
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也值得想一想。
犹豫到前面十字路口等红灯时,终于没忍住,真的拿出手机开始拨打庄静的号码。
我想,只要不透露案情,付宇新他们就说不了我什么。
这起“上帝之手”连环案,已经不能用常规思维模式去思考了,必须从旁的渠道寻找突破口,否则没办法建立起合理的逻辑。
这是我在切入案情以后第一次给心理专家庄静打电话。
可是关机。
红灯变绿,我放下手机一脚油门往前。
小海突然把头伸到窗户外面去往后看。
我问她看什么。
她答:“看老懒。”
问她:“老懒怎么了?”
她说:“刚才老懒的车在我们旁边,等红灯等得睡着了,绿灯亮了没看见,后面人按喇叭,他吓一跳,嘴里叨着的那根烟终于掉下来了。”
我想象那画面,噗地笑出声。
我加快速度,一连超了五六辆车,把老懒甩到看不见,然后想了想,觉得这会去局里没必要,现场勘查的报告和验尸结果都不会这么快出来,所以还是先回家吧。
结果才过两个路口,发现老懒的车又跟牛皮糖似的贴上来了。他要回局里的话早该转弯,跟着我们是几个意思?是有话要说?还非得跟到家里才肯说?纯粹有病。
我放缓速度,靠边停下,走到前面报亭买了两份报纸一份杂志,回转身看见老懒的车紧贴着我的车停在那,真跟块牛皮糖一样扯不掉了。我走过去,弯腰一看,呵呵,又叨着香烟歪靠着睡着了,整个人瑟缩成一团,眉头也皱紧,神情凄凉得像天桥底下累惨了的民工,像没家可归的乞丐,甚至可以说像个有今天没明天的可怜虫。
我敲窗户,他醒过来,斜着脑袋泛着眼皮迷迷糊糊看我一会,然后把车窗摇下,望着我,却不说话。我问他:“你什么意思?”
他的表情更迷糊,反问我:“什么什么意思?”
我拧着眉毛喊:“你跟着我干什么?!”
他一脸无辜的表情,说:“回局里啊,我不认路,不跟你跟谁去?”
原来是这么回事。
简直好笑。
我特没趣地回自己车里,调整方向,往局里开。他到乾州日子不长,且又专心于案件,没多余的时间了解这座城市,不认路是人之常情,总不能半路把他甩了管自己回家。
56、一问一答间过招()
一路开着车,小海时不时还在往后视镜看,我笑笑,说:”叫你帮我盯着老懒点,也不用盯得这么死紧死紧,何况也看不清楚。
她说:“闲着也是闲着。”
我说:“你老这么死盯着他看,他迟早提防你。”
她说:“我不死盯着看他也提防。”
我心里一跳,问她:“什么意思?”
她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感觉,感觉老懒那人对谁都不放心,都不相信,对谁都提防。”
我问她:“有没有明显的例子?”
她想了想以后才说:“他的睡眠很奇怪,有时候,明明是睡着的,但好像脑子里面有根弦死死绷着,随时预警。我们在他身边走来走去还好,没什么大要紧,但只要付宇新一靠近他身边,他立马就会醒过来。”
我心里又厉害地跳了一跳,感觉莫名其妙。大概是我太主观,把视线放得太窄,所以只注意到他对我的怀疑和提防,没料到对别人也这样,深想下去,隐隐觉得他横空降到乾州来当这个副队长可能不是件随机的、偶然的事情,也许有深层的东西在里面。
可是越想越糊涂,完全没有方向。
车子开进局里停好,下车,一起上楼,都不说话。老懒又换了一根新烟塞进嘴里叨着,看着特烦人,就鄙视了一记,朝他翻着白眼说:“你要抽,就点着,不抽,就扔掉。”
他说:“不抽,就闻个味,香。”
我拉开嘴呵呵讪笑,心想这世界上大概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烦的男人来了。
小海去茶水间找喝的,我跟老懒进了三楼会议室,他特客气地拉过一把椅子说:“妮儿,来,来来来,坐着聊一会。”
我又拉开嘴角呵呵讪笑,说:“怎么的?还要查我凌晨那几个钟头的不在场证明?”
他说:“你要是乐意说,我当然乐意听。”
我又讪笑,说:“真心对不起,实在没什么好说的。”
他说:“哦,那就算了,不在场证明的事,我随口一问,你别当真,我们聊点别的。”
看着眼前这张热情温和还带着笑的脸,我心里糊涂得要死,不知道他这又是想唱哪一出。
虽然有点排斥,但终于还是坐下,心想既来之则安之,你有胆子试探我,我就有本事戳你的破绽。
于是就开始聊天了,坐得这么近,几乎肩膀挨着肩膀,如果这时候白亚丰突然闯进来看见,回头肯定置我好几天的气。他不喜欢老懒,更不喜欢我跟老懒走得太近,他总觉得老懒对我没安好心,其实我也这么觉得。
这一场,其实也不能算是聊天,顶多算问答。他问一句。我答一句。再问一句。再答一句。
在一问一答间过招。
他问:“你多大了?”
我答:“二十六。”
他问:“你大学在哪念的?”
我答:“杭州。”
他说:“嗯,好地方好地方,你真是有福气,能在杭州念大学,浙大?”
我呵呵呵干笑:“不好意思,我没那么大能耐,就念了个普通职院。”
他没再纠缠这个,转而问我:“哎,你跟白亚丰怎么认识的?”
我说:“我在马路上多管闲事,正好帮上他的忙。”
他话锋一转,问:“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不打半点含糊,立刻回答:“红色绿色紫色棉麻色,只要是好看的颜色,都喜欢。”
他问:“你跟付宇新关系怎么样?”
我说:“还好,就那样,不特别近,也不特别远。”
他问:“乾州有没有什么特色小吃?”
我说:“有,酒心麻糍,蔡家豆腐羹,李子巷的麻辣黑鱼头,等手头这案子忙完,我一样一样带你吃去。”
他笑起来:“哈,就冲你这请客的爽快劲,我也得好好跟你交个朋友。”
他说完以后鬼恻恻笑:“难怪局里上上下下都喜欢你。”
我斜他一眼:“滚,他们喜欢我是因为我青春貌美冰雪聪明,谁像你似的没脸没皮围着钱打转。”
他说:“嗨嗨嗨,聊天归聊天,别人身攻击。”
说完马上又一个问题问过来:“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
他又问:“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红的人?”
“不认识。”
问到后来,我肚子里窝起一堆冷笑。
他这哪里是在跟我闲聊家常,根本就是在用他蹩脚的心理学知识试探我。他的右胳膊肘撑在桌子上,拇指和食指间捏着香烟,每问一个问题之前,他先把香烟头往桌子上敲两下。
这个动作很普通,抽烟的人常常会这么做,点火之前先在桌上敲两下。所以刚开始时我并没有多在意,可他敲烟的动作太多,并且有规律可循,都是在问出一个问题之前敲两下,问到后来我就觉出不对了。
这是一套用心理暗示来进行的简单测谎机制。
他先用烟头敲两下桌子,问我一个最简单的、平常的、完全没有必要撒谎的小问题;再敲两下,再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再敲,再问如此这般,就会在无意中给我造成强迫性和习惯性的思维模式,只要他敲两下桌子,我就会按照惯性回答出真话,等话出口再发现说漏嘴想要弥补的话,就算中他的圈套,被他找到破绽。
呵呵。
真是好笑死了。且不说我智商到底高还是低,好歹,我也是个看过美剧喜欢悬疑电影和的人,用这种小把戏来唬弄人,真不知道他是太低估了我还是太高估了他自己,做出来的事情,硬是这般叫人看不起。
再且,就算我什么都不懂,不懂心理学,不懂测谎,不懂惯性思维,就算傻乎乎钻进你的圈套,你又能从我的回答中发现什么漏洞呢?你能听出,我在第一个问题上就撒谎了吗?你以为我真的是二十六岁吗?!
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冷笑,脸上却时不时浮起暖意洋洋的笑,就好像真的很乐意跟他这个新来的副队长闲话家长拉近关系似的。
小海走进来时我们正聊起她。
老懒问我有没有去过小海的老家,我说还没机会,等这案子结了,腾出功夫以后,肯定要跟她回去看看,帮她把家里的事都打点清楚,她才能放心跟我在城里住。
我这样回答是有深层的意思在里头的,我得让他明白,不管他认可还是不认可,我都要掺和在他们的案子里,以前就是这样的,现在也一定是,将来除非我自己不高兴玩了,否则还是会参与,这是我的态度。
我等话出口以后,认真地盯着他的脸看,想从他的反应判断他的态度,到底是想踢我出局,还是觉得有我帮忙挺好,亦或是无所谓。
可惜我还是太天真。
我居然天真地想从老懒的态度中挖出他对我的想法或打算,可他能有什么态度?
他就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懒样,随口哦了一声,就转而问别的问题了。
他问我有没有吃过一种用血糯米做的糯米糕。
我说:“没有。”
他抬起脸直瞪瞪地看着我,喃喃地、用几乎是自言自语的声音说:“用血糯米做的糯米糕,韧劲很足,讲究火候,非要煮得恰到好处,不硬且不粘牙,才能算是正宗好味道,尝一口,够记两辈子。这么好的东西,你没吃过,真是可惜可惜了。”
我无言以对。
但是我听得出也看得出,他刚才这个问题不是随便问的,这些话也不是随口说的,一定有特别的深意在里头。可惜我听不懂,完全不明白他到底是在唱哪出又到底是几个意思,我跟他还没有那么深的默契。呵呵,默契别提了,杀气倒真是快要有了。他要是每天都要这么神神叨叨乱猜乱疑还胡说八道的话,我想我迟早有天得跟他动手。
白亚丰垂头丧气地走进来,一见我跟老懒靠得这么近,几乎脸贴脸,表情立刻炸了,但又不好发作,只能恨恨地瞪我一眼然后瞪老懒一眼,接着用很大的动作拖过一把椅子坐下。
来了这么团怨气,于是闲话聊不下去了,问白亚丰有什么事,他横着表情喊叫:“咋?没事我就不能来这里坐会了?你们见不得我闲还是怎么的?我还偏要闲闲地坐一会,看你们谁能咬我一口!”
一边说,一边气哼哼喝水,估计他是在外面哪里碰了一鼻子灰,随便找人撒气,所以都不理他了。
我和老懒回归正题聊案情。
我把几桩案子排出个新的顺序来,先是“砸头案”,然后是“火烧案”,接着是“七刀案”,第四件是“开膛案”,今天发生的“油画案”是第五件,如果没有更多案件发生,这个顺序,就应该是原版的顺序,它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向上升级的曲线过程。
不是每个变态杀人狂一犯罪就有固定模式,所谓的模式,往往是一桩一桩命案犯过来以后,有意识慢慢形成的。从这些案子分析,原版案件的凶手,在犯“砸头案”时,没有想得太多,只是出于某种因对方而起的或者是自身内心生出的愤怒将对方致于死地,然后多砸几下泄愤而已,但是到“火烧案”时,就有点不一样了,凶手有了更深一层的欲望,想要对方死得痛苦,所以将受害人捆绑住以后活活烧死。
梁宝市原版连环案件的凶手在升级的过程中摸索最适合自己、最能激发自己愉悦感的模式。
57、对峙()
我们之所以常常在“连环凶手”的前面加上“变态”两个字,就是因为他们变态到这样的地步,要不就是杀人不问理由不眨眼睛,要么就是花样百出残忍无度,再要么就是喜欢折磨受害人,喜欢眼睁睁看着他们生不如死。
我曾听庄静说,有些人在折磨人和杀人的时候,身体内荷尔蒙会爆棚,产生出一种类似于性高潮的激狂愉悦,对这种愉快的渴望会促使凶手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凶案。
我们眼下碰到的,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变态。
而且,不止于此。
到“开膛案”和“油画案”,凶手不但手法越来越娴熟,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讲究起画面、颜色和布局方面的东西,简言之是越来越艺术化,就像我在两个现场明确感知到的。
我相信原版“开膛案”发生时,尸体背靠着的那棵树,一定正开花,荒野萧瑟里突然一树繁华,何等漂亮。
也就是说,原版案件的凶手,不但是个高手,还是个有文化、有一定艺术修养的高手。
以前听庄静讲课,说有些命案我们无论如何找不到凶手,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凶手会是那个人。有些案件凶残致极,但犯案的凶手未必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长得凶神恶煞,脾气暴戾阴沉。他们很可能是非常普通的人,是那种扔在人群里就找不到影的人。他们可能有美好的家庭,儿女成群,有收入不错的工作,有让别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有特别高的修养,这些光环遮盖住他们嗜血的凶残本质,除非有最直接的证据,否则谁都不会将他们跟凶杀案联系到一起。
这段话大概可以作为这起原版连环命案凶手的侧写报告。
我问老懒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他默然不语。
他的默然不语让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兆头,意味着他终于放弃之前那个什么反社会人格团伙无差别谋杀的论断,偏向我的分析了。
白亚丰显然没怎么听懂,懵头懵脑的,不时扭脸看小海一眼,似乎是想看看她有没有听明白,小海仍是一副出世状态,尘世碌碌全与她无关的样子,不知道多少淡定。
我跟老懒说:“‘上帝之手’犯下的命案很可能不止这几件,也许有已经发生但还没有被我们归纳进来的,也许还有未发生但随时可能会发生的。这是原版案件中死者家属的复仇行为,不复完仇绝不会罢手,同样,一旦复完仇,联盟就会自行解体,不用担心以后还会发生。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代芙蓉以及梁宝市那边的配合,查明原版连环案件的凶手一共犯下过多少桩命案,凶手是谁,才能把调查进展往前推进。”
老懒仍旧盯着卷宗材料默然不语,好半天才抬头问我:“如果你是原版案件那个变态凶手,下一桩案子会怎么犯?”
我想了想,摇摇头:“很难说。凶手并不遵循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手段,所以没有规律可以找,他纯粹只是喜欢折磨受害人,从对方生不如死的痛苦里获取变态愉快。这样一来,有无数种可能性,从中国历朝历代所使用过的酷刑里面挑挑就有很多种可以用,剥皮、抽筋、炮烙、凌迟、腰斩、骑木驴、铁娘子、檀香刑、滚钉”
我没说完,他突然打岔,说:“咦?那个檀香刑是什么刑,挺好听的,而且好像有点耳熟,你说说看,怎么弄的?”
我白他一眼,叫他自己上新华书店买书去,有叫这个名的书,作者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他见我鄙视他没文化,赶紧换别的问题,说:“得了得了,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吧,如果你是凶手,下一桩案子,怎么做?
我说:”去,别拿我跟凶手比较,我嫌他不够档次。
说完以后扭脸看白亚丰:“你来说说,如果你是凶手的话,下一起案子怎么做。”
白亚丰本来就懵,见我突然问他,更懵了,呆若木鸡。
老懒看不下去,甩甩手说:“得了得了,你拿他跟凶手比?凶手嫌他不够档次。”
白亚丰无辜躺枪,又想不出反击的话,憋得难受,一脸痛苦。
我和老懒正讨论得入境,突然听见楼梯那边传来一片闹轰轰的脚步声和嘈杂声,付宇新在说话,刘毅民在说话,胡海莲在说话,这个问那个问题,又吩咐另外的谁去做什么。那个应着这边又应着那边,感觉像是电影里面马上就要召开重要会议时候的纷乱,紧急而严肃。
脚步声在楼梯口分成两拨,大部分继续上楼去了,有两个人往这边来,走到门口,敲敲门喊老懒,叫他赶紧到楼上会议室开会。
老懒看我一眼,懒洋洋挪着脚步出去了,一点都不配合其他人的匆忙劲。
刘毅民跑过来,急急地跟我说案情有重大突破,他们马上要开会,叫我先去吃午饭,等他们会议结束以后一起研究。
我点点头,先带小海出去吃了点东西,然后回来等。
谁知这一等,就是整整十个小时。
我们在等会议结果的十个小时里,刘毅民两次下楼找我,说事情很麻烦,叫我们先回去。
他越这样说,我越不想走,说:“反正回去也没事,在哪呆着都一样。我等得了。”
他没办法,只能随我。
白亚丰没参加会议,本来已经下班了,但是见我跟小海都不走,只好留下来陪着。他的级别和智商不够参加楼上会议室里正在召开的那个紧急会议,显得特无所事事,便没话找话跟小海套近乎,不管小海多不愿搭理都不放弃,自顾自乐呵,看上去特傻,我老是想笑,怕惊扰他那点小幸,就憋着,不理。
直到晚上十点半,会议才散,我端坐着听楼上会议室里椅子拖动的声音和纷杂的脚步声,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想着总算结束了,能开这么久的会,肯定已经从代芙蓉那边取得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