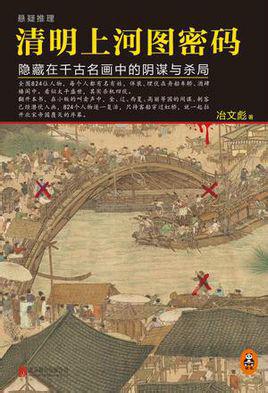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随随便便的事情。
还有现在站在后面紧箍住我身体的娘们也是,被人追杀成这样,也心不慌手不颤连心跳都没乱多少,声音里也听不出半点失措,镇定得叫人没办法相信。
换我是她们中的一个,能这么镇定吗?
不能。
当然不能。
我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但不管是去追杀别人还是被别人追杀,我都肯定做不到这么镇定。
所以,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她们彼此认识,并且,像今天这样你追我逃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大家都习惯了,这个有这个的使命那个有那个的宿命,只看谁的运气好。
弄堂深处的嘈杂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密集,那些被玻璃破碎声吵醒了的居民聚集在一起往这边看,吼着问我们到底是什么人,还丢碎砖块过来试探深浅,闹得我们很头疼,一边是生杀危险,一边是俗世麻烦。
估计这会最好的选择就是先弃车逃跑,回头再叫白亚丰来替我处理这个烂摊子。
但我身后的娘们似乎有别的打算,她手上使了点劲,把我卡卡紧,压着声音问我:“枪呢?”
我脑袋迷糊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我刚才是乱喊过一声我有枪,可那压根只是学电影里的套路吓唬吓唬人玩的,我个青春正好如花似玉的姑娘真有枪也不能随便揣在包里带着满大街溜达啊!
我想跟她解释,可嘴被捂着,没法说话,只好使劲摇头,表示没枪。
她见我摇头,呆了呆,低声骂出句脏话:“操,指望不上的东西!”
我被骂得很无语。
然后她审度一下当前形势,小心松开我,警惕地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压着声音用商量的语气跟我说:“听着,我们两个人加起来都不是她的对手。”
我点头,表示明白。
刚才那阵交手很说明问题,母夜叉除了力气比我大以外还有一种完全不计生死的狂劲,光这点我就不是对手,况且她的速度和灵敏度好像也都在我之上。
眼前这娘们再一次往两边看,然后又往上看,显然是放弃跟母夜叉拼命的打算,开始寻找逃跑路线了。
这地方虽说是弄堂,盘根错节哪哪哪哪都有路,可这会前后两个出口都被堵着,如果我们冒险往马路上逃,母夜叉很可能开我的车来撞,危险系数比较高,相比之下翻墙从人家院里穿出去恐怕还安全些。
正在做最后决定时,不远处突然警铃大作,越来越响越来越急越来越近,而且还不止一辆。
那些居民报警了。
这娘们用眼神示意我跟她一起翻墙,我一把拽住她,不让。
我要再看看情形。
果然,十秒钟后,我们就看见那母夜叉猫着腰从我车里窜出,飞奔着朝南而去,很快消失不见。
那母夜叉一跑,我就赶紧拽住背后这娘们的手腕一口气跑到马路对面,先把她塞进副驾驶室,自己再从前面绕到驾驶室里,砰地关上门,发动车子,刷地调个头,随便拣个不会跟警车碰到的方向跑。
其实我完全没必要逃跑,我又没犯法,干嘛怕警察,可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意识就做了这样的选择,下意识就认为这种紧要关头不能跟警察打照面。
后来我仔细回忆并推敲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一系列行为,觉得应该是从母夜叉骑到我身上毫不犹豫要致我于死地那个瞬间,心里就已经隐隐觉察到我跟她之间,还有那个被她追杀的娘们之间,可能都存在某种联系,所以之后的一切才会那么顺理成章。
我的直觉一向很准,这我知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发疯样凭借本能处理突发事件。
10、被追杀的女人()
开着车,我感觉到副驾驶座上的娘们偏着脸在打量我,我便也草草侧过脸去看她一眼,但太着急没怎么看仔细,就觉得好像挺漂亮。
车子开出老远,远到完全听不到警铃声以后,我才把速度放慢下来,吐着气扭过脸去认真看旁边的娘们。
她已经不看我了,正抬着脸对着镜子用手指打理蓬乱的头发,感觉到我在看她,才又偏过脸来看我,目光很淡,神情温凉。
车子还在往前开,窗外的路灯光亮一片一片在她脸上打过去,一会明,一会暗,像电影里的镜头,浓墨重彩。
多漂亮的女人。
劈面都是惊艳。
我先开口,问她:“去哪?我干脆好人做到底把你送到得了。”
她没说话,随便抬手往前面指。
我就笔直往前开,开进市区,到民府路的街心花园那里,她叫我停,我便踩住刹车。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没有经过刻意压抑的、正常的声音,公鸭嗓,有点粗,还有点哑,别有一番魅力,和她的容貌很搭。
她认真看我一眼。
这一眼很重,似乎有很多话要说。
但这时她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是短信或者微信之类的提示音,她没当着我的面拿出来看,而是开门下车,走到路灯底下,朝我挥两下手,意思是叫我可以走了,然后才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看。
我没急着走,停在原地静静地看着她,突然想起自己这趟出门的目的是去公安局,白亚丰还在那里等我,赶紧拿出手机打电话过去,告诉他我临时有事,今天不过去了,明天见。
他“唉呀唉呀”叫了两声,没说什么。
我收好电话往外面看,那娘们还站在路灯底下,正变戏法似的摸出一根香烟放进嘴里,点火打着,深深吸进一口,没再看我,只自顾自往前走去。
她点烟抽烟的动作,以及走路的姿势,都特别酷,像个优雅的女流氓。
我看着她慢慢走远,消失不见,才发动车子,调头,往家开。
这是我第一次跟黎绪打交道。
后来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这天晚上我没有出门,或者早几分钟迟几分钟出门,就不会碰见她们,也不会救到她,那她可能会被戴明明杀死,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情了。
但是再细想,又觉得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我们两个人,即使这天晚上不碰到,将来也一定会碰到。她没那么容易被那些疯子杀死,我也注定喜欢多管闲事。
我回家以后发现衣服裤子有上大片大片的血迹,吓了大跳,仔细检查发现除了右边屁股上有被尖石子割出来的一道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伤口,所以这些血肯定是母夜叉的。
她跟那个逃命的女人大概在遇到我之前就已经打过一场,弄伤了,一直在淌血,跟我滚打在一起的时候把血弄到了我身上。
想想她们也真够厉害的,浴血厮杀,把个歌舞升平的二十一世纪搞得跟古代战场一样。
我把染血的衣服脱下泡在脸盆里,心想洗不掉的话还得找个时间烧掉或者找个地方挖坑埋掉,真麻烦。
然后痛痛快快洗个澡,拿出药箱站在镜子前自己处理屁股上的伤口,破了皮流了血,稍微有点深,不过还好,只在坐下和突然起身的时候有点疼,估计两三天就能好。
从小到大我挨过多少揍受过多少伤,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很有把握的。
收拾清爽之后狠狠睡了一觉,第二天中午才起床,洗洗漱漱磨磨蹭蹭吃过午饭才出门,一路堵车。
到公安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白亚丰一个人呆在三楼会议室里盯着满桌子的卷宗材料发怔,看见我就扑过来抱,哭丧着脸喊:“唉哟我去唉哟我去,妮儿你可来了,你再不来我肯定得死在这里!”
我受不了他头发里那股子油味,赶紧嫌弃地推开,拧着鼻子往里面走,叫他废话少说,拣要紧的讲来听。
我说这话的语气也很嫌弃,因为他那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废话特别多,往往别人十句话能说清楚的事他得说上一百句,我这会没闲心情听他东拉西扯。
白亚丰有个很明显的优点,就是脾气特别温顺,从来不在意我嫌弃他这嫌弃他那,回回都乖得跟孙子似的,我说什么是什么。
听见我说要听案情,他立刻飞扑到桌子前面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卷宗分成三堆,码齐了往我面前推。
然后他糊糊涂涂把整个情况讲了一遍,中间不时夹杂抱怨的话,说年都没好好过,假也没放,大正月的全局上下都加班,怎么怎么的。
他说着说着案情突然笑起来,目光灼灼地盯着我,说:“妮儿,我要是能把这几桩案子破了,保管就升职加薪,当副队长!”
我泛着眼皮子看他,咧开嘴呵呵呵干笑,不搭茬。
呵呵,副队长,真亏他想得出来,他要是能当副队长,我估计我就能当公安厅厅长,哦,不止,大概能当国家安全局局长。虽然官位未必跟智商成正比,那也总得差不离才行。况且严副队长根正苗红能力强,又学习又进修特积极向上,凭什么把位置让给别人,
但我没说什么,只仔细听白亚丰的叙述,同时翻看卷宗材料,用心研究案情。
让白亚丰烦恼不堪的是最近发生的三桩恶性凶杀案,分别用a、b、c来指代。
a案的死者是个年轻女人,年纪在25到30岁之间,身份不明,尸体被扔在城北一间出租屋内,发现时已经开始腐烂,法医解剖结果是死了七天左右,死因失血过多。凶手用麻绳将受害人捆绑住,嘴巴贴上封箱胶带,连捅七刀,但都不在致命部位。
b案的死者叫骆波凡,45岁,是个包工头,尸体在沙湾河下游的河滩上被发现,扔在汽油桶里一把火烧成了焦炭,法医鉴定结果是活活烧死而不是死后烧尸。死者的包在不远处的芦苇丛里找到,有身份证、驾照和银行卡,还有一万元现金,排除抢劫杀人,大年初八的事。
c案发生在两天前,死者是个十五岁的男孩,初中一年级,钝器击打后脑致死,尸体埋在死者居住那个小区花园外面一堆沙子里,第二天早上被建筑工人发现。没找见凶器,警察赶到的时候,沙堆周围都是看热闹的人,现场被毁得差不多了,也没采取到有用的环境证据。
短短半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桩恶性凶杀案,上头没逼他们二十四小时睁着眼睛查案算不错的了,还想放假。
我想,如果严副队长在的话,不管哪桩案子,接到报案时就会给我打电话叫我去现场的吧。
可惜他年前就进修去了。
付大队长虽然也允许我参与刑案,但不像严副队长那么器重我的感官能力。
白亚丰和刘毅民两个肯定是为了让我好好过年所以没打扰我。
三桩案子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白亚丰讲述的时候,情绪太激动,加上他表达能力不怎么行,逻辑很混乱,完全没条理,常常说着说着这件案子,又突然扯到那件案子去。
他说到哪部分就找那部分的材料和照片以及相关报告给我看,所以之前刚刚分好的卷宗没几下功夫又被他划拉得乱七八糟。
有几次我脑子里突然闪过点灵光觉得好像有线索,可被他一搅和,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要再仔细看看相关的材料信息,也早被淹到哪里去都不知道了,简直一个头八个大。
可看他那么紧张着急的样子,很不忍心打断,只能听他讲完再作打算。
难为这货智商不高,积极性倒一直很高。看他眼窝深陷嘴唇起皮的样子就知道大概有两三天没怎么睡了,可问题是他实在太笨,不管怎么熬怎么拼,上帝都不肯给他开一扇窗,烧光脑细胞也没办法靠自己的能力破掉一桩案,养在缸里的金鱼都替他的智商着急。
说得难听点,他真的是那种天赋不够再多努力都白搭,智商不够拿命来凑的笨警察,简单点说就是满脑袋浆糊,智商全都拿来卖萌用,但效果又并不好。他甚至有种万人不及的超能力,总是能把已经糟糕了的事情搞得更糟糕,简直无法解释。
不过,话说回来,好在他姿态低心又宽,磕磕碰碰一路过来倒也没出过太大的乱子,还算如愿。刘毅民有次特无奈地跟我苦笑,说他大概就是老话说的“傻人有傻福”吧。
白亚丰终于长江黄河大浪涛涛把三桩案件情况都讲完以后,盯着我的眼睛特认真地问:“我说了半天,你到底听明白了没有?”
面对这么个货,我真是一点脾气都发不出来。
他自己经常听不懂别人在说些什么,所以自己说些什么也老担心别人听不懂。
就这么个木鱼脑袋,居然也能混到刑警队伍里来,想想真是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这里面有黑幕,怀疑他是不是凭着他父亲白老爷子以前在警队的影响力混进来的,后来特地仔细打听过,还真差不多是。
他是因为有故事,才被故事里的人合力帮着拉进队里的,原因真就在他瘫痪的父亲白老爷子身上。
11:泥石流冲出来的白骨()
我心疼白亚丰累得跟条狗样,挥手叫他躺沙发上去睡一会,让我安安静静当一会福尔摩斯。
他嘿嘿嘿挠头傻笑几声,走到沙发边倒头就睡,跌进梦里了脸上还是笑眯眯的,像个小孩子,特踏实。好像只要我来了,案子就能破了,他真的就能升官发财了。
想得可真美。
我趁他睡着,赶紧整理卷宗,一边回顾他刚才的讲述,一边对照现场照片和验尸报告,给三桩案子分别起了简单直观的代号,“沙堆案”、“七刀案”、“火烧案”。
这样做简单直接容易区别,谁听见都能刹时间明白说的到底是哪桩案子,国际惯用手法。
我从被害人的性别、年龄、死亡方式、凶器、以及命案现场、犯罪时间等多个角度着手,细细密密地铺排梳理过去,发现三桩命案的表面没有共同点或相似处,也没有直接联系,所以是不是连环凶杀还需要更多深层的调查报告,比如受害人之间是否认识,有无利益冲突之类的。
正忙着,会议室的门被推开,有个警察探进半截身子想说什么,看见白亚丰躺在沙发上睡得跟头猪样,便朝我笑笑,退出去了,还轻手轻脚带上门,很怕打扰我的样子。
我没理睬,又端坐着研究了一会卷宗,慢慢把重点放在“沙堆案”上,因为目前就这桩里面有破绽,而且是挺明显的破绽,在命案现场的照片上直白地呈现出来了。
但是另外两桩命案里面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基本上就把这桩给区别了出来,凶手也差不多应该就是那个大清早扛着铁锹出门干活顺便发现尸体的建筑工人。
十五岁的男孩子去亲戚家吃完晚饭以后,到同学家打游戏,深夜回家的路上遇袭,被钝器击打后脑死亡,尸体埋在离他家不远的沙堆里。法医从致命创口的面积和深度初步判断凶器为较大较长的金属工具,比一般家用的扳手和铁锤都要大,但还不能明确知道究竟是什么。
这件案子的第一现场在离埋尸沙堆约两百米的一条小巷子,附近都没有找到凶器。
凶器是关键。
现在离命案发生还没有过去太久,只要找到凶器就好办了。
我又看了一眼照片,十五岁的男孩子,多好的年纪,说没就没了,心里觉得惨伤。
这些年里我尽可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不对外在的人事物有过多的同情或者愤怒,但终究很难做到。
苏墨森倒是很厉害,活得跟座冰山样,又冷又硬。他说所有的情感都是多余的,只会拖延人类的进步。
我在调查自己身世的过程中,有次无意间看到一个网页,是从日本一家医院网站上摘取和翻译过来的,说有个什么什么教授已经破译人类大脑的密码,只要外科技术达到足够的水平,就可以随心所欲控制人的全部思想和情感,类似于用程序操控机器人。
那论文弄得有条有理,说得跟真的似的,倒很符合苏墨森的三观。
我走神想到苏墨森,心里冒出点寒意。
会议室的门又被推开,这次进来的是刘毅民,看见我在,吁出口气,疲惫地笑笑,说:“得亏你来了,不然我也得打电话喊你来。”
我问:“怎么了?”
他指指桌上的卷宗叹气:“这些还不够?还想要怎样?再怎样的话,我估计天都要塌了。”
我想问他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调查情况,可外面有人喊得急,他不得不匆匆忙忙走了,做了个很抱歉的手势。
刘毅民刚走,胡海莲来了,脚步生风,眉毛跳舞,看见我在,热热辣辣喊了我一声。
胡海莲年纪轻轻已经是局里出了名的泼性子破嗓子,洪钟样的声音一落地,睡在沙发上的白亚丰就打着颤炸醒了,差点没摔地上去。
胡海莲听见动静才看见他也在,故意用东北口音揶揄一句:“唉哟我去,你可真是个属猪的,咋搁哪都能睡得着,也不怕睡里梦里死过去!”
白亚丰丢个白眼给她,抹抹脸,出去了,一脸懒得跟她计较好男不跟女斗的表情。实际上却是不管从体力方面还是智商方面或者音量,他全都不是胡海莲的对手。
这两个人常常拌嘴斗气,大家都当好戏看,有阵子还闹出过绯闻,把白亚丰气得暴跳,胡海莲倒是大气,说哟,瞧你急那猴样,咋?我还配不上你?白亚丰呸她两口,她追着连踹他三脚。
还有传闻说他曾被胡海莲一个过肩摔摔得躺在床上三天不能下地过,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我认识的白亚丰,从来见了胡海莲都是躲着绕着退避三舍坚决不往前凑的,当然合作办案的时候例外。
胡海莲跟我今天在局里看到的所有其他警察一样,也是一脸倦色,几辈子没睡了似的。
和别的警察不同的是,她显得风尘仆仆,鞋子上裤腿上沾着大块的泥巴,估计是刚去过乡下或者郊区。
这阵子天气变化很大,时不时暴雨,还夹杂冰雹,有点四时不正的气象,民间很多说法,都不大吉利。
所以,如果手里几桩案子不赶紧解决的话,可能会有民怨。
这都不是最糟的。
最糟的情况是连环凶杀。
乾州市虽然不小,但也不是地狱,不是罪恶之城,不是美剧里面的拉斯维加斯。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三桩恶性凶杀案,巧合的机率真的很低。“沙堆案”的情况比较明显,可以排除在外,“七刀案”和“火烧案”就不太好说了。
万一真的是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