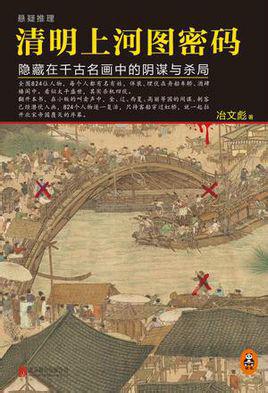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4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认真地听着,又回想起那天,代芙蓉坐在我家客厅里提到“鬼附身”三个字时闪烁不定的目光。
原来他知道这么多,原来他跟过的离奇案件这么多,原来他对这样那样的离奇事件和物件的好奇心这么重关注度这么高。
我想,代芙蓉在暗中调查的东西,和我在暗中调查的东西,有某些相似之处吧,或者可能方向一致。
我感觉口干舌燥,而且呼吸困难,好一会才想起来问他那个叫石玲的女警后来怎么样了。
他说:“从江城警方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消息说,石玲在处理陈家坞案件的遗留问题时殉职了。”
我心脏乱跳,先是替好好的一条人命婉惜,紧接着觉出陈家坞事件的后续严重性,情绪越来越紧张,声音就有点尖:“遗留问题?什么遗留问题?!”
98、我到底是谁()
代芙蓉没被我的情绪影响,继续平静地往下说:“警方是这样讲的,当时的媒体也都这样报道,在处理陈家坞遗留问题时殉职,具体情况到底怎样除了跟她一起亲历事件的人以外,大概没别人知道了。那件案子结束以后,我又去了陈家坞,还是进不去,村口有武警驻守。我谎称进村找亲戚,他们告诉我说所有村民都已经迁下山安置,那里只是一条荒村了。我就想,如果真是荒村,有什么必要派武警在那里守着,所以又想别的办法,打听到还有另外一条小路,可以从山背后的乱石丛中进入陈家坞。我就试着从与支岐山相邻的另一座山里面打听和寻找,当地村民说老一辈人是说过有条秘密小路可以通到陈家坞,好像在一个叫龟背崖的地方。我去了龟背崖,没找到路,可能因为多年没有人行走,被草木掩荒了吧。”
乱七八糟这么多事,信息量太大,我一时有点抓不住重点,只好重新回到那个被鬼附身的叫石玲的女警身上,问他对她了解多少。
他说:“案件结束以后我去过石玲家,见过他的父母,父亲是退休干部,母亲是家庭主妇,只有那一个女儿,痛不欲生,我也不好问得太深入。后来又从别的途径查,发现石玲在被鬼附身以后,好像卷入了另外一桩命案,被当成嫌疑人对待,负责侦办案件的是上海派过来的警察,所以我认为,石玲卷入的案件发生在上海,深查了一下知道,她撤出陈家坞以后,父母带她出门做了长途旅行,中间转到上海呆了几天,但我不知道上海那边到底发生过什么。”
上海?
上海!
我艰难地咽下一口唾沫,想起老懒。他就是从上海调过来的。我一直觉得他突然出现在乾州肯定有特殊的原因,现在看来,这个直觉很准。而且更加验证了另外一个直觉:所有的事情都互相关联,虽然看上去很乱,但一定能找到一条贯穿的主线!
我喝两口水,缓缓情绪,清清嗓子,再问代芙蓉对四年前陈家坞的案件了解多少。
他说:“不多,大部分都是警方正式公布的,谋杀,凶手是村里面一个离职的数学教师,谋杀方式是下毒,最后拒捕袭警时被当场击毙。”
信息真是少得可怜。
代芙蓉想了一下,补充说:“当年击毙凶手的,就是付宇新,他好像也是因为在那次案件中立功而被升职到乾州来当大队长。”
原来就是陈家坞的案件,可居然从来没人跟我提过半个字,是大家都觉得没必要提吗?还是压根都不知道?或者
或者是上面嘱咐过不准提?
我想起“人皮x案”,几次有人提到都会告诉我说是密案,于是立刻将它跟陈家坞的案子联系到了一起。
再细想,如果当年驻村查案的七个人中确实有楼明江的话,两起案子更可能有内在的联系了。陈家坞变成荒村以后驻进了武警,而楼明江至今都还在跟江城的警方进行合作,那是不是可以说,四年前陈家坞的案子,就是传说中的“人皮x案”,到现在都没有真正结束?
可惜代芙蓉没有更多信息可以告诉我了,他对此感到抱歉,说如果当初知道现在我需要那起案子的信息,就一定会多下点功夫做调查。
我瞬间被他语气里的歉意感动,觉得很过意不去,赶紧说:“没关系,我会想办法从别的渠道去打听,你不要在意。”
然后我又嘱咐他一个人在梁宝市要万事小心,宁可什么都查不到,也不能出事。
他一一应下,声音很弱。
原本到这里就该挂电话了,可他说还有一件事。
这件事乍听像是突然冒出来的,其实肯定是犹豫很久了的,之前他动不动沉默一下,大概就是在考虑措词。
他说:“明天上午十点,你到局里付大队长的办公室等电话,会有匿名者打过来,他会告诉你们梁宝市这几桩旧案的详细情况。你别问我他是谁,我要是知道的话早就找去了。是那人匿名打我的手机,问我是不是乾州市派过来协助调查几桩旧案的,问乾州市里是不是发生了跟这边差不多情况的命案,我如实回答以后他问我是谁在负责乾州市那些命案,我报了付队长的名字,然后他说明天上午十点会打电话给付大队长告知一些情况。”
恐怕这才是代芙蓉今天打电话给我的主要原因,结果却是放到最后才讲。他讲完就想挂电话,我赶紧喊住,真心实意跟他道了一句谢。然后又万分报歉地跟他说:“乾州市这起连环命案,最后也许破不了,所以你可能没办法发表有份量的报道。”
代芙蓉听了,笑一声,说:“随便吧,无所谓。”
我觉得这不像是我曾经以为自己非常了解的那个代芙蓉说的话。曾经我以为代芙蓉是个为了报道新闻不惜拼命的厉害记者,但现在他的语气听上去好像有点看破红尘爱咋咋地的味道,听着有种说不出的伤感。
我很想问问既然他无所谓报道的事情,为什么要帮我这么多,不惜在梁宝市惹上一堆麻烦。
但终究没有问出口。
那天他从我家走出去时的背影里,好像承载了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几多悲壮。
我又嘱咐了几句,才准备挂电话。这次却被他喊住。我就等。可他又沉默了很长时间。
他在电话那端欲言又止。
欲言又止。
我轻松地笑笑,说:“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
于是他才终于艰难地问出了口。
他问我到底是谁。
我万万没想到代芙蓉会问这个问题,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愣在当场。
代芙蓉见我不答,沉默了一会,轻轻叹出口气,说:“我说实话,你千万别介意。我查过你的背景,户籍和档案方面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但也不是完全圆满。资料上记录的你念过书的小学和中学我都去仔细打听过,在符合你年龄阶段的几年里,没人记得有你这么个学生。杭州那所大学里倒有人记得你,传媒系的系主任和你的班主任老师还有体育老师等人都对你印象很深,但你只读了一年便办理了休学,之后也再没回去继续学业。你没有任何工作经历,而且好像,除了警察和现在跟你一起住的那个胖姑娘以外,你没有别的朋友。所有这些都不正常,但又找不出问题在哪里。”
我听得呆住,有点没法呼吸。
他继续往下说:“所以我从你爷爷和你的户籍所在地着手去调查,那个村子里确实有个叫苏墨森的人,他还活着,但明显不是你真正的爷爷,甚至都不知道你的存在。他有孙子,没有孙女。或者说曾经有过孙女,但在出生不满十个月就夭折了。”
我闭了闭眼睛,吸呼吸。
他说:“我仔细查访了几天,发现你们跟还活着的那个苏墨森家没有任何关系和来往,所以就想,可能是二十六年前,你真正的爷爷用什么手段窃盗了那个还没入籍就夭折的女婴的身份,给她上了户籍,连同着把她爷爷的身份也盗用了。你们两个的身份都是假的,所以你真正的爷爷,本名肯定不叫苏墨森,你也不叫苏妮。”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居然能查得这么深。之前跟楼明江会过面以后,我猜想江城的警方会派人挖我的底,会把所有这些都挖出来,但万万没想到代芙蓉居然也查到了,所以无言以对。
他等了一会,又问过来:“苏妮,你到底是谁?”
他的声音很温和,没有压迫性,好像并不是非要我回答的样子。但我仍觉得很有压力,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心底不愿意欺骗他,所以只好沉默着,用力地沉默着。
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
我到底是谁?
代芙蓉在电话那边静静等待我的回答。
他的耐心可真好,仿佛能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等下去似的,而且似乎不等到一句答案或者一个解释不罢休了似的。
我终于耗不下去,轻声笑笑,准备开口回答,才发现喉咙干哑,像是积满千年万年的尘埃,呛人得很。
我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是谁,真的不知道。”
电话那边只有平静安稳的呼吸声。
我很真诚地跟代芙蓉讲了实话,告诉他说正因为想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所以才会找机会接近警察,想借用他们的某些便利,查查我的身世,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进展。
话一说完才发现自己满脸眼泪,声音里面也有哭腔,听上去痛彻心扉,混杂着无助和绝望。
代芙蓉跟我道歉:“对不起。”
然后他说:“如果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就告诉我。”
我捂着脸哭,用沉闷的声音跟他说谢谢,然后挂掉电话,呆呆地坐着,屋角的蘑菇夜灯弥散着温暖的、不真实的光,隔着眼泪看那光中的世界,仿佛离现实的生活很远。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谁。
从来都不知道。
99、等匿名者电话()
我独自哭了一阵,歪头睡去,睡得人事不知。
第二天早晨梦里觉得有急事,便轰一下炸醒,赶紧洗脸刷牙随便拣了套衣服穿上就火急火燎往局里赶,把昨天代芙蓉说的关于十点钟会有匿名者打电话到付宇新办公室的事情告诉他们。
付宇新等人立刻着手准备,安装录音、监听和逆向追踪等设备,一大拨人进进出出忙得热火朝天。
我知道他们的想法,无论这个匿名人是什么身份什么来历,只要他提供的线索属实,那么这通电话的录音就能作为参考性的证据,到时也可能需要请打电话的人出庭作证什么的。
刘毅民指挥着手下忙碌,付宇新只站在一边看,从头到尾没说半句话,脸色不太好看,但又尽量在掩饰。而老懒一直有意无意在观察他,表情里偶尔会露出一点看好戏的神色。我又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们两个人的反应,居然有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感觉。
等待的时间里,各种调查到的信息汇总过来,租车行那边已经查明了,那辆银色七座商务车是两个月前被一个叫李琴的女人租去的,租车时提供了身份证复印件并签属了租车协议,已经核实过身份证是假的,但租车行接待那单业务的员工赌咒发誓说身份证照片绝对是本人,他们有严格规定,必须仔细核对证件,当时还很礼貌地要求李琴将墨镜摘下来对比过,虽然发型什么的看上去有差别,但容貌绝对不会错,特别是右边嘴角那颗朱红色的痣。除押金以外,她一次性支付了十个月费用,现金结账。
刘毅民用手机翻拍下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发到梁宝市成冬林的领导那里,问年前跑到他们公司谈合作的李琴,是不是照片上的女人。对方很快回信息过来,给的却是个很不确定的回答,说他见过的李琴是长卷发,妆挺浓,三十六七岁的样子,脸型跟照片上有点像,但整体感觉又有点不太像。
这么一来,更糊涂了,一屋子人你看我我看你,然后又一起看那张身份证复印件。因为是新一代的证件,所以照片还是很清楚的,该表达的特征全都表达出来了,一个短发、单眼皮、弯月眉、神情冰凉的女人。
刘毅民低着脑袋使劲瞪着看瞪着看瞪着看,然后喃喃地、喃喃地、喃喃地自言自语:“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女人。”
这话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可他绞尽脑汁,哪怕咬碎牙齿,哪怕把脑袋撞得咚咚想,该想不起来的还是想不起来。
他只能肯定他的确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照片上的女人,但是完全想不起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方又是谁。他要过几天才会终于想起照片上的女人到底是谁,在哪里见过,并认定她就是凶手之一,而且是复仇联盟的首脑人物,也就是传说中的那只“上帝之手”。可惜这是几天以后的事情,在想起来之前,他且有得抓狂,常常茶不思饭不香神经质地喃喃自语转来转去。
而我却疏忽了。
我的疏忽是基于对对手的尊重。我觉得,一个这样有头脑的杀人团伙,是绝对不可能把如此明显的线索留给警察的,所以看见身份证复印件的第一眼,就下意识认定为是条死线索,自信过头地认为即使刘毅民想起照片上的女人是谁,即使查到了她并把她带到局里来面对面审问,最终也会惊奇地发现,她跟案件毫无关系。
我大意地认为租车行里调取来的这张身份证复印件就像“七刀案”现场的大衣、“开膛案”现场的脚印、“油画案”尸身上的睫毛膏一样,看上去好像都是有价值的线索,结果全部是些没用的玩意。
这才是高手过招该有的模式。
这时候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时间上,看分针秒针一点一点移动,等着十点钟会打来的那通匿名电话,战战兢兢连个厕所都不敢去上,生怕走开一秒钟就错过什么重大的事件,哪里会有精力去想一想,这世界上有些高手,哪怕就是在跟旗鼓相当的高手过招时,也会一板一眼按套路出招。
可惜不管怎么等,代芙蓉说好的那通匿名者电话却没有打过来,我们一屋子人从十点等到十二点,等到下午一点两点,老懒一觉睡醒,再一觉睡醒,再再一觉睡醒,刘毅民饿得肚子乱叫,电话还是没打来。
然后胡海莲受不了了,暴吼一声,骂出句脏话,风风火火旋出去买饭,留我们几个耐心稍微好一点点的继续等。
等到吃完饭,三点半,再好的耐心都耗尽了。白亚丰拍着门骂:“唉哟我去,纯粹浪费时间啊,天底下多少大事小事等着我去办都耽误光了!”
他不说话还好,一说话等于是提醒大家原来他也在这里,同时又把胡海莲使劲压在心里的火给点燃了,狠踹他一脚,骂:“谁让你在这耗着了?就你那点智商耗在这里能有什么屁用?!”
白亚丰摸着被踹的屁股跳着叫着跑了,像是获得特赦似的。
其他人也都觉得无聊,各各站起身走到外面活动身子。他们大概认为是代芙蓉的消息出了错,或者是那个匿名者原先确实想打电话告诉些细节,但因为某种原因又放弃了。
只有我不信邪,偏继续等。
往死里等。
刘毅民两次让我打个电话问问代芙蓉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会不会是弄错时间或者匿名者弄错电话号码了。但我不打,坚决不打,只盘腿坐在沙发里,双手合十顶住下巴,死死盯着桌上白色的电话机看,心里祈祷别出事,千万别是出什么事了。
虽然这世界上有很多规则我不懂,但我也很清楚,有些人为了自保,真的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万一哪个不想把案子翻过来的人物发现匿名举报,对其采取行动呢?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代芙容在梁宝市掀起那么大风浪,肯定早被警察盯上了,如果他们窃听了他的手机,那么,昨天那通电话的内容就全都泄露出去了,我们的匿名举报人现在很有可能已经出事。
电话迟迟不来,我只求是那人犹豫、彷徨、害怕,正在心里权衡到底应该怎么做,或者干脆已经下定决心不打电话举报了。只要他人平安无事,别的都不是问题,哪怕之后我亲自往梁宝市跑一趟,跟代芙蓉一起查,都行。就算他不肯露面,相信我们也有办法能找到他。
刘毅民去茶水间泡杯咖啡回来以后又开始瞪着桌子上李琴的身份证复印件看,喃喃发誓说肯定在哪里见过这个女人。有好几次似乎真的快要想起来了,可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关键时刻又逃走了,答案好像在他脑子里跟他捉迷藏一般叫人恼怒,简直发狂,又无可奈何。
老懒从外面走回来,头上脸上身上都淌着水,跟个落汤狗似的,大概是刚在厕所里冲了澡。
我没理睬,仍保持着刚才的姿势,盘腿而坐,双手掌心相对合在一起顶住下巴,用胳膊肘撑着腿,一动不动。
老懒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看我好一会,回头问刘毅民:“她这是什么造型?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刘毅民费力抬起脑袋看我一眼,回答他说:“是福尔摩斯的经典造型。”
老懒听了,恍然大悟“哦”了一声,说:“怪不得。”
说完不理我了,自顾自拉把椅子坐下,用他独有的姿势,脑袋一歪,开始睡觉,睡梦中继续陪我们等电话。
我盘腿盘得太久,感觉下半身有点麻,想活动一下,结果刚伸腿,猛一阵钻心挠肺的刺痒在两条腿上乱窜,麻得当场龇牙咧嘴乱叫,表情狰狞得要吃人。
老懒听见我尖叫,立刻跳起身,跟头猎豹样窜过来扶,骂骂咧咧:“装逼能不能悠着点装?”
刘毅民也绕过桌子来扶,嘴里也跟着骂骂咧咧:“我还以为你坐那儿正经思考问题呢,搞了半天是装逼,有病啊?”
小海走进来时,刚好看见两个大男人一左一右扶着我的场景,便交抱着双臂靠在墙上冷眼看好戏,一副不想管闲事的样子。
我把半个身体扒在老懒身上,踮着脚尖,尽量站稳,还是麻得不行,咝咝吸着气还不忘跟刘毅民顶嘴,说:“你怎么知道装逼的同时就不能思考了?”
他瞪我一眼,说:“就冲你这不服气的劲,也该让你麻上两天三天好好吃吃大苦头!”
闹腾了一会,各归各位,十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小海替我从包里拿出来,她看了一眼,眉头突然拧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