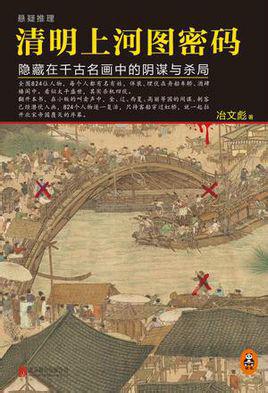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曾亲眼看见她把包括白亚丰和刘毅民在内的十余名警察同时催眠,目瞪口呆,很是服气。
她曾问我要不要试试。我没敢。虽然她说我不是那种容易被催眠的体质,而且只是进行一个很小的催眠侧试,我也还是没敢。
我对庄静的提议不是普通对被催眠的排斥,而是恐惧,对被催眠以后局面可能会脱出自己掌控的深深恐惧。
这里好像有很长时间没和庄静联系了,不知道她好不好。
我离开会议室去上了趟厕所,又到一楼接警大厅找人问了几个跟手头两桩案子有关的比较细节的问题,然后泡了杯茶,靠墙盯着钟面上的时间慢慢喝着,脑子里还在分析案情。
正入神,猛听大门那里传来纷沓混乱的脚步声,飞快回转身看,是刘毅民,后面跟着七八个人,看样子是几路人马同时收队,白亚丰他们那路也应该一起回来了。
但是等了好一会也不见白亚丰进来,便问刘毅民怎么回事。
刘毅民说:“那个建筑工人袭警拒捕,还好派去支援的人赶得及时。”
我吓大跳,问他:“有没有人受伤?”
他说:“王东升挨了一下,还好不怎么严重,现在已经把嫌疑人制服在回来的路上了。”
瞬间觉得好对不起王东升,要不是我发微信给他,他未必亲自去,也用不着挨一下。
但反过来想,如果换个人去,情况可能会更糟也不一定,我见识过王东升应对突发事件时候的样子,特别厉害。
我跟着刘毅民急匆匆往楼上走,问他这边的调查进展怎么样。
他说:“没什么大收获,但也不能算是一无所获。”
刘毅民一边回答我的问题一边吩咐后面的人把材料交给值班的警察然后全部解散回家吃饭睡觉,要大家明天下午再回局里。
吩咐完以后又回头跟我解释说大家都两天两夜没合眼了,警察也是人,也得吃饭睡觉。
我咧开嘴呵呵呵一阵哂笑,说:“你好像也是人吧,你怎么还不走?”
他说:“我等那边把今天调查的资料都理出来交到你手里以后就走。”
说着话,他把我手里没喝完的半杯茶夺过去一口吞进肚里。
我跟在刘毅民身后到了二楼他的办公室,发现胡海莲躲在里面睡觉,手机抱在怀里,双眉紧蹙,睡得很不塌实,一副随时诈尸还魂的模样,不由噗地笑,想她可真会找地方。
我不想吵醒她,就给刘毅民打了个手势,意思是我到一楼去等资料。
他点点头,没再管我。
我下楼的时候正好碰到白亚丰他们一拨人回来,纷纷攘攘闹闹轰轰的。
那个建筑工人拷着手铐被押到审讯室里去了,白亚丰因为还有很多手续上的事情要办没功夫跟我讲话,只拼命朝我挤眉弄眼张牙舞爪,有一万个意思要表达可我一个意思都没看懂。
我这会不想理白亚丰,只拽住跟他们一起出任务的另外一个警察问王东升怎么样,伤得重不重。
答说不重,只擦破点皮,没什么事。
我就不担心了,这案子前后都很明白,只等凶嫌认罪,或鉴证科那边物证的各项鉴定报告出来,就能了结。
我走到一楼等刘毅民他们今天调查回来的“火烧案”死者的背景材料,无意中听见两个值班警察头碰着头在聊闲话,说严副队长的调令已经下来了,进修完回来就直接到省厅报到。
这消息真让我吃了一惊。
严副队长去北京进修犯罪心理学的事我知道,他走前给我打过电话,聊了好一会天,但他要调走的事我真是半点风声都没听见,直到现在。
那两个警察没发现我在听,还头碰头唧唧咕咕说严副队长要调走的事,说得有鼻子有言,大概是真的了。
原来白亚丰乍乍呼呼跳着闹着叫着说他只要破出一个大案就能升副队长的事情不完全算空穴来风,严副队长一走,空出一个缺,自然要人顶上。
可我想,怎么轮都轮不到亚丰头上吧,前面还排着好几个资历能力各方面都超出他几百倍的人呢。
14、一大堆没用的线索()
调查材料没这么快整理出来,刘毅民下楼叫我别等了。然后把我叫到休息室里,一人一杯茶坐下,把他们今天调查回来的大致情况讲给我听。
我就安静听他讲调查进展。
首先,“七刀案”那个女死者的身份还是不明朗,计算机中心用了关键字检索和人脸识别技术,都没能从失踪人口系统里找到符合的记录,现在正在扩大搜索的范围。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至少在乾州市还没有人对那个已经死去的女人作失踪报警,或者压根就没人发现她失踪。
陈尸那间出租房的房东说那个房间在发现尸体之前已经有近一个月没人住了,根本不知道为什么里面会有尸体。
鉴证科检查过房门上的锁,是那种手握式的旋转锁把,锁芯被撬坏,但关上以后,看上去还是像锁着一样。所以楼里的人进进出出也没有人在意,直到邻家几个小孩玩闹,无意中推进门去,才发现尸体然后家长报警。
第一批到的警察让当时在场的几个人都辨认过,没有人认识死者,而且也都说没听见那个房间里有什么古怪的声音。
从现场的血量以及家具上的灰尘判断,那里不是第一现场,凶手只是随便找了那间空屋撬锁弃尸,并没有在里面多逗留。
也就是说差不多一无所获。
另外,“火烧案”死者身份明确,所以调查相对顺利些,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刘毅民有点沉痛地告诉我,据他们这几天的走访和调查来看,那个被烧死的骆波凡,生前品行真的不怎么好,各方各面都有树敌,欠钱不还、卷合作伙伴的投资款逃跑、拖欠农民工工资、拒发工伤赔偿款、包养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好几个女人,连朋友妻子都染指,反正除了杀人放火那种要判死刑的事,其它的,基本都沾点边,据说还与一桩毒品事件有关,只是证据不足给放了。
关于骆波凡生前的劣迹,乱七八糟囤积下来,好几页纸。
而现场装尸体那个油桶,虽然鉴证科还原出上面的字样是某某化工厂,但循着地址电话查过去,却是间倒闭了八年多的旧化工厂,仓库里还有两百多个一模一样的油桶,仓库的门窗都破损不堪,随便用点力就能进去,只要是个有平常行动能力的人,都可以偷出个桶来用,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所以完全没有指向,是条死线索。
刘毅民说了半天,就是一个意思:线索一大堆,都没什么用。
看看差不多快到凌晨了,楼里大部分警察已经回去,没回去的也都各找地方窝着睡觉了,我便起身叫刘毅民也先去睡一觉,天塌下来等明天再说。
他朝我笑笑,说:“不用你催我也得去睡了。你呢?要回去吗?要不要我找个人送你?”
我想了想说:“我反正不困,再研究一会,夜深人静注意力比较容易集中。”
他便没管,自顾自上楼去了,估计是打算在办公室里随便睡到天亮。
想想当警察可真不容易。
当警察的家属也不容易,顶梁柱常常不回家不说,还要提着心吊着胆,生怕出点什么意外。
我回到三楼会议室里坐下,拿纸笔分别列出两件案子各自的疑点和线索。
凌晨四点钟时值班警察把整理好的死者骆波凡的背景调查报告送上来给我,真有好大一叠。
草草翻了一遍,就像刘毅民刚才说的,根本是个人渣,作恶多端,各方各面各行各业都招惹几个敌人,私生活也靡烂,沾花惹草招风引蝶。
所以,不管从仇杀方面考虑还是情杀方面考虑或者是经济瓜葛方面,都能找出好些嫌疑人,一个个排除过去的话需要不少时间,仔细考量起来,这件案子哪怕死者身份明确,对抓住凶手似乎并没有多大帮助。
凶手大概也清楚这点,所以把包扔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
我觉得这凶手真奇怪,包里有那么多现金居然没拿走。就算他的杀人初衷不为钱,杀完人顺手牵个羊又不多费力气,这世道,谁能跟钱有仇呢。
所以,是两种可能。
一种是仇恨,凶手恨这个骆波凡恨到极点,恨到沾染他的钱都觉可耻。
另外一种可能:这是一桩,或者是一系列非常纯粹的谋杀,纯粹到摒弃一切旁的因素。
想着想着,我突然从卷宗里嗅到一股狡诈的味道。
非常狡诈。
一般聪明的连环凶手,会将命案现场处理得干干净净,不留任何线索,甚至可能会把死者身份给消除掉,以增加侦破的难度来逃避追捕。
眼前这两桩命案的凶手却故意留下一大堆线索,但差不多都是无用的。
这样一来,就算凶手真的不小心遗落了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或证据在现场,也会被别的那些没用的给混合,突显不出其重要性,甚至会被忽略。
所以,何其狡诈!
窗外天蒙蒙亮时,我打算先回家一趟,屁股上的伤处还隐隐作疼,得回去换药。
我下楼,跟值班警员打了个招呼,从后门出去,从右边绕到后面的停车场,抬头看看天,白蒙蒙的,可能会下大雨,这几天忽晴忽雨忽阴风阵阵没个准谱,连天气预报都混乱。
昨天来时,我把车停在最里面的位置,就是停自行车和电瓶车的蓝色遮雨棚旁边。
现在远远看过去,恍惚看见雨棚下面好像有个人影,就站在我那辆老破桑塔那的旁边,一动不动。
起先我以为自己眼花了,赶紧抹抹眼睛再看,真的有个人影在那里,并且还动了动,微微向前弯下身子,感觉像是在往我那辆破车身上涂鸦似的。心想不至于吧,公安局的停车场,谁的胆子能这么大。
看着看着心里微微有点发毛,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于是贴着旁边一辆辆排得整整齐齐的车子蹑手蹑脚往那边走。
走到很近了才看清楚是局里的保洁员。
就是那个整天没什么笑容也不喜欢说话跟谁都不打招呼的骆阿姨,性子很冷淡,平常进进出出经常碰见的。
最早时我为表示友好见了面都会跟她打声招呼,但她冷淡至极,我每次都热脸贴冷屁股,很没趣,几次下来再碰见,我的脸也跟她的屁股一样冷了,看见都当没看见,老感觉她活得像个幽灵似的,跟谁都没好脸色。胡海莲他们在背后都管她叫老巫婆。
我跟这个骆阿姨素无往来,她这会跟个鬼魂样站在我的车子旁边干什么?就是辆又破又旧的桑塔那,有什么值得她那样鬼鬼祟祟俯着身体仔细研究的?我车头上开花了还是
想着想着,脑子里突然狠炸了一下:要死,该不会是血迹吧,我车头上该不会有很明显的血迹吧?
错不了的。
肯定是血!
昨天半夜我车子开到杏花街口时碰见一场生死追杀,那个提刀的疯母夜叉踩着我的身前盖跳过去,她不知道哪里受了伤,我多管闲事跟她打了一场,回家才发现身上好几处沾了她血,当时累得慌,洗个澡把脏衣服泡在盆里就没再管,现在想想,肯定是母夜叉从我车上跳过去的时候把血弄到我车上了,那车是黑颜色的,沾上点血迹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我没注意到。
我突然就有点慌,呼吸都乱。
骆阿姨会怎么样?报警吗?还是直接问我那是怎么回事?她可不是一般的保洁阿姨,天天在跟警察打交道,耳闻目染,多少会有点职业病,看见什么可疑的都要往刑案方面琢磨琢磨,更何况我又是个常跟刑案打交道的人,出现这种情况她大概更会多想。
最容易多想的情况就是车祸,她这会脑子里大概以为我飙车撞死人逃逸了吧。
她以前看见过我飙车,有次她跟白亚丰聊起飙车的事,指桑骂槐刺过我几句。
我心里真有点打鼓,她问起来的话,实话实说肯定不行,得找个平常点的说法掩饰过去,比如流年不利得罪小人所以出门时被泼了一车狗血?
可她没给我解释的机会。
我刚往前走几步,她便猛地转过身来看我,不吱声,目光阴阴的,有点发狠的劲道,很吓人。
真的很吓人。
我虽然胆子不是很大,但也不是谁都能把我吓到的。可这女人的眼睛里面有种东西,阴的,湿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我刹时心惊,嘴巴半张着可愣是吐不出一个字。
这骆阿姨的气场太大了。
四目相对只持续很短的几秒钟时间,她转身走开,很小心地贴着走道边沿从我身旁经过。
我闻见她头发里面海飞丝的香味和皮肤上面雪花膏的味道,还有风油精的味道。
另外似乎还有一点点十分十分奇特的乳胶味,闻着怪怪的,非常陌生。
我扭脸目送骆阿姨走远,等她拐过弯彻底消失不见以后,才蹦着跳着去打量自己的车子。
还真的是有血迹,好在不是太明显。只是这几天天气不好,我懒得洗车,车身上尘啊泥啊水啊一片,脏脏的,把昨天母夜叉砰一脚踩跳过去的脚印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怪会引起骆阿姨注意。
15、有人闯进过家里()
其实冷静下来想想,我并不担心车上的血迹和脚印,真要跟谁解释也不是完全找不出说法。
撒个谎我还是会的。
只是骆阿姨刚才的态度实在让我觉得有点心惊肉跳。
我把不准她的脉,猜不透她在发现我车身上这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以后那样瞪我一眼到底包含几个意思。
不知道她会不会跟人说什么。
女人都喜欢八卦,她要是津津乐道把这事当个什么素材跟局里那些阿姨大妈大叔大伯们聊,那估计明后天就该有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说话也会阴阳怪气了。
我的身份在局里进进出出本来就尴尬,很多人看不顺眼,这下可好,自己没事找事。
一路想,一路飞车回了家,把车开进院里,顾不得进家门,先弄水把车冲干净再说。
冲完了还不放心,又从院子角落的柴间里找出消毒剂来把车子一通猛擦。
我懂犯罪现场调查那一套,用水冲过的干净不是真干净,非得用消毒剂擦才行。
这些先是苏墨森教的,后来我自己感兴趣,也自学过一些。
我有时候活得非常不爽就是因为发现苏墨森总是对的。
总是对!
我在心里把他当成个疯子,可他又总是对,所以我没办法理解这个世界,只好不爽。
我对他不爽太久太久了,哪怕现在他已失踪好几年,生死不明,我每次想起来,还都有点惧怕和咬牙切齿。
等把车子彻底处理干净,十分放心了,我才长长吐一口气,拿出钥匙打开家门。
客厅里面窗帘都拉死着,光线暗暗的,我每次打开大门,都会有恐惧,担心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躲在昏暗里伺机袭击我。
这种恐惧不是莫名其妙来的,也不是我胡思乱想来的,实在是被苏墨森逼出来的,我的整个人生都被他蒙上阴影,哪怕他已经失踪近五年都消除不掉一二分。
我走进客厅拉开朝北那边窗户的窗帘,准备打开窗户,但伸出的手犹豫几秒钟又缩了回来。
客厅的空气里隐隐约约有一股奇怪的、完全陌生的香味,像某种药草,有一点甜。
这陌生气味虽然在残留着的杀虫剂和消毒水的味道里显得特别微弱,多嗅两下又没了,恍惚是错觉,但我相信肯定存在。
我换个位置使劲嗅,便又嗅见了隐隐约约一缕,似有若无。
我慢慢移动脚步继续嗅,像警犬样吸着鼻子,心里的念头越来越坚定。
有人趁我不在时,进入过这栋房子!
而且,虽然气味不一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猛一下想起半年多前发生在百合路快捷酒店那桩命案现场闻见过的味道。
一下感觉有点心惊肉跳。
我放弃拉窗帘的打算,慢慢走到客厅中央,站定,深深深深吸进口气,然后使劲咽下一口口水,喉咙里咕咚一声响。
正前方巨大的黑色液晶电视屏幕上有我的影子,有茶几、沙发、后面隔断柜等家具的影子,没有别的什么。
那画面虽然很正常,但因为气氛不对劲,感觉就有点毛骨悚然,跟午夜凶铃似的。
仔细查看客厅,一处处一寸寸看过去,并且闻味走着,越来越确定在我去局里办事的十几个钟头里,有陌生人进来过。
绝对有人进来过,但现在有没有离开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所能够感觉到的,就是有人从容不迫进了我家,呆了不少时间,像是在里面好好生活了一场似的。
我走到楼梯口停住,目光慢慢往上抬,顺着台阶看上去,一直看到深漆漆的黑暗里面。
我闭上眼睛竖起耳朵听了一会,没听见什么动静,于是不慌不忙地走上楼去查看,把所有房间包括阁楼全都检查一遍,没发现入侵者,但房子的每个地方似乎都留有一点奇异的香味和行动的痕迹。
我能感觉到那是个女人。
我发现原来这房子并不像我从前以为的那样安全。
再猛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听见有人在家里走动,甚至试图打开我卧室的门,顿时寒毛倒竖,一阵后怕。
原来那并不是神经质的错觉也不是梦,而实实在在是有人进来过,只是当时睡中惊醒,嗅觉没调动到最灵敏的状态,昨天白天又喷过杀虫剂并消过毒,所以没发现气味方面的问题。
加上后来睡着做了个可怕的梦,全都混杂到一起自然也就把前面听见的声音当成梦了。
仔细检查以后确定家里没有被翻动过的痕迹,没丢失贵重的东西,所以,我很想知道,那来无影去无踪的入侵者跑这一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冲我,还是冲苏墨森,或者是别的什么。
没事,冲谁来我都不怕。
我的原则一向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蛤蟆来了捕而食之,所以很快又放下心来不多想了,拉开窗帘打开窗户透气,给屁股上的伤换了药,把泡在盆里的衣服丢进洗衣机里洗。
再回到客厅沙发里坐下时,还是能闻见那缕隐约的、淡淡的、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