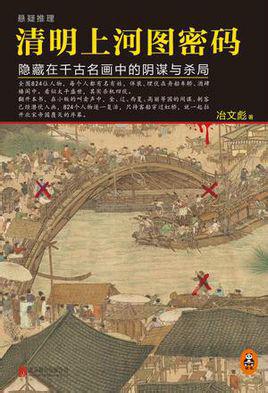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倚仗警察的力量,可不想突然间砸在一个莫名其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副队长身上。
所以挺不是滋味的,虽然脸色没什么改变,但还是好一会说不出话,也不想说话。
倒是刘毅民又开口说了一句。
他说:“城西荒田里发现男尸,我们的同事已经过去了。”
我回过神来,想问一问大概的情况,但念头一转,又把问题咽回肚里。怕他跟我说什么反而会影响到第一判断。
而他似乎也没有要跟我说什么的意思,估计是还没来得及去现场,就是想说也没什么好说。
我在彼此静默的几分钟里仔细把之前两桩命案的信息都回忆一遍,以便等会抵达现场时抓住最要紧的东西。如果真的是连环命案,那么,我应该能在即将到达的这个新的现场,发现一些必然存在的东西。
比如模式。
或者仪式感。
很多连环凶手都注重模式和仪式感,他们把杀人这件事当成事业在做,有种本能的、不受自主意识控制的精心。
刘毅民又接了几通电话,其中一通说的是媒体那边的事。
媒体这块一直都是分给刘毅民管的,他也管出经验来了,基本都能你好我好大家好地应对过去,有时对着镜头还能玩幽默,很给警察长脸。但今天的情况好像比以往严重很多,他朝电话乱咆哮,叫对方想办法把记者都疏散掉什么的,吼到后来,全身的细胞和神经都焦燥起来,乱拍喇叭。
我难得看见刘毅民这样。他在局里一向都是老好人形象,待谁都和和气气亲亲切切,同事间的周旋和调解也都得心应手。能弄成现在这样,肯定是有什么人给他捅大篓子了。
果然。
电话一挂,他就拍着方向盘咬牙切齿骂出个人名来:代芙蓉!
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但因为脑子里装了太多东西,一时没想起来,就问他代芙蓉是谁。
他黑着脸回答:“城市周刊的记者,前面三桩凶杀案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引起市民恐慌了,今天又是一桩,媒体全都疯了,特别是这个代芙蓉,没缝的鸡蛋他都能叮,何况这么大的案子。”
我有点奇怪:“今天这桩不是才刚发现吗?怎么媒体的消息这么灵通?”
他说:“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脑子有毛病,警察还没到他就发了条朋友圈,别说媒体了,看热闹的人都围了一大片!”
我哂然干笑,用安慰的语气说:“信息时代,这种事情难免。”
然后又补安慰一句:“反正我们的媒体也没多生猛,总能处理好的。”
他气性很大地说:“是,我们的记者确实不像美国大片里的记者那么厉害,但不管哪里总会冒出一两个特别喜欢发疯的,唯恐天下不乱,自己挑不起风浪就到网上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瞎围观乱起哄,搞得我们头疼死。本来警察的形象就不怎么好,老百姓哪里不满都怨我们无能,被代芙蓉这么一闹,更糟。刚刚局里打电话来,说几家媒体的记者这边讨不到新闻,扭头把省公安厅的大门给堵了,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这时候我已经想起代芙蓉这个人物了。
她还真是个人物。
刘毅民说着话,连打几次方向盘,从柏油路开到水泥路再开到黄泥小路,开到一块平坦点的地方停好。
我看见前面密匝匝站了一堆人,少说也有百来个,闹轰轰的,还以为现场就在眼前,下了车见刘毅民的手往荒田中央指,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远处一棵孤树,树下有几个人影在动,才知道现场是在那儿。
这边这些人都是闻讯来看热闹,还拿手机和相机拍尸体,结果被警察没收设备然后赶到路边的。
其中大概有好几个记者。
刘毅民要带我过去,我摇摇头,叫他不用管我,然后独自穿过围观人群,先站在路边将前面景象尽收眼底。
阴沉天色,浓厚的云,一大片荒掉很久杂草丛生的田,一棵不大不小孤零零立着的刺槐树,树底下有七八个人在那里或站或蹲忙忙碌碌,完全看不见尸体情况。
把全景扫视一遍以后我才慢慢往前走,刘毅民手下一个警察从旁边追上来递手套、胶鞋和通行证给我,哦,还有口罩。
我没要口罩。
我得留着我的鼻子在现场捕捉凶手留下的信息。
18、开膛破肚的凶杀现场()
我低声嘱咐那个递手套给我的警察,要他找个稳妥的角度,用手机里的录象功能,把那些看热闹的人全部拍下来,一个都不能漏掉。
他答应一声迅速走开,表情严肃得好像领了圣旨。
然后我开始进行独属我自己的一套现场勘查。
昨天晚上下过一场雨,轻轻悄悄把土给润了,所以到处都是脚印,凶手的脚印必然留在其中。我一边看着田里混乱的脚印,一边慢慢地、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调动全身的细胞从现场捕捉细微的线索。
空气里面有些微妙的东西。
仇恨、悲伤、愤怒、还有胆怯。
这些都是凶手留下的。
命案发生的时间离现在很近,应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所以这些感觉还很强烈,我简直能听到凶手行凶时的喘息声和血管里面血液狂奔的声音甚至是使劲压抑住的尖叫声。
我感觉出,这个凶手,不是惯犯。
我说过,我天生有这样一种神奇的能力,某件事情发生后可以在现场捕捉到很多别人捕捉不到的东西,时间隔得越近,当事人的情绪越大,我的感觉就越强烈。
如果环境特殊,我甚至能在某种虚拟的程度上还原事件发生时各方面的行踪轨迹。
听起来似乎太灵异太扯淡,起先我也觉得离谱,但在走访过几个研究相关方面课题的专家和学者以后,也就释然了。
我这能力,虽然奇特,但明明白白是有科学逻辑可以依循的。
人类的情绪里有一种肉眼不可见的、类似空气中的氧或者氮之类的特质存在,它们可能是气态或者液态也可能是固态,目前有科学家已经着手研究但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命名。
那种情绪的物质,无论什么形态,在一定时间内都会附存环境之中,比如空气、泥土、建筑、树枝树叶上,我只是有能力捕捉到这些罢了。
就像有的人天生记性好,对什么都能过目不忘。而有些人的嗅觉天生比别人灵敏,能闻见很多一般人闻不见的气味。
哦,我也有超出常人的嗅觉,眼前这个现场里除了浓烈的血腥味、粪便味之外,我还闻见空气里面有一缕止咳水的味道,还有一缕伊卡露洗发水的味道,还有还有似有若无一丁点银贝梗的味道?
这是什么情况?
我想不通这里怎么可能会有银贝梗,所以便觉得应该是闻错了,大概是某种和银贝梗气味类似的别的什么东西。
迎面一阵风吹来,又被我捕捉到一点银贝梗的味道,若有若无很隐约,还是不能太确定。
这个意料之外的情况让我有点焦急,赶紧加快脚步往前走。
前面走来一个警察,捂着嘴,满脸痛苦表情,说话都有点口齿不清了。朝我摇摇头,说:“苏姑娘,那边那边唉,你、你、你自己悠着点,那边实在有点”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我也早就从空气里面近乎逼人的血腥味料到那边的情况有多残酷多惨不忍睹了。
但我这会最着急的是想弄清楚周围哪里有银贝梗,以便提醒他们当心,那是种看上去很平常的植物,茎叶有点像野菊,开银色贝形花,所以叫银贝梗,属稀有物种,不触碰时无伤无害,但只要触碰到它的花,花芯中就会吐出一种透明的黏液,黏液本身无毒,可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寄生虫,一但进入人体,后果不堪设想。
我就是奇怪,为什么城郊的荒田中会有银贝梗。
陈伯伯的药谱上有写,银贝梗只会生长在深山老林里,背阳喜阴,活凉泉边多见。
陈伯伯还特别告诉我说,因银贝梗对环境的各方面要求都很高,在人类生活区域附近根本无法存活。
所以这会闻见它的味道,真是要多古怪有多古怪,一度以为自己鼻子出错了。但仔细嗅,虽然不多,若有若无,却千真万确存在,越闻越确信无疑。
我先在黄色警戒带外面转悠了一会,没找到可疑的植物,倒是已经把几米外那具尸体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
于是先把银贝梗的事情搁一边,集中精力对付眼下的案件才是正事。
死者是男性,赤身裸体,靠着那棵孤零零的刺槐树坐着,上半身用铁丝捆在树上,两条腿呈“人”字形大开着,从胸口下刀,像剖鱼样直剖到小腹,整个开了膛。
内脏被扒拉得一塌糊涂,红的白的黑的颜色铺得到处都是,离尸体五六米远的地方,摊着一堆红红白白的东西,不用猜也知道是内脏。
死者的脖子里勒着一根铁丝,所以脑袋立得笔直,没有往旁边歪斜,面目狰狞,五官扭曲得完全变了形,眼睛暴睁的程度超出想象,两颗眼珠已经凸出在眼眶外面,根本无法从形象上看出死者原本的相貌和判断大致年龄。
这样的死法。
唉。
我有时候觉得,也许世界上真的存在天堂和地狱。眼前这种情况,大概就是地狱里的景象了。
突然一阵风起,混着恶臭的血腥味像是迎面劈过来的一记巴掌,有个鉴证科人员当场崩溃,捂住口鼻跌跌撞撞冲到外围去吐了,隔着几十步路都能听见翻天覆地呕吐的声音。
呕吐这种事情也传染,一个呕,另一个也跟着呕,一会功夫呕成一片,刘毅民不得不喝斥几句把呕着的几个人赶开以免影响别人工作。
我站在尸体的正面静静地看了一会,再调转目光看泥地上的脚印。
因为这里偏僻,平常根本不会有人来,警察接到报案赶来时,围观的人都还没到,第一发现者胆小没敢往前凑,所以警戒带以内的现场基本完好,没有遭到任何破坏。
我来之前他们已经做完第一轮现场勘查,用白灰将凶手嫌疑人留下的脚印都标识出来了,来去踪迹一目了然。
我问旁边正拍照的一个鉴证人员为什么没有把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的脚印给标识出来。
他往围观人员聚集那边指指,说:“报警的是个摄影师,今天一早来这里拍鸟的照片,在拉近的镜头里发现尸体,根本没有靠近过,所以我们来时,这里就只有凶嫌一组脚印。”
凶嫌的脚印从几百米外的水泥路边,一条直线走到树下,尸体周围几百个脚印互相重叠、交错,很乱,有些已经不能称为脚印了,只能说是凶手留下的行动痕迹,之后,脚印往另外一个地方去,离开了现场。
圈脚印的白灰由点成线,仔细看去,凶手来的线路,和逃跑时的线路,基本以尸体所在位置为点,形成了一个九十度的直角。
也就是说,凶手没有沿原路返回,而是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
我离开尸体往回走,从脚印最初出现的地方开始,沿着凶手走过的路线慢慢地走了一遍。
从水泥路这边下来,到尸体所在地,折转脚步往东,三百来米路以后,窜进了一片差不多半人高的杂草丛中。
这片杂草丛位于低洼处,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一直下着的雨等于把整片地灌成了个浅浅的泥水塘,脚印肯定有,但彻底被水淹没,除非把水都抽干,或者等老天放个三五天太阳把水晒干,否则没办法把脚印全部提出来。
不过这不重要。
低洼处的杂草塘就这一片,范围不大,只要沿着四周查找,肯定能找到凶手窜进草丛以后又往哪个方向去了。
我招手喊来两个熟识的警察,问他们有没有找过凶手从这里出去的脚印。
他们点头,然后指着草塘的对面,说:“从这里穿出去以后直接跑上了水泥路。”
我回到起点,重新再走一遍,并仔细观察那些脚印的形态,来时的脚印深而重,跨幅不大,看得出因为凶手背着或者扛着受害人,所以走得小心翼翼,近乎如履薄冰。而离开时的脚印前面重后面轻,跨幅大,而且三百来米路里就有两处跌倒的痕迹,留下了臀印、掌印、膝盖的印迹,还有受害人的血迹,甚至凶器都掉在了第二次摔倒的地方,一把剔骨尖刀,已经被鉴证人员收走,刚才给我看过一眼。
我感觉到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整个气场都不对劲,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协调,很混乱,感觉好像青菜炒苹果那么不搭调。
我能感觉出,这种不协调是情绪上的,不是案件本身的。
我在杂草丛前面站了一会,折转身想走回到尸体那边再试着捕捉更多凶手的气息,结果一眼看见那边树下多了个体形高大的男人出来,没穿警服,头发理得像板寸,很炸眼球。
那男人一身便装站在尸体正前方,两手交抱在胸前,双腿稍微叉开,一动不动站着,山一样稳,全然不管周围动静,在料峭冷风里面挺拔得像棵白杨,或者说像是死的,像是冻住的,像是不存在的。
隔着三百多米远的距离,我都能感觉到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
心里一转念,不用问也知道那是什么人了。
他倒是真够积极的。
19、树下的男人()
我深吸口气,定了定心,慢慢地走过去。我想着走近以后,他自然而然会扭过脸来看我,我就顺势给他个苏妮的招牌式狗血小清新笑容,自我介绍一下,彼此认识,往后的日子,请多关照。
我真的需要特别多的关照。
可惜事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发展,走近了,离得只差半米路了,那男人也没扭脸看我一眼,仍旧一动不动像座雕塑样盯着尸体看,仿佛想从尸体那两只掉出眼眶的眼球里看出凶手是谁似的。
我没觉得恼怒,因为专注是项好品质,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嗯,恰好我也有这项优秀品质。
我不再理会那人,自顾自走到尸体侧前面,蹲下身仔细看,同时调动起全身的细胞去感知,我几乎能体会到凶手下刀时全身抖得几乎不能自持,第一刀下去的时候,不得不两手握刀柄并闭住眼睛。那一路刀口歪歪斜斜乱七八糟,加上撕拉硬扯,简直不能入目。
我终于知道空气里面这种绝对不协调的怪异感是怎么来的了。
是愤怒与胆怯两种情绪冲撞形成的。
这是个胆小如鼠的人犯下的凶残谋杀案。
我得再看看来去的脚印,以确定绝对就是这么回事,于是猛地站起身——我忘了我屁股上还有伤,起身太猛,股骨大痛,立刻重心不稳要摔去,好在后面伸出一只强有力的手,瞬间把我扯住,跟提溜小鸡似的把我提溜到离尸体远点的地方以免我破坏现场。
我摸着痛处转身跟那男人道谢,笑得龇牙咧嘴很是难看。
后来我老是想,如果真有时光旅行这回事情,我无论如何要穿越回去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改写一下,首先不能在如此血腥的命案现场,其次我绝对不要这么狼狈。
那男人两只眼睛定定地看着我,满脸的沧桑和皱纹。
我道着谢把身体站稳,尴尬地笑笑,来不及跟他多说什么,赶紧又走回到水泥路边,沿凶手留下的脚步,把自己置入当时的情境里面,重新把命案过程走了一遍:先把被害人背到树下,将他绑好,开膛破肚弄死,然后仓惶逃跑,逃得非常失措,好像大梦初醒般完全没了主张,路都来不及认,从这个方向来的,却慌不择路往另一个方向跑了,逃跑过程中摔倒两次还遗落凶器。
我循着脚印走到刚才那片杂草丛前面,问正在勘查的一个警察:“凶手的脚印从草丛中出去以后又往哪里去了?”
他抬手给我指,说:“跑回那边水泥路上去了。”
我问:“然后呢?然后又到哪里去了?”
他缓缓摇头,说:“那条水泥路连结乾州市和西边几个乡镇许多村子,来往车辆不少,脚印早被遮盖掉了。”
单从这件案子看,我稍微有点能理解凶手这些矛盾又混乱的情绪和行为,凶手恨树底下那个人,残忍地把他杀死,然后很害怕,慌里慌张逃走。这里面虽然还有问题,但不是特别严重,符合某类人的行为逻辑。
可它不符合一个连环凶手的行为逻辑啊,哪有一个连环凶手在前面杀死过两个人以后,还这么胆小的?
这不科学。
那么,这三桩案子并不是连环凶杀?而是各自独立的?一个月时间里面四桩独立发生的凶杀案,还全都是恶性的,这可能吗?
怎么想都不可能。
我第一次感觉到如此深重又如此真切的束手无策,三叉神经很痛,整个精神都有点萎靡沮丧。这三桩案子里所有的情况表面上看去都很正常,可搁一块儿想又完全不正常,我想不出合理的解释。
回到树下,那陌生男人还以刚才的姿势两手交抱两腿微分像棵白杨似的笔直挺拔站在那里,不过这次听见我的脚步声以后他转过脸来面向我了,拉开满脸的菊花褶子冲我微微一笑,我就听见自己心里有个声音笑起来,嗬,好英俊的一条沙皮狗。
他向我伸出右手,作了三个字的自我介绍:谭仲夏。
我伸过手去给他握,礼貌而矜持:苏妮。
互道完名字以后,谭仲夏神情平静地看着我,右边唇角微微扬起,露出一抹饶有深意的笑容。
他鼻翼两侧的法令纹深得像刀斧劈出来的一样,眼窝深陷,鼻梁高挺,有几分少数民族的相。
这男人,不可否认是好看的,特别是身材,高而壮,简直虎背熊腰,却完全不显笨拙,一身肌肉在黑色高领毛衣里呼之欲出,一看就是千斤力气很能打的那种。
我想,老天在创造他的时候,必定是当件艺术品在弄,精心得很。
唯点睛那笔差了些。
他的两只眼睛虽然大,而且双眼皮,可惜没什么神,定漾漾的,死气沉沉,实在浪费这么好的身材和脸盘子。
世间果然没有十全十美这回事。
因为不认识,好像没别的什么话好说,一时气氛挺尴尬,就继续研究眼前的案件。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