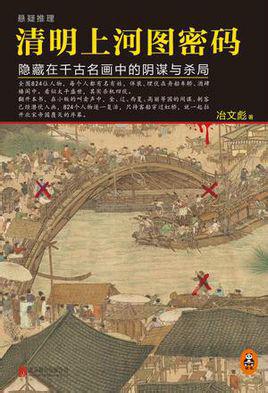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7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想,背后一定有人为操纵的因素,否则不会这么多与事件相关的人莫名其妙就聚集到一起,像被网兜住的鱼一样。
可是,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能耐操纵如此庞杂一张网?让如此多的人不知不觉都往网里钻?
我想,除了上帝应该没人能够做到。
所以换个角度考虑,觉得更可能是事件本身在发生作用,是事件在我们的生活里围织起一张网,将很多很多彼此关联的人物汇集到了一起,比如我,比如小海,比如老懒,比如代芙蓉。
哦,还有黎绪。
黎绪怎么的也脱不了干系。
我离开望远镜,走到窗户边,望向对面的房间,微弱的蜡烛光在窗帘上水一样摇曳。我在犹豫要不要过去那边探探情况,但很快否决掉这个念头,一是太清楚那怪物的功击能力,搞得不好丧命也不一定。二是怕打草惊蛇,转个身的功夫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我再要想找的话就难了,所以得慢慢来,最起码也得先跟代芙蓉碰上头,问清楚情况才能过去,而且还得先做好周全的准备,避免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倒霉结果。
对面窗户里面盈盈的那一点烛光突然灭掉,天地归于漆黑,我像突然从梦里醒来样看看时间,已经四十多分钟过去,早就超过跟小海约好的时间。刚才说好半小时见不到我就跑,然后报警,恐怕她已经报警,这会警察正往这边赶。所以赶紧拉上窗帘往外走。
门刚拉开,突然一大团东西往我怀里扑来,我惊跳着往后退又往旁边跳了一步,立刻弄清楚那团东西原来是个人。
真的是个人!
肯定是把脑袋贴在门上偷听我在屋里的动静,结果我脚步太轻动作太快,开门的时候他没能躲开,才一头撞了进来。我闪开以后,他还往前冲了两步直冲到窗边才刹住脚步,然后一个返身摆出格斗的姿势。
从身高、体型、力度、反应能力等各方面情况判断,是个男人,而且绝对练过。
现在不是打架的时候,所以我懒得跟撞进来的这人计较,连他到底是哪路上的人都不想弄清楚,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才是上策,所以不管不顾抬起腿就又往外奔。
结果我刚冲到走廊里,猛又碰上一个来意不善的货,这个的反应比刚才那个快,在我撞上之前侧身让开然后伸出一条腿来绊我,我踉跄两下,来不及站稳又使劲往前跑,以一敌二很容易吃亏何况他们未必只有两个。
最不想出现的情况,出现了,但愿代芙蓉没出事。
我在心里使劲祈祷小海那死脑筋的货已经按我们约定的报警,已经自己先跑掉了,可千千万万别跟个傻子似的还在原地等我,眼下的情况我自保都可能成问题,真未必能分出心思照管她。
冲到三楼,楼梯拐弯处又撞上一个,这次逃不开了,直接开打,形势对我太不利,所以得先下手为强,管他三七二十几,照着肩窝就是一脚,可惜对方也不是吃素的,迅速闪开,然后往前扑着试图抓我的脚,我只能往后退,退到三楼走廊里,思忖着看看能不能从这头或者那头跑。
我还没考虑好到底哪头,他就逼过来了,直接圈出胳膊来卡我脖子,我赶紧贴着墙壁蹲下身体避开去,同时踢出一记扫蹚腿,结果脚踝被他一把拽住,然后再一使劲,我整个人就被他拉了过去。
情急之下也不管不顾了,先将代芙蓉要我取的那件东西丢出,而后刷地抓住左手手腕上的镯子,按下暗扣,抽出一根像钓鱼线那么细那么透明的金属丝,借着他拽我过去的那股子巨大力量,两手一旋,狠狠绕在他脖子里,再一收紧,他不得不立刻把拽着我脚踝的手松掉来解救呼吸。
我半点都不想要他的命,所以他把我松开以后,我也立刻把他给松开,右手两根手指一松,金属丝就自动收回镯子里面,一点声息都没有。
刚才使的劲有点大,差点没把对手勒死,这会他瘫软在地上抚着脖子用力喘气,动弹不得。
我趁着这点时机,赶紧打开手电筒往他脸上照,二十五六岁的模样,浓眉大眼,如果不是被我弄得这么狼狈,肯定是个英气逼人的小伙子,完全陌生,不知道是哪路的。
153、惊魂一夜()
从刚才交手那几招看,这男孩的拳脚功夫都是实打实练出来的,又稳又准又狠,出招的路术,是某种军方的格斗数,只有那种当过好几年兵,而且是好几年里天天练天天打的兵种,才能像他这样跟我过上好几招。
所以,我猜他可能是个特种兵,或者武警,当然还可能是接受特训的私人保镖之类,不太好说。
现实情况不允许我多作忖度,赶紧移动手电的光四处找,看见刚才为保命而扔掉的东西在前面十几米远处。
正准备扑过去捡,猛觉背后有股凛冽戾气,还没来得及回身接招,肩膀已经重重挨了一脚,手电在空中滑出条抛物线,然后咚地落在地上,正对着墙角,荧荧一点光,什么用都没有。
背后又传来呼的一声,是拳风,我歪身闪过,再闪过一次,第三次拳头过来时,不闪了,实在没耐心跟他玩,只稍微侧了侧,避开胸口的位置,让他一拳砸在我右边肩膀上,在他自以为得势的当口,狠狠踢出一脚,正中他腹股沟,然后把他逼到墙边,等他反扑。
一个人在剧痛之下的反扑总是会破绽百出,所以两招一过我轻易就旋到了他的背后,准备像刚才那样用镯子里的金属丝把他制服。
可我突然之间走了一点神,给了他反攻的机会,一下子把我按到墙上,然后伸出三个手指,恶狠狠一招锁喉掐住了我的喉咙。
从他出招的手势,和三个指头扣住的位置,我知道这是很阴损的招术,掌握了人体最隐秘的穴位,生死只在他控力的分寸之间,多一分力是死,少一分力是活,在这多一分和少一分之间,还能在有几个半分的相差,是死是活是植物人还是晕过去几分钟,都在对手一念之间。
对方很慢很慢地往手指尖上运力,我开始觉得头晕,伴随着耳鸣,但还不到完全无法动弹的地步。
正要回击,局势突然翻转,一声沉闷的敲击声之后,那三根掐着我脖子里死穴的手指立刻松开。
紧接着,又是沉闷的一声敲击,眼前这人整个瘫在了地上。
之前被我撂在地上那个听见动静知道这边的同伴吃了亏,不顾自己还没缓过来,赶紧起身冲过来想要帮忙,我辨着声音想踹他一脚,还没付诸行动,他却已经唉哟叫着倒地了。
上面还有一个,鬼鬼祟祟站在楼梯转角的地方,不下来打也不逃开,就那么阴恻恻地呆着。
我顾不得管他,抓紧凭刚才那点印象摸索着把代芙蓉要我取的东西捡起来拿在手里,虽然代芙蓉几次交待如果有生命危险肯定舍弃东西保命要紧,但我总觉得不把东西给他拿回去,这趟就白来了。
这时小海已经把落在墙角的手电筒捡起来了,回转身往被她制服的两个人身上照,一个已经晕了,脸朝墙壁趴着,只能看清楚是个男的,身材挺魁梧。另外一个捂着裆部蹲在地上,把脸偏到旁边避开手电的光,刚才我想踹他来着,被小海抢先一步,而且她出脚真狠,直往人命根子上用力。
小海又把手电往楼梯上面照去,上面那个立刻闪身隐到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去。
我想把这个晕倒的男人扳过来看清楚面孔,日后在别的地方碰到,也好提防着点他那招阴损的锁喉。但小海压着嗓音叫我赶紧走,语调里面一副欠她多还她少的臭德行,看来形势比我想象的要严重许多。
小海叫我赶紧走,我本能就往楼下跑,但她却是往楼上跑,两个人一上一下差点撞一起,还好反应都快,稳住了。紧接着,一只肥胖的手伸过来死力揪住我的手腕拉扯着我往上跑。
不用问也知道楼下还有他们的人,恐怕不止一两个,所以小海才会选择最差的逃亡途径。
我跟着小海跑了几步才知道往上跑并不是最差的逃亡途径,因为四楼半的地方有个朝北的窗户,窗框子整个被卸掉了,呼呼往里灌着风。小海叫我从窗户里往下跳,我想也不想就按她说的做,正好落在隔壁一幢矮点的房子的天台上。
小海紧跟着也跳下来,手电咬在嘴里,短刀拎在手里,像头野兽似的冲到我前面去带路。
看她熟门熟路的样子,就知道她趁我去办代芙蓉交待的事情那点时间,早就上下左右察看过地形地势并把逃亡路线探明了,刚才那扇窗户,也是她事先拆掉的。
我就知道她压根没打算听我的话乖乖在车里等着!
隔壁这栋也是座废楼,天台通往楼道的破门用老旧的笨锁锁着,我没耐心等她溜锁,踹出一脚把整扇门踢掉,三步并作两步往下跑,很快出了楼,稍微辨了辨方向就往外奔,穿过几条巷弄,七拐八拐拐到了跟白云街隔着两条街的锦江大街上,想想应该已经彻底摆脱那些来路不明的人了,赶紧收拾一下乱糟糟的衣服和头发,调整好状态,打出租车回家。
出租车开到离家还有两条村子的地方停下,然后步行回家,这是苏墨森时代定死的规矩,尽量不打出租车,如果必须打,只能停在离家还远的地方。以前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当然明白了,他是为了躲人,为了避免有人通过出租车查到我们的行踪。
一路上谁也不说话,只有飞快的脚步声、风声,偶尔掠过几声夜鸟叫,越发显得凄清,而且走着走着,突然下起毛毛雨来,弄得头发湿哒哒很烦人,心情都跟着糟起来。
我在脑子里仔细回想今天晚上发生的一切,代芙蓉的房间、天花板里的东西、望远镜里看到的人和怪物,还有那几个来路不明的人想得脑袋发疼头皮发麻,终于想明白了一件简单的事情。
我突然想明白,所有后来发生的这些乱七八糟、莫名其妙、诡异万分、看上去无比复杂的情况,都是以“上帝之手”连环案件为源点,发散性关联着的,各路人马,也都是因此汇聚到了一起。
“上帝之手”连环凶杀案是源点。
从表面上看,代芙蓉的参与好像是偶然,是因为我找他帮忙,他才卷进来的,其实不是,那天他到我家里来见面,我并没有提出叫他帮我往梁宝市跑一趟的请求,是他自己要去的,他要去的原因,是出现在梁宝市“油画案”现场那些落英草,我讲给他听以后,他若有所思,我想他应该就是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才去梁宝市的,帮我们的忙只是顺带手的事。
而落英草那种世人很少有了解的东西原本就是我所追查的事件中的重要环节,说不定还是接近核心的环节,由此可见代芙蓉根本就是事件中人,“上帝之手”连环案只不过起了推动作用,把他推到了我面前,或者也可以说是把我推到了他面前。
于是我突然觉得,那只传说中的“上帝之手”,好像不仅仅只为了替梁宝市那起连环案的受害者遗族复仇这么简单。
他还有别的目的。
甚至可能,另外那个隐秘的目的才是他最主要的事业,向成冬林复仇不过是顺带。
这感觉我之前就有过,只是那时不强烈也不清晰,现在才终于有了一点明确的影子。
想想自从“上帝之手”案件发生以来,有多少人多少部门牵涉进来了,乾州和江城两处的警察不用说,还有生物研究院、精神病院、中科院、基因工程研究室。所有这些范畴里面都有人以“上帝之手”案为中心在进行或明或暗或急或缓的行动,交缠混杂在一起,隐隐约约形成几股方向不同的势力,造成了目前这种非常脆弱的紧绷状态。
我想,就眼下的局面来看,如果发生什么超出控制范围的事情,那么,绷紧在那里的弦就会断掉,原本井然有序活动在各条线上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应对动作。
搞得不好要出大乱子。
还有小海,她也不是因为巧合才跑到城里来的,她父亲失踪的时候她年纪还太小,没办法跑到外面找,也没地方可找,直到发现修叔叔藏在老床机关里面写着两个地址的纸条。
我能肯定,就算付宇新他们不去花桥镇办事,不与她认识,她也会想别的办法跑进城里,然后终有一天,会顺着纸上的线索跟我碰面,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太清楚纸条上两个地址究竟有什么意义。而“上帝之手”案件的发生,把我们碰面的时间提前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件案子,那天我就不会出现在公安局,所以就算小海搭付宇新的顺风车进城,也未必能见到我。
照这样的思路去想,恐怕别的人也都是这样的情况,林涯不用说,要不是因为成冬林,他昨天不会在医院里出现。还有老懒,他也是这件案子发生之后突然空降到乾州来的。还有江城那边的警察。还有黎绪,对,黎绪,她特地送卷宗到公安局,我们碰上了。
好像有人在下一盘巨大的棋,我们就是黑的白的棋子,下棋者精心设计着路数,慢慢把我们挪到他希望的位置。
上帝之手!
我感觉全身的皮肤都冒出了鸡皮疙瘩,一层一层冷汗。
154、这世界太不靠谱()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认定,乾州这起复仇性质的连环命案只是表面现象,而隐藏在这背后的,其实就是我一直在调查的那些事情?
关于人体的秘密。
还有之前被我忽略,但最近越来越觉得重要的,关于灵魂的秘密。
我觉往深里分析,越觉得恐怖,无法想象事件的真相,到底会以什么样可怕的面貌呈现出来。
我一边思考一边和小海并肩疾步往家走,差千把米路就到家了,雨突然大起来,赶紧跑快,发疯样跑得颠三倒四,还是淋个半湿,进屋找毛巾擦,又烧热水准备洗澡。
忙乱好一会,然后恨恨地朝小海发脾气,怪她不听我的话,叫她自己先跑然后报警结果还是乱作主张,什么什么的碎碎念了一大堆。她只顾忙自己的,压根不理睬,我拿她没办法,所以念着念着就突然恍惚起来,这个莫名其妙跑进我生活里的死胖子,她脖子里那快镰刀形状胎记真叫人绝望,我想起从前的时候我是多么天真,问修叔叔我是不是他的女儿。
呆了一阵,突然想起我那辆破桑塔那还停在宝石路上离化工厂宿舍大门不远的地方,赶紧掏出手机打给白亚丰叫他安排交通部那边的人帮个私忙去把我的车拖到公安局的停车场去,嘱咐他多安排几个人,开着公务车去,但动静不要弄太大。
白亚丰那个蠢脑子这会倒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机灵起来,听着我的吩咐觉得不对劲,问我是不是出事了。
我说:“是碰上点麻烦,但对付过去了。”
他着急起来,问我有没有受伤。我说没有。他又问小海怎么样,她有没有受伤。我往小海那边瞪了一眼,回答他说没有。他沉默几秒钟,挂掉电话帮我安排拖车的事情去了。
我倒不担心车子会被偷掉,反正是个老破车,丢就丢了,一点都不心疼。我只担心住在荒废宿舍楼里的那两个人——哦,应该说是一个女人和一只怪物——我只担心他们发现小区外面多出辆陌生的车子,会起什么心思,如果警惕心重马上搬走,我就抓瞎了。
实在不是我疑心病重,而是这世界太不靠谱。
小海趁我给白亚丰打电话没空唠叨她的空档悄无声息回自己房间去了,叉开着两条肥腿半躺在床上看电视。我倚着门,望着眼前这个面色平静毫无惊澜的女孩,简直要崩溃。今天的情况不能算太糟,假使没有她在,我肯定也能毫发无损脱身,她自作主张去救我反而可能有危险,虽然今天逃得比较顺利,但不能保证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从今天的事情我又联想到其它方面,想着万一将来哪天苏墨森回来,他们两个要怎么相处,苏墨森肯定还会跟以前一样对我,时不时打我虐我或者把我麻醉掉然后脱光我的衣服研究我的身体,小海绝对不会让他这么干,但她又不是苏墨森的对手,也许我们两个加起来能打得过他,但介于种种原因——比如他是我的爷爷,比如他掌握着我的生世秘密,比如他可能知道修叔叔的下落,诸如此类的种种原因,我们肯定不会杀死他,至少我肯定不会,所以小海的存在以及她类似于今天这样的行为模式,势必会把将来的局面搞得一团糟,天塌地陷山崩地裂也说不定。
真奇怪以前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麻烦,大概是独来独往孤单得太久,小海的出现和陪伴让我感觉到人世温暖,所以别的,都没多加考虑。
我想,也许应该让小海先回花桥镇的老家去呆着,我可以答应她等“上帝之手”案子一结束就帮她找父亲。
想是这样想,但实在有点难开口,必竟当初是我哀哀地留她下来,且之后的日子里她把我的生活照顾得很好还救了我的命,现在要赶她走,不管她能不能理解反正我都开不了口。
我正站在门边踌躇着不知道怎么开口,小海倒是不耐烦了,皱着眉头扭过脸来看我,泛着眼皮子丢过来句听着直想撞墙的话。
她说:“如果你觉得内疚,可以用钱补偿我,保姆那份工资你照之前说好的价给,打今天起我连保镖的活一块儿都干了,你看你的命值多少钱,就往上加多少钱,多了我不嫌,少了我也不怨,随你看着办。”
我先是愣了愣,有点哭笑不得,但马上觉得这可能是个突破口,她一向比较贪钱,经济的困窘是死穴,总惦着老家的房子被亲戚霸占了去,而我好像最不缺的就是钱,所以就跟她商量,给她笔钱叫她回花桥镇上开家饭店或者杂货店什么的,我出钱她出力,算合资,亏了算我的赚了对半分。
这些话以前就提起过,当个梦想说的,现在却觉得这样做最实际,大家都能清静并且踏实,就看她点不点头了。
她当然不会点头,甚至连看都懒得再看我一眼,我巴巴地说了一大堆,她只很不屑地从鼻子里面哼出一声,就盯着电视屏幕不理我了。
我倚着门框定定地看,想起十几年前第一次见她时,她穿着件大红棉袄,头发扎成两根冲天炮杖,眉心还点了颗红胭脂,好像八十年代初照相馆里面照出来的那些岁月留念照,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