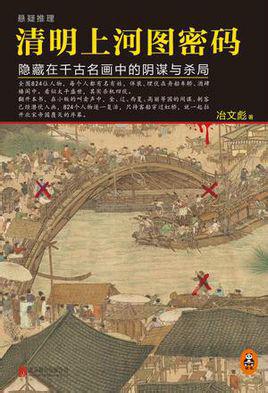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不认识,好像没别的什么话好说,一时气氛挺尴尬,就继续研究眼前的案件。两个人一左一右站在树底下,一声不响盯着尸体看,期间我偷偷瞄了谭仲夏一眼,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我还是能感觉到凶手愤怒和胆怯混乱交织的情绪,我能确定他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不自觉地哭过,这绝对绝对不是个反社会人格的连环凶手,这是个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因为狂怒和仇恨才犯下罪行。
我还能感觉到死者的痛苦。
我不知道人死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但是,受害人死前所遭遇的巨大痛苦至少还留在现场,它们跟凶手的情绪一样,也以某种肉眼看不见、语言很难形容的状态存在于周围,越专注越能感觉到,痛不欲生,生不如死,那些细微的、战栗的磁场甚至发出咝咝的声音,甚至震颤了空气,以致刺槐树上的叶子都开始瑟瑟地抖。
这种感觉有点像通灵,像是听见了一个灵魂痛苦而绝望的呐喊。
我把整个身心沉浸在里面,茫然失了声,以致对周围真实的人和事却感觉恍惚,有个鉴证人员在旁边跟谭仲夏说话,在我听来,他们的声音有点像暗夜里面魔鬼的窃窃私语,让人心里生出茫茫然的恐惧。
因为觉得再这么沉浸在阴暗情绪和感知里可能会出事,所以我赶紧用力挣脱出来,回归现实,认真听他们说话。好在我能把握分寸,旁边的人看不出什么异样,不然真把我当成神棍。
那个鉴证人员在说指纹的事。
没有指纹。
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取到指纹,凶手是戴着橡胶手套行凶的。
我问他尸体的身份确不确定,他摇头,说现场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又说要等把尸体带回去做初步处理以后才能让失踪人口部门那边查找有没有符合特征的。
这个现场没有指纹,没有死者身份证明,但有凶手的脚印和凶器。
我正在心里对比几桩案子各方面的细节,突然又刮来一阵小小的风,我猛又嗅到银贝梗特有的微酸气味,脑门上青筋都暴了暴,赶紧循着味去找。
药谱上说银贝梗绝对不能在有浊气的环镜里生存,我得知道这究竟是哪棵这么不正经,长到不该长的地方来了。
我便又在树底下走来走去,一边小心不要踩坏地上的证物和痕迹,一边使劲吸着鼻子找那点若有若无的微酸味。
这次终于给我找到了。
是从尸体身上发出来的。
非常非常少的一点,但肯定在尸体身上,只是尸身上各种味道混杂,实在没办法确认到底是在哪个部分。
对这件案子,我本来就糊涂,现在更糊涂了。
一个愤恨滔天却胆小如鼠的凶手、一个身份不明死不瞑目的男人、一缕真实存在的银贝梗的味道。
多么诡异的组合,我绞尽脑汁也找不出其中的逻辑。
我一回头,正撞上谭仲夏的目光,他用力地盯着我看,神情若有所思,见我回头,半点声色不动,问我刚才在找什么,是不是闻见什么奇怪的味道了。
他的表情很严厉,整个身体都散发着凛冽的气息。
我突然感觉到一丝凉意。
我的原则是不到万不得己的情况绝不跟人嘚瑟我天生有多少种了不起的特殊技,也不要让人知道我了解多少种不为常人所知的冷门知识。所以冲谭仲夏微微一笑,摇头,表示没什么。
可他不是那种好唬弄的人,不是我百媚千娇笑一笑就能放我一马的性格。
他说:“我从刚来的时候,就看见你跟条警犬一样在这里嗅来嗅去嗅来嗅去,怎么,有什么不能跟我分享的?”
我咧开嘴角给他一个没好气的假笑,说:“瞧你好好的一个人,说出的话那么难听,什么像警犬一样,就不能挑个好听点的词?”
他认真地想了想,似乎有所悟,说:“哦,我刚来的时候,见你在这里跟个特别优秀的警犬一样嗅来嗅”
他觉得加了“特别优秀”四个字来表扬就是好话了,我听见一万只草尼马在头顶狂奔而过,伴着几声乌鸦冷笑,满脸线条。
20、棘手人物()
我想找个话题把这事岔过去,可明摆着不可能,谭仲夏神情里有股吃定我的气势。
躲不过去,只好半真半假回答他说我闻到一点跟现场不和谐的味道,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可能是死者生前吃的食物。
我以为他不会这么容易罢休,所以又在心里斟酌到底要怎么继续编。可他居然不追问了,却猛地跳转,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问我屁股上的伤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反应再快也不可能跟上这么乱的节奏,所以呆了呆才回答,说前儿晚上跟一泼妇打架弄出来的。
这也是半真半假的回答,经得起推敲。
谭仲夏脸上没有怀疑的表情,语气却不怎么信,说:“就你的身手,什么样的泼妇能把你弄伤?”
我泛着眼皮子说:“咦咦咦咦咦,就一普通市井泼妇,碰碰撞撞起点冲突,推我一把,坐到块尖石头上弄出伤来,我能跟她大打出手?”
他用那种盯嫌疑犯的神情盯我,盯了一会又调转枪头问别的问题了,问我对这件案子有什么看法。
我感觉骨头里浸出丝丝冷意,觉得自己这回好像碰上对手了,或者是个大麻烦也不一定。
我想不明白谭仲夏到底是怎么看出我屁股上受了伤的。我练这么多年武,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行动和体态,虽然刚才起身着急差点趔趄,那也不至于能让人看出我哪里受了伤,偏偏他就看出了,而且一点没有看差。
我有种好日子马上要过到头了的幻灭感和不甘心,还有点恨恨的,恨刘毅民和胡海莲怎么不努努力把这个副队长的职位争下来,他们俩谁当都好,偏偏调来这么个厉害人物,搞得我很被动。
可再被动,也得硬着头皮往前走,总不能对方还没实际出招,我就自动缴械投降吧,那也太怂了,完全不符合我的气质。
我扭过脸去看尸体,回答他刚才问的问题:“仇杀,凶手胆子很小。”
前半部分很好理解,能把人弄成这样,肯定是有仇。但后半部分谭仲夏就有点茫然,蹙起眉头用疑问句重复一遍我说的那几个字:“胆子很小?”
我点头。
他蹙着的眉头没有松开,而是问我:“从哪里看得出胆子很小?”
我大概指了一下凶手来时和去时的脚印,把刚才的发现讲给他听,他郑重其事点着脑袋慢慢把眉头松开,表示很认可,问我还有没有别的发现或者想法。我没回答,反问过去,问他有没有什么发现。
他盯着我,伸出右手,两个指头朝地面,用力点了点。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往下看,就在我和他的中间,有一对用白灰圈起来的脚印。
那是凶手留下的脚印。
凶手留了很多脚印,尸体周围特别多,因为四处走动重复踩踏很多都模糊不堪因而没有用白灰圈,但这对被圈起来了,它在尸体的正对面,离尸体大概一米远,正面朝向尸体,非常明显,非常突出。
谭仲夏招呼我蹲下身体,说:“你仔细看,这两只脚印,比其它所有那些都要深,要大,鞋子底纹都部分重叠了。”
“是的。”
“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凶手在这个地方站了很长时间。”
他抬起眼睛看我,慢慢地摇两下头:“不是站,是蹲。他蹲在这个位置蹲了很长时间。”
我往尸体那里看了看。
他问我:“你要不要蹲到这里试试看?”
谭仲夏叫我蹲到凶手蹲过的那个位置试试,我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所以斜眼觑他,不动。但很快发现,他是认真的,巴巴地看着我,几次打手势叫我试试,表情很鼓励,那惹人厌的样子在我看来有点像是小孩子的恶作剧,但也只能听他的话走过去。
谁叫他那颗板寸脑袋上有乌纱,算是我的半个上司呢!
本着保护现场的原则,我没有踩进白灰圈里,而是往后面站,角度不变,贴着白灰圈的边缘站定,慢慢蹲下,一抬头,目光直触尸体那两只暴突的眼睛,于是立刻明白凶手蹲在这里的全部意义。
凶手真是恨对方恨到了极致呵。
他把对方开膛破肚,然后退到一米之外,蹲在这里看,只是看,看他痛不欲生,看他生不如死,直到彻底看够,自己都濒临崩溃,还扑过去扒开他的胸腔和腹腔将内脏掏出来到处乱扔,连树枝上都挂上了一截肠子,这之后才慌不择路逃跑。
我想象凶手做这一切时的画面,脊背有点发凉。
天底下能做出这样残酷事情的只有两种人吧,不是有生杀大仇,就是嗜血成性的杀人狂魔。
眼下这桩案子的凶手,从他一系列行为模式以及留在空气里的胆怯和恐惧来判断,只可能属于前者。
我没急着起身,仍一错不错地盯着尸体的眼睛看,那两只突出在眼眶外面的眼球射出的目光恐怖而空洞。当然,对死人来说,已经没什么目光可言了。他的目光,现在大概正在地狱里慢慢腐烂。
看着看着,猛又看出一处不对劲的地方来,于是一跃而起,小心走到尸体旁边仔细看他的脖子。
这人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痛苦死去,脑袋却没有耷拉也没有倾斜,是因为凶手在他脖子里绕了好几圈铁丝,生生将他固定住,迫得他直面痛苦和所有痛苦的来源。而凶手是从胸口处开刀的,大量的血液都集中在下面,脸上和脖子里很少的一点血是受害人嘴里吐出来的,除此之外,脖子里很干净,没有伤痕也没有别的血迹,铁丝勒着他的脖子但没有勒进皮肉里去。
这不合情理,但不是不能解释。
谭仲夏走过来,挨着我的肩膀蹲下,突然凑得很近,近到我的皮肤能感受到他说话时嘴里喷出的气息。
我从他的气味里闻出一种很熟悉但不明所以的东西,心里不由一颤,有点摆不正脸上的表情。
他问我:“这是你第几次直面死人?”
我有点无所谓地回答:“很多次了。”
他追着问:“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我还是很无所谓的语气:“2011年秋天,解放路发生一件抢劫杀人案,我跟警察去了现场。”
他继续盯着我问:“你那次看见死人也不害怕吗?”
于是我就明白,他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试探的意思。
他对我抱有浓烈而急促的好奇,想要一招就探知我的根底,可因为实在看不明又摸不透,只好几次三番试探着问,已经急迫到了完全不担心我察觉他的意图而生气的地步,或者说他完全不在乎我会不会生气。
当然,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生气的人,特别在这种场合,冒然跟他生气等于毁自己前程。
我也不怨他在问题里面藏些鬼鬼祟祟的意思,反而觉得有趣,所以忍不住想要跟他把这游戏玩下去,于是抬眸一笑,淡然回答:“不害怕。”
他接住我的目光,又问:“一般的姑娘,别说死人了,就是只死老鼠都能吓得尖叫,你说你正常吗?”
这用词就有点不怀好意了,可我不跟他计较。
我眼睛看着尸体,语气里带点调笑,说“有时候吧,人家姑娘看见老鼠蟑螂就尖叫不一定是真害怕,只是示弱,女人一弱,就会激起男人的保护欲,所以示弱是女人的生存技能,跟怕不怕真没什么大关系。”
他故意装出一点惊奇,问我:“你没有示弱的技能?”
我噗地笑:“就算有也不能在这里展示吧?我自己巴巴地跑到一个命案现场来,然后故意吓得连连尖叫哇哇大哭?有病吧我?”
他微微倾侧身体,也跟着我笑,脸上的皱纹全部舒展开,可是眼睛里却没有半点笑意,甚至没有温度。
两只没有温度的眼睛。
很难看出谭仲夏到底多少岁,也许三十出头吧,也许三十六七,四十应该不到吧,可他的抬头纹和法令纹太深了,真的很像一条历经沧桑的沙皮狗,说他五六十也有可能。
这是个从外表上看年龄很模糊的男人,笑起来的时候又有股子天真的劲,像个小小少年。
还是个很难看透深浅的人。
刚才的话题,他不放过我,扯着我继续聊:“那你和我说说,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你真正害怕的。”
我随便拣了个东西回答他:“蛇。”
他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撇嘴说:“蛇有什么好怕的,我是一点都不怕,有时还上山捕蛇,蛇肉很好吃,下次请你吃。”
我学他的样子撇撇嘴,说:“得了吧,我可不要吃。你能确定你吃的是蛇肉吗?蛇是会吃人的,德国有个专门研究蛇的专家出过几份据说很靠得住的报告,说人体组织能在蛇体内存在二十年之久,所以你有可能间接吃了人肉。”
我一边说一边往后仰仰身子,特嫌弃地瞟他。
他没介意我故意装出来的嫌弃,又跳转了问题:“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渐渐有点习惯他东一榔头西一锤的问话方式了,云淡风轻回答他:“平面设计。”
他静静地看着我,好一会没再吱声。
我又噗地笑,说:“怎么?觉得我学那个专业实在是浪费智商?”
他摇头,特别认真地回答:“不是。我只是觉得,你现在干的事情,纯粹属于不务正业。”
我用手撑着膝盖,把脸望向远处阴沉沉的天空,兀自笑了一会,然后问他:“你怎么会知道我很能打?”
21、如果凶手不止一个()
刚才谭仲夏问我屁股受伤情况时说的话里,明显对我的身手有一定了解,我挺介意的,所以假装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一问。
他说:“我刚来时,站在那边看了你一会,能穿着双不合脚的胶鞋在泥泞地里身轻如燕如履平地,没练过的人,不可能。你看看那边鉴证科的那个小姑娘,腿都发抖。”
我往他看的方向看了一眼,说:“呸,人家那是吐着吐着吐没力气了才抖,跟练没练过有毛线球关系!”
他假装恍然大悟般点点头,然后坏坏地笑起来,说:“其实是那边几个干外围的警察在那里说闲话时我听到一耳朵。他们之前在讨论,如果我跟你打的话,谁会赢,好像还下了五块十块的赌注。”
我想都不想就说:“你不是我对手。”
他没接这个茬,突然又跳转到别的频道了,问我:“你没有吐?这样的场面你不觉得恶心吗?我看见那个法医助理都吐了。你居然没吐。”
我实在有点不耐烦,皱着眉头说:“你不觉得你问题太多了吗?我们压根不熟还没到能对你掏心掏肺的程度好吗!”
他一脸无辜却又执着的表情,非要我回答了才肯罢休的样子。
我甩甩手,说:“我跟你讲不清楚,这个问题你得去问王东升。”
我说着,站起身,扭脸找王东升,一眼就找见了,朝他招招手。
王东升大步走过来,表情很严肃。
我请他把为什么我不会对血腥现场感觉恶心的科学依据给这个新来的谭副队长解释一下。
我完全是玩笑性质的,只想快点摆脱谭仲夏的刨根究底。
可王东升是个严肃惯了的人,还真的正正经经给谭仲夏解释起来:“人生来就是不同的。有些人生来体质强,有些人相反,生来体质就弱。那后者就需要通过后天的努力锻炼和营养支持来弥补先天缺陷。这是在肉体层面。心理层面也是一样,有些人生来心理就比一般人强大,而有些人可能比平均值要弱很多,这些都客观存在。如果说心理弱到不能承认一般的生活和工作,就需要通过特殊的训练来加强,否则很容易出现心理疾病并导致行为偏差。苏妮属于前者,而且是前者里面的佼佼者,就算万里取一也有这个概率,稀奇,但不逆科学。”
滔滔一席话,有板有眼,而且听上去很是那么回事,不服气都不行。
我跟王东升道个谢然后朝谭仲夏摊摊两手表示就这样。
谭仲夏却有点犯迷糊,指着王东升问我:“他是谁?”
我没来得及开口,王东升主动伸出右手自我介绍:“王东升,鉴证科的。”
谭仲夏也伸手跟他握:“谭仲夏,刚调来,还没上任。”
王东升点点头,没有一点笑意,问我们现场看得怎么样,能不能让他们的人进场处理尸体了。
我们赶紧让开,把现场还给他们。
然后我们两个人肩并肩慢慢往停车的地方走去。
谭仲夏似乎很绅士,走得慢,并且时不时作出一副要保护我的样子,怕我在泥泞里摔倒。
我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
他答:“早上七点四十分到局里,茶还没喝上一口,就转来这了。”
我问他:“你到局里时,有没有碰上白亚丰?”
他蹙了下眉,问:“谁?”
我想,那就是应该没碰上,或者说碰上了,还没来得及介绍。再或者是介绍了,他也压根没记住谁是谁。谭仲夏明摆着是个天份很高行动能力极强的资深刑警,这样的人难免会自恃过高,把眼睛搁在头顶,看不见底下类似白亚丰这样的芸芸众生。
我没纠缠这个问题,他也懒洋洋的没追问。
看热闹的人走了一部分,还剩下几个极顽固的留在原地,其中有两个的目光一直粘在我和谭仲夏身上。
我随便瞟了一眼,心里认定那两人都是记者,便暗暗猜想那个稍稍有点壮实的女人会不会就是让刘毅民头疼欲裂的代芙蓉。
如果真是她,我感觉稍微有点失望,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代芙蓉应该是个身材高挑容颜倾城冷若冰霜的女人,应该全身散发着女王气息,这样的形象才配得上她的能耐和她“一代名记”的名声。
一边想一边就走到了刘毅民的车子旁边,他正好在不远处看见,走过来把钥匙交给我,叫我们先回局里,他等这边处理完以后再回。
他说完,看着谭仲夏笑了笑,跟他说:“今天早上的事情,听同事说了,我替亚丰给你道个歉。你看在他还是个孩子的份上,别跟他计较。”
谭仲夏完全当没听见似的,转过身再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