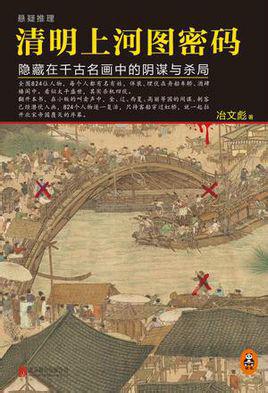异香密码:拼图者-第9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着,他指指茶几上的人皮:“你不给,我不强要,虽然说白了,我有权力强要,但我尊重你。东西收好,千万千万不能弄丢。而且你还是做点心理准备比较好,这东西,迟早得交给研究中心,你不肯也得肯。实话跟你说,我们有些谜团能不能解开,它是关键。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到解析它的方法。”
我默默把这块皮收进背包里,然后默默地跟着他往外走,不搭腔。等这个话题说完以后,我才跟他道谢,谢谢他告诉我这么多信息。然后问他为什么会告诉我。他说昨天下午还在江城的时候,他跟常坤讨论过我的情况,觉得我在“上帝之手”案件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和行动能力很强,可以试着合作,但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
说着话,已经到了停车场,他说他的人刚刚打电话来说付宇新带着枪乔妆打扮出门,不知道去哪,他必须得去和现在正跟踪着他的人会合,免得出事,问我要不要一起。
我想想,觉得没必要,说到底,除非迫不得己,我并不想直接跟付宇新撕破脸皮,跟任何人都不想,但看他们互撕我还是很愿意的,甚至有点隔岸观火的幸灾乐祸。
何志秦开车走了,我没什么事,便也开车回城西,先给代芙蓉打电话告诉他我一会就到家。
然后,我仔细把刚才跟何志秦的对话前前后后都回忆了几遍,他说他们那个研究中心在陈家坞事件之前就存在了,“廖家恶性凶杀案”的死者廖世贵就是那个机构中的重要成员,他死以后,机构重组,常坤他们才参与进去;常坤跟何志秦的“上面”似乎还有好几层人物,到目前为止没露过面,没有过半点声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所谓的“潘多拉官能异变综合症”,也就是我之前调查了许久的、民间称统称之为“鬼症”的疾病,那个研究中心的成立好像是为了寻找基因突变的原因和治疗的办法,按何志秦的说法,前者已经部分达成,目前正在进行后面那个阶段。
这样看来,它应该是个由权力部门建立的科学机构,难怪会有中科院的人和生物学基因学方面的人掺和在里面。
关于我手里这块有隐纹眼睛的人皮,何志秦说它很重要,说它是解开某些谜团的关键,只是目前还没找到解析的方法。我没有记错,他当时用的肯定就是“解析”这个词。那么也就是说,这只眼睛和它里面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是某种神秘的密码,隐藏的信息类似藏宝图之类。
于是我恍恍惚惚明白过来,也许几次入侵我家并把人皮留在我衣柜里那个女飞贼知道这玩意到底有多关键,可她看不懂解不出所以留给我,让我想办法去解析它。
挺好的。
至少这块人皮在我手里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好歹把研究中心那扇沉重而神秘的大门敲出了点声响。而且我觉得,我正一步一步走近真相,正越来越近,只要用力推开那扇门,就能看清楚里面的全部。
只是这扇门实在有点重,我大概还得再费好些力气才能推开。
代芙蓉做了一桌子热气腾腾的菜在家等我,他穿着围裙来给我开门,笑得内敛腼腆。
我看着满桌子我爱吃的菜,闻着空气里面特人间的温暖气息,望着代芙蓉脸上的笑容,突然很感动,莫名就想嚎啕大哭,但忍住了。
他督促我洗手,把我推到餐桌边坐下不要我帮忙,他在厨房里喊:“我把汤盛出来就能开饭了,你等着。”
喊完以后他轻笑着补了一句:“好几年都没正经做过饭了,也不知道好不好吃,咸了淡了你可千万不要笑话。”
我闷声不响吃下三大碗饭,味道真不怎么样,可我愿意捧他的场,一边吃一边说好吃。
第二天我没去局里,而是和代芙蓉一起在家研究代文静留下那个本子上的内容,换个思路去理解那些人名、地名、数字、简笔画、符号和最后化工厂老宿舍的地址以及杨小燕这个人物所包含的意义,十多个小时过去,还是一无所获,代芙蓉每次看我的眼神都比之前暗淡,看得我心里发凉。
晚上九点,楼明江打来电话,说:“你指定的药草已经按你说的方式准备好了,苏姑娘,别嫌我烦啊,最后再问一声,真的不需要先拿动物做实验观察观察吗?杨文烁的命很真要,错不得。”
我听着就不耐烦起来,语气里夹杂了嘲讽,说:“随便你们吧,稳妥点确实很有必要,多等一天两天没事,杨文烁不见得能逃掉或者马上就死了。”
楼明江沉吟了一会说:“我肯定信任你,但实验室的规矩很重,万一出点什么岔子,大家都会有麻烦。”
我笑笑,说:“没事,你们按规矩办,我等消息。”
然后把电话挂了,心想杨文烁也确实未必就等不了这一天两的时间,让他们折腾去吧。
这一等,就多等了两天半,老懒一直在杨文烁藏身的旅馆附近不眠不休埋伏着监视,说她每天都会出两三趟门,每趟进出都只有自己一个人,最后一趟出门是前天中午,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这种情况在之前没有出现过,怕她会不会是在外面出什么事了,打电话问何志秦怎么办。何志秦一急,立马打电话回江城跟常坤商量,一致决定通知实验室先不要管实验数据和结果,马上带着麻醉药草来乾州。
又等了近五个钟头,才全部就位。
我在楼明江抵达之前就已经换了身行头打车到城中村附近找老懒,事先给小海打电话,通知她这边今天晚上就要行动。这是她之前嘱咐过的,而且我也终于知道她的用意了,为了不让付宇新和他手下的人查到杨文烁的老窝,这几天小海到处故布疑阵,有时打电话报警说在哪哪哪看到杨文烁,有时自己神神秘秘在这里那里出没,领着付宇新安排跟踪她的几个人到处瞎窜。
她卯着劲要破坏付宇新杀杨文烁灭口的计划。
今天这边要收网,她当然不可能给付宇新有机会来破坏。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嘴里不知道在吃什么,说话含含混混的,我担心万一把付宇新惹太急,会对她不利,她刺啦啦吸着什么饮料然后用很无聊的语气叫我管好自己就行,别瞎操没用的心。
那态度,好像我很喜欢大惊小怪草木皆兵其实世界歌舞升平盛世安好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哪来的盛世安好。
204、白亚丰的危机()
我刚走进城中村一条弄堂,旁边水果店里突然窜出个人影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扯进店里面,我闻着味就知道是老懒,所以完全不抵抗,一边被他拖着走一边顺手从旁边捞过根香蕉就开始剥着吃。
站定了,回头望着他笑,见他一件纯黑色短袖t恤,乍一看真是很帅,有点电影明星的范。
只可惜那双眼睛,永远都是死人样定漾漾的,没有神采。
我想跟他说话,他朝我轻嘘了一声,伸出右手食指贴到我嘴唇上,左手按着自己的左边耳朵,是在听微型对讲机里的声音,听完以后抓住衣领往嘴边凑,低声嘱咐对方怎么样怎么样。
忙完了以后才朝我看,问我刚才想说什么。
我把手里的香蕉皮扔进垃圾桶,指指收银台,叫他去付钱。他倒没意见,转身去了,走了两步又回来,说:“反正吃了,不介意你再拿点。”
于是我就乐颠颠地挑了苹果桂圆冰糖桔,临结账又拿个大柚子,装好称好付完钱,他拎着水果,我挽着他的手臂,亲亲热热往弄堂深处走,这伪装很好,俨然是一对情侣,杨文烁这会就是迎面撞见了,也未必认得出我来。
老懒说杨文烁自前天中午出去以后,到现在都还没回来,何志秦的人已经在她房间里做好部置,门窗紧闭,药也用上了。
他说:“如果那药草的麻醉效果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杨文烁回屋以后会在不知不觉间闷倒,我就担心,她倒地的时候会不会把身上那样东西给碰坏,碰坏的话,就白折腾了。”
我说:“我也考虑过这点,但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办法,用射击麻醉的话,能不能射准两说,最重要的是麻醉速度不够快,她还有时间做最后挣扎,更不能保证东西安全。”
老懒说:“对,我也考虑过。”
我想了想,又说:“按我的想法,既然那个容器里面的东西里那么重要,制造者在处理的时候,就该考虑到平常化的意外,比如磕着碰着摔着什么的,也就该在容器的选择上有所防范,避免这种生活里常见的小意外带来的损坏,你想,用个手机还时不时摔着磕着呢,世界上哪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所以我认为,杨文烁在被麻醉失去意识后的倒地,哪怕就是磕到,应该也不会弄坏那样东西。”
他慢慢点着头,说:“阿弥陀佛老天保佑但愿如此。”
说着话,我们已经走到杨文烁下塌那间黑旅馆里,就是一幢农民自家的老旧房子,隔成一小间一小间,可以长租也可以短租,价钱便宜得要死,也不需要登记身份证什么的,很适合藏污纳垢。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打点好了,他们要了几个位置最佳的房间作埋伏用。老懒把我带进一个脏兮兮的房间,关上门,把耳朵贴在门上听外面的动静,扭脸小声跟我说:“对面就是杨文烁的房间,何志秦他们在她旁边那间屋里。”
我便也把脸贴到门上去听,和他隔得太近,几乎脸贴着脸,他的呼吸里有刚刚吃过的水果的清香。
对面和走廊都没有动静,倒是住在我们左边房间里的一对情侣在办事,浪叫声很大,听得人脸红,却又想笑,憋了一会不听了,走到床边想坐,看灯光下的床单颜色有点可疑,想想这地方出入的各种人和各种情况,没敢坐。看看沙发也没敢坐。
于是就这么傻站在屋子中央,突然有点后悔,不知道自己跑来凑这种莫名其妙的热闹干嘛,眼前的局面何志秦是老大,老懒的级别那么低,根本说不上话也插不上手,我更不用说了,纯粹就是个打酱油的。一旦计划顺利执行,杨文烁和她手里的东西被拿下,他们肯定连夜就弄到江城去,压根不会有我们什么事,真还不如在家陪代芙蓉看电视好玩。
可是既来之则安之,等着吧。
一直等到午夜,杨文烁都还没回来。
老懒神情里原本就不多的希望彻底消失殆尽,手表上指针一过十二点,他就颓丧地坐下,睁着两只死鱼眼瞪我。屋里没有开灯,外面照进来的路灯光线像地狱里面的鬼火,把他的脸照得像是浮在岩石壁上没有生气的雕塑。
我安慰他说:“也不用太急,再等等,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人,你还能指望他有正常人的作息规律不成?”
他听了,摇摇头说:“不对,杨文烁不会回来了,要不就是逃了,要不就是在哪出事了。我的人盯对面那间屋盯了整整八天,之前都很有规律,她基本会在下午或傍晚的时候出门,一般晚上七点之前肯定回来,直到昨天。”
他语气很不好,透着些冰冷的埋怨。我懂他的意思,如果楼明江他们按我要求的将药草弄好就带来乾州的话,前天就能把她抓到了,可他们偏偏讲这个那个规矩流程还要先拿动物作实验什么的,白白浪费掉最后的机会。我甚至觉得他的埋怨里也有针对我的成份,如果不是我在那里瞎出主意,非要用什么特殊药草的话,他大概已经用蛮横的方式连人带物都拿下了,未必就会运气不好把那件重要物件弄坏。
这么一来我就没什么话好说了,尴尬地沉默着。
十二点十八分时,我的手机亮,有电话进来,是白亚丰。我拿在手里没有接听,看着老懒,他挥挥手让我接我才接起来。
电话那端一片混乱,大口大口喘气的声音、狂奔的脚步声、还有风声。
好像是碰到什么危险了。
我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尽可能压抑着喂了一声。白亚丰才终于说话,喊了两声我的名字,把嗓音压得很低,声音是抖的,带着哭腔,听着很是惊心,绝对是碰上大事了。
我根本来不及问他出什么事了,也来不及考虑一下这么冒冒然打开门往外走会不会毁掉何志秦他们的整个计划,连招呼都没跟老懒打就砰地拉开房门往外跑。一边跑一边问白亚丰的所在位置。因为这会问他出什么事了实在很多余,问明白地点赶紧过去才最要紧。
白亚丰喘了好一会气才说清楚位置,什么街什么路的哪个岔路口。我脑子里一转,就在离他家不远一个小公园的东边,我们有时会用轮椅推老爷子去那带散步,所以很熟。
我刚下楼往外走了十几步,眼见着有个瘦高的女人从前面树影里往这边走过来,长卷发、大风衣、平底鞋。我心跳加速,不敢乱说话,只嗯嗯应着,疾步与那女人擦身而过,连她的脸都不敢看,生怕万一正好是杨文烁,被她认出,就全完了。这弄堂里还有人家养猪养鸡什么的,浊味很重,我也没法从气味分辨到底是不是,只能随她错过,只在心里祈祷如果是她的话,千万别再出岔子,我真是有点不耐烦了。
其实大家都已经不耐烦了,再这么拖下去,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
转过一道弯以后,我才继续跟白亚丰讲电话,叫他不要挂断。正好这时有辆空出租车卸了客在调头,我三两步窜过去爬进了副驾里,用吼的把地址报给司机叫他踩最大油门用最快速度。那司机斜我一眼,根本不听指挥,原先什么速度照样还用什么速度开。我因为通着电话,没功夫跟他扯皮,准备一会挂掉电话以后如果他还这样开的话,就把他扔下去,自己开。
电话那端喘气声还在,脚步声没了。
我问白亚丰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路灯全都不亮,黑漆漆的,很暗。我疯了一样朝他吼:“给我走到大路边去!走到有光的地方!背靠墙壁站好!注意左右和上面的动静!枪上膛!拿稳!哪里有情况就往哪里开枪!不管发生什么,不管对方是谁,开枪!首先保自己的命!”
我确实还不知道那边在发生什么,到底是白亚丰在追捕犯人还是他被犯人给袭击了,反正不管哪种情况,肯定都是他的能力所应付不了的,否则也不至于声音抖到要哭的地步。
出租车司机听见我吼的那些话,开枪、保命什么的,整个人都懵圈了,看我一眼,赶紧把油门踩到最大,然后挑红绿灯最少的路段往目的地奔。我不动声色看他一眼,继续跟白亚丰讲电话,问他有没有照我说的做。
白亚丰突然口齿含混地嚅嗫了一会,跟我说他想回去看看,回刚刚出过事的地方去看看。
我破口大骂,骂到他把回头的念头断绝以后,才稳下情绪说:“你安安耽耽照我说的做,别挂电话,我借个手机来给你报警。”
他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报警,我已经叫过后援了。”
这话说完,脚步声又响起。
他总算乖乖按我说的往有光的地方跑了。
但我的心还提在嗓子眼里放不下去,因为对情况完全不了解,也就没办法判断可能存在的危机,除了在电话里陪着他、尽快赶过去以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205、白亚丰的隐瞒()
对白亚丰,我只能指挥他逃跑,没有任何别的选择,他不是老懒,不是刘毅民,甚至连胡海莲那点应对能力都没有,碰上性命悠关的突发状况,除了逃跑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很快,他喘着气说:“好了,在大路边了。”
我这才松下口气,用温和的语气问他有没有受伤。
他说:“只是腿上擦伤了点皮肉,右肩膀在墙上撞了下,有点疼,但应该没有伤到骨头。”
他说话的时候喉咙里面咝咝吐着气,是一种完全不自觉不自知的惊惧。我怕他分神,所以没问到底出了什么事,而是重新嘱咐一遍刚才的话,注意左右和上面的动静,有情况就开枪。我叫他不要讲电话了,把手机保持在通话状态放到地上,两只手都握住枪,别打偏。
两分钟后,手机里传来警车和救护车的声音,接着是纷踏的脚步声,白亚丰捡起电话朝我喊:“后援到了,没事了。”
我这才挂掉白亚丰的电话然后给老懒打去,问他那边进展怎么样。
他懒洋洋哼了一声,说:“你走前什么样,这会还是什么样。”
我问:“我出来的时候在弄堂里碰上个女的,不是她吗?”
他说:“布置在外面的人员确认过了,不是。”
我哑然,失望透了。
老懒问:“你那边又是什么情况?胆子可真肥,招呼不打就乱跑,万一碰上杨文烁呢?”
我说:“亚丰碰上事了,好像被什么人追,具体还没来得及问,我还在路上。”
老懒呆了一呆,骂出句脏话,说:“该不会是被杨文烁袭击了吧?”
我嗓子有点尖:“不能吧?没道理啊!”
他说:“以前我们都高看了杨文烁的道德感和自律能力,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很可能会发生随机杀人的行为。”
这时我倒沉静,说:“我知道,但还是不可能,她都病得站不稳了,哪还能去袭击个持枪的刑警。”
出租车司机还算很识相,连抄两次近路,二十分钟就到达目的地,我甩了张大钱给他说不用找了然后赶紧下车。结果他比我更急,压根没想着找零,甚至没等我站稳就把车开出去了,逃得跟只老鼠样,生怕惹上这种动刀动枪可能会见血的是非。
我穿过马路往救护车灯闪的地方奔,连规矩都扔了,冲进人群就伸手去碰白亚丰,想看看他受的伤严不严重。
他倒还冷静,赶紧往旁边闪躲,做了个阻止的动作,虚弱地笑笑说:“我现在我现在应该算是证据吧?一会他们要来给我做活体取证,看看有没有抓到袭击我那个人的头发和皮屑什么的,你一碰我,你也成证据了,很麻烦的。”
我点着头往后退了两步,正想问问受伤的情况,突然发现他表情不对,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又不能说的样子,马上留了心,仔细注意他。
白亚丰确实有话要跟我说,而且是很重要的、必须瞒着别人的话。
他看我一眼,然后看左边一眼,神情很小心。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是鉴证科的几个人正往这边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