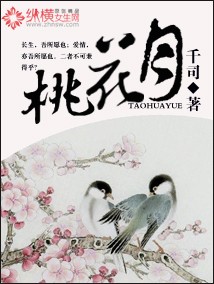���¼���-��3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Ȼ��ǰ����ԩ��Ϊ�β��Ͻ������ô��ã�����������
�����������˿��ߵ��������ɷ�ö˶˵�����������ͷ������ֻ�½�ȥ�˺�Ҳ���������⡣��
����������褵��������⻰��ʲô��˼����
������������û�п��ڣ���Ⱥ��ȴ�и������߽е��������˵���϶�����Ϊ����ү�������˼ҵ��ɷ�
����������һ�������е�����������������������״������ү������ô�ҽ�ȥ�أ���
����������褻��������������������е�������˭����ҥ���£�վ��������
������������˵�����Ⱥ���¾�����������褲��ֿ��ڣ��������DZ����ʰ���������˽���������Ŀɼ����£���Ȼ�㲻�Ͻ������������ʣ��Ǿ͵��Ŵ�ҵ����˵һ˵�������Źܼ�����һ�£�������������Ŵ�ı����������ɽ��֮�£����նŹܼҺ�Ȼ��Ե�������������𣬱��ٻ�������飬˭֪���ͺ�Ȼ���˶���������±���Ҳ���ú��ǹŹ֣������Ǿ������ŶŹܼ��й���ɽ�������͵ģ�������Ϊʲô�������Dz�������˭������ٻ�������飡ֻ����ұ�ҥ���ɱΣ��ñ��١�
�����������Ļ�δ˵�ֻ꣬������Ⱥ�е���������٣��ſڿ��ӵغ�˵ʲô����
�����������ͬʱ�����ݡ���һ������ʲô�����ӳ�����ֱ����褶�ȥ��
�����������ȫ���������������ü����ۿ���Ҫ���������ţ����һ��֮�£�������ǰ���˻���ȴ��һ֧�ֱۺ��˹�����������ǰһ̽һ�ա�
��������������������ţ�ȴ�����������ؽ��ֱ��ջأ������о�����һ����ƴ��ʯͷ�������ⶫ�����������ϣ����������������IJɷ������Թ��Ӽ��̾�Ҫ�������
����������������ϣ��ڳ�����Ҳ��Щ�ճմ�����������һ��ίʵƯ�����صÿ졢�ݡ���
�����������������з�Ӧ��������ǰ�ȵ�����˭��˭�ɵģ���������ò���Ҳ��ǰ������Ѱ����֮�ˣ���Χ�۵İ��ղ��¼�ʮ�ˣ��������µؼ���һ�����������ҳ����ֵ���˭��
����������褱㿴������ȴ������������ʯͷ������һ�����������������ǵ�ʯͷ�����ѳɼ�С�飬��褲������������졣
����������������һЦ��Ŀ������Ⱥ��һɨ������һ����������ʯ�����ǰ�û����Ⱥ֮�С�
��������ֻ���á���Ӵ��Ӵ�������ҽУ��������÷����������������Ǹ��˵��˴����������������γ��ѣ����˳��˽�ȥ��
����������Щ����������أ�Բ�֪�������£���������ŷ�Ӧ������λ��ͷ���˷��Ŷ����֡�
�����������˺�֪�����ȴ���������������Ⱥ����һ����æ������ܣ������Ǽ�Ϊ���ؾͰ����˵��ĸ������˳�������������������褸�ǰ��
�������������ˣ��������˶�ͷ���������˾��䣬�����������գ��������˺����Ѫ����һ���˵ĸ��ɣ������֡�
���������Dz�����������ֵ������ţ������������������ˣ��������Ի���һ��ʯͷ���������ӵ����ɡ���ԭ��������Ҫ����ʯͷ��ʱ������������һ����ס�ˣ����˲��ɷ�������
����������褼�������ʧ����ȵ�����������ʲô�ˣ����Ҫ�������٣���
�������������˹��ڸ�ǰ��͵������ʴ���ף��ɶ�����˵��һ�˾͵���������ֻ�ǿ������㡱
�����������ŭ��������ô��һ��ʯͷ�����б��پ��ǰ�����͢���٣��������������İ�����˲����ƣ���Ϊ�����߱��پ�Ҫ�Ӻ��𣿡�
����������һ���˱��������������Ϊ�㺦��������
����������������ţ���������˵�������⼸������Щ���죬��֪��������������
�����������������°�ϸ���˻�����������������Ƕżҵ��ˣ�����ǰ���������Ǹ��ŶżҵĽ���ȥ��¥��
��������������һ����������ɫ��Ҳ�����ٶ�˵�����Խ����ر����졣
������������ͬ����˵�������䣬���Χ�۵���Ⱥ�о����˾�˵�����������Ǵ����IJ��ǶŴҵļҶ��𣿡�
��������һʱ�������������ָ࣬��������
���������п����ֵ������˾�˵����ԭ����������������ү���Ա�⣬��˲ű��˼Ǻ�����ŹܼҸ��Ŷ�Ա�����˲��ٵĶ��£���η����ɱҲ���еġ�
����������ʲôη����ɱ����֪���żҵ�������Ļ���ҿ�������������DZ��˺����ģ�ֻ�����������˲�������ү��������������������
��������������������ϲ��Ȼ������ж��µġ�
���������Ǹ�״�ĸ��˼�״��Ҳ��Щ�����Ƶģ����ҿ���������š�
��������������������˵�����������꣬��Ҷ����������������ͼ�������ٵ����ǶżҵļҶ������Ǵ˾٣���Ȼ�DZ���ָʹ��Ļ��֮����˭����������ն����֪����˵�ż��ǵ���һ�ԣ����˸����ǣ���������������������Ϊ�������صİ���ı�������������ض�ҪΪ�������룬�������ܳƵ����ǡ���ĸ�١���Ҳ�Ե���Ƶ��ʶ���
����������������������ﰵ�֣���������������¶ϲɫ��������Щ�¶������Ϳ�һ��������
�������������û�����˵�����������ǣ����Ǵ���ү�л�����һ����ԩ���ģ������������õ�״�ӣ����ڵ��������ø���ǰ�IJ�ͬ�ˣ�����ү�������ĸ�ĸ�٣���Ϊ��ҹ�ƽ�����ģ���һ�������İɣ���
����������Щ�����������⼸�䣬�Ż�������������������褱����ѳ��ζǵ���˵Щ����Ļ�����״����ֻ����¶Ц�ݣ������ڻ���������ѡ�
���������������Ա�վ�ţ�������Ц�⣬���ڴ˿̣�ȴ�־�����������ĸо���������������ȴ������ɫ����������ǰһ�ƣ�ȴ��û�����ʲô������
������������Ŀ��һ��˲�䣬����Զ����ȥ��ԶԶ�ؽֿڴ������������Ĵ��һ����¥������¥�Ĵ��ڴ�������һ����Ӱ�������֡�
������������Щ���ҵļҶ�������ã�����������������ס���Щ�Ҷ������Ƿ������£����������ؿ���ƿ�����̷�һ�¾�ȫ���ˡ�
�����������Źܼҵķ���Ҳ˵���Ƕżҵ�����ʹ������״����������ͷ��˵���Լ������ɱΣ����ǹ�����������˵ġ�
����������褼���ֻ�����Ӷ��ѣ���������û���ɷ���˷��ˡ�
���������˶�����֮����褲ŵ��������֣�����һ�²�֪������Ǻá���
���������������������������Dz����ڿ�����ô���ܰѶ����ù鰸����
�������������ǣ�������۾�һ�������������ܶ�������������ô���������ο�����������ǣ���Ļ���֪����������Ҫ�������������˾��鷳��һЩ����
��������������������֪�����˿�����������ô���������𣿡�
�����������üëһ��������Ȼ���ᣡ���ػᾡ������������ôҲҪֻ������ȷ���е��Ѷȡ���
�������������ѵõ�Ц��Ц������ô�Ҿ�����˷��ĺ��ˣ����������������£��⼸���Ż��в���ǰ����״�İ��գ�����ֻ�����������ר�İѶżҵ���״���������Ȼ�������������һ�ݣ���Ȼ���з�������
�������������Ǻ��⣿����褲��⣬�۾��ɵ�Խ��
���������������ϱ��м���Ц�⣬���ȴ��û�ˣ���ɫҲ��Щ������ֻ��������������˵���������ˡ���
��������������������Щ������������褣���������á�
�����������������ſ����ҿ���һ��������æ�������뿪��ֻ����������һ��һ����˳��ǽ����ǰ������ߵ��˹սǴ�����վס�š�
���������ǽ�����ͷ���˷�����ǽͷԾ�£�����ү������С�������𣿡�
����������������������������ԭ���ڻ��Σ������¸����Ĺ�Ա�����൱���˽�ɣ���
���������˷���ĬĬ��������˵ȫ��֪����ֻ����ү�ʵ���˭����
����������������˭������Ҳ���������ˣ���������ɫ��Ȼ������һ�㺮˪���ţ�������������ĸ��ף���֪������
��63�£�����
����˵�꣬�˷��������������ү˵��С�˵����Դ����������˵�֮ǰ�����Ѵ˵صķ����������һ�飬������ĸ��������ټ�������Ԫ�����״Ԫ��������������£���Ԫ����������ŵ�֪�����������������ƣ����ϱ�����������ʱ���а�����������ɡ��������������ټ�������Ⱥ���佱��һ��������������
�������������������£����������ƣ�������������ȴҲ������������һ������֮���Ĵ�磬��Ȼ����û���ɵģ������ټ����Dz�����Ԫ�����ھ����ƺ��DZ������ι�ְ�ģ���
���������˷���˵������ԭ����үҲ֪���������ھ������꣬��ȷ���ڱ����ι�ְ�ģ�������Ϊ������α������ɣ�Ȼ����ھ�����Ǩ�ˣ���֪Ϊʲô�������������˴˵ص�֪������
����������������仯���������˻�������ʵ��������������أ���
���������˷��������������λ��С�㣬С��ֻ֪������������ĸ�Ů�����������ټ���Ų���˽�Իؾ�����������ة������ʱ�����������Ͼ����١���
������������������������ʵ��������Ǹ��żҾ����Ǻι�ϵ�����֪������
���������˷���������ż��и������ھ�����ְ�����ټ�����֮���ݽ����ͽᣬ��������֮���Ƿ���ʲô���˽����С���в��������
���������������룺����������飬��������ô���˵��ܵ��żң���ȴ�������ʣ�ֻ˵�������ã��������ˡ���
������������˵��֮�����ߣ����Ϲ˷�����ػ���������ү��
������������ͣ�˲��ӣ����㻹�к��£���
��������ȴ���˷����ڻ���һ�ͣ����ͳ�һ�����ӣ����λεأ����ʮ����˫�ַ������ϣ�����ү������û��˵ʲô������ȴҲ֪��������˼��һ��֮�£������Ծ���Ц�Էǡ�
������������������Ҫ���˴������ˡ�
�������������ʵ�����������������������
���������˷��������С����ǰ��Щ�������ǰ���˵أ��Լ�Ҳ����һЩ����
���������������ʣ�����Ȼ�������ӣ�����Ϊ�����װ�磿��
�����������ʵ��Ѿ���Ϊ���������������������Ϊ�˷����ǽл��ӣ��ɼ���ίʵ������ǵIJ��У���Ȼ����ô�����ӣ�����ԺóԺúȺô��ġ�
���������˷��괹��˫������ĬƬ�̣��ŵ͵�˵������С����ˣ�һ����Ϊ�����˶�Ŀ��������С����˵���Ƿ�������ŭ������������������ڲ�������ûʲô�����ˡ���
��������������Щ���⣬�˷�����仰�����˻����������ף�������ȴ�Ƕ��ġ�
�����������һ��ս�ۣ�����Ȼ���ѵش�Ӯ�ˣ�����������һ�����ϣ���ȴҲ�����ˣ������������Ĵ����ԭ������������������ֵܵ���Ѫ��ɱ��
����������ô���������ս������������������룬ȴ����Ϊ��Ѫ�����άϵ�ţ���һ����ɱ�ݻ��������ڻʶ�����ν�������һ˿������
���������˷������һ����ֻ�����ݻ��˹˷���ģ�Ҳ�����dz�������˵ʧ���˵Ĵ�ɱ��
���������ڴ�֮ǰ���������ڻ�������ط��ܲ�İ�����������Ļ��������������֯����˵��ǧ��֮�ڣ���������
�������������з������ɱ𣬵����е����ἰ���Σ����������������ʣ���ɱ���鱨��
���������˷��걾�ǻ����������ĸ�ͳ�죬�������dz������죬���ε�ͳ����ˣ�������Ʒ����Ȼ��������Ʒ�٣���Ȩ��ȴ�൱�ڵ���һƷ������������η�ɵ����֡�
���������˷��걾������ǰ;������ȴ��Ȼ���췭�ظ����·�Ӿ������������Ԩ����������˵����Ȼ���������Ĵ��������������һֱ��������Ŀʾ�ˣ����˶�Ŀ������Σ�����Ϊ���θ���Ҫ��������һ�������Ȼ���Ѵ���֮������������˵���·��Ժ�������Ѿ�ȫ��ϣ������˴�ʲô������ʲô������������˵ȫ���ֻ�ǹ��Ӳд��Ļ��Ŷ��ѡ�
���������Ѿ��������������������ˡ�
�������������ǵ����ͷ�¶��������ƫƧ����ķ�����
���������Է�����˵��������ҹ�����������˱���������������ͦ���������������DZ������������������ң��˿̵ķ��������ƹ˷���һ����������������������Ҳ��һ��������������˵��
�����������������������Щ���ܣ�Ȼ���뵽����������ȴ������һ���������⣬����Ҫ��һ���������
�����������㲻���ٵ��飬ֻ�Թ˷����������ȥ֮����������ȥ�ɡ���һ̧�֣������������ŵ����ӻ������ƻ�ȥ��
�����������������Ӹ�λ���Ӳ��ᰲ�����ˣ����һ���Ѿ��DZ���ļ��ޣ��˷������̧ͷ��˫����¶���������顣
������������ȴ���ٿ�����ǣ�����Թ��Գ������ӣ���������������ȥ��
�������������������ϵ�������ͷȥ���ߵ���·����ɫ��Ȼ������������Ҳ���ˣ��εij������·�ϵ����˷��ܣ����ţ���Ҫ�����ˣ���
�����������Ϲ���������¡¡������������̧ͷ������߶���һ�źڣ����ƻ���ӿ������������յء�
����������������ǵ�DZ����������ӱظ�·��
����������һ������������ȴ�Ƶ�·�ϵ����ˡ�����֮��ؼӿ����ٶȡ�
���������������˴壬��Ϊ�˼���ؼң���û�ߴ�·�����˴���С����
��������������һ·�ı�������������������һֱ��ԶԶ�������Լҵ�Ժǽ���ݶ�����������̴��ϣ�������һĨƮ���ĵ����������ҡҡ�ڰڡ�
���������������ţ������뵽����������ǰ�ջ����Ӱ�����ϲ�¶��һĨϲɫ��
���������������꣬�������������ﲻ�����Ͱ���ǣ���ſڣ��ƿ����Ƚе��������ӣ���
��������Ѱ�������������춼�Ἣ��ظϳ��������˷����������ˣ�ȴû�����ش�
����������������һ�����ҴҰ�������Ժ�ӣ�������ֻ������ǽ����ת�ơ�
������������������ֻĸ����ǽ�������ܱܿ����ǹ��������ֽ������ŵأ�������Ҳ��Բ���۾�б���������������ִ��˸����磬�����ǹ�������Ҫ������������
������������������Щ����æ���־ͽУ������ӣ����������᷿ȥ��ƽ����ʱ��������ͷ�������˿��᷿���Ű����š�
���������������Ž�ȥ��ֻ�ŵ�����ķ���֮�������������Ķ������ǹ����ϰ��������أ�ȴƫ�����ˡ�
������������һ���ļ�������֪��������ȥ���Ͻ����᷿Ծ������Ҳ�����Ƕ���Ҫ�����������������������ؾͽ����ݣ������ӣ������������Ժ�Ӷ���������
���������ǹ�����Ҫ������ƥ����������Ҳ��Ҫ����������ֻ�����͵�������һ��������������һ��������ͣ��������
����������������ؿ��������䷿��ȴû�ҵ��������ˣ������������ſڣ�һ����������˲�䣬������ֻ������ǰ���ڷ��衣
����������վ���˲��ӣ������һ�룬������Ȱ�Լ���Ҫ���ţ����ּ������ܳ��˴��ſڡ�
����������ʱ��������Խ�������ˣ�����������ǰ����ҹ���������Ǻں����ء�
���������������۷��ڣ��뵽��ǰ�����˷��꣬�뵽�Լ����Լ������Աȣ����Ե��Ƿ����ң�����������С�����˰����������ҡ�
��������������
�������������ַ������ȣ������ӡ�ȴ���е�в��������Ƶġ�
���������绩�������Ҵ�һ���������۾��ҿ�����ǰ��Ұ���Ų�һ��˲�䣬����������������껩��������������
��������������������ͷ�������ϣ����ϣ����ϰ�������ɫ���÷���һʱ�뵽�����˵ij�����������������ŵر����Լ�����˫�֣�������ˮŪ�úܿ����������Լ���˫�־���ϲ�ڰ��������ӡ�
���������������б��Ƶ�������ǿ�����Ź������������飬��Ҫ������ȥ���߿�һ������Ȼ�����һ��˫�۲������ŵؿ���ǰ����
����������ǰ����С���ϣ��������ֵس���һ����Ӱ����Ϊ���µ�̫����Щ�������������������������������ͷ����ϸ���ֿ���ȥ����ˮ��û����˫�ۣ�������һ���۾������ֿ���
������������ȴ����������·�ϣ�Ҳ������������������˱˴˿��˸����š�
�����������˴��˴���Ȼ��ͽ��������֣�������к���
��������������ͷ�����������ؾ�ϲ�ؽ��ţ����������Ȼ��С�������������
����������������һ�ۣ�˫���ſ�������ס�������������س��˿�����
�����������ϵ������ˮʪ���������������أ����������Լ������и�������������ο��˵��û�£���û���������ˡ�
�����������������ĵض��Ǹм����۾�ȴ�þõ�����������Ϊ������ԴԴ���ϵ����Ž��յ�˫�۳������
����������������һ�������־ɵĴ�ɡ�����ŷ��������ǰ�ܣ����˼���������վ����������أ����������Щ��������æ�ֽе��������������
���������������˺������Ż����������۾���
��������������������ɡ�ˣ����ܱ߰�ɡ���������ӿ첽�Ӽ���ææ���ܹ�����һֱ�ܵ�������ǰ������������������˵������������վ���������ͷ�ְ�ɡ�����سſ����߸߾������ڷ���ͷ�ϣ����������
������������ȥ���ˣ��������ʡ�
�������������������ҿ�Ҫ�����ˣ��·�������꣬��ȥ����ͷ���˰�ɡ����ȥ���ӭһӭ�㡱
��������������������һ�����ԡ�
������������˵��˵�ţ������͵�����ȥ������Ȼ���ַ����Щ��֣��л��㱵أ�˵��������ʲô�о���������Щ������
������������С����˵�����������ô�ˣ���
�����������������ſڣ�ȴֻ��˫��һ�ţ������ؽ���§�ڻ��
����������������ͼ����һ����ȴ�����������˵����������Ҳ����ȥ������ȥ����
��������������Щ���ж����ݷ�˵������ϡ���Ϳ�ر������ţ��о����������ƺ��ط�����������������������ʲô�����ǵ������ˣ��������ģ�̧���������������������û���ܣ��Ҿ���ȥ�����ҡ����Ժ���Ҳ�������ڼ������ò��ã��������Ժ��ȥҪ������߲��У���Ȼ��������������ô�죿��
���������������������������������Ҳ�Ű�������������Ȼ�м��ⳡ��ű�ס���������棬���������ǵ���֪���ʵ����˴�ɱ�Լ������ѹ�֮����Ҳ�����������Ѫ����ȴ��û��������һ����������ô����ᡣ
�����������ǵ�����Ҳ�Ͱ��ˣ��������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