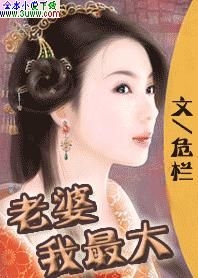双枪老太婆-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廖大哥的队伍中连女将都这么厉害,真是吉人天佑,硬怕要登金殿坐龙廷!”
夏林和几个年轻人大摇大摆地去捡枪,一边说:“张大爷你还不认识吧,这就是华蓥山谁个不知哪个不晓的……”我打断夏林的话头,说:“还不赶快打扫战场,硬要等那些残兵败将把民团伙起来,扭到你走不了路么?”
夏林吐了下舌头,不说了。一个小伙子悄悄地扯着唐老六的袖子,说:“请问你们那位大姐贵姓?”唐老六瞟了我一眼,说:“姓陈,陈三姐。”
后来,双枪陈三姐的龙门阵传得越来越神乎,我想跟这些鸡鸭贩子们多少有些关系。
顺手牵羊
在罗锅凼耽误了一天,我有些着急,催着大家赶了一百多里路,天都黑尽了才到一个小镇。
我们身上都带得有枪,又挑着两副挑子的货,不能到镇上去住,商量了一下,决定绕道去玉宝观借宿一夜。玉宝观离镇上有五里路,只有一个守庙的老者,我们人多,只要看守得紧,不怕他去通风报信。
敲开大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一跛一跛地走了出来,见我们这么多人有点诧异。唐俊清前去办交涉,老者直是摇头说:“你们到前面镇上栈房里去住嘛,这里就是我一人,铺盖也没有一床多的。”
我说:“老师父,我们是广安杨老太爷家里的。今年老太爷满七十岁,要做大生日,到重庆去办了一些干杂货回来,有一个力夫病了,走不得。”我转脸把唐老六盯了一眼,他就唉啊连天地叫唤起来。我接着又说:“你老者行个善嘛,我们坐一夜都要得。”
庙老者仔细打量了我们一番,见都是粗布长衫老老实实的庄户人,就勉强答应了。我当时就给他两块银元,向他买两升米给我们煮晚饭,剩下的就作柴火钱。他喜欢极了,点了一盏香油灯,将我们引到客房里。这个房间像是很久没有住人了,扬尘吊得多长,满屋都是灰尘,两间大床铺满了乱谷草,各放了一床烂草席,一股霉气使人发呕。我们用扫把简单地打扫了一下,将挑子放好后,决定分班放哨。唐老六是第一班,他先出去了,其余的到灶屋去烤火洗脚。
我在灶边烧火,同庙老者摆龙门阵,问场上那些廿军的人,常不常到这里来。庙老者摇摇头说,“来做什么?什么都抢走了,连碗都抢走了,就剩下这几间屋。”说着就把锅里的水舀在一个木盆里,招呼大家先烫个脚。
夏林一边烫脚一边说:“大姐,今天太累了,昨晚又没睡觉,是不是到场上去买点肉打点酒,大家好生吃一顿?”唐俊清和唐老六都说:“要打酒,就该你老夏去跑路。你今天偷奸耍滑的,我们都轮流挑担子,你光是打着甩手走路。”“只要有酒吃,跑路有啥关系。”夏林三下两下揩了脚,在碗柜里找了个酒罐,抬脚就要出门。
我往灶里添着柴说:“夏林你还是忍点嘴,眼看都要拢了,莫出去惹麻烦。”夏林一听这话,提着酒罐愣在那里。满屋的人都看着我,不开腔。
庙老者端着一升米进来,见夏林提着酒罐,忙说:“要打酒么?方便得很,前面幺店子就有,不过半里路。”唐俊清走过来说:“大姐,大家确实是累了,明天还要赶路,若是不放心,叫老夏就在幺店子里打点酒,你看要不要得?”
我看看大家疲惫的样子,也就不好再坚持,只是给老唐做了个动作。唐俊清笑笑,过去把夏林推到房间里去,下了他身上的枪和子弹,叫他快去快回。
水要烧开了,庙老者又去打了一升米来,一齐倒在锅里,又从地里扯来一些青菜萝卜,洗干净了倒在一个大砂锅里,放在火边煨着。隔了一阵闷锅饭好了,夏林还没回来;又过了一阵,青菜萝卜都煮烂了,夏林还是没回来。大家早已饿坏了,我说不等他的酒了,先吃了再说。可是饭都吃完了,老者连锅碗都刷洗归一了,夏林还是不见影子。大家就有点着急了。有的说这家伙莫不是到场上吃耍酒去了,有的说恐怕是喝醉了倒在冬水田里了。唐俊清看看我:“该不会出事吧?”我闷了一会儿,实在是放心不下,正要出去看个究竟,就听见唐老六叫门的声音。他一进门来就说:“大姐,不好了,场上过来了一个人,看样子背着长枪。”
我说声准备,大家撩开长衫,从胸前扯出枪来,咔喳几声响,所有的枪都上了红槽,各自找好了隐蔽的地方。庙老者吓慌了,站在灶边发抖,只是念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一会儿,隐隐约约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在门口停止了,接下来是打门的声音。庙老者战战兢兢地边走边问:“哪一个嘛,这样晚来做啥子?”
外面不回话,仍在使劲打着门。老者一边应着,一边吃力地取下杠子,拉开门栓,只听得哗啦一声响,庙老者唉哟一声跌倒了。我心里格登一下,心想今晚上莫非硬要干一场?就凑近木板缝隙,看见一个人跨进门来,肩上挂着两支长枪。他弯下腰去,放下手里的罐子,用双手扶起老者,说了声:“对不住,老师父,你受惊了。”
大家都从旮旯里走出来,又好气又好笑地望着进来的人。
我冒火连天地说:“夏林,你搞些啥子名堂?”这个扯客①吃得醉醺醺的,嬉皮笑脸地说:“啥子事嘛,我今天立了一个大功,你不奖赏我,还要骂我。”唐俊清气冲冲地说:“立啥子功?害得我们饿了半天,又受这一场虚惊。”
“你看嘛。”夏林将手上的长枪放在桌子上,又从肩上取下另一支长枪交给唐老六。唐老六接过枪一看,高兴地笑起来:“嘿!这还是点广货②,你是在哪里偷来的?”
“啥子偷来的哟!是场上李团总的正大堂皇送我的。”
我一看他带了这样好的两支枪回来,越是起了疑心,问枪是怎么来的。夏林说:“忙啥子,我还没吃饭呢。”说着就拿碗去添饭吃,还顺手从怀里拿出一包用粗壳纸包着的猪肉烧腊,用筷子向大家一挥:“来来,味道还不错。”唐老六说:“你打的酒呢?”
“唉呀,你不提起,我还搞忘了。”夏林边说边走向大门口,将酒罐提过来。
“不忙,说清楚了再吃。”我将酒罐抢在手上,放在一边。“要得嘛,我说了你一定要赏给我一个人吃。”夏林一面吃着饭,一面指手划脚地说开了。
“我走到前面的幺店子,酒卖完了。心想已经走了一截路,再多走几步,让大家喝几杯也好,于是就对直往场上走去。场口上,有一个小酒馆,快要收堂了。我进去,叫堂倌打了半斤酒,买了两块豆腐干,一个人慢慢地吃。斜对面四五丈远的栅子门口,有两个乡丁,一个坐在栅子跟前打瞌睡,另一个也是没精打采地靠在栅子上,枪放在右手弯弯里,手上提着一个烘笼。栅子门半开半闭的,场里边清风雅静,场口上也只剩下这一家酒馆还开着。我问堂倌啥子时候关栅子,堂倌说这一向不大清静,二更过后就要关。我边吃边想,这送上门的财喜要不要呢?正在捉摸不定,堂倌走上来问还要不要啥子,我说称两斤猪肉烧腊,明天好在路上吃。”堂倌听说我要带在路上吃,就跟我摆起龙门阵来,说这里很不清静,经常是捐呀款的;前一场还在打锣,说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要抽去打华蓥山的共老二。
“我问他山上的‘共老二’到底有多少。他说多得很,听说有好几千人;我们的乡丁都抽调完了,找来他妈的一些大烟鬼来守栅子,枪都拿不稳,还要去防‘共老二’,真是见他妈的鬼。
“我耳朵在听,心里就在打主意。”
夏林吃完了饭,燃上一支纸烟,左脚踩在板凳上,又比又划地说下去:“我叫堂倌打了两斤酒,把切碎了的猪肉烧腊包好,算了帐就出了酒馆,走进栅子旁边一个茅房,假装解小便,暗中观察动静。不一会儿,酒店的铺面门关了,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守栅子的两个乡丁比先前更蔫,瞌睡硬是上来了。我拿出一支纸烟,哼着《月亮弯弯照楼台》的小调,偏偏倒倒地走到栅子门前,放下酒罐,找那个站着的乡丁接火。那家伙把手上的烘笼向怀里一拖,偏着脑壳望了我一眼,要理不理地说干啥子的。我说你看老子是干啥子的!一步抢上前去,将枪夺了过来。坐着的那个家伙还在伸懒腰,我用枪对着他,顺手又将那支枪夺过来。我手里拿一支,另一支背在肩上,问他们要死还是要活。这两个草包乖乖地跪在地下,不住地作揖磕头,连声说要活要活。我说要活就不准声张,解下子弹带,回家种田去。边说我边解下两个家伙的绑腿,将他们捆在柱子上,还从他们身上撕下一块布,塞在他们嘴里并说委屈一下,不然你们的长官见了,不杀头也要坐监。随后就提着酒背着枪……”夏林说到得意之处,将左脚从板凳上放下来,嘴里哼着咚咚锵锵的锣鼓点,在屋里走了一圈,然后一个抚掌亮相,摇头晃脑地唱道:“打道回府——”
大家一阵哄笑,都松了口气。有的说老夏这个精灵棍儿脑壳就是灵醒;还有的说这次回去,大哥一定会好好嘉奖。夏林说:“这点本事算啥,不过是跟大哥学来的,顺手牵羊而已。那回我跟着大哥到顺庆,遇到了敌人设在小坝子跟前的一个卡子,足足有一个班的人守着。大哥一边说:老弟,把胆子放雄点,一边装着怕冷的样子把手揣在怀里摸着枪,不惊不诧地走过去。那班长走过来喊检查,话音还没落地就挨了枪子儿。我们两个就把那一班人的枪缴了,还有五百发子弹。后来上山去,把这些枪弹送给小坝子游击队作了见面礼,人家高兴得不得了,就靠着这些广货色起了家,那回劫了敌人一大笔粮款呢。”
夏林像个细娃样,把下巴扬起多高,说得眉飞色舞的。周围听的人一片嘘声,连庙老者也吐着舌头说:“我活了几十年,还没看见过这么胆大的人。”
夏林看看我,洋洋得意地说:“大姐,这下该让我吃个醉吧?”
我沉思了一下,说:“赶快走。”
全屋的人都望着我。唐俊清会意地点了点头说:“对,要走。”
夏林还是不以为然:“不要大惊小怪的,场上的乡丁都走了,剩下几个临时拉来的烟灰儿,谅他也不敢来,就是来了,也不要你们操心,包在我身上。”
我冒了火,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说:“啥子叫大惊小怪?你知道不知道这样打草惊蛇,会弄得因小失大?你只晓得这个场上没有兵,你知不知道离这里只有十五里的肖家场就有杨森的一连人?山上都眼巴巴地等着我们的枪弹,要是出了事,你有几个脑壳?”
夏林不开腔了。唐俊清说声快去准备,大家都回到房里忙着收拾担子,赶紧上路。
我叫唐老六拿出一包米花糖和一斤白糖,送给庙老者,说老人家打扰您了,以后有人来问,不要说我们来过,不然要惹麻烦的。老者忙说不会的不会的,我晓得你们都是好人,菩萨会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说话间,大家已经将夏林带回来的两支长枪和子弹都拆装好了,放在挑子里。我们辞别老者,又开始了紧张的夜行军。
整整两天一夜没好生睡一觉了,人困得不行,没担挑子的人,走路都迷糊糊的。我不断提醒前面的唐老六,不要带迷了路。好在天放晴了,星星繁亮得好,大家硬撑着,都后半夜了,才赶到大溪口我们的联络站唐二嫂家。唐二嫂披衣起来,刚拉开门栓,夏林就一个跄踉扑进去,差点没扑在二嫂子身上,吓得她唉呀一声,待看清了,才上来把我拉住说:“你们终于回来了,今天下午廖大哥带了二十多个人,来打听你们的消息,我家唐老二也跟着,像是很急的样子,连水都没喝一口,又跟大哥走了。”
我听了没说什么,心想出门由路,哪里是想好久回来就好久回来。就指挥大家,把挑子放进屋里,然后和二嫂一起从外面抱了捆干谷草进来,将就铺在地上。几个小伙子话都没说上几句,倒在上面就呼呼地睡着了。这一带已经是我们的地界,可以放放心心睡觉,明天好上山。我拦住要想去烧锅的二嫂,也进屋去睡了。
一觉醒来,已经大天白亮,浑身都在痛,骨头像散了架一般,怎么也爬不起来。我就躺在床上,听着屋外的雀鸟儿,叫得婉悠悠清亮亮的。又躺了一会儿,突然想起唐二嫂说的昨天玉璧带了那么多人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了,会不会真有什么事情?我翻身起来,走到堂屋里。夏林、唐俊清他们在干谷草上睡得正香。唐二嫂已煮好了饭在锅里焖着,坐在灶边帮唐俊清补那件挂破的长衫子,见我要想叫醒大家,连忙站起来说:“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嘛,都到了家门口,何必忙这一下。”
我叹了口气,还是把他们叫醒了。待到把地铺收拾了,唐二嫂给每人舀了碗苞谷糊糊。又从碗柜里拿出两个瓦钵,一钵是油炸海椒凉拌萝卜丝,一钵是华蓥山区的特产血圆子。唐二嫂还拿出一罐酒来说:“打这点酒走了二十里路,本来是留着昨天晚饭给你们解乏的,晚饭没吃成,就早饭吃吧。反正都小晌午了,要不是夏林兄弟又有意见。”
我把酒拿开,说:“二嫂你莫惯坏了他,哪有早上喝酒的道理,一会儿上山他大哥闻到酒气,又要怪我管教不严了。再说若不是他昨晚上贪杯,我们就歇在玉皇观了,害得大家一天跑了一百五十里路。”
夏林叹口气,做出怄气的样子,呼呼地喝着苞谷糊糊。大家又取笑他一阵,三五下就把唐二嫂精心准备的饭菜吃个精光,然后收拾着上路。山坡上做活路的农民,都在歇头道气了。大家一路说笑,走到猫儿寺脚下。猫儿寺里,除了几个年轻的和尚外,空荡荡的。正在疑惑,玉璧带人来了,一见我就气势汹汹地说:“你为啥要误一天的期?”我莫名其妙地说:“啥事这样严重?我们平平安安地把枪弹运回来,不说有功,你还要训人?”
他一听更火了:“你啥子功?误了期,按规定要杀头!”我上下看着他,拖长声音说:“杀——头?谅你还不敢哩。”
“按军纪办事,我就有权杀你的头,你是领导!”这一下可把我惹冒火了:“我是领导,领导又怎么样?总不是神仙吧?我们在路上,命都差点掉了,还白白地给你缴了十多支步枪千多发子弹回来,不过就迟了半天,你就要杀我的头?你杀嘛!我不信,没死在罗泽洲、杨森的刀下,倒死在你廖玉璧的手头!”
唐俊清在一旁,闷了好一阵没开腔,见我们越吵越凶了,才站出来说:“大哥,这确实怪不得大姐。我们在罗锅凼冲敌人的卡子,几乎打了一天一夜,打垮了敌人半个连,昨天又一点没耽误整整赶了一百五十里路,才在唐二嫂家里歇脚。”
我看唐俊清把情况说清楚了,更不服气,转身就走,一抬眼看见夏林和刘铁进来了,我冲着刘铁大声说:“我不同他一起工作,我也不要他领导!”
刘铁说:“玉屏你不知道,这几天敌人又在动了。我们把队伍都从猫儿寺撤了出来。玉璧怕你们在路上遭遇了,昨天专门带人去接应,回来的路上就和敌人打了一仗,唐老二还挂了点彩。他是担心你们啊。”
我愣了愣,可一时还是服不下这口气,就冲着他说:“你为啥不早说?!”
刘铁在旁边哈哈一笑:“这下子话明气散了吧?”
运枪接枪
从重庆运枪回来,就过年了。接连几场大雪,把山路封得死死的,杨森的队伍行动不了,就把兵撤回去了,扬言开了春再来较量。玉璧把队伍集中在半山的猫儿寺,开始休整和练兵,我在山下料理完其它事情,也到了猫儿寺。
华蓥山上,竹林深茂,流水潺潺,历来为佛教圣地,山上山下五个大庙子,平素香火都盛得很。每到寒冬,五个庙子的和尚,除了烤火守庙的都集中到山腰的猫儿寺里,听主持方丈徐老和尚讲经说法,也顺便做些腌咸菜、霉豆腐之类的杂活,等开了春再分散开去,接待香客。这些寺庙不知是哪一朝哪一代修建的,大都依山傍势,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浓荫掩映的高坡上,那些精致的画栋飞檐,为沉寂的山林平添了不少神秘。再看寺内大殿里的菩萨、罗汉,都是鎏金彩塑,一个个面目鲜活,衣裙飞动,在川北一带都极有名气。从南京回来,玉璧就常来走动,和徐老和尚已经熟识;这次带了队伍上山来,借住庙里,大家闲下来常帮着和尚们挑水劈柴,开荒种菜,相处得不错。再说有我们的队伍在,杨森和向屠户也提不了庙产,徐老和尚也就不再说什么。
猫儿寺前面,有个大坝子,天气一放晴,坝子里就满是弄枪舞棍的队员们。有的头上包了白布蓝布撕成的帕子,有的戴着遮阳帽、瓜皮帽、灰军帽,身上还是乡下人穿的短滚衫①、长棉袍,脚上大都是自己用蓑草或棕丝打成的草鞋,也有在脚上包野兔皮的。他们东一堆西一堆,有的在枪筒上吊块石头练瞄准,有的拿着梭镖、木棍在练刺杀,还有一个脱得只穿件单褂子舞三节棍,舞得那铁链挂着短棍上下翻飞,引来一片喝彩之声。我穿过人群,来到坝子的一角,见一群年轻娃娃正在这里打拳翻跟斗,我穿着棉滚衫都还觉得冷,这群年轻人穿着单衣还在冒汗,那头上的戒疤一看就知道是平日里烧香拜佛的那群小和尚。我正看得出神,听得旁边一阵哄笑,原来是夏林正带着几个小和尚,在一块两丈多高的岩石边往下跳,一个小和尚不得要领,跳了个脸扑黄土背朝天,正在一边呸呸地吐着满嘴的泥巴。夏林纵身跳下岩去,将那小和尚扶起来,双手揉着他的光头念叨:“包包散,包包散,回去莫给爹妈看……”
正闹着,金积成过来了。二十七八的人,头发蓄起卡多深,加上满脸黑蓬蓬的络腮胡子,活像个鲁智深。他拉过小和尚对夏林说:“老夏,你这细娃脾气,啥子时候才改得掉哦。法慧,你莫理他,听我说,打仗不光在平坝上打,不会爬山跳岩是要吃亏的。跳岩心头莫慌,身子要缩成一团,腰杆向前倾,脚尖先落地,像我这样,看懂了没有?要是像你先前那样,饿狗抢屎,若是栽到石头上,定是磕掉门牙,脑壳开花。”
金积成的话还没说完,小和尚又爬上岩边,蜷缩着身子一个箭步跳下来,当真稳稳当当地站在我们面前。他高兴得口里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