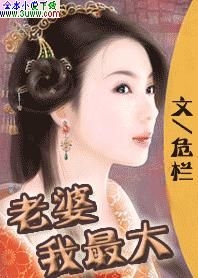双枪老太婆-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个机会,就先把起义的时间定在年关前后。
屈元亮又说:“还有一件事,于公于私都很要紧,得赶紧办了才行。现在看来,我们的时间很紧张,玉屏是不是要出个面,到广安去把你母亲接出来?”
玉璧听了,有些犹豫,说:“夏炯虽然同意收缩我们,但实际上是迫不得已,有戒心的。现在余家场铺了这么大个摊子,下一步的准备工作又很紧张,我们手边正缺人,若是把玉屏也当成人质扣在广安,我们的工作更难开展。”屈元亮说:“如果你不去把母亲接出来,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我在夏炯面前多次说过,你本来无所谓什么党什么派的,就因为母亲被押进了监狱,才憋着一口气和他打。现在看来事情都化解了,你还不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让他生疑心,怀疑你别有所图,六亲不认了?”
清浦也说:“危险是有的,可是玉屏去了,名义上是救你母亲,实际上也是做给夏炯看,你廖玉璧的妻子都去见了他夏炯,还是诚心诚意相信他的。”
元亮看玉璧还是拿不定主意,就说:“这样吧,我去找县长严定礼商量,他是夏炯的老部下,最好连他一起去,还拉上给你作保的那个禁烟处长尚贤生。我们都去给玉屏保镖,还可以再摸一下夏炯的态度。”
玉璧想了又想,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也就同意了,只是叮嘱我,处处要小心。
第二天,由我出面、屈元亮作陪,办了一桌酒席,请来了县长严定礼和尚贤生。屈元亮向严定礼介绍说,这就是廖玉璧的夫人,这几年一直在外面教书,最近专程回来办理她婆母的事情,请严县长从中玉成。
严定礼一听,连忙站了起来,拱着手直说幸会幸会,一边偷偷打量我的眼色。
大家又重新坐下。我说:“严县长,我这几年不在家乡,听说玉璧和政府之间多有些误会。可是我婆婆在家老老实实居家过日子,你们男人之间一旦有什么事就在妻儿老小身上做文章,我们可是冤枉得很咯!”
徐清浦给严定礼送了个鸡头,又给尚贤生送了块鸡腿,坐下来对我说:“大嫂,你莫生气,现在误会都解除了,廖大哥已经都成了我们的副司令了嘛,严县长会给你办理的。”
尚贤生也在一旁凑合,说:“应该放,当然应该放。”严定礼连忙说:“是的是的,我的确催问过这事,不信你问问尚处长,还有清浦!只是嘛,你母亲是夏师长关的,即使军部答应了,他夏炯不同意也不得行。这样吧,我这就给夏师长修书一封,你拿了去找他,跟他求个情如何?”清浦说:“严兄,这恐怕不得行。俗话说打水要到井边,修书不如身到,你老兄最好亲自跑一趟。”
严定礼推脱不过,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我和屈元亮一早到了县衙,只见门口荷枪实弹站了一个排。屈元亮问这是干什么。严定礼斜了我一眼,说:“路上不大清静,带点人方便些。”
屈元亮听了,哈哈一笑,说:“县长真是谨慎,有我这个司令,还有副司令的夫人给你保镖,哪个敢来打扰?这一截截儿路都保不了险,还敢保三县的治安?”
严定礼尴尬地笑笑,和尚贤生一起带了随身的两个兵,与我们一起坐着滑竿上路了。
到了广安,天色已经不早了。严定礼说要到衙门里去歇,我和屈元亮坚持在街上栈房里写了号。第二天一早,他们在一起商量,谁先去见夏炯。严定礼说:“屈司令,你和夏师长有交情,你去一定说得通。”屈元亮说:“不行,抓老太婆是县里出的面,人家廖大嫂先找到县里父母官,你再找上面,才合乎程序。”严定礼还要推辞,说:“夏师长脾气不大好,你们是同学,好说些。”屈元亮说:“我是他同学不假,可你长期作他的部下,若是不信任,咋会派你这个旅长到岳池来兼县太爷……”
我听得不耐烦,正色说道:“严县长,我求你帮个忙这么难么?我是犯人的媳妇都不怕,你是集军政于一身的大员,还怕什么?这样吧,请您和尚处长先走一趟,我坐在这里等你的消息;夏师长若是发了脾气,你们就带着大镣捉我进班房去,我一点也不会怪你们。”
严定礼和尚贤生面面相觑,最后一起去了。我问元亮怎么临阵怯场。他摇摇头说:“玉屏你不晓得,那夏炯脾气古怪,又生性多疑,风平浪静的,说翻脸就翻脸。余家场虽然离广安不近,可是最近闹得太红,要是夏炯听到了什么风声,我不是送进虎口里去了么?等他们去探探口气,也有个商量的余地。”
小晌午时分,严定礼和尚贤生来了,说:“夏师长要见见廖大嫂。”
元亮问:“你们是怎么对他说的?”
尚贤生说:“严县长说,脑壳都进去了,还留个耳朵做什么!人家廖大嫂亲自来了,说明相信你师长,有诚意的。若是我们再不放人,就怕廖玉璧要起二心,还给人家留下话柄。”屈元亮问:“你们还说了什么?”
尚贤生说:“还说你和廖大嫂晚一步才到。”
屈元亮又问:“夏师长怎么说的?”
他俩摇摇头,都说夏炯什么也没说。然后严定礼站起身来,一拱手说:“廖大嫂,我们的忙帮到这个地步,也算尽心了。今晚看你去跟夏师长怎么说,我们公务繁忙,就不奉陪了。”
严定礼他们回岳池了。我们捉摸了半天,也不晓得夏炯安的什么心肠,但是事情到这个份上,总得硬起头皮去见见他。
冬天天气短,吃过晚饭,天就黑尽了。我仍旧教师打扮,和屈元亮一起去见夏炯。我们穿过一个军警林立的大院,来到后厅。元亮叫我站一站,自己先进去了。我四周看看,院子里黑森森的,只有一个哨兵在阶下一动不动地站着,枪刺上的寒光,冷浸浸地逼人。
一会儿,元亮出来,做了个手势,我便跟他进了客厅。夏炯穿着便装,见我进来,用一种犀利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立即换上笑容,客气地让座叫茶。我也笑笑,欠身谢过了茶,就在楠木雕花的太师椅上坐下,没有言语。
屈元亮说了两句寒暄的话,就转入正题,说:“廖大嫂今天是特地为她婆母的事情,来求师长高抬贵手。”夏炯听了一笑,说:“廖大嫂,你别多心,这事都怪我一向太忙,忘了,明天叫他们把老人家送出来就是了。”屈元亮忙说:“就这么件小事,何必等到明天。师长你不知道,她在外面听到很多谣言,有人说她婆母受了刑,打断了腿,有的干脆说来迟了就见不到人了,把廖大嫂急得老远从梁山那边赶回来……”
夏炯听了这些话,又摇头又摆手,说:“那些都是乱说,我夏炯再下得手,也不犯于在一个老太太身上出气。”说着端起茶碗,呷了一口放下,开口说:“廖大嫂……”
我微微欠起身子,说:“夏师长,我姓陈,陈玉屏。”夏炯一听:“哦?哦,陈老师,陈老师!听说陈老师出生于岳池县里的名门世家?”
我笑笑:“不敢说是名门,不过是多了几缕书香。母亲祖上,曾中过晚清的翰林大学士,还放过外省的主考;父亲这边,也还算是小县里的一支望族。”
夏炯一边听我说,一边点头:“我还听人说,陈老师年轻的时候,是这里远近闻名的名媛才女,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倾倒了这一方多少风流人物。”
我又笑笑:“夏师长言过了。其实那都是小城里那些没有见识的人编出来的流言。要说琴棋书画,这琴,我倒不会,棋也下得不好,不过是略知道些‘马走日、相飞田’而已。只是这书画,倒是一直爱好,教书之人生平清淡,全靠它添些情趣。”
夏炯一听,立即来了兴头,站起身来连连说道:“好、好、好!我夏炯虽说是来此地不久,却对陈老师的画早有耳闻,不知道陈老师今天是否肯赏个面子,让我这行伍中人也开开眼界?来人!文房四宝侍候,为陈老师备案!”
不一会儿,画案便收拾出来。我站起身来,款款走上前去,用笔尖蘸蘸砚中的墨汁,问道:“不知道夏师长喜欢什么?”夏炯一挥手:“我们军旅中人,图的就是一份豪气,画个关羽张飞或者梁山水泊里的好汉,看你的方便!”我说:“夏师长,我们当年习画,不过花花草草,哪有闺阁女儿画那些舞枪弄棍的角色?这样吧,我想你们成年在外拼杀,图的还不是个建功立业,封妻荫子!我这就画一幅水墨牡丹,愿您前程似锦。”
说着,便饱蘸墨汁,或酣畅走笔,或细心点染,不一会儿便大功告成。夏炯在一旁看神了,伸手便要来揭画,我轻轻挡住,在画上落了款,放下笔,这才说:“夏师长,忙不得,这宣纸吃墨,得晾一晾才行。”
不知道这夏炯是真的懂点字画,还是在附庸风雅,不绝口地只是称赞我画得好,然后双方重新落座。夏炯话锋一转,突然说道:“听说你们武器很差,子弹也不够?回头我拨点款子去置办一些。现在局势乱得很,装备不齐怎么行。”我欠了欠身,很斯文地说:“夏师长,我这几年都在外面教书,跟廖玉璧连书信都少有往来,这次是为了婆婆的事情才赶回来,办完了就要回去上课。你们公务上的事情,还是直接找屈司令和廖玉璧谈谈才好。”
夏炯看了我一眼,笑着点点头,又扯了些闲话,然后一挥手叫来卫兵:“看我只顾了跟陈老师说话了,正事还没办呢。去,去把廖家老太太请到这里来。”
不一会儿,卫兵带着母亲进来了。老人家一见我,就眼泪汪汪地扑了过来。我连忙起身扶住,说:“妈妈,你快谢谢夏师长。玉璧现在和师长都是一家人了,叫我来接你回家的。”
母亲听了,看看我,又看看夏炯,一脸的疑惑。夏炯在一旁得意地点着头,说:“陈老师你看,老太太不是好好的吗?”我说了些道谢的话,就对屈元亮说:“屈司令,你和师长还有公事,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不料夏炯喊了声:“等等。”我一惊,回过头来,却见他叫过勤务兵,拿了二百块钱来,对我说:“陈老师,今天我们初次见面,多谢你的画了。这钱,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是给老太太补补身体;另外呢,外面的栈房不干净,你们今晚上就在这里安排了吧。”
我一听,松了口气,忙说:“不麻烦了,我们来的时候就把栈房订好了。”说着就扶着母亲出了大门,在街上拐角处叫了两乘滑竿,一口气抬到罗渡溪一个亲戚家住下。
听说我走了之后,夏炯颔首不语,若有所思,最后长叹一声说:“没想到啸聚山林的廖玉璧,娶了这么一位温文尔雅的夫人,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看来此地民间关于她舞枪弄炮的那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了。”
屈元亮后来说起这件事,还直摇头说:“简直是到老虎口边去办交涉。亏得玉屏稳得起,要不然别说是救老太太,只怕是她自己也走不了路的。”
风云突变
从广安救了母亲回来,我又到重庆去运了一趟枪弹,因为路上受了些风寒,一回余家场就病倒了。这天已经是腊月初四,夏炯的一个参谋长结婚,派人送来了请帖。罗平精见了很高兴,说我们该去吃喜酒咯。刁仁义刁大哥在一旁没开腔,玉璧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说:“现在时局这么紧张,最好莫去惹事。我们派人送份厚礼去,就说改天再去祝贺。”初五,我烧得厉害。玉璧很着急,要我到元亮家去养病,说他那里清静些,屈大嫂也好照看一下。我说:“没关系,是太累了,歇两天吃两剂药就好了。”玉璧有些着急地说:“最近有些情况你不晓得,夏炯对我们的意图可能察觉了,昨天请我去吃喜酒说不定就是试探。现在形势这么紧张,我们要提前起事,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能够留在队伍里?”正说着,屈元亮和刁仁义的女人都来了,是听说我病了,专门来照看的。玉璧松了口气,说那也好,转身又忙他的去了。屈大嫂和刁大嫂围着我转来转去,我吃了两副药,又喝了点稀饭,昏沉沉地睡了两天,觉得好多了。
腊月初七的晚上,已经打过了十二点,组织上派段前迪同志送来两份党的重要文件:一份是党中央的政策指示,用白连贰纸石印,字极小,四寸长三寸宽的样子,有六七页;另一份是组织上给玉璧的密令,指示迅速整训好队伍,作好准备,以配合徐向前司令对通、南、巴的进攻。
第二天中午,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玉璧正在拿着昨晚段前迪送来的文件看,忽然一个人气喘喘地跑来说:“城里变了!”
玉璧吃了一惊,手上的文件一下掉在桌子上。
“大哥,真的变了!屈元亮险些被捉,已经跳城墙跑了。他身边的几十个人全被抓了。”
玉璧站起来,两手撑着桌子,望着对面的那张作战地图。这时又跑来一个人说:“大哥,事情不好!徐清浦叫我送信来,昨晚上城里抓了几百人。现在夏炯、罗润德带了四千多人,马上就到。”
“马上集合。”玉璧叫我赶快收拾好东西,又把文件交给我,就出去了。
立刻,军号声哨子声脚步声响成一片。余家场附近的老百姓听说我们要走了,知道大祸要临头了,都惊慌起来,痛哭流涕地跑来送行。玉璧把队伍集合在场口的一个坝子里,站上一个土堆说:“弟兄们!现在敌人已经从城里出发了,想一网把我们打尽。我们目前准备不够,粮弹缺乏,不能同敌人硬拼,要暂时撤回山去,再找机会狠狠地打敌人。弟兄们!赶快回去把住地打扫干净,不要留一点痕迹,以免老百姓遭害……”
弟兄们回到驻地,急忙地收拾行李,打扫院坝,归还借老百姓的东西。忽然,我们的警炮响了三下,顿时枪声四起,敌人已经赶到了。我连忙和屈大嫂、刁大嫂一起,由八个战士护着,随着队伍往外冲,跑着跑着,就和队伍冲散了。我病还没全好,这一跑一急,就直冒虚汗,脸色苍白,靠着屈大嫂只是喘气。刁大嫂急得不得了,带着哭声说:“大姐,我们冲不出去就回去。他杀人总杀不完,男人们做的事和我们女人有什么关系……”
我四处看看,队伍已经走得很远了,枪声也渐渐稀疏,已听得见敌人吆喝老百姓回去的声音,看样子是跑不出去了。我再看看手里的两支枪,子弹也打完了,只好由屈大嫂、刁大嫂扶着,转回去在后街上一家老百姓家里藏了起来。屋里的人都跑光了,一锅饭焖在锅里,发出一阵阵香气。我四下看了看,将我的两支手枪和川陕苏维埃银行发行的二百元纸币,放在床底下的一口烂铁锅里,然后叫屈大嫂和刁大嫂到楼上藏好,自己也找了地方藏了起来。
半下午了,街上只听到一声声零落的枪响,敌兵开始搜索了。一批走了二批又来,在楼上搜出屈大嫂,一脚将她踢下楼来。屈大嫂滚在地上,口里鲜血直流,两个敌兵伸手在她身上乱摸。我实在忍不住了,从灶屋里走出来,大喊一声:“不准动手动脚的!”
那几个敌兵吓了一跳:“你是谁?”
“我是这屋子的主人。”
这时候,几个敌兵不知从哪里拉来一个老太婆,指着我们问她认不认识。
老太婆看看我,又看看屈大嫂,一时愣在那里。这时候,刁大嫂不晓得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一下子跪在老太婆面前大声哭喊:“妈,我是你的媳妇呀,你跟他们说,我是你的媳妇……”
老太婆扶起刁大嫂,点了点头。那些敌兵转过头来,盯住我和屈大嫂,两把雪亮的刺刀顶住了我的胸膛。我用手一挡,手上立即被划开一条口子,鲜血直流。一个敌兵说你还恶呢,抽出通枪的铁条子就向我打来。另一个领头的一挥手,说:“给我检查。”两个兵挽起袖子就要上来。我两手一推,说声莫忙,接着就自己动手,解开棉袄,敞开衣服说:“人人有六亲,个个有姐妹,你们看可以,不能动手脚,我一没有银子钱,二没有违禁物。看嘛,检查什么?”
几个兵你看我我看你的,没有人敢上来。那领头的说:“这两个婆娘恐怕不简单,押到罗旅长那里去!”说着就先出门走了。我掠了下头发,趁机转过头看看刁大嫂,又看看床底下。她憋住哭声,微微地点着头。
我们被押到楼外楼我和玉璧住房兼办公的那间屋,一进门就看见肖心如毕恭毕敬地站在屋里,绑都没绑,当时心里就格噔地一下子。听唐俊清说,这人是队伍到了余家场才参的军,先在机关当通讯员,后来因为他吊儿郎当,表现不大好,就下到支队里去了。看他这样子,莫不是出了问题。
正想着,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转过头来。我一看,那人被大烟熏得黄泡肿脸的,一口黄牙,还安了两颗金牙巴,一对耗子眼睛,总是偏着脑壳偷着望人。
他一见我就死死盯住,问这问那的。一个敌兵说搞不清楚,这个女人歪得很。
肖心如立即弯下腰去,在他耳边说:“旅长,她姓陈,陈玉屏,廖玉璧的女人。”
罗润德贼眉贼眼地向我打量了一番,发出一种很奇怪的笑声说:“啊,是廖大嫂,请坐,请坐。”他又指着屈大嫂问肖心如:“这位是谁?”
“屈元亮的女人。”
“哼,跑了男的,捉到女的。”
一个兵走进来对他说:“旅长,外边营长有要事找你。”罗润德站起来,死死盯住我说:“我马上就来,先把她们带到关帝庙去。”
我们被押到了关帝庙,看见上殿下殿关了三四百人,老头、妇女、年轻人、小孩都坐在地下。外面飘着雪,天气很冷,一个老头子就把殿上的菩萨打来烧火烤,一边打一边骂:“谁说菩萨保佑,放他妈的屁。老子几十年来向它磕头,脑壳都磕肿了,还是穷,还是受气。妈的,我早就想把这个庙烧了,来,打!都打了,我心头才舒服……”
一下子,庙上的“二十八宿”都打烂了。庙内升起了浓浓的烟雾,烟气呛人。那个老头子见我和屈大嫂坐在冰冷的地上,冷得发抖,就招呼我们坐过来点,好烤火。我们坐了过去。老人往火里添着柴棍子,叹口气说:“这年成,太不像话。他妈的,把青杠木当成泡桐树来整。这么好的队伍,说是共老二,是匪,要撵走。他们正派?正派个屌!到处杀人放火,抢女人……”
旁边一个老头也说:“李老头,我一篮子油炸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