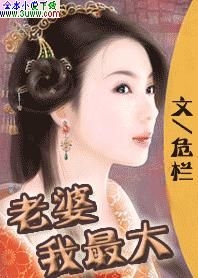双枪老太婆-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徐魏氏给我带来了二十块钱,我拿了十块给袁大娘。她高兴死了,拍着巴掌乐颠颠地说:“天哪,我当了这么多年的管狱婆,还没有人这样大方,给我这么多钱!我今年要过个热闹年了。”
剩下的十块钱,托袁大娘给我们买了些棉衣棉裤进来,好过冬。
没几天,有几个犯人出去了,袁大娘打紧安排,把那几个女犯人都移了出去,小屋里就剩下我和江胡氏,以后就方便多了。
开年的这几天,外面闹得很凶,说是徐向前司令的队伍进了川,打到了通南巴,又说华蓥山也打得厉害,又谣传玉璧要来劫狱……杨森出了布告,不准老百姓放鞭炮,岳池、广安天没黑就关城门,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大年初五的早上,刚吃过早饭,袁大娘说严县长的那个弁兵要会我。
我说:“什么弁兵不弁兵,我认不得,不会。”
袁大娘说:“就是那天送你进监的那个弁兵。”
这一提,倒引起了我的注意,不过转念一想,敌人的鬼名堂多得很,还是不会。
袁大娘出去回话,一会儿又转来对我说:“他说你不会,他也要来看你。”
话还没有说完,走进来一个人,穿一套灰布军装,斜背一把盒子枪,二十多岁的样子,瘦高个,看去很精干,一进来就喊廖大嫂。
我把脸转开,假装没看见。
这弁兵看看我,想说什么又停住了,转身说:“袁大娘,你不出去照看,在这里守着我干什么?”
袁大娘笑了笑,一脸的诡秘,走开了。
他这才移过来,说:“哦,廖大嫂,你还不晓得,我叫李仲生,专门来告诉你:现在华蓥山打了胜仗。廖大哥的队伍打垮了夏炯两团人,师部现在恐慌得很,各个卡子都增派了队伍。徐向前司令又进了川,看样子,四川立刻就要红了……不过,我们这边牺牲的人也不少。”
我还是没理他。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到这里,还没有人来看你吧?不要紧,以后有我照顾。你缺不缺钱用?我这里先拿点去用吧。”说着,随手摸出了十块钱来递给我。我说:“我不要。”
他说:“大嫂,我真的不是外人。”
“不要。”
他慢慢地将钱放进衣袋,又说:“牢房里的伙食不好,我给你在外面包好了送来。”
我不耐烦地回答:“不包。”又把脸掉在一边。他看我仍然冷冰冰的,只好强装笑脸说:“那,我以后再来看你。”
第二天晚饭后,我在走道上放风,李仲生又来了。我一见他,心头烦得要命,掉转头就往回走。他跟着我后面,很着急地说:“大嫂,大嫂,我有话跟你说。”
我进了牢房,背对着他站着:“你有什么话就快说。”他很委屈的样子:“请你不要多心,我真的是上面派来照顾你的。”
上面派来照顾我的,为什么组织上没有和我联系?自己说是就是了?也不看看眼下是什么时候,这样的把戏哄三岁的孩子,还差不多!
我把头一摇,还是不理他。
他紧跟在我的后面,不停地说:“真的,我真是上面派来照顾你的,你以后就会明白。”接着上前一步,轻声地对我说:“屈元亮那天跳城墙逃跑,还是我放的信。年前腊月二十那天,我从严县长那里探听到他们又要想抓徐清浦,就在深夜装着查号去放信,徐大哥当晚就跑了,师部把徐大嫂弄来问了几次,正在四处探听哩。”
李仲生见我仍然不动声色,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大嫂,我知道你不信,这是徐大哥临走时交给我的任务,叫我照顾你,保护你。我的事只有刘政委、廖大哥和徐大哥知道,不信,你找人去问,我不是坏人。”
李仲生停了停,又继续说:“前一向风声很紧,怕背嫌疑,我不敢露面,这两天松了一点,才来看你的。外面传说华蓥山死了好多人,你不要信那些……”
他还要说下去,袁大娘走进来了,说:“李仲生,你也该走了,我们收风了。”
他站起来对袁大娘说:“你不要把廖大嫂当一般犯人待,要好好照顾啊。”
袁大娘说:“我晓得,谁要你多嘴。”
李仲生转身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仍然充满了疑惑,决定找个时间,向陈亮佐和支部汇报一下。第二天吃过早饭,李仲生又来了,同行的还有两个人,说是严定礼要见我。
我看了他们一眼,没说话,洗了脸,梳过头发,又换了件干净衣服,就说走吧。走出监狱,李仲生说:“大嫂,这两位弟兄你恐怕不认识。这是周辉同,这是黄锡成,都是严县长的内弟。”
我瞟了两个人一眼,只见那周辉同团团的脸,矮个子,很年轻,很结实。黄锡成三十岁左右,像农民,也不开腔,只是盯着我。我横了李仲生一眼,心想:你这话问得奇怪,严县长的内弟我怎么认识,又哪里犯得着去认识。这两个人也是,看上去老老实实的,怎么别人的内弟不做,偏去给那个万事莫抓拿的严煤炭作了内弟!
我只顾往前走,周辉同赶上两步说:“不要怕,他们要恐吓你。”李仲生说:“今天县长要在三堂上审问你,还有些师长、旅长,要你交廖大哥。他们现在恐慌得很,杨森要把队伍开去打徐司令,廖大哥又在山上拖住了他们后腿,杨森急得双脚跳。夏炯派队伍去清剿,可是小队伍去,总是有去无回;大队伍去,又找不到影子,他们最怕廖大哥的麻雀战术。夏炯天天找严县长商量,谈来谈去,就在你身上想办法。今天摆的是鸿门宴,装好装坏都有,你要察言观色,随机应变……”
走进三堂,空空荡荡的。李仲生端了一把椅子来给我坐着;周辉同给我倒了一杯茶,就同黄锡成一道进去了。屋内一个人也没有,透过窗花格子,西厢房里传来一阵阵搓麻将和大声武气说话的声音。李仲生想进去报告,我摇摇头,暗示他等一下,听听他们说什么。
“嘿嘿,自古英雄爱美人儿,陈玉屏年轻漂亮,能说会画,我就不相信廖玉璧这样心狠。我们这叫做愿者鱼儿上钩来!”李仲生说:“这是杨森的侄儿杨汉忠的声音,是个师长。”“看牌,二筒!早就听说廖玉璧和陈玉屏感情很好,上钩倒是一定会来上钩的,只是上面催得太急,光是等不行。今天要说动陈玉屏,硬是要她开口动手,把字签了。”李仲生说:“这是张旅长张俊昌,对这个人要小心,一贯笑里藏刀。”
“唉,你们莫把陈玉屏看简单了。我跟她打过交道了,这女人,嘴巴狡得很,搞不好,恐怕还得放长线钓大鱼。”这无可奈何的声气,一听就知道是严定礼。
“严老兄,你这人就是窝囊!一个女人都斗不过,还当什么县太爷。叫他们把刑具都给我搬上来,嘴狡就打板子!”李仲生悄悄说:“这就是向廷瑞向屠户。”
我听了,只觉得自己的牙齿已在格格作响。
我给李仲生使了个眼色,他放重脚步,走进西厢房,大声报告说人已经带来了。
里面嘈杂的声音戛然而止。一个穿呢子衣服的人首先走了出来,眼睛一瞅一瞅的,看那样子就知道是杨汉忠。他走到我面前,对着我的脸看了又看:“你就是陈玉屏?”我一转身,不理他。
他又跟着转过来,死盯着我的脸说:“你老实说,廖玉璧在什么地方?”
我又转过身,还是不理他。李仲生在旁边,瞪了他一眼,他才觉得自己有些失态,没趣地走开了。这时,几个士兵走进来,把老虎凳、羊桷凳、绳子、杠子稀哩哗啦摆了一屋,然后站在一旁。严定礼咳了一声,从屋里走了出来,拖着声问我:“陈玉屏,那个铁窗风味——好不好受啊?”我不开腔。
“你——受够了没有啊?”
我还是不开腔。
他连续问了三四遍,我把头转过来,用背对着他。他叫李仲生端把椅子,坐在我的对面说:“你——怎么不开腔?”“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你的这个问题,军长的意思是要你交人,要你把廖玉璧交出来。不然,就对你不客气!”
我说:“你们把大队人马开去都抓不到,我关在牢房里,有脚无路,到哪里去找人?”
“我把你放出去找。”
“我有病走不动。”
“抬你去找。”
“抬去也找不到,天地这么大,脚长在他身上。”杨汉忠又叼着纸烟走过来说:“陈玉屏,莫装疯,廖玉璧就在华蓥山的毛桠口一带嘛。”
“你既知道,何必来问我。你自己去找就是。”“这个这个……”瞅瞅眼一愣,把大半截纸烟用力往地上一丢,又走开了。
严定礼又过来说:“那你写封信去好不好?”
“我不会写。”
“哼!大学生,教员,还不会写信,真是滑稽。”“滑稽的事还多呢。无凭无据,我犯了什么罪,要弄来关起?”
“算了吧,不谈这些大道理。这还不是为了你好、廖玉璧好、大家好!张旅长你说是不是?”
这个张旅长,显然就是张俊昌了。他手里捏着一串佛珠,笑吟吟地说:“陈玉屏,陈老师,你莫误会嘛,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来跟你商量,想在夏师长面前给你和廖玉璧作保的。只要廖玉璧肯下山,我们保他作旅长。杨师长,夏师长,叶旅长,还有向司令,你们都可以具结是不是?再不信,可以找地方上的士绅和团总出来担保。我们已经把廖玉璧围在华蓥山,打不死,也要饿死冻死。我们不为廖玉璧着想,也要为你着想,年纪轻轻的活守寡,那时候呀,我看你才受不了……”
我站起来,一口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呸!无耻,下流。”“你好大的胆子,敢骂人?拿板子来,打嘴!”向廷瑞捋着袖子,朝着我大喊大叫。
张俊昌连忙上来,一边把向廷瑞往厢房里拉,一边说:“廷瑞兄,息怒,息怒,不要与女流一般见识。”“不行,拿抬盒来,我杀死那么多的共匪都不手软,不信制服不了你陈玉屏!”
“哼,莫说你拿抬盒、杠子,就是杀我的头也就那么回事。你们只有强权,不讲公理,杀死我这样一个无辜的女人,算不了你们有本事。”
“一个无辜的女人?说得好轻巧。哪个女人有你这样泼,有你这样硬?你就是共产党。”
“你们都是当大官的人物,抓不到廖玉璧,就拿我一个女人来出气。我也不可能帮你们去哄他来投你们的圈套。你们要杀就杀,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算了吧,陈玉屏,”向屠户挣脱张俊昌走到我的面前,用手指着我的脸,声音发抖地一字一顿地说:“啥子瓦全不瓦全,我要一刀一刀地剥你的皮,割你的肉,叫野狗扯得你五马分尸!”
向廷瑞暴跳如雷,几个人连忙把他拉进厢房,在里面叽叽咕咕商量什么。李仲生看了我一眼,长长出了口气。一会儿,向廷瑞出来了,狠狠瞪了我一眼,冲出门走了。张俊昌捏着佛珠,踱到我面前,不紧不慢地说:“陈玉屏,听说你也吃斋信佛?好,好,我们志同道合。佛经上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唉,你看你们两口子,鼓动那么多老老实实的老百姓,闹什么革命,讲什么共产主义,死了这么多的人,徒使老百姓遭受劫难之苦……”
我转过身来,看着张俊昌,也不紧不慢地说:“张旅长,张善人,我是女流之辈,不懂什么革命、主义,也听不得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劝世文。我只想问一句,今天这么多师长旅长济济一堂,来审问我,无非说我是共产党,是廖玉璧的同伙。只是不晓得,有没有人出来作证?”严定礼过来,摊开两手说:“嘿嘿,真是奇谈,这还要人作证么?廖玉璧是共产党的头子,这是没话说的了。你呢,是他的女人。他把岳池县都赤化了大半边,未必就没有赤化你?你不是他的同伙是什么?”
我说:“严县长,你老人家好健忘啊。廖玉璧作三防司令,是你出面作的保人,这才几天,我们还在一张桌子上劝酒吃饭,你还同我一起到广安,在夏师长面前帮我说好话,放了我的婆母。难道你就忘了我在外面教书,就那两天才赶回来的吗?我跟廖玉璧早就断了关系,哪件事情给他做过同伙?”我这一说,那些师长旅长都不开腔了,只顾看着严定礼。严定礼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气急败坏地指着我:“陈玉屏,你莫在这里混淆视听,这些都是屈元亮、徐清浦和你勾结起来哄骗本官的,他们都是共产党……”
我站起来,盯着他慢慢地说:“是啊,我听说了。你的三防司令是共产党,副司令也是共产党;老团练局长是共产党,新局长也是共产党,还有底下的脚脚爪爪都是的!那么你呢?你就是好人了?你们合起做了些脱不了手的事情,到头来却在我这个几年没回岳池的女人身上打主意,到底是要哄骗哪个,只有你心头明白……”
严定礼两只眼乱瞟,揣摸周围那些人的脸色,黑黑的一张脸成了猪肝,口里叫着:“押下去,快给我押下去!这个该死的共产婆……”
李仲生押着我往监里走,很高兴的样子。我问他:“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坐在一旁没开腔,那是谁?”李仲生回想了一下,忙说:“那是叶济,叶旅长。”
晚上放风的时候,我悄悄找到刘铁,汇报了今天的事情,特别问到李仲生的情况。刘铁说:“李仲生,他确实是我们的人,是通过徐清浦介绍给严定礼背枪,打入敌人的内部探听敌情的。周辉同、黄锡成是严定礼的舅子,通过李仲生做工作,也是我们的人了。为了不出岔子,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知道,看来他们这次出力不小。”
我说:“这个李仲生也是,也不通过组织上接个线,莽莽撞撞的就跑来找我,我还以为是敌人玩的花招呢。”刘铁说:“我现在是扯红了的,太打眼,他哪里敢通过我。不过你这样谨慎,是对的。”
后来杨森听说了这次审讯的经过,便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她陈玉屏会说,我杨森会关,看我们谁犟得过谁!”于是我就不审不问地被关了起来。
长歌当哭
日子过得很快,论季节已是早春,只是牢房里潮湿,仍旧像冬天。当初为了摆脱罗润德的纠缠,说自己吃斋吃长素,没想到袁大娘当了真,每到初一、十五,还帮我到庙里去烧香还愿。我索性和她一起,半真半假做起了居士,每日里吃些清淡的饭菜,身体居然慢慢地恢复了,只是久没吃肉,心里痨得不行。牢房里的日子太难熬,组织上这一阵子又没有派人来,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只有等袁大娘来了,间或打听一点消息,摆些婆婆妈妈的龙门阵,只觉得自己这辈子,难得这么清闲过。
一天,袁大娘对我说:“外边有人要会你,说是姓唐。”姓唐?是谁呢?是唐俊清吧?不会。唐老六吗?也不会。他们都是战斗中得力的人,听说山上近来打得很凶,不会冒险到这里来。再说组织上指定和我联系的,只有范永安和徐魏氏,哪里又钻出一个姓唐的来了呢?我对袁大娘说:“不要开门,就在牢洞口看看再说。”
袁大娘出去,把牢门关上了。我走到门口,见牢洞口露出了半边脸来,一顶博士帽还把眉毛都遮了。那人大声武气地说:“我是廖大哥派来看你的,他很担心你。”我说:“你是谁?”
他说:“我姓唐,叫唐德彬,是广安的。大哥叫我给你带五十块钱来,请你打个收据。”说着就伸出手,递进一大包东西来,还故意抖得哗哗作响。
我想我们广安是有一个唐德彬,可是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为什么组织上派他来呢?再说,现在山上很困难,怎么会给我这么多钱。我白了他一眼说:“你拿回去,我不要,我已和他断绝关系了。”
那人一听急了,大声说:“那怎么行,廖大哥把任务交给我,我冒了好大的风险才进来的啊。”
他这一喊我更怀疑了,我们的人哪有这样莽撞,在敌人的监狱里大喊大叫的?正要再说点什么,就听见外面有人悄悄地说:“人长得还漂亮。”
我心里全明白了,伸手接过他递进来的那包银元,照着那半边脸揍出去。他一让,银元落到外面的地上,滚得叮叮当当的遍地都是。外面的人直说:“啊啊!好歪好歪。”那个自称是唐德彬的人还不死心,又扑在牢洞口说:“你不收吗,就写个‘退还’,落上你的名字也要得,要不然叫我回去,咋个扯回销?”
我说:“你手头有钱,还怕扯不了回销?你还不走,我就叫人抓你进来关起!”
他还想说什么,江胡氏说:“你真的还不走么?”说着就直起嗓子,直喊袁大娘。
那家伙一听慌了,连忙说:“我走我走。”说着就和外面的两个人一起慌慌张张把钱捡起来跑了。我和江胡氏在屋里,捂着嘴笑得直不起腰来。袁大娘进来,问我们笑啥子,江胡氏说:“袁大娘,你二天没钱花了就找陈先生要,她的名字值钱得很,人家给五十块大洋请她写一个都不得行。”袁大娘听了愈是莫名其妙:“刚才那些人来找你写字了?出了五十块钱?”
我哼了一声,说:“陈玉屏三个字,现在是一文不值,千金难买。老虎凳、大杠子摆在面前都没落笔,这五十块钱算什么!”
第二天上午,陈亮佐对我说,刘铁、金华新他们要解到广安去释放了。我听了觉得奇怪,问:“释放为什么一定要解到广安去?”
亮佐笑笑,神秘地说:“哄你做什么,人家王胡氏把杨森周围的人都说通了。除了王胡氏的女儿去找杨森几个宠爱的老婆说情外,凡是与杨森挨得拢的人,像杨森的老丈人刘老太爷、朱彩壁参谋长、杨汉忠等都去说情。王胡氏光是请客送礼活动费就花了好几百元。听说杨森的口没有先前紧了,说可以考虑考虑,带到广安来审讯后再说。人家王胡氏,今天也要跟着去。”
正说着,有人喊收风了,接着外面一阵嘈杂。我连忙走到牢洞口,见刘铁、金华新他们都出来了,个个都高高兴兴的样子。我不能暴露和他们的关系,不能喊,不能和他们告别,只是噙着眼泪笑。刘铁、金华新走过我的牢洞口,也停下来,笑笑,然后高兴地举起带着镣铐的手,大声说:“再见了弟兄们,多保重……”
监牢里的每个牢洞口都打开了,伸出许多枯瘦的手,向他们挥动。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