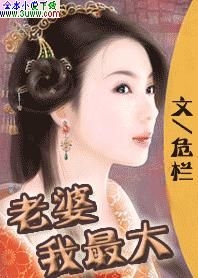双枪老太婆-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管怎么说吧,南京毕竟是我生命中的一块绿洲,我期望一切都从这里重新开始。
我们到南京快一个月了,玉璧和他的两个朋友才到,大家投入全部精力复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每天早晨四点半钟,我们就到东南大学农场里去读书。这个农场在东南大学后门的北极阁,树林茂密,青草绿茵,一条小溪向东流去,溪上一座小桥,桥下的荷花开得很好,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来这里读书的人很多,我和玉璧认识了黄明、何超腾、何幻生等一批好朋友,这年秋天,我们几个一起,都进了南京东南大学。虽然很多人劝我学美术,我自己还是想教书,就考入了教育系;黄明在文学系,超腾在政治经济系,远光和玉洁表姐则转到上海考美专和文科去了。只有玉璧不知道发什么疯,那么好的成绩,却去考了体育系,说是中国人身体太差,学体育把身体练好了,才不受帝国主义的欺侮。进了大学,学习更紧张了。我和玉璧白天各上各的课,晚上要做功课,余下的时间玉璧他们还常关在黄明和超腾房间里开会,忙得连夫妻俩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当时我并不知道黄明是学校共青团的书记,只知道他家里很穷,没钱供他读书,他自己办了个刊物叫做《学诗》,就靠这个刊物卖点钱来维持生活。黄明这个人,平时对人热情谦和,可一旦争论起什么问题来,却是水清见底,不由得你不佩服。见他常和玉璧、超腾一起开会争论,我也想听听,但每次他们都把门拴上。有次不知咋的,一推门就开了,我便走了进去,他们一下子慌了,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书呀本子的。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们在开什么会,他们你看我,我看你的,支支吾吾说是在开读书会。我一听很高兴:“读书会呀?我也来参加一个吧!”说着就坐了下来。他们口里说欢迎欢迎,可是接下来一个个都不开腔。我哑坐了一阵,玉璧不高兴了,瞪了我一眼:“你今天不做饭了?”
我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出去,心里却窝火得要命。看来他们是有事情瞒着我,可是我哪一点又不值得他们信任呢?他们是学校里的进步分子,难道我就不进步吗?我和你廖玉璧自由恋爱,和刘灼山作斗争,这些都不算进步?做饭做饭,你廖玉璧和我结婚,就想找个做饭的?!
寒假,玉璧接到岳池县邮政局长熊尧蓂①的信,回了一趟家,正月间还没回来,一封上海的邮件又到了。我想一定是玉洁表姐和远光大哥来的,就把信拆开,谁知里面是两本《向导》杂志,还附了一封短信,上面写着“简文兄,上次委托之事,不知办妥否……老肖大哥问你好”,剩下的文字,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什么。我心里更奇怪了。这廖简文,是玉璧在家乡的小名,在这里是没人知道的,何况这人的签名我也不认识,还有什么老肖大哥。
没两天,玉璧回来了,我把信交给他,还没说话呢,他就火冒三丈:“你为什么要拆我的信?”
我莫名其妙地说:“信有什么拆不得?又不要你的。”“你今后不要拆了。”
我想起他平时对我东躲西藏的样子,一赌气说:“我偏要拆,拆了又怎样?”
“拆信不道德,你不知道吗?”
“嗬,这就算不道德了?那天下不道德的事情多得很呢!我问你,这信是谁写给你的?老肖大哥又是哪个?你成天什么事情都瞒着我,还说我不道德,我怎么不道德了?!”
这是我们结婚后,玉璧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而且仅仅是因为拆了一封信。我委屈极了,气得哭了一场。半夜里,玉璧把我摇醒了,好言好语劝了半天,最后说:“今后除了家信之外,朋友来的信你不要拆。这里面有些很重要的事情,你又不知道轻重,万一说漏了嘴,泄露出去了不好……”
说了半天,还是不让我知道他的事情。我翻身坐起来,瞪着他说:“你告诉我,你们是不是在搞什么秘密组织?”
玉璧没想到我会这样问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我说:“你不说,我也不追问你,如果真有这事,我要参加。”
玉璧听了说:“也不是不可以,只是有一点,不该问的事情,你不要问;到时候条件够了,我们大家会通知你的。”
说了半天,是嫌我条件不够!我气得眼泪花花的,钻进被窝里不理他了。
玉璧没办法,用指头轻轻地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一九二五年初,我在医院里生下一个女孩,取名宁君,小名江宁。有了孩子,又要读书,由于产后没休息好,我身体不大好,虽然请了保姆,还是觉得应付不过来。多希望玉璧帮我一把,可是他更忙了,常常是半夜三更不回家。不久,上海的日本人枪杀了纱厂工人顾正红,传单很快发到了南京,学校好几天没上课。紧接着,上海学生和群众举行反帝游行,又遭租界巡捕开枪镇压,酿成“五卅”惨案,在全国激起反帝高潮。六月三日,南京东南大学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玉璧、黄明和何超腾都是学联的重要人物,成天忙着组织全校师生上街游行,给罢工的工人募捐。我把才三个月的宁儿交给保姆,揣上几个烧饼,也参加了游行募娟的队伍,和何超腾、何幻生他们编在一个组。南京街头,愤怒的人流从一条街涌向另一条街,口号声惊天动地,不断有商人、工人和市民加入我们的队伍。每到一个街口,我们的同学就要站上长凳去演讲。群众涌进大大小小的商店,把里面的洋货统统拖出来,当众烧掉,整个南京城到处烟雾腾腾,火光冲天。
九日早晨,玉璧很早就起身了,要和超腾、幻生、黄明他们到下关合记洋行开办的工厂里去,那里被日本人看得特别紧,直到现在还没罢工。玉璧叫我这天别去募捐了,中午准备六七个人的午饭。当时街上什么也买不到,我把存着的腊肉和豌豆、海带煮了一大锅,一直等到下午五六点钟,他们几个才回来,都兴奋得不得了。
我见他们满头大汗,连忙倒茶倒洗脸水,这时才发现两个陌生人。一位穿着海苍蓝的洋布长衫,另一位外穿半新旧的毛蓝土布长衫和长裤,里面穿着白土布汗衫,长着麻子的脸上满是汗水珠子。玉璧叫他把衣衫脱了凉快凉快,他直说不热不用脱。幻生说:“你真不愧是个‘处女’,脱了长衫怕人家笑话吗?”他看看我说:“我怕密司陈说我没礼貌。”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黄明说:“我还没给你们介绍呢,你就开起玩笑来了。”我这才知道那位不肯脱长衫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萧楚女①,刚从四川来。我在家乡读过他在《新蜀报》上发表的文章,玉璧对他也是很推崇的,没想到今天竟成了我家的客人。
刚刚才三个月的宁儿,看见屋里这么热闹,也手舞足蹈地在摇床里咯咯地笑。萧楚女走到摇床边把她抱起来,和几位客人嗬嗬地逗着,一边对我说:“密司陈,老廖他们挺厉害啊!我和老刘从上海赶来,还准备帮着组织一些大的行动呢,没想到他们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
我对萧楚女很钦佩,觉得他既风趣又有才华,还是玉璧他们“组织”中的重要人物,说不定那封神秘的信里的那位“老肖大哥”,就是指的他。可是以后就再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很快地就回上海了。
萧楚女他们走了之后,形势很快就紧张起来,学联的成员很多被指名通缉,也有同学失踪,出去就没见回来。眼看风声一天天紧了,玉璧要我着手准备,随时都可能转移。一天,我到邮局去寄一封挂号信,催促家里寄点钱来,柜台里照例递出一张挂号单,我也照例在上面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出门的时候,一个军官盯了我两眼,我也没在意,径直回了家,然后换了件衣服,准备去学校。
刚刚走出大门,一辆汽车就在外面刹住了,一个兵从车上跳下来,对我说:“请陈玉屏小姐上车。”
我心里咯噔一下,反问他:“你找谁?”
“找陈玉屏。”
看样子这个兵还不认识我,我往巷子深处一指:“陈玉屏没住这儿,在那边。”
那个兵一边往里走,一边说:“我们料定他两口子住在这里。”
我赶紧抱出宁儿,七弯八拐穿小巷到了学校。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又来了,可我们已经人去屋空。
这以后,我们连续搬了两次家,都不安全。眼看南京是不能呆了,玉璧说:“组织上让我们先把孩子送回家,然后转移到上海去。”
我问是不是“老肖”的意思,玉璧点点头。
不久,我们回川了。这时,何幻生已经离开南京到了上海。黄明也准备走,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大约是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吧,玉璧在合川县遇见何超腾,才知道幻生已在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了,听说是被“腰斩”的,死得很惨。超腾还告诉玉璧说,几乎在幻生牺牲的同时,萧楚女也在广州被杀害了。超腾自己,后来在万县死于刽子手王芳舟①的屠刀下。
我们在南京的几个好朋友,都这样壮烈地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耕耘播火
八月初,我们离开了南京。
天刚亮,黄明和其他几个同学赶来送行,一起到了下关码头。码头边一大群人围着一男一女两个英国佬,守着一大堆行李发愁。平常这点行李,两毛钱就可以搬上船,可是今天出了五块钱也没有人给他们搬。一个工人抄着手说:“在咱们这群人里啊,你出五百元也买不出个卖国贼。还是去找吴佩孚吧,别说是这两件行李了,就是叫他的那些警察给你们舔屁股,也是没得二话说的!”
两个洋人没办法,只好弯腰合抱起一只大皮箱,很吃力地向囤船走去。女的穿的高跟鞋,踩到刚落过雨的跳板上,脚下一滑,差点摔进水里。岸上的人看了,都拍着手哈哈大笑。
我们上了囤船,看见苍蝇蛆虫爬得满地都是,腥臭味熏得人直是想呕。一打听,原来是英国太古公司的鸡蛋,打算运到上海,可是码头工人不准搬上船,就在这囤船上放了两个月。南京天气这么热,鸡蛋生了蛆,一些人见了直说可惜,我却说了声活该坏了这些臭鸡蛋,也叫洋鬼子晓得咱们中国人是不好惹的。
汽笛拉响了,旅客与送行的人互相道别,码头上一阵呼喊,黄明拿着一张手帕,不断地在空中挥舞。轮船破开浊浪,在江面上行进,风渐渐大了。我把宁儿抱进舱里,哄着她喝了牛奶,又拍着她乖乖地睡着了。待我走出舱来,玉璧还站在船头,一动也不动。
我递了块饼干给他:“呆了?想什么呢?”
“我在想一句话,一句从前我最不愿听的话:百无一用是书生。”
我说:“你今天怎么自卑自弃起来?孙中山先生说,要唤醒民众,没有我们书生,民众怎唤得醒?”
玉璧说:“你又在宣传你的教育救国了。”
我说:“是啊,我的教育救国没有用。中国人体弱多病,挡不住丘八警察们的枪棍,要是个个身强力壮,打不赢也跑得快,看来你的体育救国才有道理!”
玉璧笑笑说:“都没用,我们都没有用。除非手头有了枪,枪杆子才有用。”
一说起枪,我就想起军阀的烂兵和警察,我不喜欢那黑洞洞冷冰冰的东西。望着水天交融的远方,我的心还留在南京,留在中山陵,留在玄武湖,留在东南大学农场的小桥边。此刻,桥下的荷花开得正是时候,那清香越过烟波浩淼的江面,一直飘进了我的心里。
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从此我再也没能回到南京,生活为我铺开了另外一条路。
一个黄昏,轮船驶进了朝天门码头——重庆到了。刚靠拢囤船,一群力夫就涌上来,挤进我们的房间抢着要搬行李。我紧紧地抱着孩子,玉璧忙去招呼,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喊廖大哥。我抬头一看,原来竟是夏林。他头上包一条蓝布帕子,身穿一件没有袖子的麻布汗衫,腰间拴根棕绳子,脚上穿双草鞋。玉璧一把拉住他:“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夏林推开一个力夫,伸手抓住我们的皮箱和铺盖卷:“嗨,一言难尽。走,上岸去再说。”
夏林和玉璧是偏毛根儿朋友,同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小时候一起放牛割草,后来又一起读了几年私塾,像亲兄弟一样。玉璧在南京时常叨念他,今天竟意外会面了,自然是很高兴。我们找到了一家小豆花馆子坐下,玉璧破例地要了一瓶酒。
一阵寒暄之后,夏林叹口气说:“大哥大嫂你们走了两年了,不晓得现在的世道有好乱,捐啊税的多得吓死人,连那些军阀烂兵揩屁股的草纸钱也要我们出。原来来收钱的是保甲长,本乡本土的,说点好话塞几个鸡蛋说不定就过去了,可是后来干脆派个兵把你跟着,还要你管吃管住管草鞋钱。你们晓得我老爹不在了,我老娘靠帮人把我们拉扯大。前些时候我在广安新街帮我的寡妇幺婶跑腿,她老人家喜欢我,要收我做儿子,继承她那点家产。哪晓得夏家祠堂的族长夏三公想占她的家产,就暗地串通人要整我,害得我跑了回来。现在我屋头,糊三张嘴都不得了,哪里还有钱来交捐呀款的。狗东西的王尧!大哥你晓得的,现时是阳合场的团总,又是资马十二场的民兵大队长,他站出来说话了。说老太婆你没得钱,你屋头两个大成人的儿女就不是钱吗?要么你那姑娘跟我做小,你就是我的丈母娘,我王尧一天有吃的你也有吃的;要么你那儿子就去当兵,还可以卖几个钱,等二天当官发财回来讨婆娘,免得遭土匪拉了去,落个人财两空。”夏林接着说:“我老娘听了吓得发抖,一趟子跑了回来,当天晚上就打发我们姐弟两个跑了。我把姐姐送到合川姑妈家,求她看在我死去的老爹份上,给我姐找个厚道点的婆家,我自己就到了重庆,凭着力气挣碗饭吃。”
玉璧听了,好久不开腔,最后说:“不要紧的,你跟我们一道回去,以后自有报仇的机会。”说着他付了饭钱,我们一起到千厮门找了个旅馆住下。
孩子受热,整夜没睡。第二天我们同夏林起了个早,由千厮门码头坐汽划子到合川,然后找了个力夫挑行李,我抱着孩子坐滑竿,走旱路。玉璧腿长,和夏林说说笑笑的,总是走在我们前面,到太平场口,两个人跑得影子都见不到了。场口的栅门边守着两个兵,看见滑竿就喊检查。我说学生回家,有什么好检查的。一个兵眼睛一瞪,说学生是专门捣乱的,回来也要捣乱,更要检查。说着三下五下把我的行李打开,一阵乱翻,我抱着宁儿站在旁边,气得不得了。
挑夫默默为我收拾好行李,招呼着重新上路,一路上只是摇头说:“糟啊,先生娘,这年头儿比从前更糟。上个月英国人在重庆‘开红山’①,打死了四个,伤了一大坝。王芳舟那狗日的烂军阀还护着洋鬼子,重庆的工人和学生闹得好凶,他们自然是恨你们学生的。”
太阳升高了,滑竿又没有凉篷,宁儿受不了热,在我怀里只是哭闹,我们便赶到前面一棵大黄桷树下歇脚。玉璧和夏林早到了,像细娃儿一样在树丫上坐着。我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肚子的委屈。夏林听了连忙问丘八们抢了什么东西没有。玉璧听了只是冷笑:“他们还晓得学生是专门捣乱的么?”
我还在生气,玉璧却朗声说道:“玉屏,你看,快拢家了,青山绿水的,还是家乡好。”
我没好气地说:“好什么!吃的是苞谷红苕,看的是石头泥巴,恶霸当道,土匪成群,我讨厌这个鬼地方。”夏林在一旁,帮着玉璧逗我高兴:“大嫂,你不晓得,这两年有些变化呢!尤其是华蓥山那边,闹热得很。山下的大溪口、枧子沟和毛垭口都开起了炭厂、窑场和碗厂,工人和运力都有好几千;每逢场天,那些炭啊碗啊石灰的都从我们黎梓卫的码头上船,场上会挤得你脚都立不稳哟。还有,华蓥山上也好嘛,去年冬天我约了四个人去打猎,两天工夫就打回三头野猪、一头豹子,差点拖不拢屋。那野鸡野兔多得撞脚,我们理都不爱理得。”
两个抬滑竿的也听出了神,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说:“山上好是好,就是土匪多。”
夏林说:“嗨,要看你撞到的是哪一伙。要是打散了的烂兵或者是那龙背上成了器的浑滩弟兄伙①,当然是说不得了。可是这两年,那些实在是活不出来逼上山去扯棚子的,也不少。说来你们不相信,今年我就碰到过一回,青天白日去卖了柴回来,半路上就遇到土匪。两头路口一卡,就喊过路人站成两边,一边是入了袍哥的①,一边是没有干系的。我不想冒充,心想这几天的辛苦钱还不够他们填牙缝的,搞不好不死也要脱层皮。哪晓得他们挨一挨二地搜身完了,又把我的一块钱还给我,喊我快走,却把那一堆说是入了袍哥的人抢了个精光。那中间有人直叫唤,说咋个不认簧,我们是拿了言语‘善服’,亮了底的哟。那个为首的土匪头子说:你们有‘善服’,走到哪里都好说;他没得这份福气,走到哪里也没办法,就给他留些吧……”
夏林绘声绘色的,也不晓得是真是假,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离开家乡两年了,真可谓江山依旧,人事全非。这两年四川遇上了特大的旱灾,川北一带还遭暴风冰雹,庄稼只有三四成收获,灾民们饿死于路野,甚至有杀子而食的报道,屡屡见诸报端。而此时的四川,军阀们已拥有十七八万条枪,拉起九个大山头,人人都想作四川王,为抢地盘打得昏天黑地。岳池县今天过狼,明天过虎,有个月竟换了好几任“县长”,换朝官儿刮层地皮,别说是县城了,就是许多乡场也被搜刮一空。
许多亲戚朋友来看我们,说起自家的情况,都直摇头。二姐夫说:“有这些军阀在啊,我们老百姓就不得安宁。眼下守着这一方的罗泽洲,更坏。两兄弟都抽大烟,强迫全县人民种鸦片;一年要征几年粮,稀奇古怪的捐啊税的多如牛毛。莫说是没家没业的,就是我们这些小户人家,也实在是交不起。说别人你们不晓得,石垭场的杜海金该有耳闻吧,交不起粮款被先关后吊,现在一家人不敢落屋。”婆婆抱着宁儿,也过来插话说:“晓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