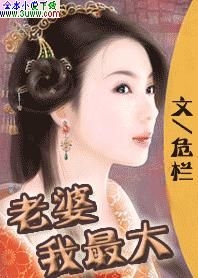双枪老太婆-第4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火把到了跟前,我一下子愣住了:火把下站着刁仁义、陈亮佐、徐清浦,而站在最前面的,竟是李荣华!
我迎上去,握住李大哥的手:“李大哥,你也来了?”大家在火堆边坐下,李大哥说:“我早就该来了。当年我就跟廖大哥说,我要上来,我能和他搭伴。你们这么多人,只有我走路走得过他,一天二百里。我们又谈得拢,打仗的事情也好商量。可是他不同意,他说我有声望,在重庆又有关系,不上来起的作用更大。唉,现在我上来了,可他又不在了。”
我说:“李大哥,你上来,恐怕大嫂她……”
李荣华一摆手:“玉屏,你别大嫂大嫂的,那女人,就像廖大哥常说的,是为了面包问题,她就是为了面包,为了钱才跟我的。她怎么会真心爱我?我为什么又要万事都依着她?我现在只要你,只要你们在座的各位弟兄了解我,只要跟你们大家在一起,我就死而无怨。从现在起,我不住重庆了,回广安老家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你们只管说,我拼了这条命也要帮忙!”
大家一阵掌声。又摆了一阵,眼看快天亮了,仲生、辉同他们和刁大哥说了几句什么,刁大哥迟疑了一下,点点头站起来,把我拉到一边。说:“玉屏,大家有点心事,要我来问问你。”
我说:“刁大哥,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他长叹了一口气:“现在廖大哥不在了,你拖着两个娃娃,人又还年轻,你会不会、会不会……”
我一听,什么都明白了:“你是问我会不会再去嫁人?”刁大哥点点头,支吾说:“玉屏,我们都晓得这是你自己的自由,你一个寡妇家拖着两个娃娃是艰难,可是大家怕万一你要是嫁了个不跟大家一条心的,会不会……就不革命了?你要晓得,我们这里的这么多人,都是把你当成了廖大哥的人,现在也只有你才统得起来,要是你不管了,这支队伍就真的完了哟!”
我转过身来,看着火堆边的同志们,他们一个个都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他们都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和革命联在了一起,和他们的廖大哥连在了一起。如今玉璧不在了,他们就这样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像玉璧一样,带领他们,把这条路走到底。
我能担起这个重任吗?就像刁大哥刚才说的,我,一个才三十五岁的寡妇,还带着两个孩子?我目光扫过他们一个个的脸,扫过这些满是沧桑的脸。这支队伍,这支由我和玉璧,还有刘铁,还有许多人一手拉起来的队伍,这支在华蓥山区转战了十年的队伍,这支面临着绝境的队伍,在等待我的回答。
十年了,该走的走了,该散的也都散了,就只剩下了这些人。可就是他们,在人们心中播下了那么多充满希望的种子,他们相信了共产党,他们愿意跟着我们共产党走,不管路有多么艰难,也不管这些共产党人是男人还是女人。难道像我这样的共产党人,就在这关键时刻不管他们?可这还是有这么多人的一支队伍啊。现在红军北上了,领导们走的走了,牺牲的牺牲了,全川的党组织都破坏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长期带着这么大的一支队伍,往哪里走?
篝火熊熊地燃烧着,火光把每一张脸膛都映得通红,闪烁着一种奇异的光芒。
我又想起了当年我和玉璧在那只小船上说的话。是的,那个时候,我还年轻,我完全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个场面,可是我说了,我要和玉璧一起在这条路上走到底,不管前面有多么艰难。还说了,我们这一代走不完,还有孩子,我们祖祖辈辈走下去,看谁能斗得过谁。如今玉璧他走在了我的前头,难道我就……
我咬咬牙,一转身走到大家面前,说:“刚才刁大哥跟我说,大家愿意推我出来领这个头,好继承玉璧的事业,和大家一起革命到底。我现在给大家表个态,我陈玉屏这辈子,再也不结婚,不嫁人,我要和大家一起,和军阀反动派斗争到底!”
火光中站出了一排排墙一样的身影,爆发出一阵欢呼。因为我要回来,仲生他们把该通知的人员都通知齐了。大家聚在猫儿寺内,开了两天的会,作出了六点决定。
一、提高警惕,加强团结,防止坏人破坏,在山上坚持等候上级指示。
二、不增加枪支,只增加子弹,将枪械修理厂恢复起来,搬上山,没有吃的,也不能变卖枪弹。
三、在山上生产自救,打土豪,开仓济贫,解决生活问题。
四、恢复山边的联络站,打通邻水、大竹的交通要道,帮助附近农民干活,建立广泛的群众关系。
五、派范永安带领一部分人转移到大竹后山,建立根据地,作我们的退路,并把伤病员迁去,彭医生、唐二嫂负责照顾。
六、将山上队伍整编成一个大队,由周辉同、李仲生负责,其他领导人分赴附近各县清理队伍。
最后,决定集中山上全体战斗员,在宝顶寺前的欢喜坪宣誓。
清早起来,我和刁仁义、李荣华、徐清浦一行二十多个人,朝山上走去。天气很好,遍山遍野都是雪,白得晃眼,长长短短的冰棱子挂在树上,透亮。前面开路的同志,把雪都铲干净了,露出了清清爽爽的一条路,远远看去,半山腰里一抹云雾。仲生见了,说今天要出太阳。
走到欢喜坪,太阳果然升上了宝顶寺的塔尖,阳光透过云雾,折射出一道隐隐的彩虹,大家都说这是个好兆头。欢喜坪上燃着许多火堆,周辉同、陈亮佐他们和大家一起,正忙着往火堆里添柴,摆凳子,一见我们来了,都跑过来拉的拉,扯的扯,让我们上前排坐着。陈亮佐说:“几位大哥大姐先到台子上看看,布置得要不要得?”
那面红旗,挂在一根大楠竹上。红旗下是用九张方桌搭成的台子,四棵刚砍来的大柏树,栽在台的四角上,沿台口还立着一排松枝柏杈。台上的方桌上,点了九支大烛,并排放着三支大香,一把雪亮的马刀系着红绸,放在香的旁边。我问陈亮佐:“台口为什么不朝着东方?”
亮佐说:“我们中央红军都到陕北了,当然要朝着西北方。”
我们下了台子,看见唐俊清抱了一大卷白纸上来,压在台口,白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烈士们的名字。我逐一看去,第一张写的玉璧、老刘政委、刘铁、金华新、唐庆余、王道纯、刘昆仑……都是一些主要领导人;其他几张就是夏林、陈伯斋、僧法慧、僧法能、谭之中,杜仁杰、唐老六、何明轩、唐裕德、李老幺、罗平精、徐老和尚……我知道,这些名字都是这几天山上的同志们凑出来的,密密麻麻写满了几张大纸,足足有上千人。他们中间有参加起义的战斗员,有支援我们的群众,有的死在战斗中,有的死在刑场上,有的被沉河,有的被活埋。在他们中间有共产党员,有群众,有世世代代做牛马的长工,有终年辛苦不得一饱的农民,有长年累月在活棺材里的炭厂工人,有在烈日暴雨中拉船的纤夫,有石匠、木匠、泥水匠、染匠、剃头匠,有裁缝和医生,也有博学的知识青年,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有刚出世的婴儿,有卧病不起的老妈妈,有打富济贫的好汉……十年了,十年来,我们牺牲了多少人,这密密麻麻的几张大纸,抵不上敌人杀害华蓥人民的十分之一啊!
我转过身来,向山下望去,开会的同志一个个从云雾中走出来,有的穿着很旧很烂的长袍短褂,还有的披着蓑衣,脚上大都穿的用蒲草打的草鞋,见了我都围着说长说短的。李仲生突然碰碰我,说:“唐二嫂来了。”
我连忙拨开众人迎上去,只见唐二嫂扶着一位老太婆,后面还跟着一些披麻带孝的女人和孩子,向我走来。唐二嫂一见我,就背过脸去,眼泪像珠子一样落下来,浸湿了衣襟。我拉着她冰冷枯瘦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擦擦眼泪,抬起头来,对我吃力地笑笑,把身边的老太婆推到我面前说:“大姐,这是李老七的母亲。”
李老七是夺了一把马刀,砍死了几个敌人之后才被乱刀砍死的。他的妻子、妈妈和妹子躲在粪坑里才逃出来。她们看见我,都哭。她们身后的孤儿寡母们,顿时哭成一片。我说了些安慰的话,让唐二嫂带着她们在前排先坐着。山边的一些老农民和炭厂的工人也来了,五十多岁的张老大走到我面前,很激动地说:“大嫂啊,廖大哥死了,我们大家屋里都死了人,我们都拥护你,你要带着大家报这个仇啊。”
云雾散开了,太阳照到欢喜坪上。陈亮佐招呼大家安静下来,请烈士家属在前面的几排竹凳上坐着,其余的同志站在后面,接着把手一挥:“奏乐!”
由陈仁勇临时组织的一支乐队,把庙里拿来的锣鼓敲了起来,其中还夹着笛子、箫之类的,一群队员朝天鸣放火药枪,枪声在山谷间荡起回声,惊起一群雀鸟,漫天飞舞。过了几分钟,喧闹声平息了,陈亮佐又喊:“全体肃立,向烈士敬礼,向党中央领袖毛泽东、朱德敬礼!向中央苏维埃政府敬礼!向廖大哥、老刘政委和其他死难同志敬礼!”在场的人都默默地站起来,向着西北方恭恭敬敬地鞠躬。
陈亮佐主持会议,说了些鼓舞人心的话,台上台下口号声响成一片。最后他大声说:“同志们,我们的大哥死了,但是大姐回来了,现在我们请她表示态度!”说完就跳下台来。
台下噼噼啪啪地拍起掌来。我走到台口,向烈士名单鞠了一躬,然后站上台去。
台下稀稀落落站着两三百人。我们这支整整战斗了十年,打得罗泽洲、杨森焦头烂额的队伍,如今只剩下这么一点人,其中还包括一大群孤儿寡母。他们衣衫褴褛,面带菜色,他们手中的枪,或许只有一颗打算留给自己的子弹,或许连这最后的一颗子弹也没有。他们都站在这里,像一尊尊雕像,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我的面前。冬天的山风撩起他们草一样的头发,背后是一堆堆燃得很熊的篝火,火光上空弥散开来的烟雾,将他们身后的山景幻化成迷茫的一片。
我站在那里,停了好一阵才大声说:“同志们!我今天在红旗面前,在死难烈士的面前,在你们的面前宣誓:我带着玉璧留下的两个孩子,孤儿寡母也要闹革命,决不半途而废。我请在座的同志们监督我,今后若有三心二意、背叛革命的行为,就有如此香!”说着拿起马刀,把三根大香一下斩成两段,又指着刁仁义、徐清浦、李荣华他们说:“我请几位大哥监视我,今后若有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同志、对不起玉璧、对不起后人的行为,也有如此香。”说着又是一马刀,把剩下的三根半截香,也斩成了两段。
刁仁义挥着手大声说:“加香来加香来!”
陈亮佐抱来一大把香放在桌上。没有风,烛燃得很好。刁大哥向着烈士名单行了三个礼,然后跳上台去,大声说:“……这多年来,廖大哥、老刘政委和其他许多同志同我们在一道,风里来,雨里去,敌人的刺刀架在颈项上,也是英勇不屈。他们是英雄、是好汉,死得光荣,死得值得!他们死了,我们还在,大姐还在。大家都看到了,大姐是女的,还这样和我们一道同甘苦共患难,我刁仁义虽然还不是党员,也决心自始至终革命到底。今天我也在此,对天盟誓:天昏昏,地冥冥,如我今后有反意,做出对不起党、对不起死难的同志、对不起大家的事,也有如此香。”他一马刀斩下去,香头在空中跳得老高。
李荣华脱下身上的毛皮大衣,穿一套呢制服,站在台前很激动地说:“弟兄们,我很惭愧,十年来我只是在后方做些枪弹的供给工作,没有同大家一样,上山打仗。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也要革命,我请在座的各位大哥和全体兄弟们监督我,今后我李荣华若是三心二意,不跟共产党走,死无葬身之地!”
李仲生也代表全体战斗员上台宣誓:“不管天大的困难,我们决不放下枪杆,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保住华蓥山的红旗!……”
接着徐清浦、周辉同、陈亮佐他们都一一跳上台去斩香盟誓。唐二嫂最后跳上台去,举着拳头高喊:“我们要报仇啊!——”
台下一个叫邓大爷的老头子站起来,抖着双手颤巍巍地说:“你们大家都说要报仇,我也要报仇啊,我一家人被杀光了,我活到八十岁也要把仇报了才死!……”
起风了。山风卷动着竹竿上的红旗,满山的松柏竹树,隐雷一样轰鸣。
晴天惊雷
宣誓的第二天,大家就行动起来。范永安和唐二嫂、彭医生一起,带着伤员向大竹后山转移;周辉同和李仲生着手组织山上的同志,一边生产,一边准备对付敌人的“清剿”;我和刁大哥带着一批人,下山到各县清理失散的人和枪。
天气晴和得很,就是冷。我们大家都化了装,谭老五和唐俊清还是扮成鸡鸭贩子;刁大哥穿了件质地很好的马褂,成了一个富富泰泰的地主;陈仁勇成了我的长年,这个角色以往都是夏林扮的,现在交给了陈仁勇。我也扮成了一个男人,上穿一件海苍蓝的长衫,下着一双剪口布鞋,头上戴了一顶灰色的博士帽,还拄了根山藤做成的拐棍。我人矮,又面嫩,他们都说我像刁大哥的大少爷。临行前,李仲生给我们送行,端着鸡血酒的手抖抖索索的,半天才说:“大姐,你要保重,我们没有了大哥,可不能再……”
陈仁勇一看,又想说笑话,可是话到了嘴边,没说出来,只是伸手摸了摸腰上拴的红绫。我们每个人不但都带了枪,还都拴了红绫,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一去生死未卜,开不得玩笑。
我盯住每个人的脸,一字一句地说:“大家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必须遵守一个原则:保存力量,不准蛮干!完了之后,到陈明宣的栈房里等我,他那里是个小场,背静,还没有驻兵。”
大家分散着出发了。我和几个同志到处走了一圈,赶到陈明宣那里,已经是大年三十了。谭老五把我带到陈明宣的栈房里,自己当天就去了铜梁。陈明宣夫妇是自己人,可是不认识我,只是听从谭老五的吩咐,把我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等人。
晚上,陈仁勇回来了,一进屋直喊着饿坏了,跑进厨房端出两大碗稀饭,唏里呼噜就吃了个风卷残云。我坐在旁边等他吃完了才问:“你跑了这么几天,情况怎么样?”陈仁勇说:“杜仁杰牺牲之后,他的那个当乡长的恶霸叔父就倒向了军阀,把肖家场和赛龙场的口子都扎起来,抓了我们近百人,好多人都牺牲了。但是杜仁杰的枪都藏在几个贫农家里,没被发现,他手下剩下的那些人也都潜伏下来了。我悄悄找人把窖里的五十多支枪都起了出来,找了几个可靠的人运到山脚下,仲生派人来接的。肖家场的同志们都要跟我们上山,正发展人呢,说要跟着你去报仇。”“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唉呀大姐,你莫要考我了,跟了你这么多年,这点原则性还不晓得?我跟他们说,坚决不准乱动,等候上级指示。”接着又小声说了一句:“只是不晓得,这上级的指示好久才来得到哦。”
我没理会他后面的那句话,想了想说:“不知道现在罗渡溪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这一片,可是我们苦心经营了十年的根据地啊。”
陈仁勇说:“大姐,要不要我回去看看?”
我叹了口气说:“算了吧,你差点在那里死过一回了,不要去了,犯忌讳。”
陈仁勇嘿嘿一笑,说:“大姐,你还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呢,还迷信!阎王不要命,谁还敢要我的命?留着我跟他们作对呢,这是天意!只是……”
我说:“只是什么?”
他嘿嘿一笑,支支吾吾说:“只是我的枪丢了。”“你怎么会把枪丢了?咋不把脑袋丢了?”
“我没办法,如果当时不丢枪,恐怕只得丢脑袋。大姐你别乱猜,我是看见敌人来了,到处抓人,连那些出门人手腕子上拴的一根避邪的红丝线都说是共产党的暗号,你说容得我的那支枪?我灵机一动,就把枪丢进了水田里,心想等他们走了再去捞。可是没想到那些龟孙子就是不走,我又不敢不走,等到天黑了摸回去,硬是找不到了……”
当时我们有规定,就是丢了脑袋也不能丢枪,这个陈仁勇他……可是又一想,难道真的让他去白白丢了脑袋不成?可是我们的枪,尤其是有子弹的枪这么缺。出来的人,带着枪是很危险,可是少了枪,又怎么行?
陈仁勇一咬牙:“大姐,我保证从他们手里去搞支枪来,将功折罪好不好?”说着一转身,就要往外走。我说:“回来!”接着就从腰上抽出一支枪来,掂了掂,递给他说:“这是李大哥给我的一支枪,这么多年来一直跟着我,从没离过身,你就先拿去用吧,什么时候有枪了,就还给我。”陈仁勇接过去,也掂了掂,一下子插进腰里说:“大姐你放心,要不了十天半月的,就会完璧归赵。”
说完一猫腰出了门,哼着小调走了。
我摇摇头,这个陈仁勇啊,什么都不当回事,既讨人喜欢,又让人担心。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吃过了早饭,陈明宣家的老太太邀约我们上街去转转。我心里有事,不想去,却经不住老太太半拖半劝的,转念一想,老在屋里呆着也闷得慌,再说这个清清静静的小地方,想来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就跟着上了街。
这个场镇,确实小,就一条街,除了两间杂货铺和一家茶馆之外,只有几间破草房。这一向风声紧,有钱的人都躲进碉楼去了,街上除了穿红着绿的娃娃们,就是些妇女和老人,见我都有些诧异。一个戴毡帽的人问一个老头:“张大爷,您看这小伙子是哪里来的?”
那老头含着叶子烟杆骂了一句:“不晓得,倒男不女的样子,活像一个怪物。”
我一听这话不对,连忙回到了陈明宣的栈房里。晚上,和陈明宣一家人吃过年饭,夜已经很深了,我和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想到往年的今天,虽然不一定全家团聚,但总还有个家,总还有个人在;现在玉璧死了,两个孩子托给了别人照管,今后这个家,也就名存实亡了。又想到当年和玉璧恋爱的时候,山盟海誓的,以后这么多年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