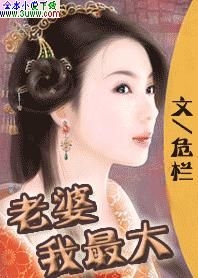双枪老太婆-第6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问她妈妈买糖回来了没有……”
梅侠一听,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哭了一阵才问:“那罗木匠,是谁啊,怎么要到他的坟上去抓土?”我说:“那罗木匠,是一九三二年和我们一起迎红军时候的苏维埃主席,后来被地主吴老肥勾结敌人杀害的。这么多年来,当地的老百姓都说他是好人,在世的时候为穷人分了地主的财物才被杀的,死了之后连坟上的泥土都是救人的神药,一有了什么灾病,就到他的坟上挖泥巴泡水来吃。”大家都不说什么了,好久一青才长叹了一口气说:“要是在城里,只需要一支盘尼希林针,我们的冰华就得救了。好乖的娃娃啊!”
宁君前脚一走,我们后面马上就搬了家,这样即使她出了什么事,也不会找到我们了。宁君去的时候,袁建正在着急,说是这几天解放军都打过白马山,突破乌江天险,连彭水县城都围住了。国民党的达官要人们,跑的跑逃的逃,再不送钱来就要晚了。
是啊,再不送去就晚了。解放军进军的速度,不但敌人没料到,就连我们也没有料到。这几天满城都在嘈,说重庆到成都的公路上,逃窜的兵车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好多兵为了逃命,所有的行李和辎重都丢掉了,只剩下一身单衣;而重庆的白市驿机场则挤满了狼哭鬼嚎的官太太和少爷小姐们,每天挤掉的高跟鞋和丢掉的行李,都要用汽车装……整个重庆的秩序,异常混乱,常有散兵和走投无路的特务们,闯进大商店和有钱的人家,任意以私通或者窝藏共党的罪名绑架人质,动辄就要价成千上万的,弄得重庆街头人心惶惶,关门闭户。
我惦着宁君,正在家里坐立不安,梅侠又一头撞了进来说:“诗伯,不好了,原来曾经告发过我的一个三青团的骨干,今天街上又碰上了,跟了我好几条街才被我甩掉了,这家伙会不会……”
于是我们刚刚搬了两天的家,又得搬了。我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问:“你哥呢?你哥他有两天没回来了吧?不晓得这两天,你嫂子那里怎么样了。”
梅侠一边收拾一边说:“诗伯,我哥哥晓得,人家是两口子啊。你今天又说了一天了,说得人家心里怪紧张的。”
这天晚上,下着小雨,半夜里我被一阵隐隐的雷声惊醒了。我把梅侠推醒说:“这寒冬腊月的,哪里来的雷声啊?”梅侠听了一会儿,突然翻身起来,飞快地打开收音机,我们的电台传来了解放军攻克南川县的消息。梅侠一下子抱住我说:“诗伯,南川解放了,这不是打雷,是炮声,是我们解放军的炮声!南川离重庆,就只有半天的路程,解放眼看就在这两天了!”
天快亮的时候,我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刚一打开门,一青就拉着宁君扑了进来。我一看,连忙扶住说:“怎么了?宁君你怎么回来了?石泉他们的事情……”宁君在床边坐下,抹了一把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说:“妈妈你别说了,没办法了。昨晚上半夜都过了,袁姨爹才回来,说那张法官回话了,他托的人,昨天晚上坐飞机跑了,跑台湾了。还说即使没跑,也来不及了,蒋介石都已经下了密令,执行大屠杀和炸厂计划,所有关押的政治犯,一律就地处决。”
梅侠一听“就地处决”这几个字,啊了一声,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第二天,我们全都进了城。按照宁君打听来的这个消息,到处奔跑,想办法救人救厂。重庆所有的兵工厂、电厂和电台,都是敌人破坏的目标,护厂队的同志已经发现敌人安装炸药的迹象;各个学校的学生,也纷纷组织起来,连夜守护学校。只是救人的事情,跑了两天一点眉目都没有。十一月二十八日早上,一青跑回来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渣滓洞那边,响了一夜的枪声。”
接着,报上登出了消息,敌人终于在逃跑之前,先后杀害了关押在那里的我们的全部同志,还包括从城里罗汉寺、新世界、老街等监狱里押去的政治犯,一共大约七百余人。
走进黎明
重庆解放了。满街都是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游行队伍,满街也游荡着乱七八糟的散兵、流氓、妓女。地下党的同志们,一瞬间就从“地下”转到了“地上”,驻进了和平路国民党的市党部里。我则带着孩子们,到临江门的介中公寓,挂出了“脱险同志联络处”的牌子,并在报上发了消息。一青他们找来了十多个人,有的当勤杂工,有的当采购员,有的到被服厂去找来了衣服,还有的到什么地方去找来了奶粉、鱼肝油之类的补品。梅侠负责接待,亚彬负责警卫,一青负责对外联络,我管内务。我号召大家先凑了点钱,去办伙食,脱险的同志们找到了这里,没饭吃怎么行。
正在铺排,来了一个人。这人隔着桌子,看了我半天,然后才上来说:“你,你还认不认得我啊?”
我一看,是个勾腰驼背的小老头,蓬头垢面的,浑身上下襟襟吊吊,没一块好布。我想,这说不定就是我们脱险的同志了,可是看了老半天,实在是认不出是哪个来。那人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联诗啊,是我,是老肖、肖中鼎啊!你不认得我了,连你都不认得我了。天哪,我活出来了,我又见了天日了,我见到解放了!……”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肖中鼎,没想到我会见到这个样子的肖中鼎!当年在万县的时候,他还是个英英武武的军官,现在竟成了这样一个小老头!我连忙扶他到里面坐下,说:“老肖啊,你真是死里逃生啊,晓不晓得我们还有哪些同志逃出来了?陈作仪?刘石泉?丁鹏武?还有谁逃出来了你快说啊!”肖中鼎一边喝着梅侠为他冲的一杯奶粉,一边喘着气说:“不晓得,不晓得啊。当时耳边全是枪声,好多人就在我的身边,一个个地往下倒,直到我们冲垮了那堵墙,跑出好远了,还有人在倒……我躲在歌乐山上的树林子里,躲了三天三夜啊,听见农民们都在说城里解放了,我才敢出来的。我一步一步,从歌乐山走到了这里,这几十里路,也不晓得是怎么走过来的。逃出来的还有,我们都跑散了。我都找到你们了,他们也一定会找来的……”
梅侠听了她肖伯伯这一说,高兴得不得了,蹦着跳着又出去忙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老肖,你听说了刘石泉的什么消息没有?”
老肖停下来问:“谁?刘石泉?让我想一下。对了,是不是那个关在牢八室里的老刘、刘石泉?不错,这个人不错,有骨气,也有办法,既不吃软也不吃硬,敌人把他吊在梁上打啊,也没说出半个人来。”
我说:“是啊,只要说出半个人来,我们全家就也会进了渣滓洞,也就不知道还有没有今天了。”
老肖听了,看看我,仔细想了一下说:“他好像没有跑出来。大屠杀那天,下着雨,天都黑了,敌人才开始点名,第一批就有他,和蔡梦慰他们十二个人一起的。蔡梦慰你不熟吧?诗人,在牢里还在写诗。”
我说:“后来呢?”
“后来,敌人又点了两批出去,都押到了松林坡。剩下的敌人来不及了,就把我们全部都集中到楼下的牢房里,用机枪和卡宾枪扫,最后特务还进去补了枪。我是在敌人补枪之前,拉了一个死人挡在前面,子弹从我的脖子这里擦过去的。”说着他偏起他的脖子,我看见一条深深的伤痕,都已经结了血痂。
我还要问什么,突然听见外面一阵喧嚷,接着就听见了梅侠的哭声。我奔出去一看,一个矮矮的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正站在梅侠的身边,梅侠拉着他的手,哭得死去活来。一青拦住我说:“诗伯,你让她哭哭也好。作仪牺牲了,她盼了那么久,哭哭心里好受一些。”
我咬咬嘴唇,没说什么,扶着梅侠到里面坐下,那个年轻人也跟了进来。我说:“你和作仪关在一起的?”
他点点头,说他叫刘德彬①,和陈作仪都关在牢六室。我又问:“作仪牺牲了?”
他又点点头说:“他要不是为了掩护我们,也许还不会……敌人扫射的时候,他躲在门后的死角处,没有受伤,可是后来跑的时候被打伤了脚。他一看自己没法跑了,就对我们说我来掩护,你们快跑,说着竟然颤巍巍地站起来,对敌人大声喊你们这些笨蛋,怎么打脚啊?有本事就打我的头,打我的头啊……”
刘德彬说不下去了,好一阵才又说:“要不是作仪他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许就跑不出来了。我这衣服上,还溅着他的血呢!”
我们全家陪着梅侠,到渣滓洞去认领尸体。
重庆的冬天,灰蒙蒙,雾沉沉。梅侠抱着她的儿子,她那个还没见过父亲的儿子,走在我们中间,默默地一声不响。我们在牢八室的牢门前站住了。离牢门不远,就是同志们突围时推倒的那堵有缺口的墙,墙的周围,横七竖八地卧着一些像木头一样的桩子,仔细一看,是些残缺不全的人体,全都烧成了黑糊糊的一团,哪里还分得出是谁,或者不是谁。
刘德彬和几个逃出来的同志围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然后指着其中的一团说:“梅侠,作仪他当时就是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站起来,对着敌人大喊的。也许、也许这一具,就是他,就是你的陈作仪……”
梅侠低头一看,一下子就跪了下去。
我们大家都哭了,哭都哭不出声来。这哪里是人的尸体,这只是一块不过三尺长的焦糊糊的东西。作仪他一个堂堂正正英气勃勃的汉子,一个发誓生要站着生,死也要站着死的人,竟被那浇了汽油的大火,烧成了这个样子……举眼望去,荒草之中,牢门内外,遍地都是尸体,都是烧焦了的、和整座监狱一起、和这个罪恶的世界一起被烧焦了的尸体。什么地方,还袅袅地冒着青烟,带着燃烧后的汽油味和浓浓的血腥在空气中弥漫。苍苍茫茫的歌乐山,默默地站在这个被烈火烧毁的世界背后;在它的后面,还是山,是云遮雾绕的重重叠叠的大山;初升的朝阳透过云雾,把山头涂上了淡淡的血色,像一座座汹涌起伏的血的浪头。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玉璧,还有夏林、金积成、陈仁勇、唐俊清……还有竹栖,还有好多好多的我不认识的人,都踩着这些山峦,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们在我身边不断地倒下,他们用自己的尸骨,为我填起峰谷,托着我和我的孩子们,走到了今天。
我转过身来,前面已经没有山,没有了横亘的遍地尸骨,没有了浓浓的血腥。烟波浩淼的长江上,传来船工们沉沉的号子声,千舟万舸正挂起云帆,直济沧海。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邓照明同志的那句话。刚刚随着解放大军一起回到重庆的邓照明和黄友凡,昨天紧紧地握住我和一青的手,哽咽着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还活着啊!”
是啊,我们还活着,好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我们走到了黎明,我们看到了黎明,而他们,却没有。
不知什么时候,雾散了,柔和的阳光铺洒下来,把一座莽莽苍苍的歌乐山,照得清朗而明丽。
后记
陈联诗是我们敬爱的外婆。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一直都在做种种努力,要把她和外公廖玉璧的那些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是待我们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完成了这部书时,已经是一九九五年的春天。从外婆口述它算起,整整过了三十七年。
此书写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外婆的遭遇,就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了。解放以后,她任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副部长期间,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和一批老党员一起被强行“劝退出党”。曾经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亲人、献出了自己一生心血的外婆,一下子失去了她视若生命的党籍,心中的凄苦可想而知。但她却没有因为这样的不公正而颓丧。从妇联出来之后,外婆被派到小南海金戒山劳动教养院工作。当时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患着肺结核病,为了工作,每天要上下一千多级石梯。一年以后,她当选为人大代表。以后,由当时的西南文联副主席邵子南同志奔走呼吁,外婆被调到了重庆市文联。她又拿起了放下多年的画笔,成为一名专业画家。她以画花鸟和仕女见长,尤其擅长画蝴蝶。她画的“百蝶图”等曾参加全国美展,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文联工作的那些日子里,她还努力学习俄语,想圆当年没实现的赴苏联学习之梦……可是最令她魂索梦绕的,还是那支不屈不挠的革命队伍,还是我们的外公和牺牲在华蓥山下那些可歌可泣的人们。她要把这一切说出来,写出来,这个想法得到了邵子南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组织安排西南师范学院学生杨淑敏、傅德岷记录外婆的口述回忆材料。当时的重庆作协曾打算抓紧将她的回忆录整理出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多年艰苦的斗争生活,摧残了外婆的健康,可为了实现这个心愿,她付出了全部心血。
她晚上想,白天讲,不停地讲了好几个月,直至累得吐血,住进了医院。两个月之后便因淋巴癌与世长辞,享年仅六十岁。这个时候,华蓥山游击队的斗争还没有被承认,外公的“身份”尚未确定,许多游击队员及亲属还在蒙冤受屈,连外婆最疼爱的女婿——我们的父亲,也成了“右派分子”,在她临终前也未能见上一面。外婆拉着我们母亲的手说:“你爸爸的血,还有你那么多叔叔伯伯的血,都白流了吗?”“难道我这个为党奋斗了一辈子的人,到死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还有那部书稿,你们一定得整理出来,要不然就对不起我和你爸爸,也对不起华蓥山的那么多牺牲的人……”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外婆去世后,正当省作协将整理外婆的回忆录列入议事日程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来四川组稿,副社长韦君宜同志决定由该社组织出版。于是由四川省作协的负责人沙汀和艾芜两位老作家主持,将我们的父母借调到作协,整理这部书稿,同时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刚刚“摘帽”的“右派”作家扬禾。这期间,父母还多次去华蓥山地区采访,收集到不少宝贵的文物资料,如当年作为联络暗号的破毡帽和手杖,苏维埃农协会成员的名单……最珍贵的是当年的老交通员魏银安保存的外公一九二五年的照片的底片。他取出来交给母亲时,含着眼泪说:“这是一九二八年陈三姐交给我的,现在物归原主,我也算对得起廖大哥和陈三姐了。”
春去秋来,两年过去了,一九六四年一月《华蓥风暴》初稿终于完成。由父亲和扬禾这两个“摘帽右派”整理一位被“劝退”的“老革命”的回忆录,其心理上的压力可想而知。书稿初成,其魅力吸引了许多人,其中长春电影制片厂和西安电影制片厂都打算将其改编成电影。
正当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准备修改的时候,“四清”来了,接着又是“文化大革命”,一场是非不分、人妖颠倒的风暴,将一切都搅得变了样。加上江青的一句“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不但书出不成了,我们本来就倒霉的这个家,又因为这部书稿雪上加霜。家里多次被抄,材料大多散失。母亲牢记外婆临终前的话,四处奔走告状,最后忧愤成疾,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去世。为此伤透了心的父亲,从此也就断了念头,再也提不起笔来。
时间到了一九九五年,我们也到了当年父母整理书稿的年龄。抢救这部书稿,恢复华蓥山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应有的地位,为外公外婆和千千万万的先烈们树起一座精神丰碑,已经历史性地落在了我们肩上。好在这些年来,许多人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文革”中,茅盾先生曾暗地托人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取出《华蓥风暴》书稿,寄还给我们,并嘱之“幸原稿尚存,当俟诸它日”。“文革”后,岳池县、重庆市、四川省的党史研室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为华蓥山游击队和牺牲的烈士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并为我们的外公补发了烈士证书;同时重庆市委也为外婆公开平反,恢复了名誉。一九八六年,由岳池县政府和重庆市文联出面,在家乡为外公外婆举行了隆重的合墓仪式,前文化部副部长吴雪和许多老同志都专程到会,表示祝贺。
于是我们又拿起了笔。除了全家在十年浩劫中拼死保存下来的原始资料和那套由茅盾先生寄回来的《华蓥风暴》,年逾古稀的父亲还日夜兼程,赶写出十多万字的材料,补充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并指导我们参阅大量的党史、文史资料,完成了这部书稿。书稿带到北京之后,立即受到老作家陈模同志的支持,将它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并从全书的立意、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增删等方面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这部书还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陈浩增同志的重视;副总编郑一奇和责任编辑刘艳丽同志,对该稿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为我们的创作和修改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我们相信这部在许多人的关怀和希望中产生的传记文学作品,对人们了解华蓥山区革命斗争史、了解那个时代革命者的精神风貌,都会大有益处。
鉴于时代久远,事件人物繁杂众多,尽管外婆有着非凡的记忆力,我们也查阅了上千万字的历史资料,还采访过许多人,仍然难免疏漏,此书也一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好在这本书的魅力,在于书中女主人公本身的真实性,在于她的那些传奇感人的故事,在于她那令人钦佩的百折不挠的超越了历史局限的崇高精神,因此我们相信会得到读者谅解的。
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代表九泉之下的外公、外婆和母亲,也代表我们全家,谨向在写作过程中给予大力支持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向曾给予我们指导和关心的茅盾、沙汀、艾芜等文学巨匠;向张秀熟、漆鲁鱼、李维、肖泽宽等老同志;向罗广斌、刘德彬、胡康民、高缨、王志秋、沈伯俊等老作家和专家以及许许多多提供过资料、给予过帮助的同志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林雪 林民涛
1995年7月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