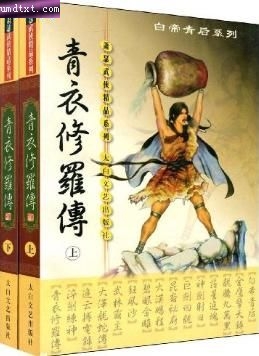老子传-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蜎渊浑身水湿,一张脸青黄得没有人色。他因为刚才连冻带累,已经头晕眼黑,有点迷糊,加上他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不知事情的深浅,生恐挨皮烂着骨头,心中害怕,不敢承认,就说“不承认,给我搜!”
几个家丁不容分说,就往他身上搜了起来。没用几下,就从他的怀里把那只玉蟾蜍给搜了出来。
“好你个顽固的盗贼!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愿意老实承认,来人,给我吊起来!”那壮年家丁这样一说,不知当紧,几个鲁莽的年轻家丁,不容分说地把他背剪子捆着吊到了一棵大树上。惊吓的打击,寒冷的进攻,苦累的折磨,加上又遭捆绑吊悬,如此屈情,此时的他境况可真算是坏,真算是否呀!
“冤枉,我冤枉!我没偷你们的玉蟾蜍,我真没偷你们的玉蟾蜍!我是个读书的,我投师回来,走到这里,掉井里啦。我看见砖头缝里有个白东西,拿起来一看,是个玉石刻的蛤蟆,我以为是原来就有的,不知道是你们放的。我不是偷,真不是偷,我亏,我亏呀!”蜎渊面色苍白,嘴唇青紫,勾着头,挤着眼,忍着胳膊的疼痛和空吊的晕眩,一口气说了这些。
一个嘴巴上蓄着山羊胡子、上了点年纪的家丁,从他的神情和语调之中好象看出了什么问题,转身向拥过来的家丁们一挥手,让他们重新钻进树林,继续搜索。那个主持捆绑蜎渊的壮年家丁,冷笑一声,泛着白眼,一连看了他几下,然后一手按地,斜坐在青草上,得意地看着吊在树杈上的蜎渊,讥刺地说“我说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亏!我真没偷你们的玉蟾蜍!”
“咦!你还嘴硬!顽固蛋!”因痛苦之中的蜎渊说出话来急声急气,一下冲了这壮年家丁的肺筒子,他一恼火,唤过来六个打手,每人撅下一个鸡蛋粗细的小树股,掰去枝叶,照着蜎渊,没头没脑地乱打起来。蜎渊几经折磨,又遭毒打,皮肉受痛,心如刀绞,苦不堪言,真是否到了极点!又是一个万没想到,就在他否到极点的这个时候,居然当真出现了泰来。
“找到了!偷宝盗贼找到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几个家丁拧着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往这里走来。这是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身穿蓝色单袍,下露红色裤脚,除了头上没扎牛角而是蓬松着头发,除了那张三角贼脸,其余装束,甚至身材的粗细长短,都和蜎渊基本相似。“怪不得找不着他,他钻树身子里头啦!”上了点岁数的山羊胡子一边用手拧着盗贼的胳膊,一边喘喘呼呼地告诉尚不知道情况的家丁说。
“叫他说一遍,叫他把偷宝之后藏宝的情况再说一遍!”一个年轻家丁对大家,也是对偷宝的盗贼说。
“我偷了你们家的玉蟾蜍以后,跳墙逃走,见后边有很多人追,跑到这树林边上,吓得不知道咋好,就跳到井里,把玉蟾蜍塞到砖头缝里。我恐怕我藏在井里不保险,就扒着砖头缝子爬上来,钻进树林,藏到了那棵空心的白果树里头了。”偷宝贼顺从地将他刚才说过的一段话背完之后,弯腰仰脸地看了大家一眼就又勾下头去。
“押走!”几个家丁拧着胳膊把盗贼押下去了。
主持吊打蜎渊的壮年家丁,见此情形,面现愧色,霎时脸红多大“吁——站着!”就在这个时候,一辆马车忽地停在他们的面前。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从车上跳下。老人乌衣白裙,头戴紫金发束,脚穿高底缎鞋,一副带着权贵印记的隐者模样。
他就是那壮年家丁刚才提到的那个姬员外。
员外走到众人面前,皱起眉头,用询问的目光看了一下,没有说话。当几个家丁把刚才发生的情况向他学说一遍之后,只见他眉头渐渐展开,脸上慢慢地布上了慈祥的笑容,“这就好,找到了就好。可是,”眉宇间开始换上同情和难过的神色,“可是你们未免太冤枉了这位少年了。你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要吊打人家,事到如今,怎么办,这该怎么办呢?”不知不觉地把责备的目光转到了那个主持吊打蜎渊的壮年家丁身上。
“我,我……”壮年家丁十分害怕,“我给他磕头赔情,姬爷,我给他磕头赔情!”扑腾一声跪到蜎渊面前。一连给他磕了三个头之后,又伏在地上不敢起来。
姬爷并不急于去唤那家丁起来,而是上前一步,和蔼而同情地伸出双手,搀起蜎渊的一只胳膊,“这位少年小哥,我们冤了你,这不是磕一、两个头能补偿得了的。我决定送你一锭金子;再者,你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我要把你带上朝去,请求封你一个官职。来,先把那锭黄金拿来。”转脸抬腕,伸出右手食指往马车上面指了一下。站在车夫身边的那位侍从,急忙跳上马车,从一个蓝色的小包裹里拿出一锭黄金,递向姬爷。
当姬爷接住黄金,转脸递往蜎渊的时候,蜎渊心情十分复杂,说不了心里是甜丝丝的、热呼呼儿的,还是苦不阴的、辣酥酥的,他流着泪大声说“那你……”姬员外一时不知该当如何是好了。
“我不冤枉,你们没冤枉我!别跪我,赶紧起来!”蜎渊迅速把壮年家丁拉起,用手擦着眼泪,言而由衷,十分动心地说“你老师?……噢。……”姬员外凝起眸子,他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了。
“俺老师,是的,他姓李,叫李伯阳,人家也叫他李老聃,他中,他真中!他学问大,又很有德行,这样的人,要是叫他当官,看好不好!”
“李——老——聃,……噢,那好。改日一定前去拜访!”
这位姬爷,轻轻点一下头,慢慢地笑了。
苦县东门里边的大松树底下。李老聃正神采飞扬地讲述着什么,在场的人们听得津津有味。这里不时响起一阵阵发自肺腑的笑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十四岁的蓝衣少年,忽然之间跪在他的面前老聃先生见跪在他面前的这位少年是曾经来过又走了的蜎渊,感到异常惊奇,“咋着回事儿?这是咋着回事儿?”等蜎渊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之后,他心中激动地笑了
论“变”作“囚”
李老聃先生做非正式讲学的第二天上午,天上飘满无数个游动的云朵。太阳在那里钻出钻进,使大地上的绿色时而明亮,时而暗灰,浓浓淡淡,变幻不一。这种变幻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它进行在沃野芳草之上,也进行在麦禾田垅之间,进行在白杨翠柳的树枝梢头,也进行在走在苦县县城东门外边的那个身穿文官官服的骑马之人的衣帽上边。
这个从外地办事归来的官员,分明是一身文官装束,按当时的一般规矩,他这种身份的人,外出行事,应当坐车(带有屋轿的马车,相当于后代官员的坐轿),可他偏偏骑一匹烈性大马,马前有一人牵着缰绳,两边有四人紧紧护卫,后边还跟着一群差役。这些象是抬轿轿夫一般的簇拥者的任务,一方面是替主子助威壮色,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防止万一马惊会把他从马上掀翻。这位老爷之所以故意摆出这种说文官不是文官、说武官不是武官的矛盾姿态,最终目的是为了向百姓们表明他是一个既儒雅又勇烈的文武双全之人,他从这里一露头面不知当紧,那些挑挑担担进城的百姓,在他前边走着的,赶紧飞步进城,象是惊蛇归洞;走在他后边的,赶紧收着脚步,甚至转身返回,不再进城,霎时一条路上人影全无。据说后来的朝代,有的官员,在街上行走,为了让百姓回避,专意让人鸣锣开道,而他,这位老爷,则是不鸣锣道子自开。百姓见了他,象是老鼠见猫一般地自动回避。人说见官三分灾,看来,这里的百姓若要见他尊容,那灾难,不是三分,而是六分了。
此人姓敫名戕,官居苦县县正(后来,秦实行郡县制,称为县令),官小根子粗,是陈国国君一位朋友的小舅子。在他来这任职期间,不仅没给百姓造福,反而带来不少祸害。因前几任县正中,有被土匪绑架的事情发生,他为了保住自己性命的安生,就来了一个明治土匪,暗纵土匪对于这种局面的出现,敫戕的心里不仅不感到责备,反而感到欣慰,因为在对于人生和政治的看法上,他有着自己的与众不同的信条,他认为尽管外表上需要做做样子,但在事实上做个好官不如做个孬官好。他曾对他的夫人说,“说什么君子重于义,说什么小人重于利!这是我一向从内心深处反对的。清官、好官为民掌权,唯他,唯义,唯空,是没有看透红尘的傻子;赃官、孬官才是洞察世事的大刁人。”用他夫人跟他开玩笑时说的话来形容他的人生哲学,那就是除上述特点之外,这敫太爷还有另外两个更加突出的特点他们前牵后拥地走进县城东门。找岔太爷往北瞟了一眼,见那里围坐着一群人,他们在听中间那人讲说着什么。他没留心这群人在干什么,因为他对这些小民不屑一顾。他昂头挺胸,直视前方,不大会儿就走进了城中心那坐坐北朝南的县衙。
县衙正中,有一座风度较为庄严、样式较为讲究的厅堂。此屋,是敫戕处理公事(如问官司等)和外出归来暂时歇脚的地方(后来的朝代把问官司的地方专设一处,称为大堂)。屋内的空间共是三间,东山墙有一个挂着竹帘的小门,从这里可以通往另外一间卧室。正房(明间)的后墙之上,挂着几幅白绢制成的条幅,上面写有周公姬旦的典章摘句。当间靠后的砖墁地上,放置着一张紫木(秋桐)制成的桌案。案后有两把古香古色非乌木大椅。其中的一把椅子上坐着刚刚归来正在小憩的找岔太爷敫戕。这敫戕虽然“鞍马风尘”,刚刚回转,但是仍然威严十足,神采未减。他一手捻着嘴巴儿上那缕小胡,一手端着茶杯出神。由于他那喜强爱胜和好找岔儿的脾气的催动,一个无名的念头在脑际一闪,便转脸向他身边的衙役问起话来“刚才我看见东门里边围坐着一群人,你们知道他们是在干啥子的吗?”
“听说那是众人在听李耳讲学。”一个衙役随口答了一句。
“讲学?啥子讲学?讲啥子学?”
“不清楚。”
“啥子样个李耳?他是否是在妖言惑众?是否是在借机对本县政事进行非议?你们哪个前去看看?”
“我去!”单六从敫太爷的脾性和态色之中看见,一个最适合他大显身手的机会从天而降,功利正在不要任何代价地向他走来,便抢先担当此任,没等主子再次发话,就抽身走了。
敫戕目视单六虎虎地走出屋子,非但没有感到自己不该没事找事,反而自己受了自己的激发,象是突然临阵,精神炯然地振作起来。他睁圆一双斗鸡小眼,把茶杯猛然往桌面上一放,一手按冠,三分“怒气”地揣度起那个“借讲学来议论他的是非”的家伙的言语和举动来。
一刻时辰之后,单六气喘吁吁地跑回来禀报说敫戕一听,火冒三尺,“他妈的,这个姓李的老家伙这样坏!我早料到他是在妖言惑众,借机非议。这个狂徒,太猖狂了,他真是太猖狂了!”他越说越气,手脖子微微哆嗦,脸色开始微微发紫。
这单六实在是个能人,他不仅溜拍有方,而且篡改有术——老聃先生论“变”的原话是李老聃的“恶毒攻击”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敫太爷的愤怒,“小小李耳,竟敢在我管辖的地盘上利用讲学进行攻击,狂妄,狂妄,真真的狂妄!单六,你快带两个衙役一起去把这个老混蛋给我抓来!”
“是!”单六声情激昂,如同一个早想出战的将军突然接到挂帅平贼的圣旨。
……
“杜九,胡择,来,听我跟你们说。……”路上,单六诡秘地眯着眼睛,小声地向两个差役安排一阵,然后昂起头来,得意地看着天边边儿上那变幻不定的游云,“不是吹大气,咱老单不能不算个弄家儿。”……
东门里边的大松树底下。老聃先生真的是在讲“变”。
在对待“变”字这个问题上,李老聃是矛盾的。他是东周王朝的维护者,就其本意来说,他是衷心希望周天子的政权永远永远的不变,永远永远的存在的,尽管这个时期已经明显地出现大分崩、大变化的现实,但是他无论如何也还是不希望天下的事物是在无情地变化着的,虽然如此,可是,因为他那一颗未来哲学家的求真求实之心的支配,他毕竟还是把一个“变”字道出来了,利用讲学方式正正规规地道出来了。不希望变,又主动地道出来变,这就不能不说他的论“变”是有点违心的了。此时,在他做非正式讲学的此时,利用公开场合大讲“变”字,在政治上是要承担几分风险的,因为此时正处“尚恒”的“三代”之末,尽管时局正在剧变,但在理论上和世人的心态上仍然崇尚不变,谁若标立“变”字的新论,他想逃脱“提倡异端邪说”之嫌,那是不大可能的。
老聃先生正在眉飞色舞的讲“变”,忽见三个身穿黑衣的差官从不远的地方向他走来。那个个儿高一些的小头目就是单六。
单六从人圈外边沿着人缝来到圈里,圆圆的脸蛋笑成一朵含着毒汁的黄菊花。他站在人圈当中,两眼眯成一条线,躬身拱手地向李老聃说老聃先生惊讶地站起,稍稍愣了一下,接着,由吃惊变感激,“太爷他,他请我……太爷唤我,怎能称‘请’?如若称‘请’,卑人我,担当不起。……”老聃先生谦恭地拱手应酬着,但是他此时仍然心中无数,不知内里究竟是怎么回事,“太爷他……?”他不敢直接打问,说了个半截话,乐和和地看着单六,把一个看不见的问号礼貌地投到他的脸上。此时,所有在座的人无一不感惊奇。他们互相传递着眼神,但是没有一人敢随便插嘴。
“太爷请你,大概是有个问题须要向你领教。”单六仍然笑眯眯地看着老聃,这笑里没被发现地透露出一种审视和窥测的蛛丝。
“是的,太爷是有个问题须要向你领教。”站在人圈外边的两个差役见老聃先生有点迟疑,特意对单六所说的“领教”帮腔似地进行了附和。
老聃先生心中感到一阵欣喜,但是,对于敫戕,这样一个在心态上惯于压倒一切的精神霸王突然提出要向他领教,他实在是不解其意,“卑人才学浅疏,孤陋寡闻,在太爷面前,永远是个学生,太爷提出要……,不知太爷他是要我……?”
单六发现老聃对“领教”二字产生了疑虑,扬头哈哈大笑一阵,“先生不必过谦,我说的全是真的。太爷本打算亲自前来,用车子来请先生,后因考虑到先生一向谦恭,喜欢简便,就让我们三个先到这里说上一声。先生若愿随我们前去,这就可以使太爷少跑一趟;先生如若不愿随我们前往,待一会儿可能太爷会亲自坐车前来。他确是有事请您领教,至于领教的内容,太爷没说,我们确实不知。一个大夫一级的县正,如此看得起先生,我想先生不会不……哈哈哈哈。”说到此,和和美美地开心笑了。
“好,我这就去,这就去。太爷如此看重卑人,这是卑人的荣幸。”老聃先生由衷感谢地说到这里,转面亲切地向在场的听众环视一下,抱歉地拱手向他们说“先生去吧,快去吧,这个,我们明白。”
“太爷看得起先生,这是先生的光荣,快去,先生快去。”
一个个把欣喜和庆贺的目光投向老聃先生。
“好咧。”老聃拱手和众人告别,跟着三个差官,步履轻缓,恭恭谦谦,乐乐和和地向着县衙的方向走去。……
四人走进县衙厅堂。怒靠在桌案后面的敫太爷一见老聃到来,霍地凛然坐直,习惯地抖起他那慑人的威风。衙役们精神猛震,紧张地列站两边,一个个把严峻的目光投向面前的“敌人”。回看单六,态色大变,和刚才的样子相比,完全判若两人,只见他请功似地向敫戕禀报说情态和氛围的陡然转变,使老聃先生简直无法经受得住,仿佛是居暖室猛进冰窖,正三春忽逢严冬,登山巅突跌深涧,游天国顿入冷宫,他实在感到难以适应了。
不适应也要适应,他头脑一懵,身子摇晃一下,在心里跟自己说敫戕并不答话,威严地坐着,黑红的大脸阴冷得似乎能拧出水来,一双仇视的斗鸡小眼一转不转地盯着老聃先生的鼻尖,凶声凶气地向他发问说“是的,太爷,我叫李耳。”
“‘变是天下规律,受苦受难的平民百姓无法逃脱这个规律,荣华富贵的显官贵人也无法逃脱这个规律’,这话是你说的吗?”
“是的,太爷,这话是我说的。”
敫太爷见老聃毫不含糊地公开认账,立即确认,“这老家伙,利用讲‘变’,发泄不满,指桑骂槐,恶毒攻击,全属真实,半点不假!”一阵由带点虚意而转为全真全实的怒火按捺不住地从心底深处升起,一张本不慈祥的黑红大脸被烧得变青走样,显得更加难看,更加凶狠。“啪!”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案“跪下!快快跪下!”站在两边的衙役们趋炎附势,火上投柴,助风加威。
老聃先生并没感到害怕,反而突然感到十分可气,非常可笑!他想,“这个帽子店的大掌柜好厉害呀!论述一个‘变’字,有这样严重的罪过吗?这位敫县正怎么这样荒唐,这样无礼,这样粗野!他可能是因为十二分的骄傲,十二分的要强,十二分的不把百姓放在眼里,我讲学,没有事先拜访他,触动了他十二分高傲和嫉妒的神经,才引得他如此发火。这姓敫的真不愧是百姓们所议论的找岔太爷,赖太爷,他确实是一个无知无识、妄自尊大的坏家伙!”他越想越气,他不能向这个荒唐而恶劣的小小狗官下跪。他不是没有人格,不是没有尊严,他有声有望,有着不可侵犯的风骨,他曾城头却敌,面临万千兵马而不怯阵,这些,只是因为你姓敫的一班人来得时间浅又自恃高傲,不察下情,才不知道。他满怀恭谦,出山讲学,并无半点恶意,刚一露面,就碰上你找岔太爷,你如此无礼,如此叫人过得不去,怎不叫他深深的愤恨!他按捺不住一腔怒火,他真想发动他那三寸不烂的枪唇剑舌,以极为锋利的言词,狠狠地驳斥他一顿,弄他个马翻人仰,一溜斜歪,叫他招架不住,狼狈不堪!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姓敫的家伙手中有权,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你处置,在他这号人面前,有权就是有理,没权就是没理,当忍不忍,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