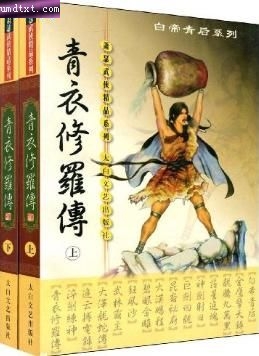老子传-第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出他的家乡住址。玉珍一心要报救命之恩,让叔叔派人给李耳送去金银,哪能想到,李耳不求答谢,又让人把金银全都送回。一切全无结果。不管怎样,玉珍总算是认识了生前有缘的李伯阳。
说起来也怪,红石山李耳救命,不仅没给玉珍带来安慰,反而使她心头之恨又增加了一重。她恨,恨自己命运不好,一个鲜花一般的姑娘,将要葬送给一个会吃会喝的肉蛋,——小生命并不足惜,大不了一死了事,怎奈又欠下了人家的恩情之债,就是死了也是负债而死,死了也不安然!真不如那张二是个掂刀杀人的,要是当时一刀捅死倒也干净!她恨,恨自己当时没有向那救命的李耳说一句感恩的话语!她恨,双重的恨!不,还有一重就在玉珍悲观厌世,大恨小喜、喜也成恨的时候,她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近似怪异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非常的强烈小船悠悠向前。水波漾动,晃碎她们主仆二人倒映在河水里的身影,使之成了一片零落的凄蓝。蹇玉珍哪里管得了这些,此时她整个的身心全被“两边”占据当小船划到离南岸不远处的地方,她不知不觉地停下了手里的桨板,痴痴地进入了麻木状态的呆想。此时正在和她合着拍节同时操作桨板的春香,见小船几乎停滞不进,就探下身子,用力往前划动一下,没想到小船猛一扭头,晃了几晃,玉珍双脚一跐,“扑通”一声栽到河水之中。她心里一凉,头懵多大。她挣扎几下,折身露出头来。大概是由于她身材苗条,体质轻柔,大概是由于她那身丝织的衣服一时没被浸透而有一定浮力的缘故,她竟然没有下沉。
“救人哪!”丫头春香害怕地喊了一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偏僻而幽静的小小渡口,平时很少有人来往,此时天色将晚,外出的人大多数都已归家,哪会有什么人前来相救?春香吓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愣了一下,才想起把小船划到落水者身边,探身去捞。万没想到,因六神无主所致,没等够到玉珍,自己也一头栽到水里。
世间无奇不有,也无巧不有,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前来观赏映趣渡异景的李耳跑了过来。适才地听见有人喊救人,心里猛一惊,接着,飞速地向河边跑。来到近前一看,见两个公子模样的人在水里乱扒乱拱,心中十分着急,打算连衣裳带人地扑过去抢救,猛然想起自己不识水性,扑过去不仅救不出他们,而且自己只能白白地送命,就没有主意了。他心里紧张,一时手足无措。他不能眼看着别人淹死而不顾,而又无能为力。怎么办?见两个落水者离河岸不远,他陡然想起了什么,于是连袜子带鞋地跳到水里,双脚踏着水中的斜坡,一步一步地往里挨。当走到接近落水者的时候,就探着身子伸手去拉他(她)们,又没想到,脚下一滑,腿一打漂,跐到深水之中。他在水里翻转几下,露出头来。一张带有白胡的俊气脸膛,在玉珍面前一闪,使她心中一震,掠过一丝预示着将要得救的喜意,“又是他!那个李耳!”她差点儿没喊叫出来。她猛一扬手,伸把去抓李耳的胳膊,但是她抓了个空,没有抓到。两个人在水里乱扒乱蹬。李耳在水里沉浮了几次,一连喝了两口水,一张脸惨白得没有血色。玉珍在水中连蹬带扒地极力挣扎。这时,春香已经挣扎着接近河岸。小船也已漂到岸边。
春香上岸之后,迅速地将船头那条红色麻绳解下,把一头抛向李耳三个人浑身水湿,活象三只落汤鸡。李耳不知为啥,他刚才怎么指挥得那样得心应手,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急中生智,他心中不由得生出一股庆幸感;玉珍不知为啥,她一个不识水性的人,仅凭极力挣扎,除了被呛得差点儿没有喘不过气来之外,竟然没喝一口水。
李耳看看自己身上的湿衣裳,又看看两个已经脱险的“公子”,对他们说“我们,我们……”春香不知咋说才好,转脸看了玉珍一眼。
玉珍正在心里喊叫“你们不认识我,我叫李耳。看见人落水,谁也不能不救,我可不是为了叫人谢我。你们快去吧,别冻着了,湿衣裳我可以到家再换。”李耳说着,拔腿要走。
玉珍的心里一下子着了慌,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真是慌不择路,她把头一懵,什么也不顾了,干脆皱起眉头,捂着胸口,往地上一蹲,装起“难受”来。
春香心里比谁都明白,她赶紧插嘴说“这位小弟快别说了,”李耳赶忙截断春香的话,“救你家公子要紧,来,咱们快扶他到你们蹇家楼去!”说着和春香一人架起玉珍一只胳膊,往蹇家花园走去。
相亲
一轮明月悬玉盆,盆将银水泼园林,林间花影弄楼影,影影可见室中人。
你走上高高的台阶,即可进入观春赏月楼的第一楼。这里,轻影如梦,灯光似水,画栋雕梁,典雅庄丽。当间靠后墙的地方,放置着一张墨紫色的大条几。条几上站立着尧与舜两位贤明君主的彩色泥塑。塑像前边摆着四盏带有金莲立座的大铜灯。铜灯前边吊着深红色的帷幕。帷幕往两边张开,分别挂在两边明柱上系着的大铜钩上。再靠外,是一张大红方桌。方桌两边放着两把刻有寿桃的红木椅。楼房的东间和西间,分别被两堵雕花乌木隔山隔开。东间里,椅净几明,一张刻着龙凤图案的顶子大床,上面铺盖着崭新的红绫被褥。蹇玉珍从红绫被里露出半个斜躺着的身子。
她,蹇玉珍,一手捂胸,双眉紧蹙,但是,那眉眼和鼻口之间却无法掩饰地露出发自内心深处的喜悦。她真没想到,这次不幸落水竟然因祸得福,竟然奇迹般地又一次遇上了她的空头“丈夫”。事物的发展,从大方面看是有一定路络的,但在某一件具体事情上,它走动的路络,有时真象一个无形的怪脚兽,忽而跳到东,忽而跳到西,实在是奇幻得令人难以捉摸“虽然如此,”李耳说,“我仍然不希望蹇家再去计较仇恨。”玉珍提出要找张二烈报仇,李耳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玉珍想,不报仇也罢,反正见到了恩人,这比什么都好。
她感到由衷的欢喜,而且有些喜出望外,没想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报恩和报仇的心愿一下子都可以了却了。她要报恩,仇可不报,恩不可不报。她要报答两次救命的双恩人。世上有恩人,几乎没有两次救命的双恩人,如若双恩都不去报,到临死的时候是谁也会不无遗恨的。“要抓住这个报答的机会死死的不放!”她狠狠地下着这个决心。李耳是个不要别人向他答谢的人,刚才,他们三个人分两处换过干衣裳之后,她向他说出要报答的话语,李耳又一次抽身要走,多亏玉珍随机应变,说自己又一个劲的心翻难受,心里冷得厉害,希望能快快得到热酒热菜,以压惊驱寒。春香急急下厨,忙乱得不可开交。早已萌发了普救众生思想的李耳当然不会甩袖不问,他急忙帮助春香烧火,拾掇餐具、酒具,力争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将热酒热菜备齐。
“咦,我的娘哎!我自己也感到可笑,我竟然跟我的空头‘丈夫’兜起圈子来啦!”玉珍咬着嘴唇偷笑一阵。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脸色郑重下来春香用托盘端来热酒热菜,一样样小心地摆放在当间的方桌上。虽说称不上丰盛的筵席,但是俱是香美可吃之物。
李耳走进东间对玉珍说玉珍从床上折身坐起,擦下床沿。春香和李耳一起走过来搀起她的胳膊。玉珍心里怦怦地跳着,她努力地掩饰着内心的欢喜和激动,说,“不要搀我,我能走,心里觉得比原来好得多了。”
三个人一起走到当间的方桌旁边。玉珍让春香从东间搬来一把椅子在原有的两把红木椅旁放好,然后请李耳和春香与她一起就座。李耳说自己平时不喝酒,不愿就座。玉珍急忙装作生气的样子说李耳笑了三杯酒下肚,李耳感到浑身热乎乎的,心里很兴奋。玉珍小心地搜寻着投之所好的话题,她说没想到只这一句问话,一下子引起了李耳谈话的兴趣——
“是的”,他说,“天道自然。天道,自然,天道和自然是不可分开的。天道(规律),即是天走的道路;自然,即是和顺而自在。春过去了是夏,夏过去是秋,秋过去是冬。——春天过去之后,为啥要接着夏,再接着秋,再接着冬?那是天要那样走路。天为啥要那样走路?是谁要它那样走路?那是它自己要那样走,别人没对它强求,它自己也没有对自己强求,那是它自自然然的去那样。早晨过去了是上午,上午过去是下午,下午过去是夜晚。——早晨一过去为啥要接着上午,再接着下午,再接着夜晚?那是天要那样走路。天为啥要那样走路?是谁要它那样走路?那是它自己要那样走,别人没对它强求,它自己也没有对自己强求,那是它自自然然的去那样。一个生在天底下的人,少年过去是青年,青年过去是壮年,壮年过去是老年。——少年过去为啥要接着青年,再接着壮年,再接着老年?那是天要那样走路。为啥要那样走路?是谁要它那样走路?那是它自己要那样走,别人没对它强求,它自己也没有对自己强求,那是它自自然然的去那样。天道的精髓是自然,前边的两个字是‘天道’,后边的两个字往往是‘自然’。有时‘天道’后边没写上‘自然’二字,那是‘自然’二字化入了‘天道’二字之中。‘天道’,‘自然’,紧紧相连,合而成为玉珍听他说到这里,平时对他的敬慕之情,此时陡然倍增,”了不起!“她心里说,”好一个有着大智大慧头脑的学问家!他知识是那样的渊博,口齿是那样的如同悬河,他对世理的论述是那样的深入浅出,清楚透彻!他实在是个叫人爱慕的人!这可爱的大学问人,得到他该有多好!……我要得到他!我应该得到他!因为他是……多好啊,我面前坐着的这个可爱的人竟是我的双恩人和指腹丈夫!娘哎,俺心里真说不出是个啥滋味!“她感到他们之间的感情一下子拉得很近很近,理性的爱全部化成了感性的爱,他那俊秀的面孔,他那慈眉善眼,他那笔直的身材,他那高雅的风度,没有一样不叫她感到可爱的。这深深的爱慕之情象一股看不见的巨大拉力,不可抗拒地拉着她向他靠近和倾斜。”李兄,您说的真好,真好!“她笑着,”李兄这样的学问家真叫人敬爱!真的!听说李兄三十多岁了,还没娶妻,不知为啥?……“她发现自己有点忘情,有点说跑了嘴,脸蛋微微一红,赶快勾下头去,努力地掩饰。为了不使对方看出来她在掩饰,她赶紧抬起头来。
李耳并没在意,是的,一个关系象兄弟之间的近乎的男青年(此时他只以为她是个脸蛋漂亮的美男子,他确乎还没发现她是个女的)问一句为啥未曾娶妻,能有什么呢?他很喜欢他的这个漂亮的贤弟,他坦然地笑着,愉快而认真地去回答他(她)直面地向他提出的问题李耳也被他(她)们的情绪感染,心里十分兴奋,高兴得合不拢嘴。
“喝酒,李兄喝酒。”玉珍说,然后转脸看着春香,“斯童,来,咱们陪李兄喝酒。”
“是的,先生,咱们喝酒,别忘了喝酒。”
李耳兴致勃勃,忘了推让,举杯和玉珍、春香一起,高兴地喝下第四杯酒。
“叨菜,先生叨菜。”
“是的,李兄,咱们叨菜。”
李耳也没推让,举筷和玉珍、春香一起叨菜。他感到这菜肴吃起来,淳香而有后味,真是说话投机,人情融洽,饭菜也显得味长。
“男女相亲相爱,合乎天道。李兄说的得合情理。”玉珍放下筷子,心里甜蜜蜜,脸上笑盈盈,动情地看着李耳,“李兄至今还没娶妻,以后,以后还打算不打算……”她不敢往下再问,开始有点心跳脸红。
春香见此情形,赶紧接着话茬说“这个吗,我还没想。”
“想也罢,不想也罢,李兄能不能……能不能在这一点上,说说自己的,想法,看法?”玉珍小心翼翼地追着不放,心里怦怦跳了几下,生怕话题被什么不祥之物弄断。
李耳兴致不减,他坦然地笑笑玉珍对他很同情,眼圈潮湿了,她深情地看着这个坐在她面前的中年人,看着这个一心想着助人和济世而把自己全部忘掉了的人,看着这个她感觉着真是自己的丈夫的可怜的空头丈夫。她真想一下子扑到他怀里,喊一声“亲人!我可怜的亲人!”
“蹇弟,你怎么了,蹇弟?”李耳发现玉珍失神的情态,感到惊异。
“她是同情先生的艰难和孤苦,我家公子是个很有感情的人。”春香赶紧打着圆场说。
玉珍见自己失态,心里一惊,赶快使自己脸上恢复原来的神情,她不自然地笑笑说,“我劝李兄快娶妻室,不要再受‘婚非圣人’的钳制,一个象您这样研究学问的人,很需要有个妻子对你关照,安慰。李兄为钻研学问,只知道一个劲的苦哇苦,累呀累,弄得昏昏沉沉,晃晃糊糊,头重脚轻,神魂颠倒,吃饭是饥一顿,饱一顿,热一顿,冷一顿,有时一坐一天吃不上饭,衣裳脏了没谁洗,烂了没谁补,多苦啊!……当然苦是学业成功之本,可是,李兄若是只要艰苦,不要身体,到头来,学业也会中途失败。李兄钻研学问那样艰辛,谁曾向你说过一句可怜的话?李兄若是有个知冷知热的妻子,端汤送茶,缝补浆洗,对你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使你衣食饱暖,精神得到安慰,一颗心全部投到研究学问中去,该有多好!”
“蹇弟说得对,全是真情实话。”李耳被感动了,眼圈也潮湿了,他感到他面前坐着的这位大家的公子不但是个脸蛋俊俏,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话说得多体贴人,多通情达理呀!他感到他们之间的感情一下子拉得很近很近,他觉得他就是他的亲弟弟。他看着他(她)那白嫩的脸膛,看着他(她)那好看的鼻口和眼眉,仿佛在哪里见过,他承认他(她)的话说得对,但是他真的还没想过他是否要娶妻室,“婚姻之事,我没有想过,唉,算啦,象我这样的年龄,穷家破院,没谁会愿意跟着咱,算啦,算啦。”
“我给你……”玉珍接了个半截话。她本打算说“我给你提一个”,没想到说个“我给你”,就停到那里了。她发现自己的话说得不妥,脸一下子红了,她想掩饰,没想起来该怎样掩饰,因为心里慌乱,脸越红越很,而且连脖子都红了。
“我家公子是说,想给您提个媒。”心里透亮得象盏灯的春香急忙出来圆场,“因为他要提的是,——这个我知道,刚才他给我说了——,因为他要提的是自己的姐姐,所以不好意思。公子,”她又把脸转向玉珍,“有话可以直接说,不要不好意思,先生向来通情达理,说得不妥,他会谅解。”说到这,轻轻站起身来,借个故走出去,然后转身轻轻把门关上。
李耳见此情形,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此时玉珍的心情紧张得怦怦跳个不停,她急忙趁势接着话茬低声而急促地说“这是咋着回事?这,这到底是咋着回事?”李耳感到十分惊异。
又是没有想到,李耳这么一吃惊,反而使玉珍镇静下来。她不打算再瞒着他,她打算把真情实话全部向他吐露,她推心置腹地说玉珍说到这里,李耳仍然十分惊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这不可能,不可能!蹇公子,你疯了吗?疯了吗?”
“我没有疯,李兄,我不是蹇公子,我是蹇玉珍,不信,我让你看。”说着。把外衣脱掉,取下头上的帽子,让头发松开,复原,露出一个春花一般的姑娘,高高的发髻,黑黑的云鬓,紫色中衣,粉红罗裙,和在红石山坡时的装束一模一样。
“是她!是那个被我救过的蹇玉珍!”李耳在心里承认地喊着,而且他也听人说过当年他父亲指腹为婚的事,但是他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只觉着自己是在梦里,是梦里碰上了狐仙神女,“不可能,我不能许亲,我救了你,请你让我走!”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走。玉珍几步踱到门口,拦住李耳的去路,此时她啥也顾不得了,一手抓着他的衣襟,几乎是半跪在地上,“李兄你不能走,你就这样走了,是叫我死是叫我活?俺已经不顾羞耻地说出了这样的话,你叫俺以后咋去见人?你不能不长不短的就这样走,你走了,我没脸再活,我,我,只有碰死!”
李耳愣着了,他象傻子一般地站在地上。此时,正在窗口偷看的春香为玉珍捏着一把汗,她紧张得把心提到喉咙眼儿上。两个巡逻的家丁走过来,问屋里出了什么事。春香赶忙把他们支开。
屋里,李耳开始劝慰玉珍“我不能活,没脸再见人!”
“我走吧,让我走吧,让我走吧!”李耳说着,硬是开开门走出去了。
春香走进屋来,搀着玉珍,走到椅子旁边,让她坐下,自己站在她的面前,不知如何是好,“这咋办?姑娘,这该咋办?”
玉珍的心象是被打碎了一般,头懵多大,她痛苦地勾着头,挤着眼说“姑娘,你不能死!不能死!你的仇还没有报,你不能死!你还年轻,不能就这样去死,你不能死!”春香竭力劝慰着。
玉珍勾着头,挤着眼,一声不响。她开始意识到,她对李耳这样的人,这样许亲,是很大的失策,但是她又不能不这样,因为机会一过,一切落空,她发现她太急了,为了急于跳出火坑,逃个活命,加上她十二分的爱他,她急得爱得着了迷,是有点疯了,傻了,她悔恨,恨自己把事情弄坏了,后悔也晚了,她恨得要死,摔头找不着硬地,她无处发泄,恨不得掂刀杀人!她没有啥话可说了,啥也不打算再说了。她沉默着。没想到她忽然地抬起头来!她想起了什么,忽然想起了什么,她大声的说
报仇
“不让报恩,我们报仇”,蹇玉珍这句话里包含着对张二烈的仇恨,也包含着对恩人李耳报复性的发泄。
“李耳不让我们找张二烈算账,他是恨他恨不起来,好吧!这回我要叫他……!”她对春香小声安排一阵,然后抬起头来,“你知道曲仁里家后那所山上留门的小屋,那张二烈,他娘刚殡埋出去,他还在家里没走。你就说‘戴家庄你表叔戴金山请你到观春赏月楼有要事相商’,要想一切办法把他弄来!”
“他在红石山坡见过你,他来了以后,要是看出来是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