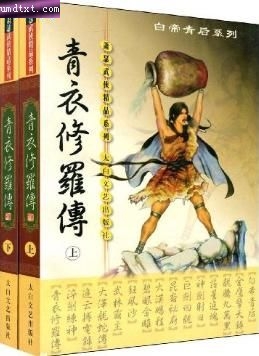江青传-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唐纳写了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聂耳与他合作,配上了乐曲,使这两首歌广为流传。现摘录《塞外村女》片段,以飨读者:
暮鸦飞过天色灰,
老爹上城卖粉归,
鹅毛雪片片朝身落,
破棉袄渍透穷人泪。
扑面寒风阵阵吹,
几行飞雁几行泪,
指望着今年收成好,
够缴还租未免祸灾。
唐纳长得一表人材,有如“奶油小生”,居然被电通影业公司的导演袁牧之所看中,要他当演员!
那时候,袁牧之正在自编自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找不到合意的男主角。在袁牧之心目中,男主人公李梦华是一个贫穷潦倒而又富于痴情的知识分子;他一见到眉目清秀的唐纳,仿佛是扮演李梦华的“本色演员”。虽说唐纳从未上过银幕,而这一回要领衔主演,他又居然一口应承下来。
于是,一九三五年,唐纳从“艺华”调入“电通”,当起演员,同时主编《电影画报》。
多才多艺的唐纳,演戏也演得不错。在影片中,他神魂颠倒地追求由张新珠饰的女主角张小云。特别是在演出失恋时饮毒酒自杀,简直演得活龙活现!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的《影与戏》,这么形容唐纳:
“提起唐纳,大凡是略微关心一些影坛的人,谁都晓得他是一位很活跃的影评人。他,可以说一个身子,半个站在电影圈里,半个站在电影圈外。”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时报》,曾以《青年作家酷嗜电影》为题,简略地介绍过唐纳身世:
“唐纳现年二十二岁(指虚岁——引者注)。原籍苏州。曾肄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自幼即嗜电影,且爱好文艺,笔名‘罗平’。为文简洁流畅,颇得一般人之好评。当在圣约翰大学二年级时,即大负声望。影界友好多怂恿其实行入电影界工作,唐亦不能自持,乃于前年秋季入艺华公司担任编剧事务。去岁经袁牧之介绍入电通公司,主演该公司声片(即有声影片——引者注)《都市风光》。初上银幕,即大露头角(时其爱人蓝苹亦在该片中充当重要角色)。唐除在该公司担任演员外,并主编电影画报,工作颇称努力。惟任职不久,电通公司即告歇业。本年六月一日改入明星公司,仍担任编剧职务。”
唐纳颇“帅”,一表人材,又多才多艺,时而影评,时而编剧,时而演员,何况在圣约翰大学学的是英语,能著能译,是一位“评、编、演、著、译”的全才。
不过,唐纳当时最有影响的是影评。他是《晨报》影评专栏的主要评论家,与《申报》的石凌鹤旗鼓相当,人称“影评二雄”。
除了以《晨报》为“据点”之外,唐纳还涉足《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时报》等影评专栏。人们用这样的话,形容唐纳的评论对于影片、对于演员的影响:“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如斧铖。”
唐纳的为人单纯、热忱,但性格有点如同吴语一般软绵绵的。他思想倾向进步,活动于左翼电影界人士圈子之中。
从三十年代迄今,人们向来以为唐纳即马骥良,马骥良即唐纳。
其实不然!唐纳是两人合用的笔名。另一人是谁?
当我得悉唐纳挚友夏其言在沪工作,便于一九八六年八月四日前往拜访。
炎夏酷暑,柏油马路都有点酥软了,我叩响一幢小楼的房门。我以为,倘若夏老不去黄山、青岛避暑的话,定然在家午睡。
出乎我的意料,夏师母告知,夏老上班去了!他和唐纳同岁,也属虎,已是七十有二了,照样天天去报社上班,工作日程表排得满满的。
几次打电话跟夏者约时间,他不是接待外宾,便忙于业务。总算他有了空余,与他得以长谈。
除了听觉差一点之外,夏老身体甚健,记忆清晰。他谈及了世人莫知的奥秘;唐纳乃马骥良与余其越合用的笔名!
余其越,我从未听说过的陌生姓名,究竟何许人也?
夏其言如此深知唐纳身世,说来纯属偶然:夏其言高中毕业之后,正值刘鸿生开办的中国企业银行招收练习生。夏其言考上了。跟他一起考上的,有个青年名叫马骥善,意气相投,遂结为好友。
马骥善之兄,即马骥良。马骥良常到银行宿舍看望弟弟,跟夏其言结识了。夏其言也随着马骥善喊马骥良为“大哥”,虽然他跟马骥良同龄。
那时候,马骥良参加了“C。Y”,亦即共青团。夏其言呢?正追求进步,悄悄地在读马列著作。正因为这样,他跟马骥良相见恨晚,非常投机。
一天,马骥良神秘地对夏其言说道:“我有一个朋友,很有学问,可以教你懂得许多革命道理。不过……”
说到这里,戛然而止,马骥良用双眼看着夏其言。
夏其言立即明白他的意思,说道:“我不怕风险。”
马骥良这才轻声地说:“他没地方落脚,你敢不敢收容他?”
夏其言一口答应下来。
过了几天,上海长乐路抬安坊,多了一位青年“房客”。
正巧,这位青年也属虎,跟马骥良、夏其言同庚。
怡安坊离“十三层楼”不过飓尺之遥。“十三层楼”,即如今的锦江饭店。夏其言的父亲,在那里掌厨。他家住石库门房子,独门进出。
那青年“房客”跟夏其言住一间小屋。此人足不出户,终日闭门幽居,邻居从不知马家有“房客”。所谓“房客”,只不过夏其言对父母的遮掩之词罢了。
“房客”叫小琳,常用的笔名为史枚,真名余其越。此人跟马骥良同乡、同学,总角之交。(总角之交,即少年朋友。总角,少时所梳之小髻也。)
余其越乃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杨树浦活动时,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往苏州反省院。
那时,苏州反省院有所谓“假释放”制度:如果有两家铺保,“犯人”可以“假释放”两个月,届时自回反省院,仍旧关押。“假释放”的本意,是让“犯人”体验一下“自由”是何等舒坦,以促使“犯人”早日“反省”。
然而,余其越却趁“假释放”之际出逃了!
余其越请马骥良帮忙。神不知,鬼不晓,他隐居在夏其言家里。国民党警察局急得跳脚,也不会查到夏家,因为在此之前,余其越跟夏家毫无瓜葛。
余其越擅长写作。在隐居中,写了不少文章,署名唐纳,由马骥良送出去发表。马骥良自己写的文章,也署名唐纳。于是,唐纳成了余其越和马骥良合用的笔名。
马骥良本来以“罗平”为笔名。常用“唐纳”之后,渐渐地,人们以“唐纳”相称;以致后来变成“唐纳=马骥良”。
余其越跟夏其言朝夕相处,教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引导他走上革命之路。在余其越的影响下,夏其言于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余其越隐居夏家,唯一的常客是马骥良,以下该称之为“唐纳”了,以适合广大读者的习惯。
至于余其越,以下该改称为“史枚”,因为他的真名已被伪警察局记录在案,他改名史枚。
当唐纳跟蓝苹相爱之后,蓝苹也成为夏家的常客。
唐纳、蓝苹、史枚、夏其言是同龄人,然而,不约而同以史枚为长。因为他是“C。P”(共产党),而且学者风度,老成持重,唐纳、夏其言尊敬他理所当然,蓝苹在他面前也颇恭敬。就连她跟唐纳吵了架,也常常要到信安坊来,在史枚面前告状——此是后话……
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
追溯起来,在蓝苹主演话剧《娜拉》时,唐纳便和她相识。那时,唐纳在业余剧人协会负责宣传工作。不过,他们只是相识而已。
关于他们如何由相识发展到相爱,后来客居法国巴黎的唐纳,曾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毛泽东传》作者R?特里尔说及。
特里尔如此记述:
他说,他迷上蓝苹,是从金城大戏院看她主演《娜拉》时开始。他发现了她坚强的、激动的、性感的魁力。和她会面,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闷热的晚上,唐纳步行到电通影业公司去,他兼任公司出版的杂志(引者注:即《电通画报》)编辑。霞飞路(引者注:今淮海中路)上挤满了散步者、卖吃食者、互相搂抱的情侣、叫花子等各色各样的人。在那里,唐纳看见蓝苹在霓虹灯下,穿着蓝色绸旗袍,板着刘海头发,拖着改组派的脚步走过来。这是她儿童时期缠足的遗产,是无可救药的。
蓝苹认出他是唐纳,唐纳也知道她是何人。两人都踌躇了一下。唐纳裂嘴微笑,好像一只活泼的猫,蓝苹伸出了她的手。唐纳说,他非常钦佩她演的娜拉;蓝苹说,她久仰他的文名。
她对这位在上海颇有名气的左翼文化人,突然讲出一句:“我是革命党人。”对于这位奇异的、武断的、言不择时的女子,唐纳觉得她了不起,对她更加迷恋。
“这事使我非常兴奋。”唐纳回忆当时的情形。“这位从山东来的,富于诱惑力的新进女演员,在霞飞路上,对我宣称她是革命党人。”
也许因为唐纳写的影评左翼色彩很浓,蓝苹误以为他是同志,故初次见面,在霞飞大路上竟唐突地说出自己是革命党人。其实,唐纳和共产党毫无关系;虽然承认他自己左倾。(如前所述,唐纳那时其实已加入共青团。后来,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蓝苹到电通影业公司访问唐纳。这时期她是自由的。自从和俞启威分手后,她未和男人同居。她仍然漂流在上海的人海中,她积极地接近唐纳,她的新鲜、活泼的态度,使唐纳陷入情网。
唐纳回忆当年的印象说:
“纵然在上海,像她那样大胆,也是例外。不要想象她是胆小怕生的中国女孩。她不是你通常所见的羞答答的中国女孩。主动地和男人谈话,她毫不在乎。她的行径,一如男性。啊,她是勇敢的女性。”
当蓝苹、唐纳相继进入“电通”,特别是同在《都市风光》剧组,朝夕相处,由相识而相爱了。
当年的《电影新闻》,这样报道了唐纳跟蓝苹结合的情形:
在电通影业公司,“有一天,有人亲眼看见蓝苹挽了唐纳的手臂,肩并肩的出去,剩下来的睁大了眼珠对他们看。”
“当天晚上,他俩没有回来。第二晚,也没有回来……”
“直到第三天下午的六时许,才见唐纳与蓝苹,仍旧手挽手,肩并肩,满面春风的回来。”
“他们一回到公司,就往经理室而去。到晚饭的时分,才和经理马先生回到膳厅。饭吃到一半,马先生立了起来,对大众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同事唐纳先生,与蓝苹女士因意见相投,互相了解,而将实行同居。’说完后,轰雷似的一声,都围住了二人,一半祝贺,一半要他们报告同居前的过程。这一晚的晚饭,就在这样纷乱喧嚣中过去。”
这是一九三五年秋在拍摄《都市风光》的时候。
《都市风光》的编导为袁牧之,摄影师为吴印咸,音乐为吕骥、贺绿汀、黄自。影片中穿插的一段动画,由著名的万氏兄弟设计,即万籁鸣、万古赡、万超尘、万涤寰。
这部影片属音乐喜剧片,通过几个公民的眼睛,从西洋镜里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唐纳主演,饰无聊的知识分子李梦华,蓝苹演配角。
就在蓝苹和唐纳同居不久,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的《娱乐周报》上,已有人指责蓝苹的行为了:
“据该公司有人云,蓝苹已经不是一位未嫁的小姐了。在北平,她早已有了丈夫了。如果此事属实,不是要闹出一场醋海潮了吗?好在他们不过是同居而不是结婚,否则蓝苹不是要犯了重婚罪?”①
①三友,《蓝苹与唐纳同居,在北京的丈夫怎么表示》,《娱乐周报》一卷二十三期。
怪不得,篮苹早就公开声明“反对结婚”!
然而,就在蓝苹和唐纳同居了半年多之后,忽然上海许多报纸刊登消息:蓝苹和唐纳要结婚了!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八点半,杭州钱塘江畔,八辆黄包车透迤而来,奔向六和塔。
为首的一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风度潇洒、西装革履的青年;最末押阵的车上,坐着一位精神矍铄、长髯飘拂、礼帽长袍的长者;中间六辆黄包车,三男三女,喜气洋洋。
那青年即郑君里,长者为上海法学院院长沈钧儒,三对男女乃赵丹、叶露茜、唐纳、蓝苹、顾而已、杜小鹃。
三对男女朝六和塔进发,为的是在那里举行婚礼。郑君里负司仪之责,手中拿着照相机,兼任摄影师。沈钧儒为上海著名大律师,证婚人也。
到达六和塔前,最忙碌的是郑君里。他让证婚人居中,三对夫妇列于两侧,接连拍了许多照片。
三对夫妇为什么远道从上海至此举行婚礼?
这是“秀才”唐纳的主意:六和塔又名六合塔,高高矗立于月轮山上。唐纳取其“六和”、“六合”之意,建议六人来此举行集体婚礼,当即一致通过。
文人雅士如此奇特的“旅行结婚”,顿时传为新闻,纷纷刊登消息及塔前婚礼照片。
沈钧儒诗兴勃发,于塔前口占一首:
情侣浪游在沪杭,
六和塔下影成双。
瑰丽清幽游人醉,
沉酣风波会自伤。
拾级婉蜒登高塔,
居高一览钱塘江!
老先生吟罢,诗兴未尽,又作一首:
人生何处是仙乡,
嘉偶良朋一举觞。
到此应无凡鸟想,
湖山有福住鸳鸯。
塔影湖声共证盟,
英雄儿女此时情。
愿书片语为君祝,
山样同坚海样深。
几天之后——五月五日,晚八点,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九楼餐室,又一度成了新闻中心。三对新人在此招待亲友。
新郎一律西装,新娘一律旗袍。“蓝苹的身上是一件新的白地方格的灯笼袖旗袍。小叶蓝地红花的旗袍。小杜是白地红花的旗袍。”
影星汇聚,连“电影皇后”胡蝶也到会祝贺,吸引了众多的记者。
在掌声中,人们要新娘蓝苹当众发表感想。
蓝苹只说了三个字:“很快活!”
晚会在《六和婚礼贺曲》声中结束。
这贺曲由孙师毅作词、吕骥谱曲:
偎情郎,
伴新娘,
六和塔下影成双;
决胜在情场,
莫忘胡虏到长江。
喝喜酒,
闹洞房,
五月潮高势正扬,
共起赴沙场,
同拯中华复沈阳。
次日,上海各报又纷纷刊登消息,有的甚至用半版篇幅详加报道。
向来关心报纸的唐纳,读着大报、小报,秀气的脸上漾着微笑。
他的笑,只有他知,蓝苹知:他真诚地爱着蓝苹。在蓝苹之前,虽说他也曾追求过别的姑娘,但那只是追求、恋爱而已,并无其他。正因为他真心实意地爱着蓝苹,所以他不愿只是同居。一而再,再而三,他向蓝苹提出要求结婚。然而,遭到了蓝苹的坚决反对。她,不愿意结婚……
当他得知好友赵丹、顾而已都有了心上人,提出了“六和塔婚礼”的建议。赵丹、叶露茜、顾而已、杜小鹃、唐纳,已经五票通过。迫于孤立,蓝苹只得点头——唐纳还编造了一条理由,一旦正式结婚,他可以向苏州老家索一笔钱。
然而,蓝苹只是答应举行婚礼,却绝不签署婚书。
唐纳无奈,依了蓝苹。
这样,在三对新婚夫妇之中,唯独唐纳、蓝苹是没有婚书的!
唐纳是笔杆子,跟各报社广有联系。他煞费苦心,广请记者。“六和塔婚礼”在那么多报纸上登了报道,唐纳出了大力。
唐纳得意地翻阅着大报小报,用剪刀一篇篇剪下婚礼报道,精心地贴成一本。
他想,这些婚礼报道,不就是印在报纸上的“婚书”!成千上万的读者都知道蓝苹跟唐纳结婚了,这比“婚书”的威力还大——难道你蓝苹能够撕掉这些印在报上的“婚书”?!
唐纳笑了!
可是,唐纳笑得太早了!
婚变使唐纳在济南自杀
六和塔婚礼结束后,蓝苹和唐纳相处尚可。蓝苹曾随唐纳回他苏州老家住了半个月。那时,蓝苹跟唐纳的生母、嗣母相处,也还算可以。
可是,回到上海环龙路住所之后,蓝苹就不时和唐纳发生口角了。
口角迅速升级,以至酿成轰动上海的“唐蓝婚变”新闻……
那是“六和塔婚礼”整整两个月后——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晚八时,蒸汽机车冒着黑烟、喷着水汽,疲惫地拖着长长的“平沪快车”(那时北京称北平),驶进济南站。
从车上下来一个疲惫的男人,他的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梳,个子修长,一身西装。他的手中除了一只手提包之外,别无他物。
下车之后,他雇了一辆黄包车。
“先生,上哪家旅馆?”
“不上旅馆,到按察司街二十七号。”
彤云密布,下起渐浙沥沥的冷雨,衣衫单薄的他在黄包车上打了个寒噤。
黄包车刚刚在按察司街二十七号前停下,他就急急跳下了车,砰砰连连敲门。
门开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出现在门口。
“请问,蓝苹小姐在吗?”
“先生贵姓?”
“我是阿仁!”
“喔,妹夫,快请进!”
来者阿仁,便是唐纳。阿仁是他的小名。
这儿是蓝苹的家。唐纳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岳母、姐姐,他什么礼品也没有带——他是在极度仓促、惶恐之中跳上“平沪快车”,赵丹和郑君里送他上车……
“云鹤不在家!”蓝苹的母亲、姐姐,这样答复专程赶来的唐纳。
“她上哪儿去了?”
“她不在济南!”
“不在济南?她在哪儿?”
“她没说,俺不知道!”
“不知道?她走了多少天了?”
“十几天了!”
当唐纳不得不告辞的时候,雨更大了。黄包车早走了——车夫以为已经送他到家。
冰凉的雨点,打在他消瘦、白皙的脸上,他反而觉得舒坦一些,清醒一些。
雨水和夺眶而出的泪水,混在一起。
他浑身湿漉漉的,走进商埠三马路济南宾馆。
茶房赶紧让他住进楼下五号房。
很快地,茶房发现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