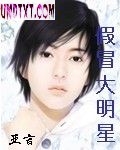大明龙腾-第4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女孩摇头道:“小女子没有家人,纵是有,将我卖到这勾栏之地,亦是没有了。”又道:“相公既然给我赎了身,从此我便是相公的人,听相公的使唤便是了。”
张伟听了此话,也只是微微一笑,心里打定主意,将这女孩送回台北,找一户人家寄养。他一时冲动,出手便是上千两的银子,买回这小姑娘却还得费功夫安置,又见张瑞和一众飞骑正自挤眉弄眼,心里懊恼,只得回头斥道:“笑甚笑!待明日派个人将她送到福建,令台湾派船接过去,再寻一户老成稳重人家,给些银子,令人好生看待她。”
说罢也不在意,领着一伙人慢慢踱步往回,半路上却又遇着几艘花船,张伟却相中了一艘船上的女子,见她容妆淡抹,娇艳不妖,一时间按捺不住,便令周全斌带着那小女孩先回,令张瑞等人在外守着他在这花船上过夜,他却窜上花船,一夜里胡天胡地,享受一番。
第二天一早起来,见张瑞等人挤眉弄眼,张伟老脸微红,他来自现代,有些道德观的东西早深入其心,在台北平日里忙的要死,也就罢了。现下游历这六朝金粉之地,一时按捺不住发泄一番,却只是在心里不好意思。
当下洗漱一番,领着张瑞等人匆匆往客栈而回,到得客栈门前,却见周全斌领着看守行李的数人正于门口等候,那小女孩亦站在门口处张望,张伟冷不防见了这许多人在外,心里一慌,因向周全斌问道:“全斌,因何都站在外面?”
“爷,您昨儿说这南京无趣,不如早些北上办正事要紧,怎地忘了?”
张伟“喔”了一声,这才想起。他原本抱着好好游历一番的心思,却不料后来才知,这古时的南京城内,除了破败不堪的民居,便是豪门贵戚的大宅,哪能容他近身?若说那南京宫城,却哪里是平常百姓能进的去的?那夫子庙,秦准河,一晚上逛的张伟兴致索然,于是昨日便吩咐周全斌准备好行李,一早便动身渡江,由山东入直隶,向北京进发。
见各人神情似笑非笑,那小女孩亦眼波流转,脸上浮现笑容,张伟大惭,心道:“怪道人说色不迷人人自迷呢……才一晚上头脑便不清楚了。”
干咳两声,便令各人收拾了行李,一行人到得下关码头,便要渡船过江,张伟向一干练飞骑令道:“你将这小姑娘送到福建,然后你坐船到北京泉州会馆寻我们。”
那飞骑领命,便要带那小女孩儿离去,却见她向张伟身边行得数步,蹲身一福,道:“小女子柳如是多谢恩公搭救……”
“咦?你不是叫爱柳么?”
“那是干娘给我起的花名,去年我因读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诗句,便自取了名叫‘如是’,那干娘一时没有改口,故而还叫我爱柳。”
张伟在脑中想了半天,方记起秦准八艳之首的柳如是正是在崇祯十三年年约二十五六时嫁了钱谦益,算来此时她已有十二三岁,不想竟然教自已偶遇,当真是飞来艳福……
他正待仰天长笑,却一眼又见眼前的这柳如是,她现下是稚龄少女,虽是肤白似雪,红唇乌发,却是身量不高,瘦弱娇小,现下娇怯怯站在张伟身前,只堪堪高过张伟腰部,见张伟眼中暴起寒光,目视自已,那柳如是却也不惧,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只目不转睛的反看着张伟,不知道这位一掷千金的公子哥儿又犯了什么毛病。
张伟心中暗叹:“果然不愧是八艳之首的柳如是,河东君。小小年纪这胆量和见识便是不凡。”
这柳如是十五岁便失身接客,后来成名后又曾与抗清义士陈子龙相识相爱,与之分手后又嫁给大自已三十多岁的钱谦益,待清军入江后,她又力劝钱谦益自杀。钱得罪清朝高官,又是她写状词诉冤,请以身代。又不惧世俗礼法,因钱谦益降清而致失望的她与人通奸,那钱谦益到也有趣,听说自已儿子告了柳如是通奸,气的与儿子相约死前不相见,且又沉痛向人言道‘亡国之人,何谈礼义?士大夫尚不能以身殉国,何枉求一女子乎?’”
张伟向来最欣赏这位奇女子,觉得她比那八艳中汲汲于自身爱情追求的所谓才女强上许多。他原本没有指望在此时能遇到这位一向心仪的女子,却不料无巧不巧的为她赎了身,只是此时这柳如是尚是稚龄少女,古时女子固然是早早儿便能结婚生子,这十二三岁年纪也未免太小了些,纵是他人能容,张伟也过不了自已的一关。当下心里甚是为难,团团转上几圈,便又将那飞骑道:“这小妹妹甚是知礼,我很喜欢。交与寻常人家,我不放心。便送到何府,交给何夫人细心照料,待我回台北,再做打算。”
那飞骑自是没有话说,只有那柳如是年纪虽小,却看出张伟与适才不同,只是蹲身又福了一福,便随那飞骑去了。
张伟见她离开,心头郁闷一阵,却怎样也无法将眼前这个尚未发育的小女孩与历史记载上的那个美艳多才的柳如是连接起来,叹一口气,向周全斌吩咐道:“上船吧。”
一行人上了渡船,将马匹系在船尾,货物放下,那船家吩咐各人坐稳了,便将缆绳一解,用竹篙一撑,那渡船便向前一滑,向那江心行去。张伟坐惯了海船商船,却是头一回乘坐这种渡江小船,眼见船头随着江中波浪一沉不浮,不时有江水漫过船头,仿佛一个大浪过来,这艘小船便随之沉没。再看那船家,却是不慌不乱,因江面无风,便随同几个船伙计一同在那船身两侧划浆,见张伟目视于他,便向张伟笑道:“客倌是头一回坐这渡船吧?”
张伟笑答道:“正是。”
“客倌莫慌,这船只是随着浪头起伏,顺着它的脾气走,不会有事的。”
张伟向船家点头微笑,自又走到船头,那江风拍打他衣服下摆,打的啪啪做响,有时浪头稍大,便从他脚底掠过。这长江正值涨水时间,四顾看过一片苍茫,此时尚没有什么工业污染,青碧色的江水奔腾啸涌,人在这小小帆船上,直如沧海中的一叶孤舟,任凭这天地之威肆虐。十八年后,正是在这浩瀚长江之上,郑鸿奎、郑彩率郑氏水师数万人布防江上,听闻得江北四镇兵溃,立时便出海而逃,长江天堑立时便被清兵突破,由镇江上岸,南京城内文武大员并十三万大军开城投降,想来当真是可气,可叹。
待船行过江,张伟一行便上岸向北而行,经江阴、准安、徐州入山东,直行了半月有余,方到了北京城外。
入京后便命人找了茶行将所带茶叶处理掉,张伟却与周全斌张瑞二人自处闲逛,他虽是在台湾称王称霸,于这京城内却是一人不识,因是偷偷前来,却也不敢拿着拜帖上前去请见,故而这京城内的高官大佬是一个也没有见到。到是跑到福建人所设的几个泉漳厦等同乡会中,很是结纳了一些在京师的福建人,又借着同乡会的名义,交结宴请了一些六七品的福建小官儿,什么中书主事之类。这些官儿手只管伸的老长,却是什么内幕消息也透露不出,原本便是些佐杂小官,贪图吃请方能让张伟这白身之人请动,若是什么翰林、给事中之类的清要官员,就算是品秩不高,也不是张伟这样的商人可以结交的。在京中混了数日,只是知道崇祯已派了袁崇焕赴辽,平台召见后皇帝赐袁尚方剑,御制诗,许袁便宜行事,袁崇焕则许帝五年复辽。张伟听说此事,心中明白这位袁督师命不久矣,只是如何干预此事,他却是还没有想好。
袁崇焕是位难得的人才,张伟心慕久矣,只是他明白这样的高位大臣却不是自已能够掌控的,即便是崇祯皇帝要杀他,只怕也很难令其归顺。越是想到袁的忠义,张伟就很难对历史上评价不一的崇祯皇帝有什么好感。此人刚愎自用,刻薄好杀,对百姓不肯抚慰,对官员也甚是寡恩。临死时还说什么:“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又曾说:“文臣皆可杀。”,此人到临死都不知道正是自已亲手断送了大明江山。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听闻京师被围,千里勤王快速而回,在北京城外领关宁铁骑与清兵大战,直到将清兵撵走。却不料战事一息,便被崇祯皇帝逮至诏狱,不经审讯便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至此,明朝在辽东最后一位将才被自已的皇帝亲手杀死,到了明朝要亡国之际,崇祯下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领关宁铁骑入卫京师,吴三桂故意拖延时日,待听说京师陷落,崇祯上员而死,方又领兵退回山海关。两相比较,袁崇焕的遭遇便更令人扼腕长叹。
张伟在北京盘恒了十数日,便又随意购买了一些关外需用的物品,只说去宁远贩卖些关外特产,辞别了这些时日来打的火热的福建商人,一行人出了西直门,便向山海关而行。待出了直隶,离那山海关近时,那一路上休说是风光景致,便是行人客商也没有几个,这关外情势一向吃紧,若不是任了袁崇焕为督师,阻了那清兵靠近,依天启年间的朝议,关外之地尽弃,只是依关而守,只怕这长城重镇,早便是草木皆兵,一日数惊了。
这山海关因是战略要地,修建的雄伟异常,箭楼附近还放置了内城城头少有的红衣大炮,入关之时关防甚严,将张伟等人花钱买的路引查验了数次,又奉送了数两白银,那守城门的百户方才挥手放行。辽东之地苦寒,汉人居民原就不多,努儿哈赤打下沈阳后,居住在附近的汉民不堪忍受女真人的奴役,纷纷逃亡到这山海关至宁远绵州一地,居民人数到比原本稠密的多,饶是如此,待张伟等人进入宁远这坐历史上有名的边城之后,还是觉得大街上稀稀拉拉,虽是大响午的,却少见人影。
因自出南京后便是陆行,虽说各人都是骑马乘车的,到底一直走路,风餐露宿辛劳不堪,待行到这关外边城,自张伟以下,各人神色皆是疲惫不堪,张伟便向张瑞笑道:“咱们也别寻饭馆吃饭了,赶紧着寻家客栈歇息了。”
张瑞答道:“我也是累的紧,想来客栈大半都有饭食。咱们这便去寻客栈去。”
其余人等自然也是无话,便在这宁远大路上寻将起来,张伟在车中坐的脚麻,便跳将下来,换了马骑,左顾右盼之际,心里却是不安,向周全斌道:“全斌,这宁远城便是没有什么百姓,到底也是辽东大城,怎地大白天的一个人影不见,这当真是怪异。”
周全斌闻言也是四顾而看,半响方答道:“难道咱们运气甚好,正巧遇上了女真人要攻城?”
“不会呀,在城外没有什么异常举措,若是女真要要来攻城,咱们还能进的来?”
两人正在纳闷,张瑞却已寻得一家客栈,看那客栈门头不小,远远的便有幌子迎风招展,上书四个大字:悦来客栈。
只是说来也奇,客栈原本是要打开门做生意,象张伟这样的大股客商,平常时日早该有伙计上前招呼,只是那客栈大门紧闭,张瑞管自敲了半天的门,却是没有半点儿反应。
张瑞见张伟骑马而来,便回头苦笑道:“这事儿还当真是怪了!”
周全斌沉声向那客栈门内说道:“里面的人听了,我们是住店的客商,不是歹人,出门在外,请老板行个方便。”
说罢,便令身后飞骑一同上前擂门,各人冲上去将那客栈的大门擂的山响,不消一会功夫,便听到那门吱呀一声,有一中年男子打开大门,气道:“哪有你们这样的!小店今儿关张,不做生意!”
说罢便要关门,张瑞急忙上前一步,用脚将那大门抵住,陪笑道:“老板,咱们千里迢迢从关内过来,实在是累的受不住了,请老板你行个方便,如何?”
说罢将一锭银子递将过去,那男子将银子拿在手中,捏上一捏,便在那脸上挤出笑容道:“也罢,与人方便,自已方便。各位快请进来,耽搁不得!”
就手将门拉开,催促道:“几位,快快,若是迟了只怕性命不保。”又向那店内喊道:“小五,柱子,快点过来帮手!”
张伟几人见那老板催的紧急,急忙赶着马匹、骡车鱼贯而入,一入店门,便有那伙计将马匹接去,自牵到后院喂食草料,那老板见各人进来,急急忙忙关了店门,又砰砰将店门反锁,抵上石条。待张伟等人收拾停当,那老板已是一头的暴汗。
张伟见店堂内无人,便自捡了一张干净桌子坐了,又吩咐那店内伙计上茶,上毛巾,舒舒服服的喝着热茶,不自禁长伸一个懒腰。因见那老板忙的脚底生烟,便笑道:“老板,何故如此惊慌?莫非那女真人要来攻城?便是如此,城内有袁督师在,城头有红衣大炮,那蛮子是攻不进来的。”
张瑞在张伟坐定,正用热毛巾擦脸,只觉得浑身舒泰,见张伟问那老板,便也笑道:“怪道说这辽东是兵凶战危之地,城外也没有见女真人的影子,这城内便乱成这样,若是女真人到了城下,那还了得!”
那老板听他们说,却只是不理会,又指挥着伙计们多加了几块石条,方才转身抹汗,他一说话,却只是没好气,道:“两位也太小看咱们宁远的百姓,甭说现在没有女真人来攻城,便是来了,咱们这些男子也早就至城墙处协助大军守城了。”
“那怎地街面上不见行人,老板你又大门紧锁,还堆上石条?”
那老板叹一口气,自在张伟一边的桌上坐了,啜一口茶,方答道:“此事说来话长……”
张端见他慢条斯理,摆出长篇大论的架式,急道:“这位大哥,咱有话快些说成不?”
“快些说也成,很简单,城内兵变!”
张伟几人却正是带兵之人,一听说“兵变”二字,却是比常人敏感的多,周全斌双手一撑,立时站起,厉声问道:“是城内兵马要与那女真人里应外合?”又问道:“有多少人马叛变,城内袁督师可是在弹压?”
张伟疑道:“老板莫非是在说笑,我们进城来那守城兵丁一切如常,这城内也没有厮杀声,如何便是兵变了?”
“我适才说了说来话长,偏那位大爷让我快说……”见张伟等人神色不愉,那张瑞大有冲上来教训他的模样,便又急道:“此次兵变,到不是和那女真有关。实在是因为这城内军士三个月没有关饷,军士们自然是急了,虽说袁督师素有人望,可军士们家里有老有小,都等着关饷买米下锅,这么些日子不发饷,谁不着急?前日便有数十军士到袁督府前要饷,袁督师只说早就奏报了圣上,这何时关饷却是只字不提。城内军士都急红了眼,昨儿又有人去闹饷,袁督师便尽数捕了,捡了为首闹的凶的斩了五人,又急报了北京,到底如何处置却还没有下文。现下这城内军心不稳,咱们都怕大兵们急怒之下尽数反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可不是最倒霉的么!谁还敢没事上街晃悠,家家都是闭门落锁,只盼着朝廷早点儿发饷,不然的话,这日子就没法儿过了。”
张伟三人听那老板说完,一时间只是面面相觑,这台湾兵士每月五两的饷银从未曾拖欠过,是以“欠饷”这种事情,在台湾的带兵将领心里竟然是全无概念。张伟却是心知肚明,晓得明末时朝廷根本不管军队饷银,故而带兵将领只得纵容士兵四处劫掠,到了南明弘光朝时,朝廷居然让江北四镇划地自征粮饷,使得原本听从调遣的四镇成为不折不扣的军阀,欠饷,在明朝已算不得什么新闻了。
周全斌疑道:“朝廷在天启年间便加了几百万两银子的‘辽饷’,怎地还会拖欠军饷?”
张伟笑道:“说是为了辽东战事征饷,其实朝廷用度不足,哪能把加派的银子都用在辽东,便是每年藩王的俸禄就得拿去朝廷一半的正斌,这还是打了折的。再加上官中用度,官员贪墨,能用在辽东的,十之其一罢了。”
那老板亦叹道:“这位爷的话可是说到点子上了。若不是这样,每年真把几百万两银子交给袁督师练兵铸炮,甭说现在守住宁绵,便是打回沈阳和赫图阿拉,又能怎地?”
说罢摇头,道:“没用了,国家烂到根子上了!”
张伟听他如此说,便也不再搭话,只令那老板叫人准备好了房间,便与各人自回房歇息,自他而下随行各人都疲累不堪,也没人叫饭,自这晌午时分一觉好睡,一直到傍晚时分,方见各人打着呵欠次弟出门。张伟叫人送上热水,细细梳洗了,才觉得数日奔波的疲劳一扫而光,精神一振,腹中却雷鸣般鼓噪起来。便向张瑞笑道:“快,吩咐伙计做饭,吃完了咱们出去。”
张瑞听他说要出门,到是一楞,只是他一向听令惯了,也不多问,自去令人整治了一桌关外特色酒席,什么孢子肉,野参炖鸡,老烧刀子,一股脑儿端将上来,一时间那酒菜香气飘满整个店堂,张伟等人都饿的狠了,见了美食哪还客气,乒乒乓乓筷如雨下,立时便将满桌酒菜吃的精光。待各人吃饱,张伟抚肚笑道:“各人歇息片刻,随我出门!”
张瑞抹嘴道:“爷说上哪儿,咱们跟去便是了。”
周全斌笑道:“这会子出去怕是不妥吧?万一突然兵乱了起来,那可是太过危险。咱们最后在这店里等局势稍好一些,再做打算。”
张瑞斜看他一眼,道:“周大哥,你害怕不成?”
周全斌涨红了脸,怒道:“我怕什么?你这小子不知好歹,要是爷出了什么差池,你当你担待的起么!”
张瑞吃他一训,低头道:“我却是没有想到此节,是我的不是,对不住了。”
张伟见周全斌着急,方笑道:“全斌,你不须着急。一会子我是去拜会袁督师大人,他那府中必定是防备森严,哪里有什么危险。”
“那半路上遇到乱兵怎办?”
“哪有这般巧的!一会天黑出门,专挑僻静的小道走,此处离那督师府不远,纵是遇到小股乱兵,我带这十几名高手是用来耍子的?”
周全斌这才无话,待天黑掌灯时分,张伟命店家开门,那店家却不管张伟等人好说歹说,硬是不肯,后来无法,只得从后院攀墙而出。依着那店家指点,各人自宁远城内的小巷穿梭而过,约摸走了半个时辰,方才转到一条大道之上,看着不远处高挂的“袁”字气死风灯,张伟笑道:“这可不是到了。”
待到了督师府前,见门前有巡逻兵丁来回巡守,张伟略整一下衣衫,见那府前已有巡官前来查看,便向张瑞道:“拿我的名刺给那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