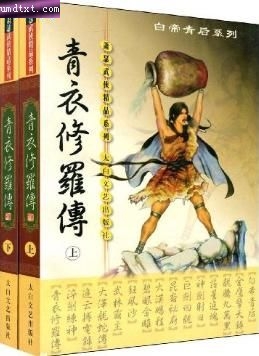梵高传-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附上几张画,告诉我为什么卖不出去,怎样才能有销路。因为我一定要挣几个钱,买张火车票去摸一下“不,永远不,永远不”的底。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感到一种新的健康的活力在增长。他的爱情使他百折不挠。他已经驱走了那疑团的萌芽,现在他心中以为,只要能见到凯,帮助她了解他实实在在是个什么样的入,他就能把那个“不,永远不,永远不”变成“是!永远!永远!”他以一股新的活力重新作画,虽然他知道他的画工的拳头还不听使唤,但他坚信:时间会把这扫去,就象会把凯的拒绝扫去一样。
第二天晚上,他写了一封信给斯特里克牧师,详细地阐述了情况。他直言不讳,当他想到可能会从姨父嘴里吐出来的咒语时,不禁咧嘴笑了起来。他父亲不准他写这封信,一场真正的争吵在牧师住宅里酝酿着。泰奥多勒斯是以严格的顺从和规矩的品行来对待生活的,他对人性的变化一窍不通。如果他的儿子不能合上这个模子,那末一定是他的儿子不对,而不是模子不对。
“这都是你读的那些法国书害了你,”一天晚上,泰奥多勒斯隔着桌子说。“如果你与窃贼、杀人者为伍,谁能期望你有孝子和绅士的品行呢?”
文森特从米什莱的书上抬头望着,感到有点惊奇。
“窃贼和杀人者?你把维克多·雨果和米什莱都叫作窃贼吗?”
“不,但是他们写的就是这类东西。他们的书充满着邪恶。”
“睛说,爸爸,米什莱的书就象《圣经。一样纯洁。”
“我不要听你的亵渎神明的话,年轻人!”泰奥多勒斯义愤填膺地叫道。“那些书是不道德的,你的法兰西思想毁了你。”
文森特站起身来,绕桌而走,把《爱情和女人》放在泰奥多勒斯的面前。
“只有一个办法能使你信服,”他说。“你亲眼看几页吧,你会感动的,米什莱只想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难题和我们的小小不幸。”
泰奥多勒斯以一个善士摈弃罪恶的姿势,把《爱情和女人》扫到地板上。
“我不要读!”他怒声说。“我们几·高家的一个叔祖父染上了法兰西思想,结果酗酒啦!”
“一千个抱歉,米什莱老爹,”文森特喃喃地说,把书拾了起来。
“为什么叫米什莱老爹,如果我可以问一下的话?”泰奥多勒斯冷冰冰地说。“你是想侮辱我吗?”
“我根本没有这种意思,”文森特说。“但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如果我需要什么忠告的话,我一定比向你求教更快地向他求教。那可能是更合时宜一点。”
“嗅,文森特,”他母亲恳求道,“你为什么要讲这种话?你为什么要破坏家庭关系呢?”
“对,你就是在这样做,”泰奥多勒斯嚷道。“你是在破坏家庭关系,你的行为是不可原谅的,你最好是离开这所房子,到别的地方去生活。”
文森特上楼走进他的工作室房间,在床上坐下。他无聊地自揣着:为什么不论什么时候一受到重大的打击,他就坐在床上,而不是坐在椅子上。他环顾房间墙壁上的锄地者、播种者、劳动者、女裁缝、洗衣的女孩、樵夫和临摹海克的画。对,他有进步,他在向前进,但是他在这儿的画尚未画宅。莫夫在德伦特,下个月才会回来。他不想离开埃顿。他是舒服的,在别的地方生活将花钱更多。在一去不返之前,他需要时间把他的拙劣的表现手法砸碎,抓住布拉邦特型的真正精神。他父亲已经叫他离开这所房子,真的在咒诅他,但这是在火头上说的,如果他们真的说“滚!”,并且意味着……被赶出父亲的房子,就真的对他那么不利吗?
第二天早晨,他收到邮局送来的两封信。第一封是斯特里克牧师寄来的,是对他的挂号信的回复。其中夹有牧师的妻子的短笺。他们用毫不含糊的字句概括了文森特的经历,告诉他凯另有所爱,那是一个有钱的人,他们希望他立即停止对他们女儿的粗野的袭击。
“诚然没有比教士更不虔诚、更硬心肠和更庸俗的人了,”文森特自言道,狠狠地痛快地把手里的阿姆斯特丹来信撕得粉碎,就好象在撕裂牧师本人一样。
第二封信是泰奥寄来的。
“画表现得不错,我将尽力把它们售去。随信附上二十法郎,作为赴阿姆斯特丹的车资。祝你好运气,老兄。”
文森特离开中央火车站时,夜幕开始合拢。他迅速地往水坝走去,经过王宫和邮局,抄近路到凯泽斯格拉特街。那时候,所有的店铺和办公室都空了,没有一个职员和售货员。
他穿过辛格尔街,在希伦格拉特桥上站了一会儿,望着花船上的人在露天的桌旁吃面包和青鱼的晚饭。他向左拐人凯泽斯格拉特街,经过一长排狭窄的怫兰德式住宅,到达斯特里克牧师住屋的短石阶和黑栏杆前。他记得第一次站在那儿的时候,是他的阿姆斯特丹冒险的开头,他领悟到有一些城市里的居民,他们永远是倒霉的。
他一路冲上堤岸,以最快的速度穿过市中心,现在他到达目的地了,却对进去感到害怕,犹豫不决。他向上望望,看到铁钩伸出在天窗上。他想这给一个要上吊的人,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他在宽阔的、红砖砌的人行道上信步走去,站在镶边石上,俯视脚下的运河。他知道下一个钟头将决定他的外在生活的整个进程。只要能见到凯,对她讲话,使她了解,那末一切都能解决。但是,年轻姑娘的父亲掌握着前门的钥匙。假使斯特里克牧师拒绝让他进去呢。
一艘沙船缓缓逆流而上,驶向夜泊处。沙从中央舱内铲走后,在黑色的船舷上留下了一条微湿的沙痕。文森特注意到从船尾到船首没有晾晒湿衣服,瞎想着其中的缘故。一个瘦骨磷峋的男子,前胸的一边挺着篙子,用力地顶着,踏着窄窄的船沿向后撑去,那厚实粗策的木船,在他的脚下逆水滑行而上。一个穿着肮脏围腰布的女人,坐在船尾,好象一块水蚀的石头,手伸在背后掌着粗笨的舵柄。一个小男孩、一个女孩和一头逍遏的白狗,站在舱顶上,起劲地凝望着凯泽斯格拉特街上的房民
文森特踏上五级石阶,拉响门铃。隔了片刻,一个女仆前来开门。她盯着站在阴影里的文森特看,认出了他,突然转过胖胖的身躯,缩进门里。
“斯特里克牧师在家吗广文森特问。
“不,他出去了。”她已经奉到命令。
文森特听到里面的声音。他粗暴地把这个女人推往旁边。
“别挡住我的路,”他说。
女仆跟在他后面,想不让他进去。
“全家在吃饭,”她反对地说。“你不能进去。”
文森特走入长长的厅堂,踏进餐室。他刚一进门,只见那熟悉的黑裙边在一扇门里隐去。斯特里克牧师、他的姨妈威廉明娜和两个小孩坐在桌旁。桌上放着五份餐具。空椅歪斜地向后推去的地方,有一盆烤小牛肉、没有吃过的土豆和菜豆。
“我拦不住他,先生,”女仆说。“他横冲直撞地进来。”
桌上放着两座银烛台,高高的白烟发出唯一的光。加尔文像,挂在墙上,在黄色的光线中显得神秘而可怖。雕木餐具柜上的银餐具在黑暗中闪烁,文森特特别注意到小小的高窟,他第一次和凯说话的时候,就在这窗下。
“嗯,文森特,”他姨父说,“你似乎愈来愈没有规矩了。”
“我要与凯谈谈。”
“她不在这儿。她出去看望朋友了。”
“我拉铃的时候,她就坐在这个地方。她已经开始吃饭了。”
斯特里克向他的妻子转过身去。“把孩子们领出去。”
“文森特,”他说,“你惹起了不少麻烦。不单单是我,家里所有的人都对你完全失去了耐心。你是一个流浪汉,一个二流子,一个乡巴佬。依我看,你是一个忘恩负义、道德败坏的人。你竟然敢自以为爱上我的女儿?那是对我的侮辱。”
“让我见见凯,斯特里克姨父。我要跟她谈谈。”
“她不要跟你讲话。她永远也不要再看见你!”
“是凯讲的吗?”
“对。”
“我不相信。”
斯特里克大吃一惊。自从被授予圣职以来,第一次有人指责他撒谎。
“你竟敢说我不是在说实话!”
“我不听到她亲口讲,我是永远不相信的。就是听到了也不相信。”
“我想到在这儿阿姆斯特丹,在你身上浪费了全部宝贵的时间和金钱的时候。”
文森特无力地一屁股跌坐在凯刚才空出来的椅上,两臂搁在桌上。
“姨父,听我说。告诉我,即使一个教士在他的三重铁甲胄下也有一颗人心呀。我爱你的女儿。我不撤死活地爱她。我日日夜夜在想念她,渴望她。你是侍奉上帝的,你就发发慈悲,给我一点儿怜悯把。别对我这样残忍。我知道我还没有取得成功,可是如果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成功的。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把爱情奉献给她。让我帮助她理解为什么她应该爱我。你一定也恋爱过的,姨父,而且你也清楚一个人能经受得起何等的痛苦。我已经受得够了,让我能有一次机会找到一点幸福吧。我所请求的不过是一个赢得她爱情的机会。我一天也无法再忍受这种孤单和不幸了!”
斯特里克牧师低头对他看了一会儿,说:“难道你是这样一个脓包和懦夫,连一点儿痛苦也无法忍受吗?你一定要永远为此啜泣吗?”文森特通地跳了起来。他的全部温和都消失了。仅仅是由于他们彼此站在桌子的一面,隔着银烛台的两支长触,才使得这个较年轻的人没有动手殴打牧师。两个人目不转睛地望着对方眼睛里的闪闪光点的时候,受伤的沉默在房间里嗡嗡作响。
文森特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他举起手,放近蜡烛。“让我对她讲几句话,”他说,“只需要我的手能在火上放多久的一点时间。”
他把手糊过来,手背悬在火上。房间里的光线顿时赠了下来。蜡烛发出来的碳气立刻使他的肉变成黑色。几秒钟内,黑色变成了天然的火红色。文森特毫不畏缩,眼睛不离他的姨父。五秒钟过去了。十秒钟。他手背上的皮肤噗地涨了起来。斯特里克牧师的眼睛恐怖地瞪着。他似乎瘫痪了。他几次想讲话,想动一动,但身不由主。他被文森特冷酷的、刺探的眼睛压住了。十五秒钟过去了。涨起来的皮肤裂开,但是手臂甚至抖也没有树一下。猛烈的肌肉抽搐终于使斯特里克恢复了知觉。
“你这个疯子!”他技直喉咙狂叫。“你这个发狂的呆子!”
他的身子扑过桌面,把文森特手下的蜡烛一把抢去,用拳头捣火。然后,他如蜡烛俯身下去,用力吹熄。
房里一片漆黑。两个人撑住桌子站着,面对面隔着桌子,盯着黑暗,什么也看不见,但彼此把对方看得一清二楚。
“你疯了!”牧师嚷道。“凯从心底里看不起你!滚出这所房子,永远不准再来!”
文森特在黑暗的街上小心地、慢慢地走着,不知不觉到了市郊。他站着俯望带咸味的、停滞的运河,那死水的熟悉的臭气刺入他的鼻孔。角落里的煤气灯光照在他的左手上——某种深深的本能一直使他的作画的一只手贴在身侧,他看到皮肤上有一个黑洞。他越过一连串狭窄而运河,闻着一般淡淡的、早已忘却的海的气息。最后他发觉走近了芒德斯·达·科斯塔的家。他蹲坐在一条运河的岸上。他往厚厚的绿色的青苔毯上扔了一块小石子。石子往下沉去,甚至一点也看不出绿毯下面还有水。
凯从他的生活中远去了。“不,永远不,永远不”是从她灵魂深处发出来的。她的叫喊现在变换了位置,成了他的财富。它在他头脑中乱敲,重复着:“不,永远不,你永远不会再见到她。你永远不会再听到她声音的较快低吟、看到她那深邃的蓝眼睛里的微笑、触觉到她那温暖的皮肤在你面颊上的抚摸。你永远不会认识爱情,因为它不能生存,即使你的肌肤能够忍住火烧的痛苦之严酷考验,它也不能生存!”
一阵无声的悲伤巨涛涌上他的喉咙。他举起左手捂住嘴,压住阿姆斯特丹和整个世界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他已经受到判决和被认为一钱不值的喊声。他的嘴唇尝到了事与愿违的惨苦的、惨苦的幻灭。
第三章(一)
莫夫还在德伦特。文森特在尤尔市门街附近东找西寻,终于在雷伊恩火车站后面找到了一个每月租金十四法郎的小地方。这工作室——在文森特租下前一直是作住房的——很大,墙上有个凹处可以烧饭,朝南一扇大窗。一个角落里低低地蹲着一只火炉,一根黑色的长烟囱伸向天花板,迈进墙壁。称壁纸色彩素净。从窗口望出去,文森特可以看到房主堆放木材的院子,一片碧绿的草地,然后是茫茫沙丘。房屋座落在申克韦根街,这是海牙城与向南延伸的草地之间的最后一条街。雷伊恩火车站上轰隆轰隆地开进开出的机车喷出的黑烟垢,洒满一街。
文森特买了一张坚固的厨房用桌、两把厨房用椅和一条以备睡在地板上对盖用的毯子。这些费用耗尽了他手边不多的一点钱款,但第一个月剩下不多几天了,泰奥将寄来商定的每月一百法郎的生活费。寒冷的一月天气不允许他在室外作画。因为无钱雇请模特儿,他只能把时间空坐过去,等待莫夫回来。
莫夫返归尤尔布门街。文森特马上到他表兄的工作室去。莫夫兴奋地在竖起一大块画布,被在前额上的一绝头发落在眼睛上。他正打算开始今年的一项大计划——送往巴黎美术展览会的一幅油画,他选择了由马施上斯赫维宁根海滩的一条小渔船作为主题。莫夫和他的妻子叶特,压根儿不相信文森特会来海牙;他们深知,差不多人人在他的一生中都会有当一个艺术家的模糊的感情冲动。
“你终于来海牙了。很好,文森特,我们将使你成为一个画家。你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找到了,在申克韦根街一百三十八号,就在雷伊恩火车站后面。”
“那很近。你的钱怎样安排呢?”
“哦,我没有多少钱好用。我买了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
“还有一张床。”叶特说。
“没有,我一直睡在地板上。”
莫夫悄声地对叶特讲了几句话,后者走进住屋,片刻后带回一只钱包。莫夫取出一张一百盾的钞票。“请收下,是我借给你的,文森特,”他说,“替自己买一张床,晚上必须好好休息。房租付掉了吗?”
“还没有。”
“那就别管它。光线怎么样?”
“光线充足,不过那唯一的窗是前南开的。”
“那不好,你最好把光线固定下来。太阳每隔十分钟就会使你的模特儿身上的光线改变一次。买些窗帘吧。”
“我不想借你的钱,莫夫表兄。你肯指教已经足够了。”
“废话,文森特,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次要建立一个家的,到底自己买,来得合算。”
“对,是这样。我希望能很快卖去几张画,那时我就可以把钱还给你了。”
“特斯蒂格会帮你忙的。当我年轻还在学画的时候,他就买我的画。不过你应该开始作水彩画和油画,光用铅笔画的素描,是卖不出去的。”
莫夫,尽管身材魁梧,但做起事来却有一股子急于求成的倔脾气。他的眼睛一旦碰上了所寻求的东西,便挺出肩头,如那个方向猛扑过去。
攸,文森特,“他说,”这是画箱,里面有水彩颜料、画笔、调色板、调色刀、油画颜料和松节油。来,我来做给你看,该怎样拿调色板,怎样站在画架前。“
他教了文森特一些基础知识。文森特接受得很快。
“好!”莫夫说。“我本来还以为你很笨,看来不是那样。以后你可以在早晨来,画水彩。我将提名你为皮尔克里的特别会员,你能一星期有几个晚上去那儿画模特儿。此外,这将使你与画家们有所交往。你开始售画后,就能成为一名正式会员。”
“是呀,我要画模特儿。我想雇请一个天天来的模特儿。一旦掌握人体,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不错,”莫夫同意。“人物最不容易掌握,但一旦掌握了,村呀,牛呀,等等都简单了。那些无视人体的人,他们之所以那样,是因为发觉人体实在太难了。”
文森特买了一张床和窗帘,付了房租,把布拉邦特速写钉在墙上。他明白,这些速写卖不出去,他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缺点,但这些画中蕴藏着某种自然力,这些速写是由相当的热情画成的。他无法指出热情在哪儿,亦无法指出怎么会在那儿的,他在与德·博克交友前,甚至没有认识到这些速写的全部价值。
诌·博克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他很有教养,风度翩翩,财源不绝。他在英国受的教育。文森特在古皮尔公司时认识他的。德·博克在各方面恰恰都成了文森特的对照,他随随便便,对什么都无动于衷,浑身上下打扮优雅,他的嘴就象鼻孔一样大小。
“请光临舍间喝杯茶,”他对文森特说。“我想请你看看我的近作。我以为自从特斯蒂格销售我的作品以来,我有了新的鉴赏力。”
他的工作室在海牙的贵族化地段威廉帕克街。墙上挂满了素色的天鹅绒帷幔。屋角里摆满了坐垫十分舒服的长躺椅。房间里有好几张烟桌、装满书的书架和东方地毯。文森特想到他自己的工作室时,感到自己象个隐士。
德·博克点起俄式茶壶下的煤气,叫他的管家去买蛋糕。然后他从壁橱里取出一块画布,把它拥在画架上。
“这是我最新的作品,”他说。“一面看一面抽支雪茄吧。也许这会对看画有所帮助,谁知道呢。”
他以轻快的、玩笑的口气说。自从特斯蒂格发现他以后,他的自信心升到天上去了。他知道文森特会喜欢这幅画的,他拿出一根俄国长烟卷——他以此闻名海牙,注视着文森特的脸,想看出脸上掠过的评价。
文森特透过德·博克的昂贵雪茄的蓝色烟雾,仔细观看那画。他从德·博克的态度中,感觉到一个艺术家第一次把自己的创造给一个陌生人看的时候所产生的那种可怕的提心吊胆。他该说些什么呢?风景不坏,但也不好。那太象德·博克的性格,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