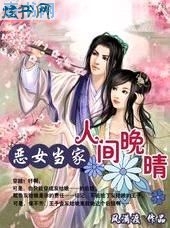人间-第6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探下头说:“不下来吗?那我一个人先走了。”
大概魏晋名士都这么神经兮兮!无奈地跟他下车,踏着纽约街头积雪,忽然感到了自由。
对面恰是中央公元,他像小孩那样兴奋地说:“兄台,我们进去走走吧。”
兄台?一下子跳跃到了武侠小说,那我该叫他贤弟吗?
踏过一片白雪覆盖的树林,四周路人已越来越少,走到深处竟只剩我们两个。在拥挤喧嚣的曼哈顿,能有这样闹中取静的所在实在难得。他调皮地抓住一把新鲜的雪,砸向旁边的一盏路灯,不禁惊起几只鸽子,他伸出舌头做了个鬼脸:“哎呀,对不起,没看到你们。”
虽然刚刚遭遇行刺,与死神擦肩而过,我的内心却如此轻松,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因为中央公园里的雪警,还是眼前的美男慕容云?
“高能,我们从此兄弟相称如何?”
“什么?”
“你不是说要答谢我吗?”他抓着空中飘落的雪粒,狡诈地微笑道,“既然你那么吝啬,就以此来答谢我吧!”
“你我结拜为异性兄弟?”
“没错。”
我像看妖怪似的看着他,这是什么年代啊,难道还有刘关张桃园结拜?何况这是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
“你不愿交我这个兄弟吗?”
“不——可是。”
白色汉服在雪地里一晃:“你不想感谢我的救命之恩?”
这话像是对我的侮辱,我连连摇头:“不,你说怎样我就怎样!”
“好,既然这么说,那我们一齐跪下吧!”
没等我听明白,慕容云已抢先跪倒在地,接着将我应拽下来——两个男人都已双膝下跪,面朝纽约的天空。
“苍天在上!小弟慕容云。”
他已双手抱拳对天致敬。
而我跪着愣了几秒钟,陷在积雪中的膝盖却动弹不得,痴痴地看着他的眼睛不知所以。
“快说啊!”他重重地拍了拍我的后背,“快说愚兄高能!”
完全无法拒绝这双眼睛,既然已经承诺“你说怎样我就怎样”,便下意识地跟着说:“愚兄高能!”
“就此结拜为异性兄弟!”
“就此结拜为异性兄弟!”
此情此景彻底震撼了我,面对这个汉服飘飘的古代人,唯有跟着他一同穿越时空。
慕容云的表情极度认真,绝非少年人开玩笑或恶作剧,无法从他的目光里分辨出谎言。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我又下意识地重复一句,心底忽然升起一股庄严,如同满眼白雪纯洁无暇。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回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来,古装片里常见的情景,在中央公园鹅毛大雪下重现。
我们的膝盖都已湿透,他拉着我从雪地站起来,毫无顾忌地仰天大笑:“哈哈哈,大哥,小弟有礼了!”
最后那句“小弟有礼了”竟是某种古典戏曲的唱腔。
“请问我高能何德何能,可以赢得你这古代人的青睐?”
“因为你的眼睛很特别。”
“真的吗?可我一直觉得自己长得很平凡。”
“是,但你的心很不平凡。”
“难道你也能看到?”
我这句话说得过分托大,刚有些后悔,他就摇摇头问:“看到什么?”
“没——没什么!既然我们已是兄弟,那么贤弟能否告诉大哥,你究竟是什么人?”
“地球人。”
“哦,这个地球人都知道。”对着美少年苦笑一声,“你从哪里来?别回答我还是地球。”
“另一个世界。”
“你几岁了?”
“25岁。”
这个回答让我有些意外:“可你看起来像二十岁。”
“为什么总是有人这么说?我希望自己看起来像四十岁。”
“你住哪里?工作了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只能说我自由自在惯了。”
话音刚落,慕容云迎着雪花撩起额前的一绺长发,宛如踏雪寻梅的少年剑客。
“自由职业者?”
“可以这么说吧。”
“干什么呢?”
“什么都干!”
等于什么都没说。
“小弟,能告诉我电话号码?”
“抱歉,我从不用电话。”
“不可能!除非你真是穿越时空而来的。”
他擦去落在睫毛上的雪粒:“为什么不是呢?我又没说过我的出生年份。”
“25岁不是1984年生的吗?”
“不,我是公元543年生人。”
“公元543年?南北朝时代?”
这回牛皮吹大了吧?
“没错。”
“那你不是一千四百多对了吗?”
“不,我在25岁时就死了。”
“那你是个幽灵?”
“也许。”
不想再和他玩游戏了:“可你现在嘴里分明在呵着热气!”
“这是你的幻觉。”
“你的存在是我的幻觉?”
“不,我是真实的。”他后退了几步,嘴角微笑迷人,“大哥小弟告辞了,后会有期!”
“等一等!”
慕容云不再理会于我,飞身闪入白茫茫的树林,白衣很快被大雪掩盖,再也看不到踪影。
我着急地向前追去,我发现雪地上的脚印居然没了!
曼哈顿寂静无声。
踏雪无痕的轻功?还是我脑中幻想?
抑或真有穿越那些事儿?
2010年。
农历小年夜。
车窗外白雪茫茫一片,几个钟头见不到任何生物,从一望无际的荒凉戈壁滩,覆盖到遥远的落基雪山,却是一年中最湿润的季节。
坐在改装的悍马大车里——装运过莫妮卡棺材的灵车,但它最适合这种恶劣路况,而且可以抵御小型导弹的攻击,我也不会对自己深爱过的女人感到晦气。前后各跟着两辆安保越野车,年底曼哈顿刺杀事件后,所有保镖都被解雇,重金聘请了一群退役的海豹突击队员。
宽敞的车厢足够躺下睡觉,车载电视放着最新的财经消息,我却一直看着窗外,抚摸冰凉的防弹玻璃。
五个月前,我逃出肖申克州立监狱,经过荒漠深处的甘泉山谷,独自步行穿越数百公里,奇迹般地获得了自由。
明天,我将离开美国,乘坐专机前往中国。
该回去了!已在新大陆漂泊一年零五个月,其中十二个月在大牢里度过。妈妈在家早哭干了眼泪,尽管我给她汇了几百万,并请她到美国来玩了半个月。
为了风雨飘摇中的天空集团,我必须回到祖国,这是集团凤凰捏磐的必由之路。
上个星期,捷报终于传到总部,我赢得了上任以来第一场胜仗。
天伦保险与北美石化部门,同时宣布与买家签订出售协议。
三个月的艰苦谈判与反复折腾后,天伦保险卖给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保险公司,从而打消了美国公众的疑虑——我并没有把美国的平派低价甩卖给中国人。
至于争议更大的北美八个石化工厂,我化整为零地与不同买家谈判,分别卖给俄罗斯、沙特、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土耳其、巴西的公司,但最好的一个工厂,留给了一家中国民营企业。
此次出售总共为公司收进六十亿美元的流动资金。
虽然,在应付美国政府和工会方面,我们还得付出很大代价,但在资金捉襟见肘的时刻,六十亿美元足够让集团再盛三个月。何况,不再需要补贴两个严重亏损的部门,集团总支出将大大降低。但这笔宝贵的流动资金,并非简单地投入运营,而将集中力量支持亚太区发展。
但集团依然极度危险,如果三个月内没有新动作,等到这笔资金耗尽,就会无可避免地宣布破产,高管层的问题积重男返,以财务总监为首的那些家伙,总是处处与我作对,感觉我的政令不出纽约总部。明天飞往中国的计划,也是为了摆脱他们控制,大造真正属于我的大本营与亲信队伍。
上个月,我已走出了第一步。
替换我的CEO助理,马屁精莫利斯本想死心塌地跟着我混,拼命揭发财务总监“小萨科奇”等人的造反阴谋,却被我第一个解雇了!
惊我亲自出马反复挑选,从北美分公司调派了一名基层业务经理——三十对的德裔白人,曾被外派到中国、中东、拉美等分工四,我与他秘密长谈三次,每次超越三个小时,发现他具有全球化视野,有独立主见,不会人云亦云,更不会溜须拍马,对我提出许多反对意见——完全不用于原来的高管层,可以培养成我的心腹。
还是莫妮卡死后的第四个月,我的表现已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一个不到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最高职业资力不过是小小的销售员,却可以指挥天空集团这样的跨国巨头,成功出售拥有上万雇员的两个老牌部门。
但我依旧谨小慎微,保持高思国的低调作风,拒绝所有媒体专访。自从跑车拍卖会的刺杀事件以后,更不再出席任何公众活动。我知道几天锻炼不出一个董事长,但钢铁也不是很多年才能炼成的!
永远不会忘记对莫妮卡的承诺。
但是,今天我想到的是另一个人——他仍被关押在肖申克州立监狱,在我们同处一室的数月内,他成为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朋友,让我发现真正的自己,并给我勇气寻找自由。
你们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终于,我的彻底会停在一群白色建筑前,四周荒凉萧瑟的环境,宛如月球上的科考基地。
我的秘书已给联邦调查局打过电话,否则车队会引起狱警恐慌,以为防弹悍马是来武装劫狱的。
第一辆车里的人跳下来,经过一番简短手续,其余四辆车都停再外面,只有我和座车可以开入大门。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之后,我下车走进第二道大门,只有两名保镖可以跟随左右,但佩枪都被狱警卸下。
果然看到一张老面孔——典狱长德穆革,这家伙居然没被免职,因为我被证明是清白的,这次越狱并未危害社会,所以他被减薪后留用了。
原以为这回冤家聚头,德穆革会趁机对我发难,却没想到他满面笑容,仿佛老朋友久别重逢,几乎要把脸贴到我的屁股上了:“哎呀,高董事长!热烈欢迎您莅临肖申克州立监狱,大家热烈欢迎!”
他的身后站了一排狱警,全部穿戴整齐的制服,抬头挺胸站得笔挺,富有节奏地大力鼓掌,好像奥巴马前来视察!
其实,这些狱警早就对我恨之入骨,因为我的越狱让他们砸掉三个月薪水。
只有犹太人德穆革拎得清,知道我早已今非昔比,成为堂堂天空集团大老板,更要趁此机会好好拉拢关系,免得将来退休之后晚年凄凉。
看着他那副满口马屁的嘴脸,听着他说每天都想念我的肉麻话,真想抽他两个耳光,大概这家伙也会欣然接受,再换另一边的脸让我继续打。
贱就一个字!
“高董事长,我在就看出你是非凡人物,能够逃出这座监狱,更证明你有超人智慧,你现在是我们最大的偶像啦!”典狱长德穆革已说得眉飞色舞,每一个音节都散发着贱味,“;来来来,快到我的办公室坐坐,我为你准备了上等的咖啡。”
“对不起,我来这里是为了见一个人。”
“难道不是我吗?”
他还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呢!
“不,是我的室友萨拉曼卡。马科斯。”
“什么?”德穆革的目光骤然掠过一丝恐惧,“你是专程来见他的?”
“是,我想现在就要探视他。”
“这个……这个……这个……”
他的吞吞吐吐让我有几分担心:“怎么了?他提前释放出狱了?”
我知道老马科斯今年就该刑满释放了,但不会这么早吧。
“不是的,真是太不巧了!太不巧了!”
“到底怎么了?”全然不顾典狱长在此惟我独尊的地位,抓住他的肩膀大喊,“告诉我!”
没人敢来阻拦我,德穆革也卑贱得像只老鼠:“对不起……就在昨天半夜……老马科斯……心脏病突发……死了……”
“死了?”我突然松开手,但又固执地摇摇头说:“不!不可能!你在骗我!他那么健康,怎么会突然就死了呢?就在我来看他的前夜,是不是你们害死了他?”
说完我一拳砸到典狱长鼻子上,打得他满脸鲜血。若平时谁敢袭击典狱长,早被抓起来痛打一顿,关上两个月的禁闭,在追加两年刑期。单我打他却谁都不敢动,就连他自己都抹着鼻血爬起来,孙子似的哭丧着脸说:“高董事长,你相信我吧,这完全是个意外,我知道老马科斯是你的朋友,我哪敢害死你的朋友呢?不信你可以去停尸房看看他。”
我仰头长叹了一声,许久没回过神来,仿佛老头传奇而不屈的灵魂,依旧飘荡在肖申克州立监狱的上空,一如永远流传的掘墓人的阴影。
老头啊来头,你怎么没有等到我回来的这一天呢!
HERO啊HERO,你怎么没有早点来看你的好朋友呢!
再也不用和典狱长罗嗦一个字,就在他苦苦哀求我息怒之时,我一言不发地拂袖而去。
走出监狱白雪覆盖的大门,保镖簇拥我上了悍马,车队迅速掉头驶力此地。
永别了,肖申克州立监狱。
永别了,老马科斯。
我将成为一个真正的Gnostics,谢谢你!
基督山伯爵得到了看得见的财富。
而我得到了看不见的财富。
那就是我的命运。
明天,就在明天。
我将回到中国。
第十三章 王者归来
中国。
2010年,除夕夜。
深夜,十一点。
我的中国我的国。
我的天空我的天。
我的人间我的人。
十几个小时的长途旅行,天空集团专机飞越太平洋,降落在浦东国际机场,舷窗外闪烁停机坪的灯火,是黑夜梦幻的宫殿,而我只是这座宫殿谦卑的仆人。
此刻,我绕着许多人眼中的挂能够换,作为天空集团全球董事长兼CEO,却丝毫不敢想象“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这些字眼——我的天空仍然危在旦夕,我的人间依旧云遮雾绕,我的眼前黑夜连绵不断,我的敌人还躲藏在秘密角落,此行必须为集团开拓一片蓝海。我是唱着《大风歌》归来,而是肩头压着千钧负担,时刻内心惶恐夜不能寐。
飞机降落的刹那,心底一阵莫名冲击,不仅来自于地心引力,也因为离家太久了——掐指算来竟已有十七个月,这个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愿不要感觉太陌生。
终于,我踏上故乡的土地,长途飞行让人几乎站立不稳,双眼触电般无法动弹。冬夜的机场寒风呼啸,秘书赶紧给我披上厚厚的大衣。四辆加长版凯迪拉克早已开入停机坪,天空集团亚太区的牛总,放弃了回台湾过年,除夕之夜留在上海,带着一群黑衣人迎接我。
很多人以为我会第一个消除牛总,因为他曾批准将我裁员,但我力排众议留用了他,反而令他对我感激涕零——尽管当年失业让我痛不欲生,但一切都是过去时了,我已不会再怨恨任何人,只要他还能证明自己的能力——亚太区业绩是全球各分公司最好的,作为集团高管层唯一的华人,牛总是我改造天空集团的一枚重要棋子。
牛总跑上来与我握手,照例又是嘘寒问暖了一番。他给我安排了一批中国报表,虽然不能像在美国那样佩枪,但都是身怀绝技的退役特种兵。
我坐进新专车,认识了新司机与中国秘书。牛总特地坐在我身边,自然想要拍我马屁。但我没有任何客套话,上车就是开门见山,直接询问亚太区业务情况。牛总已做恶劣充分准备,打开笔记本汇报公司各项数据。
车队飞快地开出机场,虽是午夜空旷的道路,开进市中心却还需要些时间,我忽然问了一句题外话:“几点了?”
“十二点整。”
虎年到了,但我并不因此而兴奋,却喊道:“快点打开电台!”
“什么?”
我撇开牛总对司机说:“打开电台!”随后报出了一个电台的频率。
司机的反映倒是很快,车载音响迅速响起——
“随着我们节目的开始,新的意念也来到了,我在电波中给听众们朋友们拜年!这是个寒冷的除夕夜,不知道会不会下雪?我的声音将始终陪伴在你左右,这里是‘面具人生’,我是秋波。”
是的,就是这个广播节目——《面具人生》,这个充满磁性的声音,这双永远看不见的眼睛。虽然离开中国一年半了,回来想起的第一件事,却是电台里秋波的声音。
我闭上眼睛完全沉醉,回到2008年的夏天,内心最挣扎郁闷的时光,她的声音曾陪伴我度过绝望。
车子飞驰在午夜大道,善于察言观色的牛总,再也不敢打扰我了。司机把音量调到更大,寂静车厢内只剩下耳边的秋波,仿佛地就在坐在我的身边,倾听我那曲折而悲伤的故事。
接听完几个电话之后,秋波轻轻苦笑一声,似乎隐含着某种苦楚,那是比听众的故事更深的无奈,她的声音故作轻松:“女孩,请不要再哭了,今晚是大年夜,可不能流眼泪哦!我这个双目失明的人要个告诉你,无论你多么自卑,无论你多么伤悲,请相信一句话——野百合也有春天!”
停顿了几秒钟后,电波里响起罗大佑的歌声:
仿佛如同一场梦
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
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
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
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用不变
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
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
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也野百合也有春天
我和司机、秘书还有牛总,都屏着呼吸慢慢听完。台湾人牛总年轻时也是罗大佑的歌迷,不知在悼念那段逝去的连请,叹息着道:“野百合也有春天,可惜我已经老了。”
听这首歌的前半段,我的脑中自然浮现起秋波的脸庞,后半段却想到了另一张脸——“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用不变”,唱的不就是我的莫妮卡吗?她像一阵春风吹入我心中,又像一片秋雨消失在遥远的大陆。但她不曾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只是去了那个遥远的天国,自己成为一株常开不败的水仙。而我曾经是,现在也依然是,那朵寂寞的山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