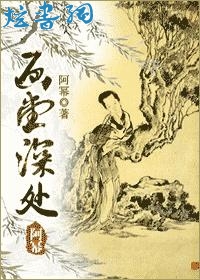骷髅画-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私通乱党,翼助叛逆,犯的是通匪大罪,冷血脸色变了变,反问道:“这案子结了么?”
李鳄泪怔了一怔,“什么案子?”
冷血道:“盗响、杀人、抢画的这一件案子,已查明了是‘神威镖局’和‘无师门’的人所为了?”
李鳄泪道:“犬子确是‘无师门’的人杀的,有言氏兄弟、易映溪、聂千愁为证,画也同时失窃;那笔税饷的确是‘神威镖局’的人监守自盗的。他们局里的镖师就可以证明此事。”
冷血不知怎的,突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像流星自长空划过,刚亮起便熄灭了,再追寻却已无从。冷血却知道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已没机会再想下去,只说:“黎笑虹?”
李鳄泪似乎微有些错愕,随即道:“便是。这个镖师大义灭亲,勇气可嘉,我已将之严密保护,任谁也不能伤害他。”
冷血哼道:“案子审判了没有?”
李鳄泪一愕道:“这倒还没有。”
冷血紧迫地道:“既然案子尚未定罪,那‘神威镖局,和’无师门‘的人充其量只能说是嫌疑犯罢了。我协助他们只是为了要方便破案,不能说是纵犯。”
李鳄泪也冷笑道:“冷捕头,万一他们真要是罪犯,你知法犯法可也不轻……你知道,定他们的罪是再轻易不过的事,冷捕头跟他们非亲非故,前程远大,犯不着为他们冒险。”
冷血道:“不过在真相未大白之前,只要一天未审判定罪,我就有责任去追查真相,弄清楚谁才是真凶,谁才是受害人。”
这一句话一下,两人都静了下来。
好一会,李鳄泪才大笑道:“好,好!有种!有志气!”
然后说了一句:“你可知道,傅丞相那儿也来了几位朋友?”
冷血淡淡地道:“有李大人在这儿坐镇,傅丞相还用得着操心吗?”
李鳄泪神神秘秘地笑道:“冷捕头太看得起在下了。傅大人神机妙算,计无遗策,烛见万里,自比我等识见高妙得多了。也许他老人家早已算出这次剿匪的事有阻挠吧,丞相大人体恤军民,特遣身边三名爱侍:‘老、中、青’三位高手过来,披荆斩棘,摧陷廓清一番,看来,这次盗匪可谓劫运难逃了!”
冷血长吸一口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自牙缝里吐出来:“老、中、青?”
李鳄泪眼睛闪亮着:“老不死、中间人、青梅竹。”
冷血的手紧握剑柄:“是他们三人?”
李鳄泪人没有笑,眼睛却笑了,笑得满是狡狯之意:“当然,他们三位来意只是杀叛贼、起回贡品、押送税晌,与冷捕头无关。”
冷血抿起了唇,使得他坚忍的五官更加倔然:“这个当然。如果是为冷某而来,李大人和‘福慧双修,以及这里百来位哥儿儿们,已绰绰有余了,何需烦师动众。”
李鳄泪的黑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道:“冷捕头知道就好。”
冷血道:“不过,纵是为了抓拿反贼,护送贡品、保押镖银,出动到‘老中青’三位,也未免小题大作了罢?”
李鳄泪笑道:“这是呈给皇上的贡品,反贼胆敢窃夺,傅丞相处处为皇上效忠,自然派高手平定。”
冷血点点头,道:“如果没有什么吩咐,李大人,在下就告辞了。”
李鳄泪忽道:“冷捕头,传言中你有一柄天下难得之快剑,吾久欲观之,今日得逢一见,不知可否赐下一赏?”
冷血愣了一愣,李鳄泪虽然不是他直属上司,但官位极高,冷血如非分属御封“天下四大名捕”之一,有免死铁券、生杀金牌的话,李鳄泪倒可一语格杀之。
据说冷血的武功,全在剑上。
而今李鳄泪竟提出了一个要求:要看他的剑!
如果冷血没有剑,对方动手,他用什么武器还击?
如果冷血拒绝给他观剑,那么,敌意毕现,李鳄泪一怒之下,下令攻杀他,这局面又如何应付?
冷血刷地拔出了剑。
李福、李慧身子一晃,已掠到李鳄泪身侧,手按剑柄。
李鳄泪微笑依然,神色不变。
冷血托剑平举,剑尖离李鳄泪胸膛仅及一尺,道:“请看。”
李鳄泪缓缓地、缓缓地,用两只手指,夹住剑锋,眼睛盯着剑势,一眨也不眨,笑道:
“这样赏剑,未免凶险。”
冷血却一震肘,“福慧双修”锵然拔剑,不料冷血把剑柄已交到李鳄泪手上,道:“李大人厚爱,请拿去观赏便是。”
冷血这种做法,无疑是等于把剑全交到敌人手上。
这连李鳄泪脸上也变了变,李福、李慧两人各望一眼,怔怔收回长剑。
李鳄泪拿着剑,嗤嗤在冷血身前划了两个剑花,只闻剑光犹在剑风之先,李鳄泪道:
“好剑,好剑!”
这刹那间,也静到了极点,只有老者惨淡的咳嗽声。只要李鳄泪陡然出手,或一声令下,冷血只怕就难免杀身之祸。
李鳄泪双眼凝视着剑身,剑光映寒了他的脸,他忽将剑递回给冷血,道:“剑看过了,好剑法!”
他不赞剑却赞剑法,众皆愕然。冷血接过了剑。李鳄泪一稽首,返身呼道:“启轿!”
步入轿中,整队起驾而去。
冷血抓住剑柄的五指,因过分用力而发白。待队伍远去之后,他汗湿衣襟。
捕王静在那儿,李鳄泪由始至终,未曾正式望过他一眼。他是名动八表的捕王,因人皆不识是他,所以谁不觉意他的存在。他站那里,有种深沉的悲哀。冷血感觉到了,不过这悲哀之外似是有一种更深沉的遽动,冷血就不了解了。
轿子队伍走了好一段路,在轿旁的“福慧双修”还互观看,弄不明白:——那明明是一个除此眼中钉的大好机会!
李福、李慧是李鳄泪的义子,两人武功都由李鳄泪亲身指点,李府之中,以聂千愁武功最高,但最贴心的是这李福、李慧,其次轮到言氏兄弟和易映溪。
在轿里忽然传出了声音:“你们都觉得奇怪,是不是?”
李福、李慧惶惑的对望一眼,感觉到轿中人仿佛能洞透他们心中所思似的。
“我也想杀他,”轿里的李鳄泪发出一声叹息,“只是,我才拿到他的剑的时候,旁边那个痨病鬼,突然发出比剑气还要凌厉的锋芒!”
李福、李慧大吃一惊,没料到那个看来毫不起眼的褴褛老者竟有那么大的威胁性!
“我纵能一举杀掉冷血,但是,不一定能制得住这两人联手;”李鳄泪仿佛很惋惜,“没有把握的事,我总要等待时机、等到更有把握的时候才做。除非……除非是逼不得己……希望这逼不得已的日子永不要来临。‘”
“其实”老中青‘主要是负责取回骷髅画,上头派了一个人来,这个人才是四大名捕的死敌。“李鳄泪的声音在微微颠簸的轿子里显得很恍惚:”这个人除了奉命杀叛死贼外。必要时,还可以把四大名捕逐一自世间消失。“
李福失声道:“捕王?”
李慧接道:“李玄衣?”
李鳄泪道:“便是捕王李玄衣。我接到线报,李捕王已逼近这一带……”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低沉得只有李福、李慧两兄弟听得到:
“……其实我刚才也不想动手,因为,我带来的人那么多,难保没有一个泄露出去说:
冷血是我杀的,这样,我不但要受到各方面的指责,而且,还会引起诸葛先生对丞相大人起疑心,预早防范,这叫小不忍大谋则乱。“
李福也用一种很低微的声调问:“这些人不都是忠心耿耿效忠大人的吗?”
李慧亦用细微的语音道:“谁有异心,请大人指示出来,我俩兄弟先把他剜心剖肺!”
李鳄泪淡淡地道:“谁是卧底,我不知道,但卧底想必是有的。诸葛先生的心腹,不也一样安排了我们的人吗?以诸葛先生的智慧,不可能完全没有安排的。要做这些事,可以暗的来做,三几个人来做,不然,我们只干掉他一个手下,却落入人口实,乱了阵仗,那就化不来了。”
以李鳄泪与“福慧双修”的功力,说话要只他们三人听到,那就决不会有第四人听见;纵然有“第四人听,”也不敢听。
李福李慧听得又敬又佩,齐声道:“是。”两兄弟心中都同时想到:政流斗争汹涌翻沉,但有李大人在后面罩住、傅丞相前面指示,他们一定能官运亨通、出人头地、平步青云、稳操胜券的。
李鳄泪的心里却在寻思:那个痨病鬼是谁?那个痨病鬼到底是谁?
第二章 名捕与捕王
冷血和老者又走了很远,鸡啼和鹅叫掺在一起,还有犬只汪汪地吠着,这些声响交织起来,使人想到幽静的村落,还有慷倦的午憩。
冷血望到远处有一棵树,强悍的棕色树干托着一大把茂盛的翠绿,却在盈活的翠意里,长着一丛又一丛的鲜红花朵,好像鲜血绽在青苔上燃烧,美极了。
老者咳嗽着说:“青田镇,快到了。”说着自衣襟里摸出包芝麻酥,是刚才小滚水的村民送给他路上吃的,“你饿不饿?一起吃罢。”
不料才打开纸包,芝麻酥像粉未一般散倒出来,老者一时没提防,掉了一地,老者愣了愣,用舌头把纸包上余剩的饼未舐了个干净,又吹了吹沾有粉未的手指,还颇惋借的看着沾着星星自粉的裤管,解嘲的人道:“嘿,没想到这面粉发得不匀,都碎散了。”
冷血淡淡地道:“不关面粉的事,刚才您聚起功力,吓退李鳄泪,撂在怀里的芝麻酥,又怎抵受得住?”
老者许是因为舐饼末时呛了喉,大声咳嗽起来,支吾地夹着语音道:“哦?是么?我自己还不知道哩……”
然后像意外似的发现远处道旁有一座茶寮,喜道:“我们过去泡杯茶再说。”
虽然是在晌午,这茶馆十分冷清,人客也没多几个。冷血和老者坐下去后,老者就不断地在咳嗽,冷血问那小二:“有什么吃的?”
店小二说了几样,都是馍馍、烤黄豆之类,冷血于是叫:“来碟毛豆,两个枣泥馅的自来白,一碟花生和两碗龙须面——还有没有卤肉?”
店小二苦着脸道:“客倌,这儿一带,哪还有肉吃?别说枣泥馅的,就算蒜泥馅的也没有。——就吃卷切糕。将就点好罢?”
冷血忙道:“好的,好的。”店小二一搭白布转身去,冷血忙喊:“来两碗高粱!”
店小二又苦着他一向就已愁眉不展的脸容道:“客倌,这儿哪来的高粱!”
冷血只好道:“自干,白干吧!”店小二这才去了。
老者一面吃力地咳嗽着,一面挤出了话:“随便点,随便点吃。”
后来桌子也有几个人,一个也是愁容满脸,一个嘴里怨气连天,一个更惨,吊唁般的脸孔。只有一个矮子,笑嘻嘻的,一副什么都可以的样了,看装束言谈,都是乡巴里人。
怨氯连天的人道:“两位敢情是外地人,不知道这里比兵荒马乱还凄惨,咱们这儿,纳完前贡又后税,咱们做牛做马。也缴不完苛税暴征!”
那吊唁脸孔的人着急地示意说话的人示意道:“小心,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冷血道:“诸位放心,我不是来征税的公人,贵乡的税收,怎么这样厉害法?”
愁容满脸的人仿佛脸上写满了“愁”字,以致说话的时候一个个“愁”字吐了出来:
“在我们这儿,多养一只鸡就多一只鸡的税,多种一棵树就多一棵树的税,所以我们宁可把鸡宰了,把树斫了,可以省下重税。”
冷血道:“你们不是已经缴了税么?”
怨气连天的人道:“你以为这些税银容易缴么,交不出来的有上万的人,他们现在,不是死了,就四肢不全,或在监牢里等死,或者充军垦荒去了。”
冷血勃然怒道:“哪有这种事!谁执行这事的!”
那怨氯连天的人哈了一声道:“这你都不晓得么!官府呀,当然是官府呀!”
老者喃喃地道:“这还有王法的吗……”
愁容满脸的人道:“这儿只有无法无天,没有王法可言。”
老者问:“那您阁下的税可缴出了没有……?”
愁容满脸的人惨笑道:“我们一家五口,一年辛劳工作所得,不过三五两银子,而今税收六两,教我从哪筹去、我要交得出,也不必成天愁眉苦脸了。”
老者又问那哭丧着脸的人道:“你呢?”
哭丧着脸的无精打采的说:“我祖上三代,一块田也没剩下来,跟人耕作到现在,那官吏不知怎的一算,算到我有田七亩,不由分说,要我缴税……”说到这里,真要哭出来了,“您老说,教我打哪儿拿银子交去?”
冷血只好安慰他,见怨载连天穿得较光鲜,便问:“您——?”
怨气连天的道:“我刚把老婆卖到外省去,交了年税,不料又报称税饱叫人劫了,现在,叫我卖什么好?”
冷血苦笑了一下,见剩下一人仍笑嘻嘻,心里有一线希望,问:“人人都为缴税苦,阁下倒是欢容满面,不知——”
笑嘻嘻的人仍是笑嘻嘻,木然地望着冷血。
怨气连天的叹道:“唉,他已经给征税的人逼疯了,哪能回答你!”
哭丧着脸的人道:“我们带他吃完这餐,就任由他自生自灭了,我们也没能力再照着他了。”
愁容满脸的人道:“我倒羡慕他,一家子死的死,疯的疯,猪也没养一只,连块遮雨瓦也没有,倒是不再怕征税了。”
冷血听了,极为愤怒,这时酒菜已经上来了,酒菜淡粗,颇难入口,老者仔细而津津有味地吃着,吃到一半时,后面那四人便叹息怨愤着离去。
冷血仰脖子一口干尽了杯中酒,道:“天下哪有这样子的征税法!”
老者淡淡地道:“偏偏此际天下都是这样子征税法,只是看执行者是不是变本加厉,贪得无厌罢了。”
冷血忿然道:“这样子,怎么不变得官逼民反!”
老者在吃着最后一块卷切糕,并小心地掏起最末一片葱丝,听到这话,忽抬起眼来,眼光森寒:“你这句话要是给别人听到,报上去可是抄家之罪!”
冷血冷笑道:“抄家就抄家,我没有家,要就定我一个死罪!”他本来不喝酒,由于激于义愤,便喝多了,再斟时壶已干了,扬声便喊:“小二哥,再来瓶酒!”
小二懒洋洋地应:“大爷,小店就只有这些,再喝,也没有了。”
冷血也没心情吃得下,匆匆便起来付帐,老者慌忙道:“我吃的,我来付。”只见他连馒头皮也吞个干净,见到有脏处便用手揩去,揩不去的也照吃不误。
冷血道:“这餐要您赏面,算我付的。”
老者道:“不行,我付,我付。”
冷血摇手道:“这小小意思,还算什么!”
老者正色道:“我吃的钱由我付。”
冷血这才意识到老者的坚持,愣了一愣,便道:“这,这一点小钱,怎么算呢?”
老者一字一句地道:“我向不习惯被人请。我用劳力赚来的钱,替自己付帐,我不要人请,也不要请人。”说罢,又剧烈地咳呛了起来。这次咳得那么剧烈,仿佛连肺叶都要呛出来似的。
冷血忙道:“好,你付,你付。”他加了一句,“你请我好了。”
“不,我不请你。”老者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老实说,我请不起你。”
他自怀里掏出了一些碎银,算着算着,还不到一两银子,老者苦笑道:“实不相瞒,我的俸薪一年只有四两银子,只能省着用,不能乱花的。”
冷血看了于心不忍,道:“尊驾的工作,年饷这般的少,如——”
老者截断他的话,脸上浮现了一个满足的笑意:“我喜欢我的工作,钱,多少不是问题,何况,我已干了三十多年,不想再转行了。”
冷血也顺着他的意思,没有再说下去,但仍颇为难的看着他手上的碎银。——那五钱的帐只怕这小店还找不开来。
老者把碎银端到鼻端细看着,仿佛舍不得,又似分辨不出,那店小二正要苦着脸说:
“客倌,你给我这撮碎银,我们还是找不开的呀———,话未出口,却听喀哧一声,老者用拇食二指一捏,真的切下一小截正好值五六钱的银子来,塞到他手心里。
店小二直了眼珠,不相信他刚才看到的是真的。
冷血也吃了一惊。他知道这老者武功深得不可测,但不知道对方内力竟深厚到了这个地步;那块碎银只有指甲般大,要用两只钝指夹下小月形的一块来,这是连冷血都无法办到的事。这人的武功大大超出了冷血的估计。
老者再用手秤了秤,似乎对自己切得很适当,很满意,点头起身道:“走了。”
两人走了出去,沿官道行着,附近人家也多了起来。沿路的溪流都有缝纫机的声音,吱咕传来,又有捣衣声,咯一下咚一下的,都是人间清平乐好的声音。
忽见一家屋字竹篱外,有几匹官马停着,门前有人吵闹着。
只见一个师爷打扮的人物,手里翻着本黄皮册子,另一只手持毛笔,眯着眼凑近书页去看,另外有两个衙差,干瘦的一个托着砚钵,供师爷书写,粗壮的一个手里握着刀柄,一手扬鞭,大声的呼喝着:
“挨千刀的,你们的税,给是不给!”
那屋门前的老头儿拄着杖几乎没跪下去,哀求道:“宫差老爷,再通融通融,再通融通融吧!”在他身旁还有一男一女,是儿子媳妇。
那师爷“嘿”地一声,好暇以整地道:“生寿老爹,你这是啥意思你要我们通融,咱找谁通融去?这可是天子皇命交下来的差事,咱们有几个头,敢不依时依候做好挨砍头?
吭?“
生寿老爹皱纹折出了老泪,哀求道:“师爷,再宽限多几天吧。”
那扶着他的男子生得黝黑,是他的儿子,怒道:“你们讲不讲理,咱们只养了一口猪,却要纳一头牛的税,这算什么嘛。”一老一少都用悲愤但情知无力的眼光望着来人。这时,屋里传来婴儿的哭声,那女的匆忙把手在围裙上擦两下,一扭腰就要转入屋里去。
那师爷仿佛这才发现那女人似的,用他那又瘪又瘦的身子一拦,涎笑着说:“这女人是您媳妇儿吧?”
那男子气冲冲地道:“你要怎的?”
师爷一耸肩嗤笑道:“没什么怎的,”转过头去问生寿老爹:“要纳一头牛还是一口猪的税,要看我手上的笔了。”
生寿老爹一声声地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