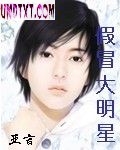调教大明-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他紧握着的这个女人,是自己在这个时代最亲近的人,松了手,他就成了真正的无根浮萍,什么依靠也没有了。
马蹄声越来越近了,同时似乎还听到人的沉重呼吸声,那是嗜杀的凶兽在杀人前的激动的喘息,在这样的野兽面前,哀求乞怜毫无用处。
“乖惟功,你不要怪你生父,他有他的苦衷,如有可能……”
最后关头,许素娥到底没有把惟功生父的信息全部说出来,而是用尽全身力气,甩脱儿子的小手,往相反的地方跑过去。
“娘!”
张惟功撕心裂肺的叫起来,眼看着娘亲奔向死亡,叫了一声之后,他反过身来,往着深山的方向跑过去。
跑……跑,一直跑!
似乎只有自己的呼吸,呼吸的太快了,胸膛都似乎快燃烧起来,两只腿也似乎不再是自己的,只是不停向前的工具。
脚很快磨烂了,因为布鞋跑丢了,等他窜进荆棘从中,被针叶拉的全身是血的时候,全身已经木直僵硬了。
良久之后,他才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感觉到全身都在疼痛着。
马蹄声在四周响了很久,他听到追赶的骑兵彼此商量,为了推卸责任,打算回去禀报时说他已经掉落山崖而死。
其实一个山民小孩,便算不死,又能如何?
在这个时候,他才听的真切,这一股明军是辽东镇李成梁总兵官麾下,领兵的将军,姓陶。
在灌木从中,惟功冷笑起来,他擦了一下眼角,隐约也有血迹。看娘亲的那一眼,用尽了全身力气,眼角迸裂了。
他没有在意眼角迸流出来仍然不停流淌的鲜血,只看着村落的方向,轻声道:“此生,誓杀汝!”
万历二年春的边患只是小患,甚至都不大有资格被记上史册,在几年之后,插汉部大举入侵,规模是成千上万时,这才被兢兢业业的史官们记录上了一笔。
只有在辽东镇上报给兵部的文告上才有这么一笔记录,万历二年五月十七,插汉入寇杨家台,辽东陶游击率部出援,是役斩首五十五级,算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
陶游击因此加封为都指挥佥事,世职荫千户,兵部上报给皇帝之后,小皇帝私人给陶将军赐银五十两。
寥寥几笔的文告根本没有多少人关注,没有人知道,几十个字的文书背后浸透了山村中普通百姓的鲜血,小小村庄的下场在陶将军的报告中是被蒙古人夷平了,妇孺要么被掠,要么遇害,村庄也被焚毁,善后事宜,边镇将领不便插手,交给当地官府处置了。
因为村落无人,官府也没有花力气重建,这一带地广人稀,就算是余留下来的土地都没有人眼红,几年之后,整个村庄成为一片废墟,被灌木和野草围绕其中,其间发生的一切,对活着的人来说都只是故事了……
……
张惟功在山中藏了五六天,在陶将军和地方官府扯皮打笔墨官司,县上官吏来查察村庄损失,统计死难人数的时候,他根本没有露面,只是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
亲身经历官兵杀良冒功之事,使得他对大明的朝廷和官府已经失去信任,谁会相信一个孩童的话,又有哪个地方官会为一个小孩的话得罪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
一直到官吏们和官兵都退走,整个村落再无人踪的时候,张惟功才如一只小猫般的溜回了村中。
五间茅草屋曾经是他的家,现在已经被焚毁了大半,只有房梁屋架还犹在,烧秃了的院墙和房顶看起来如一张惊愕的脸,透着一股难以言表的凄凉和诡异。
一切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包括爹和娘的尸身。
这些天,官府一直在善后,爹的尸身怕是多半被斩去首级,剃掉头发,当成蒙古人送去报功了,娘的尸身,怕是和遇难的妇孺一起,被葬到乱坟岗中去了。
这一次张惟功没有哭,他在屋中翻出一个瓦罐,将院中的黑土抓了几捧,放在罐子之中。
将罐子毕恭毕敬的放在残破的堂屋正中后,他伏在地上,郑重叩首。
在后世,他是一个孤儿,在今世才知道父母之爱,可惜,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还有人呢……是个小孩。”
“莫不是就是那主儿吧?”
“看年纪,象!”
院外突然响起人声,惟功回头一看,见是一个头戴着瓦楞帽,身着蓝色长袍男子骑在一匹健骡上,瓦刀脸,三角眼,山羊胡,正目光炯炯,上下打量着自己。
两个穿着青色上衣,灰色上裤,腰身杀着布裤带的小厮模样的,也随着骡身上的男子一起盯着自己看。
适才的议论声,自然是他们发出来的。
“兀那小孩,你叫什么名字?”
这般无礼,惟功又是伤心惨痛之时,原不想答他,想起适才这三人的话,心中一动,便是答道:“姓张,名惟功。”
“妙,妙极了。”瓦刀脸十分高兴,从骡子上跳了下来,整张脸都放出光来。上下打量着张惟功一小会后,便是点头道:“名字对,模样象,对了,这一次可是真对了!”
第四章 途中
瓦刀脸叫杨达,打京城里来,天子脚下精明外露的人物,在大宅门里头当外宅执事,这样的人没要紧的事儿是不大可能出现在这距离长城防线不远的小山村里头……他此行的唯一任务,便是寻访张惟功。
“小人见过五哥儿!”
杨达长揖,跟随他一起过来的两个小厮也忙不迭过来,兜头便拜。
张惟功有点楞征,知道自己娘亲不是寻常人,但……这也太戏剧化了罢!
“你们是何人,为何来拜我?”
“这个……五哥儿身份尊贵,绝不是寻常人家,等回去见过了太爷,大爷、二老爷,自然就有说法,但请放心!”
杨达一心拿张惟功当一个寻常人小孩,料想山村居住,能有什么见识?当下没口价只哄着骗着,一句实在话也不曾说,哄了几句后,又叫跟班拿出预备好带来的泥人儿等物,哄张惟功玩。
见状如此,张惟功心知有异,于是装出懵懵懂懂的模样,拿了泥人儿在手中玩弄不已。
这村落如此模样,杨达原本也是绝望的了,能遇到劫后余生的张惟功,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运气。
历史在这里转了一个小小的弯,但所有的当事人都是茫然无知。
眼见此地不宜久留,杨达将自己的大黑骡让了出来,抱了张惟功在骡子身上坐稳了,然后两个小厮一前一后牵着骡子,一行四人,往村庄外头逶迤而去。
在踏上出村的石桥时,张惟功悄悄回首,身后这一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梦中再见了……
……
一日之后,杨达一行抵达迁安县境,在县城骡马行租了一辆大车,杨达和张惟功坐车,两个小厮骑骡相随,一路上十分辛苦,骡车十分颠簸,春夏天时干燥,可容四五辆大车并行的官道上浮土有半条腿深,一阵风刮过来,整辆车的人都是灰头土脸。
杨达为了赶路不免省却了享受,每天按着驿站的点赶路,国朝天下有一千五百多个驿站,往辽东的驿站星罗棋布,沿途每隔三十里便是一个,再夹杂骡马大店和急递铺等补充,只要想赶路,尽可风驰电卷一般往前便是。
每到一处驿站,杨达便取出怀中所藏的兵部发给的勘合,入内吃饭或是住宿,都与出公差的朝廷驿使或是官员一样,他明明不是官员,亦非公差,但只要有勘合在,便但住无妨。每住一次,还要补充清水和干粮,或是一些零碎用具,驿站无不供给,十分方便。
张惟功冷眼看着这一切,倒是长了不小的见识。
从迁安过丰润、玉田,再往前不到百里,便是蓟州。
过了玉田境最后一个驿站时,杨达明显松了口气的模样:“过了蓟州就是通州,离京城不过几十里,就算是到了家啦。”
杨达的北京口音和后世的北京人还是有点儿区别的,词汇更有很大不同,语音也稍硬一些,仔细听的话,还有一些南直隶一带的口音,再有一点儿河南口音……令张惟功感觉十分之怪异。
“杨爷,前头似乎有一伙剪径的贼。”
杨达闻言一震,对说话的小厮沉声道:“春哥儿看仔细了。”
“看多少次了,错不了。”
“好家伙。”杨达皱眉道:“通衢大道,他们胆子可真大。”
说是通衢大道,但官道上黄土漫天,两边是农田阡陌纵横,有一些土地不适合耕作的,就是大片的荒地,人烟稀少,此时天色将黑,确实是抢劫的好地方。
张惟功好奇心起,趴在车窗往前方看,见到几个戴高椎帽的少年,以粉涂面,打扮模样十分怪异,身形有高有矮,骑在黄马或青骡之上,呼哨来回,一看就知非善类。
“坊间恶少年,尚不算正经响马。”
和张惟功一样观察了一会儿之后,杨达便放了心,倚回车壁,吩咐道:“春哥儿和秋哥儿一起上,惊走他们便是。”
“是,杨爷放心。”
两个小厮都是十七八岁年纪,最喜欢生事的年龄,一路上来回奔波,着实腻味,杨达一发话,两人便是满脸兴奋,立刻策骡向前。
离近了之后,倒是看见这贼年纪不大,高冠涂粉,打扮怪异,身上衣饰凌风飘摆,是上好的丝绸所制。
“你这小子不学好,吃俺一弹。”
春哥儿是喜欢生事的年纪,看着对方年纪似乎和自己差不多,更起争胜之心,但见他手在胸前一翻,一副打造十分精良的弹弓已经取在手中,左臂前舒,左手持弓,右手引丸,电光火石之间,一颗弹丸已经“嗡”然一声,往着对面的恶少年直飞过去。
身手这般利落的小厮,张惟功又是吃了一惊。
穿越这几年,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小山村里,所见最厉害的无非是村中顶尖的猎户。这个时代,在很多方面是无法和后世相比的,但在一些需要手艺和苦功,还得有耐心和时间的事情上,却是有后世工业化时代不能比的优势。
几百年后,是不大有可能使得一手好猎弓的猎人了,至于费十几二十天功夫,从找寻地点到挖坑,再到守候猎户,这般的细致心思,更无可能。如大明南京那样,绣金织锦的特产名胜,数百年后工业产出的成品反而不如,这就是人力用到极致的区别所在。
春哥儿这一手,动作漂亮干净,比惟功见过的最好的猎户在反应和动作上都要快上三分,再加上弹丸的破空声,显然是劲力使的不小,这样一手功夫,真是叫惟功开眼界了。
但春哥儿快,对面的恶少年却是更快!
一般的起手式,一般的弹弓,一般的使法,这边弹丸已经破空而出,那边才刚刚反应,但在场所有人但听得“叭”的一声,两颗弹丸却是在半空相遇,大力之下,在半空中撞的粉碎!
张惟功看的目瞪口呆,对面把脸涂的象鬼一样的小丑模样的少年,居然使出这么一手漂亮的弹弓术!
这一手功夫,便是山村里使了二十年弹弓的老猎手也是远远不及罢!
“好弓法……”
春哥儿呆住了,他对自己的手上功夫还是颇觉自信的,此番出来,一直没有机会用上弹弓,谁知道头一回使用,便是一头撞上铁板。
对面的恶少年露出一手神技之后,并没有趁胜追击,把玩着手中弹弓,淡淡一笑,问道:“你们是京里哪一家的?这一手弹弓,是在家里学的吧?”
“那你们听好了,咱们是英国公张府!”
杨达知道眼前之事凶险,人家有五六个人,没准还有人藏在暗处,自己这边原仗着春哥儿和秋哥儿都有不俗的本事,但春哥儿明显不如人,再不把大牌子亮出来,今天就危险了。
虽是如此,心里也是惴惴不安,这些打劫的恶少无赖哪里知道什么英国公?若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来,或是干脆杀人灭口……想到这,杨达面色如土。
“哦,是银锭桥新园出来的……”
怎料这少年一说倒是挺内行的样子……杨达几个有点呆征住了。
英国公府是国朝顶级的大世家,能位列国公,与国同休的也就是那么几家,老英国公府原本是在城东柴市文丞相祠边上,御赐的大园子,称为英国公家园,后来勋戚都多半居于城西,所以又在银锭桥观音庵附近兴建新府,称为英国公新园。
这么一点小区别,不是内行人,还真的分不大清楚。
杨达眨巴着眼皮,死盯着对面的那恶少年不放,心中着实奇怪,这位小爷,是打哪儿冒出来的怪物。
“甭盯着我看,也甭打听我是谁,今儿这事就揭过了,只当没发生过。”
恶少年仿佛看穿了杨达的心思,呵呵一笑,收起了弹弓。
他身后呼哨一声,五六个一样打扮怪异的少年全部冲了过来,笑骂声中,一起越过骡车,往过来的路折返回去了。
“今日之事是玩笑,你们在驿站时是不是脾气不好,这位管家爷拿皮鞭打了个驿夫?”临行之际,为首的恶少驱着大青骡停在骡车一旁,皱着眉道:“驿夫是苦人,下回别这样了。”
“是,是!”杨达满头大汗,哪敢驳辩,他这才知道,人家不是来劫道,却是替别人打报不平来了。
“我走了,这小孩好玩,一点不怕咱们。”离的近了,这涂粉脸的少年才被看的清楚,原来年纪也不大,十三四岁的样子,但猿臂蜂腰,一看便知道是身手不凡的好手。他夸了惟功一句,从怀中掏出一锭小小的金锭,抛仍过来,笑道:“拿去玩吧。”
“多谢。”张惟功知道眼前是个异人,不是普通的坊间恶少打劫的无赖光棍,小小年纪,也是郑重拱了拱手,至于抛来的金子,他倒没多看一眼。
“有意思,哈哈,有意思。”少年呵呵一笑,又看了张惟功一眼,笑道:“我记住你了,咱们有缘再见。”
说罢打着骡子飞驰而去,那大青骡也是十分神俊,四蹄翻飞,没一会儿功夫便是去的远了。
“今日好险。”杨达擦了擦额头的汗珠,看看脸上十分无趣的两个伴当,再看看张惟功,心中也是一阵索然,挥了挥手,道:“走吧,赶路要紧!”
第五章 蓟州
接下来的路程就十分顺当了,从玉田一路过了几个驿站,都是风平浪静,两日之后,终于抵达蓟州城下。
这座城池是当时的蓟辽总督和蓟镇总兵官平时驻节所在,周长十余里,是北部边境十分巍峨雄违的大城,因为军事作用强,所以城池之外,又多了二十几里长的羊马墙,羊马墙之间又建有大大小小的堡垒,箭楼,放置着鹿角拒马等军事设施,加上那些持矛挺戈明盔亮甲来回巡逻的士兵,整个城市,气象十分庄重森严!
到了此处,再往西几十里便是通州,离京城已经很近,而且人烟稠密,再不会出现前两日那样的险情,杨达几人,心思都是放松了不少。
连日赶路,各人都觉得身上乏的厉害,杨达曾经来过蓟镇,熟门熟路,带着大家从东门进城,验过勘合路引等物,顺顺当当的进了城。
张惟功还是头一回来到这样规模的大明都市,坐在车上,两眼四处观望着。
这座城池,不愧是军事重镇,城中到处都是穿着各式甲胃的军人,平民和文吏、商人相加的起来都远不及军人为多,而军人的精气神都还不错,身上甲胃厚重,手持的兵器擦的雪亮,人人都是昂然而行,军官们都骑着高头大马,披着各色斗篷,在亲兵的护卫下排众而行,模样都是十分神气。
整个城池,都因这些军人的存在而有一种奇特的活力。
建筑除了城防设施和官衙之外,多半是泥土和茅草夯实而建,砖石木结构的很少,道路上尘土和垃圾混杂在一起,也没有人打扫,十分肮脏,两边的排水沟渠全部是明沟,沟中散发着一阵阵的恶臭。
大明的军事重镇,不过如此!
“庆瑞楼……就是在这里了!”
杨达来过蓟州几次,熟门熟路,引着惟功和两个小伴当一路往西,在蓟州西门长街尽头,有一幢三层十来丈高的酒楼,十分气派,门前当户,各摆两排长凳,二十余个打扮出挑,浓妆艳抹的妓女对列而座,看到杨达等人上来,便是立刻上前来招呼。
大明洪武年间为招待天下来往百姓商民,天子下诏在各大都市兴建酒楼,南京建十六座,其余各城各按所需兴建,酒楼之中有教坊司的官妓承接客商,赚取银两,军民百姓可以随便出入,只是不许勋贵和官员士子进入。
时隔一百多年,规矩早就和当年不同,杨达大步流星的入内,在路过脂粉阵时略有犹豫之意,后来强忍冲动,将那些莺莺燕燕挥手赶了开去。
四看盘四干果四时蔬八冷盘八热菜,杨大爷到底是勋戚人家出来的大管事,手头十分阔绰,不一会功夫,店家将银盘摆了满满当当的一桌,异色粉呈,鲜香扑鼻,令人食指大动。
“来,五哥儿尝尝这家的鹅掌,鲜嫩可口的紧。”
“这卖海参十分可口,入口紧滑,鲜香扑鼻。”
“这松鼠鲑鱼虽不及南边的地道,在蓟州也难得了。”
杨达不停的给惟功夹菜,将惟功面前堆的小山也似,看到小惟功吃的香甜,便转过头与两个伴当随意说起话来。
“此番虽有小小波折,到底还是顺当了。”
“托杨大爷的福。”
“我兄弟二人还望杨大爷多多提携,日后有什么差事,咱们一定跟着,绝不敢有二话。”
秋哥儿比起春哥儿话多不少,大灌杨达迷汤,杨达神色十分满意,便与这二人推杯换盏起来。
几巡酒过后,三人话更多,口风也不再严密。
杨达看向惟功,感慨道:“五哥儿大约也隐约明白了,咱们是什么样身份的人?”
惟功塞了一嘴的菜,嘴唇上全是油光,只傻笑着摇头。
他知若是自己表现的机灵醒目,这些管家仆役胆小谨慎,恐怕未必敢接着说下去,此时不如藏拙好些。
杨达心道:“到底是乡下孩子,前几日看着还机灵,到了城里就现原形。”心里这般想,嘴上却道:“五哥儿你是咱们英国公府大老爷所出,你娘亲是当年老太夫人身边的丫鬟,生了你之后,大老爷怕老太爷生气,所以叫你娘出府别居,原说是等事情平定再叫你们母子回来,谁知道你母亲性情刚烈,没有住在大老爷安排好的别居里头,居然不辞而别……这一晃六七年过去了,哥儿你已经长的这么大,你娘亲却已经不在人世,这真是从何说起来啊。话说你娘亲天姿国色,在咱们府里头是很出名的……”
杨达口中啧啧有声,也不知道是感慨世事无常,还是想起惟功娘当年的美貌而痛惜。
至此,张惟功心中的疑惑也得到了解答,怪不得母亲虽然是嫁给了山村里的农夫,却是识文断字,说话雅致,原来是从国公府中逃出来的大丫鬟。
只是娘亲带自己已经走远改嫁,自己生父似乎也没有费力寻找,这个杨达算是怎么回事?
他心中尚有疑问,杨达却又与另外两人推杯换盏,继续痛饮起来。酒意上涌之后,杨达更是高兴,拍着桌子笑道:“此番我等立下这般大功,二老爷必定重重有赏。”
春哥儿刚刚说话不及秋哥儿好听,落了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