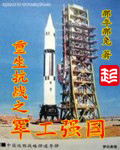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建立豪门-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幸亏,二小子贪吃,在外面疯玩了一阵,趁屋里没人也摸到李大婶房间里偷吃馒头。
馒头用一只篮子装着,用一根麻绳拴在屋梁上,篮子用线吊得高高的。
那篮子馒头,是一家人三天的口粮。
这样高高地吊着,一是怕老鼠偷吃,二是防止孩子偷吃。
谁知道,刚推开门,进到房间,猛地听到了凳子倒地的声音,二小子还以为是老鼠在活动呢。
心想,好大的老鼠!
屋里很暗,农村的房子是没有窗户的,尽管是白天,可是,没有窗户,光线透不进来,房间里仍然看不见。
二小子就摸着往里走,觉得房间里好像有呜呜的声音。
摸着,走着,忽然,头撞到了一样东西,他一摸,是一双挣扎的脚,眼睛适应了光线,猛地抬头一看,“我的妈呀!我奶奶上吊了!”
二小子连滚带爬的冲出门外,大声喊隔壁邻舍的人:“快来啊,快来啊!我奶奶上吊了!”
金生大叔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人们正在安慰婆婆。
金生大叔一路上已经听别人介绍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小姑子离得不远,听说她母亲出事,赶紧回来了。
小姑子告诉大家,她知道母亲在家里受虐待,就偷偷为母亲买了些吃的回来了,扯了几尺布,让她缝一身衣服。
母亲却得知女儿买东西的时候,女儿婆家村人都看到了,害怕村人告诉婆婆,害怕女儿在婆家不好做人,坚决不要,让她给自己的婆婆拿回去。
这个袋子里,就是那几尺布。
说着,抖了抖袋子,掉出衣料。
金生大叔平时对这女人多有容忍,平时吵呀骂呀的都不算什么,她给自己的爹妈剩饭剩菜吃的事,他也睁只眼闭只眼,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他这下要被所有人指责了,母亲上吊死的话,他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于是,就按住李大婶,拼命打起来。
众人看到李大婶被打,心里别提多舒坦了,像三伏天喝了凉水似的。
大家都做出似拉非拉的样子,假心假意地劝架。
一点也不止痒的劝道:“别打了!别打了!”
金生大叔气势凶猛,喝道:“谁敢拦!我连你都打!”
众人巴不得这句话,一哄而散了。
金生大叔一边打一边狠狠的说:“我打死你个婆娘!我打死你个黄婆娘!”
这地方称遇事不清的人为“黄”,和“清楚人,明白人”的“清”是相对的。
李大婶被打的拼命叫喊,活像鬼哭狼嚎似的。
大妞二妞见势不对,一股劲跑到灵凤家,一把抱住母亲的腿:“陈大妈,快去救救我妈!来不及了,我爹要打死我妈!”
这件上吊之事,母亲是知道的。
但是,本着“清官难断家务事”,倒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李大婶挨打之事,灵凤家离着还有点距离,暂时还没有传过来的。
听说要出人命了,母亲忙扔下切菜的刀。解下围裙,匆匆忙忙,跑起来了。
灵凤也像尾巴似地跟了过来。
这里挨近大河,害怕水患,因此农村所有的房子都建在高台上。
走到李大婶家附近,就看到房屋高台下面聚集了不少人,就听着李大婶的尖叫声:“救命啊!救命啊!”
大家窃窃私语,好似有点幸灾乐祸的神情。
母亲走过去,劈头盖脸的来了几句:“你们这些人,就等着看打死人,看笑话啊!”
几个大男人忙表白:“不是!那咋能这样啊!我们拉不开啊!”
母亲炸药似的说话很冲:“这倒是稀奇!拉不开?我今天看我拉不拉得开!”
旁边几个人都笑道:“那是!你是哪个啊!除了你,哪个拉得开啊!”
母亲也不理他们。
一转身,呼呼生风地冲到柴堆旁,抽出一根棍子,然后三下五除二地把细的部分用膝盖一顶,拦腰折断,只留下短粗的部分。
拿着这根棍子,冲进了院子里,看到金生大叔把李大婶摁在地上,左一嘴巴,右一嘴巴,正一嘴巴,反一嘴巴,抽打得林大婶满嘴满脸都是血。
然后金生大叔又揪着她的头发,把她的头使劲朝地上撞。
可怜平时像跳蚤的李大婶这时叫都叫不出来了!
母亲一个健步冲上去,“啪,啪,啪,啪”,一棍子,再一棍子,再一根子,打在金生大叔的屁股上。
金生大叔“哎哟”“哎哟”去捂屁股,转身从李大婶身上下来了!
看到是母亲,金生大叔很恼火的还准备冲上来还手。
母亲高高的举起棍子:“咋啦!你还准备还手啦!我打死你!”
金生大叔一看棍子,气势就矮了一截,又见母亲那生气的样子,平时的虎威都摆在那里呢,他不敢造次了!
但是,金生大叔嘴里还不肯示弱:“我打我婆娘,关你屁事!”
母亲看他还这样,破口大骂起来:“怎么没老子事?你大丫头,二丫头,大小子,二小子,没了妈,你去坐牢,去挨花生米(子弹的样子像花生,人们形象的称枪毙人吃枪子,吃花生米),他们来找我,我能不管吗?”
夏大叔冲动之下,下了死手,这会儿,偷眼看去,李大婶满脸是血的躺在那里,这才感到害怕了。
母亲赶紧招呼大妞二妞,给她母亲端点水来。
过了一会儿,李大婶睁开眼睛,呼天抢地高唱一声:“陈——大——姐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农村女人的哭很奇特,他们哭,不是嘤嘤的哭泣,而是大声地用唱的形式表白自己,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委屈和痛苦。
母亲又去了二小子奶奶也就是灵凤称的吴三奶奶的房间里。
吴三奶奶躺在床上,女儿在床边抹泪。
三爷坐在床边握着三奶奶的手,不发一言。
母亲叫着三婶:“三婶哎,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啊!你看你这一去,倒是解脱了,你儿子怎么办啊?
他要一辈子被人指脊背沟啊!他这一辈子都脑袋扎在腿空里走路啊!他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啊!
你孙子怎么办啊?大妞二妞连婆家都不好找啊,大小子二小子还要打光棍地啊!
你幺女怎么办啊,以后娘家的路就要断了啊!有点委屈找哪个说啊。
那个黄婆娘她是不会说话啊,你看你儿子把她嘴都打烂了,以后也不敢说你了。
再怎么说,她也是你四个孙子的妈啊!打死了怎么办啊,四个孙子要成孤儿啊! 儿子怎么办?要吃枪子了。
三婶啊,千看万看!看在儿孙的面上,莫想不开啊!”
又拉着李大婶小姑子的手:“妹妹啊,你揉揉心啊!
这不看别的啊!看在你妈的面子上啊!
只要你妈在,这娘家的路还得经常走啊!
这妈也不当家了,该应酬的还要应酬啊,该敷衍的还要敷衍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妹子啊!你听我一句话,嫂子不会害你的!
这以后,长的短的,一把挽起,什么也不要说了啊!”
小姑也是个聪明人,听了这话,如何不明白!
忙说:“陈大嫂啊,我知道了!我什么也不说了!我妈以后还烦你多照应!我去说说我哥!”
小姑就来和金生大叔说了,这事不要怪嫂子了。
金生大叔打老婆一是生气,二也是为了给母亲妹妹扑气。
如今看妹妹不怪了,有了一个台阶,如何会不赶紧下来,自然而然就应下了。
母亲既泼辣、胆大,又有担当,肯讲理,这李大婶在这个营子里除了母亲,一个朋友也没有。有谁和李大婶发生了冲突,只要找来母亲调解,没事,一准能成!
哦,李大婶,原来,你也怕个人啊!
仔细又想了想,说怕,倒是不很恰当,应该是佩服啊!对,佩服啊!
作者有话要说哦:
都过了四万字了,亲们喜欢本文的话,给点鼓励吧!欢迎票票,鲜花,评论啊!
亲们给我鼓励,我才能更有动力写下去啊!
第十六章 与生俱来的责任感()
灵凤很在乎家,在乎家里的每个人。
这是来源于她的血液里的每一个分子,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
上世,她一直觉得自己对家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和初恋男友恋爱时,家里人是反对的,全家人省吃俭用,供她上了大学,实指望分工出来,帮衬着家里人,谁知道谈了一个外地的男友,大家心知肚明,都害怕她一走了之。
那年春节,灵凤把男友带回来了。
灵凤自己认为这个男友长得还算潇洒,那时她是一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喜欢带点忧郁气质的温柔的男生,这样的男生给少女的思想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尤其,弹吉他的男生,更让人迷恋。
灵凤首先自己陷入了单相思,在她的想象里,这男生就是最完美的。
上课,她会坐在他的后面,从背后看着他,想象他在记笔记呢,还是在思考问题呢?
下课,她在他经过的路上走得很慢,等着他经过自己的身边。
经过他的宿舍,她会想,他在做什么呢?在弹吉他,在聊天,在给朋友回信,还是在看小说?
晚上,在校园的操场大草坪上,一听到吉他声,她就想循声而去。假装无意的在旁边走来走去,可是,没有一个弹吉他的人是他。
等到男生终于向她表白了,她忽然发现,男生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深情和内秀。
那年放假,她把他带回家。
两个当家人,嫂子和母亲都不太高兴。
等他走后,母亲嫌弃说:“看他长得哪有个人样?一张马脸,”
顿了一会,补充到,“一张驴子脸!”
嫂子也扯扯嘴角,一脸的不屑:“长的像个啥啊!”
那个“啥”,可不是疑问的意思,那是百分百否定的意思。
得,都成动物了!
大家脸色都不好看,灵凤没敢做声,心却在想:“她们这都什么审美标准啊!”
又在暗地里用手比了比男友的脸:“是有点长,但也不至于是马脸,驴子脸吧!”
要分工了,男友家乡分配原则,本着,哪里来哪里回去的原则,必须回去的。
男友说,他可以留在这里。
前提是,找一个上调的指标。
两个穷学生,是不可能找什么指标的。
无用功做了很多,找了很多天,黄花菜就这么凉了!
然后男友要求她,既然我不能留在这里,你可以跟我走啊!大学生我们那里需缺得很。
实际上,当时,大学生哪里都是需缺的,所以才会有定向分配一说。
灵凤毫不犹豫的做了选择。
走,那是不可能的。
我的父母亲,我的哥哥嫂子,我的亲人都在这边。
我不可能这么自私,放任自己去追求自己也不太有把握的爱情,放跑她们所有的希望。
我在这里,就是她们的希望!
灵凤有时候也很奇怪自己的矛盾性。
明明很多人都说,她有文艺范,是一个骨子里浪漫至极的人。
可是,面对亲情,她毫不犹豫的放弃了爱情;
明明是很清高的人,可是对着一个混迹于官场的前夫,她却包容极了;
明明是个很心性单纯的人,可是却对周围的乱象却又理解得透彻极了!
灵凤留在家乡,不为别的,只为哥哥嫂嫂没有孩子。
只为:“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后来,灵凤一直都会这样想:“我走了,他们怎么办?”
虽然,很多人会说,“离了张屠夫,也不会吃带毛的猪!”
可是灵凤就是觉得离了自己,他们会活得很艰难。
灵凤自己解不开这个结。面对需要自己的人,她总是像老母鸡一样,张开她直愣愣的翅膀,去保护他们。
后来,她遇到丈夫出轨,极度痛苦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种感觉:如果自己再在这个屋子待下去的话,有可能会自我了断,那时,哥哥嫂子她已经不担心了,侄女已经成家了。
她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我如果走了,我的孩子怎么办?”
不行,我得出去!我不能再这样下去。走出去,就好了,走出去,就好了,就好了!
她好像一直觉得自己负有很多责任。这个责任让她有一股力量,向前奔走。
靠着这股力量,她走出家门,也走出了心门!
作者有话要说哦:
都过了四万字了,亲们喜欢本文的话,给点鼓励吧!欢迎评论啊!
亲们给我鼓励,我才能更有动力写下去啊!
第十七章 引子招子()
哥哥嫂子没有孩子,可是,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所以,在灵凤小时候的记忆里,他们一直都是形影不离的。
哥哥是独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虽然,现在已经不是那万恶的旧社会了,但是,子嗣的问题,在农村在城市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最重大的问题。
嫂子从进门起,一直都在喝那难闻的中药,前世后世都是一样,也不知道从何处弄来的那么多的中药。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打听出:“陈大妈,离我们这五十多里的岭前村,有一个老中医,看这个病神得很,某某家媳妇,结婚八年了,没孩子,吃了十五副中药,三个疗程就好了!这才半年,现在已经怀上了!”
于是,不管多远,哥哥嫂嫂都会去的。然后抱了一大堆中药回来。每月总有十几天在熬药,然后嫂子皱着眉头喝药。
十几副药喝下去,半点作用也没有。
又过了不久,又有热心人打听到,离着这里一百三十多里的吴家庙村,有一个巫医,灵得很,只要喝下她的佛水,就会有孩子的。
于是,哥哥嫂嫂不远百里,搭车换车,到了那里,花了老多的钱,喝了水,还如获至宝地装了一大袋树叶子,枕在头下。
仍然,不见半分音讯。
前年,又有人出主意:“听有人说,引一个孩子来,叫‘引子招子’,传轩家,抱了一个娃,那还真是个引子,不是后来连引来了三个吗?”
嫂子是想过继自己的侄女的,嫂子娘家哥哥,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女儿也才三岁多,越小的孩子和亲娘家感情越浅,养父母越容易培养感情。
灵凤那会儿也听说了。
后来,母亲大手一挥:“那可搞不成,她们俩都姓秦,到时候虐待我儿子怎么办?我儿子那么老实,我死了,他饭都吃不上了,怎么办?就抱大姑娘家的老三。”
大概母亲心里担心引子的作用吧。
大姐家共三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老三是闺女。老二已经大了,很懂事了。抱养孩子,是不能抱太大的孩子的。
只有老三小点,才一岁。可是问题也来了,人家就这个闺女,抱走了,人家也没有闺女了。
大姐对于母亲的安排哪敢说个“不”字,不仅如此,还得积极促成。
要不然,会挨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心里还得思量一下,以后,你还想回不回娘家,你以后和丈夫婆婆发生了矛盾,谁来为你出头!
当时,政府正在实行计划生育,如火如荼地实施强制节育手术。
凡是家里有了三个孩子的必须进行结扎手术。
大姐的婆婆是个非常传统的老人家,自己唯一的孙女,怎么会让别人抱走呢。孩子一岁的时候,正是好玩的时候。
母亲的意思,必须让大姐的婆婆同意。
抱走这个孩子,儿子和媳妇都不用结扎了。
不让抱走的话,你儿子去结扎。
你儿子是工作人员,不需要下地干活,结扎没有什么危害,我姑娘还要下地干活,结扎会伤元气的。
那时的人都认为结扎是会危害身体的,伤元气的。
就算不做农活,谁也不想孩子去结扎啊。
大姐的婆婆心疼自己的儿子,无可奈何的同意了。
事后,一直都唉声叹气地对大姐说:“你那个妈哟,太聪明过火了!太精明过火了!哎哟,搞不赢啊!”
然后边走边摇头,还拖长声音叹息:“搞不赢哟!”
大姐心说:“是啊!你只能搞得赢我!我妈你可搞不赢!在我面前,你怎么耍赖都行得通!在我妈面前,你们都要现原形!”
在灵凤八岁的时候,嫂子就来到这个家。
这个家里,母亲是个火爆脾气,父亲是个闷葫芦,二姐大自己五岁,可是一个姐姐样都没有,老是和自己争东争西,寸步不让。
一天到晚,都和自己揪头打铁(打架吵嘴的意思)。
嫂子来到这个家,脾气温和,处处谦让,任劳任怨。
有时候还和灵凤一起帮她做作业。
灵凤喜欢跟在她后面,学她的一举一动。
嫂子做事,灵凤凑在旁边,看看有什么能帮到她。
嫂子拆白手套,需要一个人拆,一个人缠成团,用这个白棉线为家人打毛衣,打背心。(当地人称“织毛衣” 为“打毛衣”),灵凤就自告奋勇的说:“我来帮你!”
哥哥当兵的时候,有一件旧毛衣,过了这么久,有的地方破损了,嫂子在夏天需要把它拆掉重新织一遍。
穿了这几年,拆掉的时候,是会有很多灰的。
这个毛线,必须先洗一遍,晾干,才能重新织成毛衣。
因此,要将毛线均匀的拉成一圈一圈的,每二两线,做成一绞,中间用一根白色的线系好。以免绞在一起。洗干晾净,然后织成新的毛衣。
缠毛线的时候,灵凤会说:“我来帮你举手!”然后,举起手,将毛线头捏在手里,将毛线缠在左右手臂上,左右循环转动,小孩子,哪有韧劲,一会儿就举疼了,嫂子问:“举得酸了吧,放下来歇一会!不要太快了!匀匀的转动就行!”灵凤羞涩的笑笑,放下了手臂在腿上,歇一会,继续再转。
那时没有别的布匹,只有棉布。
棉布很不结实,再加上农村人干重活,衣服很太容易弄脏,棉布又很重,洗衣服要用棒槌到堰塘的石板上使劲捣捶,因此,这衣服每年穿不到一季,就会破了,损了。
每到换季的时候,自家里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