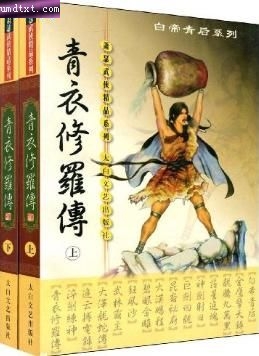痞妃传-第17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只是比划比划,就她这模样,怕是这一拳,不用太用力,就给她打到下头逛黄泉去了。
油尽灯枯。
猴子不只一次听着人这么形
着人这么形容舒玉,然真的瞧见了,却真的觉得,她能活的过今年,也许就是万幸了。
“你就是这样,女人家家的,都不按个规矩,咱们园子里,多少个女子再有心机都是勾心斗角,偏你一个,不是耍拳头就耍刀,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年的庙会,你回来给我肚子上那一拳,打我疼死了,我那时候还跟我自己说,不看着你石猴子倒霉,我舒玉誓不为人。”
“怎么着,跟我翻旧账来了?”猴子笑笑。
舒玉说:“嗨,跟你翻有几个意思?我要知道你这货从前是干土匪的,谁跟你一样的,失了身份!”
“怕就直说,小爷儿不笑话你。”
“有什么怕的?”舒玉笑笑:“从前我还真是怕你,凶巴巴的,总是要吃人似的,可现在我可不怕了,你也瞧见了,我这脚前脚后的也就去下头念佛了,我有什么怕的。”
“呦呵,带种了啊。”
舒玉道:“谁还能一辈子窝囊不是?”
一股子晨风顺着帘子吹进来,俩人相视一笑。
舒玉先问的:“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缘份。”猴子言简意赅,又问:“那你呢?”
“姐姐第一次见二爷就是在这儿。”舒玉陷入往事,那病肓的脸,都像是泛着光泽:“先帝在时,有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便重新整修了这先农坛,修好之后第二年的春天,就在这儿举行了祭祀先农和亲耕大典,那年我才五岁,姐姐长我两岁,额娘回来与我们说:‘带你们去玩儿可好?’,我和姐姐高兴极了,这么大的热闹,我们哪里见过?那一天,额娘带着我们姐俩在这先农坛里四处的转着,我吃惊的不得了,就连姐姐那样能端着的性子,也连连感叹,鬼斧神工什么的,大典举行的时候,热闹着呢,额娘去忙,我们姐俩不敢上前,只能躲在一边悄悄看着,我瞧着皇后的衣裳好看,就想走近看看,我往前走,姐姐就来拉我,我这一耸,就给她怂了个跟头,嘭的一声,闹了不小的动静儿,这下坏了,皇后一嗓子,斥了我们,我一下就懵了,当时姐姐拦在我身前,三言两语的念叨了几首敬农、悯农什么的酸腐诗,就把皇上哄的十分高兴,不只不恼了,还笑问是谁家的孩子,额娘吓坏了,也跟着叩头,也摁着我的脑袋跟着叩头,磕的直晕,结果等我起身时,当时十岁的二爷竟上前自己扶起了姐姐。”
“其实想想,二爷那时候的眼神,就跟姐姐紧紧缠在一起了,我从没看过一个男子那般看着一个女子,眼睛里只有她,其它什么都不重要。真的,就算七爷宠你宠成那样,也不及十分之一。”
猴子挑挑眉毛,舒玉接着道:“那样的海誓山盟,一生一世一双人,曾经让我嫉妒的发狂,便是做上许许多多的糊涂事,也想要那样的爱,可现在,我才明白,凡事物极必反,那样的感情根本就是两个人悬在钢丝上,失了一个,另一个连活着都不会了。”
“太有情,也是无情,无情,亦是有情,二爷有情,姐姐也有情到头来反是不比,你石猴子无情,七爷更是无情。”
舒玉叹息:“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个道理,我明白的太迟了些。”
猴子手指做弯,揉揉眉心,“别念经,说人话,我听不懂。”
舒玉笑笑:“你懂的,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瞧我这模样,也活不上太久了,咒你的,骂你的,那些年我也说够了,欠你的这句谢谢,我不想带到下头。”
小猴儿挑眉不语。
舒玉道:“春禧的事儿,我谢谢你,我这辈子做过最错的,就是这件事,我欠姐姐的太多了。”
“用不着你谢我,白玉霜是我石家人。”
舒玉苦笑:“你啊,真是,让我喜欢不上的人!”
“可别,你可别喜欢我,我以后还得吃饭呢。”
……
三日后,当小猴儿从碗里拣出第九个黄豆粒儿时,秋萍急匆匆的进屋来传。
“姑姑,姑姑,睿王府的侧福晋,殁了!”
小猴儿怔了片刻,失笑,随手把手里的黄豆粒丢到痰盂里。
嘣儿!
声音极脆。(。。 )
第廿七回 开封有个包青天 俩腿一蹬乱人间()
上回书说到舒玉殁了,因那葬仪上生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变,咱们暂且放到后头再说,先来说说那事变的另一诱因。
日子划过两月前,咱们得从老七刚到开封府时说起。
来的路上,琏琛一直忿忿。
“太后娘娘让你来河南查亏,是几个意思?这河南去年才遭了灾,又给捻子闹的鸡飞狗跳,现在老百姓饿死多少都是个悬案,这还不够乱么,还让咱们来查亏?再杀一批官员,不是添乱吗?”
“她也是头疼,想让我想想办法,又不愿许我御史的大权。”
老四的脾性直,听了就气,“都成她的了,你凭啥白给她干!”
“你这话说的,百姓饿死了入她纽祜禄家的祠堂不成?”
“……”琏琛丧气一叹,“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觉得看她得意不爽,使唤了你斩了阿灵敖的翅膀,还使唤你收拾这烂摊子,然后就在朝中给几个文官的位子,说的好听是户部归了你,可这户部现在就是个没奶的娘,什么还不是靠你自己?到头来,你这猫的好处,还不如安抚那耗子阿灵敖的多。瞧瞧现在,他在京中舒坦的当他的一品候,咱们在外头缝补破衣烂衫!”
“不然还能怎么着?你去找她掐一架?”
老四被他一语说重,忿忿然的敲的案几咣咣响,“哼,女人就是女人,牝鸡司晨,叫的没个章法!”
“你可别敲了,我这点烟丝儿都让你给我敲飞了。”老七慢条斯理的把珐琅烟盒盖上盖子,笑笑道:“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至少阿灵敖瞧不出的,她瞧的出,说到底这查亏抓贪虽是治标,却不治本。”
“瞎说!”老四又不乐意了,“咱们累死累活忙乎这一年多,国库不是也有余富了?各省亏欠的田赋都争回七七八八,阿灵敖造那大钱的窟窿也给咱堵上不少,物价也回来不少,咋能叫没成效?”
“你怎么不说你自个儿的瑞丰宝号屯了多少官票?”
“诶,那怎么了,除了咱们谁敢承兑那烫手的官票?”说起瑞丰宝号老四颇为得意,转念一想,“诶,不对,你打什么岔子,不是说这个的。”
老七摸胡子,笑不语,气的老四直嚷:“你这性子真他妈惹人厌!”
老七挑挑眉,也不恼,半晌只听外头热闹声由远及近,外头驭马的于得水道:“二位爷儿,就快到开封地界儿了。”
老七和老四各自掀开帘子瞧着,却见这临近城门口的官道上设有围栏,围栏中热气升腾,周围有兵把守,那围栏里头人头不过二三十,外头却是乌央乌央的遍地饥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许多人一动不动,不知是人,还是尸。
前去探路的精卫回来说:“前头是福祥县设的一处粥厂。”
“哼!又是个做样子骗朝廷的!”老四忿忿道:“这些个芝麻小官,官不大,胆子却不小!什么银子都敢贪!连赈籍都拿来卖,多笑话!银子少的捐个次贫,银子多的捐个极贫,一个个的争着抢着朝廷这些灾粮!真正饥民,只能喝风!都说这父母官父母官,一个个的生生看着那些饥民饿死,是他妈哪门子的父母?”
“气死我了!”老四气的不成,坐都坐不住,“走!咱们下车瞧瞧去,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张狂!”
老七拉住他,“坐下吧你,你管得了多少?”
“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啊!”
“你四爷跟这儿发了威,消息传到城里去,里头的几十家粥厂全都立马装了菩萨,到时候你上哪儿瞧出问题来?”
给他一语说中,老四虽气的不成,却也没再动作,这在外头这两年,他也瞧在眼里,这陋规绝不是一两处,画面之悽悽也不是头回见,就像黄河一带近年最常为人道的那首诗说的——
东舍出男西携女,齐领官粥向官府。
日高十丈官未来,粥香扑鼻肠鸣苦。
忽闻笼街呵殿高,万目睽睽万口嚣。
一吏执旗厂前招,男东女西分其曹。
授以粥签挥之去,去向官棚施粥处。
投签受粥行勿迟,迟迟便遭官长怒。
虬髯老吏拦门前,手秉长勺色如嗔。
……官厂已收催还家。
片席为庐蔽霜雪,严寒只有风难遮。
道逢老叟吞声哭,穷老病足行不速。
口不能言唯指腹,三日未得食官粥。
……
到了开封府城门前,老七一行人弃驾上马,随行从简,如以往一般,以往来商人为由,进了城。
却说这开封可是八朝古都,曾几何时,可是有着‘天下藩封数汴中’的美名,而如今瞧来,却全然无昔日繁华,街市虽然热闹依旧,却远远衰于直隶各省,更比不得的江淮一带。
待到了城中,精卫道:“主子,咱们弃马步行吧,听闻这城里的捻子不少,专挑大户吃,万一让人给盯上了,麻烦。”
“哼!憋屈,咱们做官的倒怕上匪了!”老四今儿这火就没降过,可也安生的下了马,随老七一块。
说来折腾半晌,肚子也饿了,几人原是想寻个去处吃些东西,却被一奇景给生生引了过去。
这‘奇景’二字怎讲?
与沿途所有粥厂的冷清都不同,眼前的这个粥厂,非但人头攒动,比肩叠踵甩了半条街市,而且兹从那打了粥的人碗里稠稀来看,绝对符合朝廷
稀来看,绝对符合朝廷‘插筷子不斜,布巾包裹不渗水’的标准,而且自那人头来看,那赈籍绝对远超上报朝廷的标准,如此黑透了的世道,白不是奇景又是什么?
铛!一声敲锣。
“下一位。”士卒唤着,极有秩序。
兹一打听,原来是开封府官绅合办的一处粥厂。
老七一行人已来到那栅口处,便是便装,依然难掩他们身上的贵气,粥厂里走出来一中年人,笑的和气:“几位瞧着眼生,想必不是开封人士吧。”
“大人好眼力。”说话的是老四,兹瞧这眼前人圆润且锦衣华服,只想他便是那些饥民口中的再世包青天,今日亲自打粥的知府包兴。
“诶,几位误会了。”那人失笑,对老四的意思也是了然,“金某只是区区一届商人,诸位口中的大人,是那位。”
顺着他所指,几人只见那热腾腾的大锅前,一布衣老朽奋力搅动着那长棍舀子,那细细的棍子跟他胳膊差不多,他搅的相当吃力,却也相当卖力,那满头白发做辫乱糟糟的垂在脑后,怎么瞧着都与那外头的饥民无异。
“他是包兴?”老四震惊的声调抬了老高,那老头回头,满头是汗:“谁叫我?”
……
再次见这包兴,已是半月后,彼时他依旧瘦骨嶙峋,躺在那木板上,直挺挺的,硬了,脖子上一条黑紫的印儿,舌头老长的跟外头当啷着。
那长长的木板旁边,还躺着他娘、他媳妇儿、他儿子、他儿媳、他闺女。
就在老七这个睿亲王上门前。
一家七口,一块儿上吊,死了六个,唯剩二十岁的幺子托了房梁不结实的福,剩口气。
放眼望去,这只有三个房间的小土房,四处破败,家徒四壁,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找不着,和那一板子的六具挺尸一样,布衣菜色,骨瘦嶙峋,这朝廷四品大员的府邸,每一处,都写着一个‘穷’字。
可老七此时手里的那本秘密详查的账本中,明细——
知府衙门,仅瞒报田赋一项,便亏空高达十五万余两。
“这是给谁顶的罪!我非要揪出来不可!”老四气的直抖,又去拎那半死不活的包兴幺子的领子:“你爹糊涂啊!”
却听那小子竟仰头笑了出来,“我爹可不糊涂?我爹若不糊涂,如何落得这个下场?”
“说!是谁?给谁顶的罪?他的冤我四爷给他作主!”
“呵,有什么冤的。”那小子瘫跪在地,缓缓回头看了一眼那包兴,“我爹没给谁顶罪,那些银子,就是我爹贪的。”
“你放屁!你当我们都是瞎子不成!”老四气的又要踢他,被精卫拉住。
老七缓缓道:“贪下的银子可是用来赈粥了?”
“赈粥?”那小子嘲道:“赈粥多是乡绅来出,哪里用得上那么多银子?”
“王爷,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放肆!”于得水上前,却被老七摆手摒退,他只看着那小子道:“有什么怨,本王给你机会,说吧。”
“好,那我就给王爷算上一笔账。”那小子豁出去似的,他指指这破屋子,“就这破院子,租上一年要十五两,我们全家一个奴才没有,吃喝拉撒要二十五两,我奶奶吃药五两,教我和哥哥读书的先生五十两,这便是九十两,我爹是从四品知府,一年奉银却只有八十两,外加八十斛米,就算我娘精打细算,想要够用,我们小的也是要饿上几顿的。”
“再说那知府衙门,租院子要一百五十两,所有衙役的开销一年要八百两,三个师爷要两千两、吃喝拉撒、车马费等等暂且不算,就说去年剿捻一项,就花了银子八万两。”
“朝廷派了兵剿捻,你们用银子做什么!”老四听得不爽。
“招待,只京中来人在府上吃住以及打理驻军琐事,就花了八万两!敢问王爷,这笔银子不从那田税上抽,哪里变来?”
“你爹一个知府,会没有下头孝敬的冰敬、炭敬?”老四非要与他辨。
那小子道:“我爹若能收下这,何至于如今的家徒四壁?有道是拿人手短,那孝敬的银子哪个是白白给吃的?”
“……”老四无语了,说出不的憋闷堵的慌,他看看老七,却见他不知何时已经踱到那包兴身前,伸手阖上他死不瞑目的眼。
当日,琏珏替包兴还了那十五万田税亏空。
包兴的丧仪办的极为隆重,这‘隆重’二字并非仪制,而是那抬棺之时,沿途送行的百姓,乡绅、竟甩了几条街那么长,彼时人皆哭嚎,长呼青天已逝,再无温饱。
河南巡抚大怒,原欲派兵驱散,无奈一打听,那行人之中居然有那睿亲王和慎亲王,是以只能作罢。
棺椁入土时,老七在包兴坟头放了一块豆腐,一捆青菜,寓意清清白白。
包兴的幺子包梓跪地给琏珏连连磕了三个响头:“小人谢王爷肯让我爹一世清白!我爹在九泉之下终于能阖眼了!”
一时间,河南的百姓都知道,这天下还有个青天!
……
待三日后,风波渐过,老四问老七:“你这回怎么闹这么大动静?想必京中不日已经收到消息了。”
他虽蠢些,却也不糊涂,老七这些年始终低调,为何在包兴一事上做如此大的文章?
那些个带头送行的乡绅,没有
乡绅,没有他睿亲王的默许,哪里敢撺掇这么一场得罪巡抚,惹乱民心的游行?
老七笑着吃了口茶,把案几上的折子给老四丢了过去,“先看看再说。”
摊开那折子一瞧,老四的眉头越拧越紧,待罢了,他俩眉头都快接在一起。
“养廉银?”
“怎么,不好么?”
“好,当然好,按照各省度支给予些银子,有了费用,自然不用逼的包兴那样清廉的官也必须贪,可你要知道,这前些年,提出减了官员俸禄的可是阿灵敖,那可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政绩,你这个时候提这个,不是摆明了跟他对着干么?”
“万一到时候他反参你一本,想要借机拉拢官员,结党营私,太后娘娘定是不会向现在一般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呵,我就算只在家吃茶,他们一样防着我。”老七漫不经心的道:“道不如,要闹,就闹的大一些。”
“你这不是逼她愿不愿都要许了你这提议?”老四竟有些担忧,尽管这两年,他见惯了这小子的行事之周密诡谲,也知道总有一天,这暗箭要变做明枪,可当真要对上之时,说不担忧,都是假的。
他很清楚,这不是他们当年兄弟看不顺眼,动动拳脚的事儿,这是党争,成者王侯,败者断头的事儿。
“这么大的哑巴亏……她能白白吃么?”
“吃了再说。”老七吃了口茶,目光清俊:“我大清不能再出现第二个包兴。”
“可……”
“可什么可?”老七不耐烦的讥笑:“再不想想治根儿的办法,咱们哥俩儿这么低头查贪,十几二十年也杀不完的杀,你不嫌闹心,我还嫌手麻。”
“去!”老四摆摆手,“你这杀人不眨眼的阎王,跟我这儿装什么菩萨。”
“诶,对了,老七,你既要送这折子,何不让那包梓进京跑一趟?说真的,他那天算的那笔帐,给我都惊着了,咱们都是身出富贵的,哪里听过给区区几十两银子逼的过不了日子的?你要让他去亲自跟太后娘娘再算一遍那笔帐,她就是再防你,也知道这事迫在眉睫。”
“呦,这开封的水土想来不错啊,你这猪脑袋也能开了窍。”
“去球!”老四甩了一句河南话,“我说认真的,你别闹。”
却见老七摇了摇头,吃茶不语。
“我算明白了,你是不想把阿克敦装进去吧。”
那包兴亏空中,最大的一笔招待费,招待的便是去年来剿捻的将士,而这为首的,正是阿克敦,不论他有心无心这点儿银子,说起来总是不妥。
见老七依旧不语,老四坐实了心中的想法,一时间,他心中五味陈杂。
人人都道他这个弟弟心狠手辣、不近人情,可就是这块冰,却生生能捂热所有追随他的人。
……
三日后,开封府十里长街送青天的消息和老七的折子一前一后的到了京城。
不出一日,上书房便送来的多达十八个折子,本本都是应和睿亲王这养廉银的提议,更有大胆者,还逐一抨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