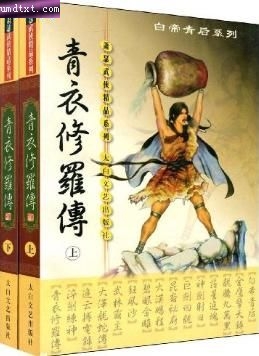痞妃传-第18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婧雅美眸一厉,心知来者不善:“谁把话传过去的?”
“没、没人呐,院子里的奴才一个都没出去过啊!”
没人?
婧雅心下一忖,忙与鄂伦道:“亲家老爷,我知你现在心绪难平,可说到底这是咱们自家的事,有道是家丑不可外扬,恁是如何,咱们都该关起门来解决,这事情究竟如何还尚未可知,若是这个当口给有心人利用做了文章,那便是咱们家的损失了。”婧雅一副小辈姿态,无奈鄂伦却根本听不进去,反是更怒——
“福晋不必这么瞧得起我鄂伦,若是当我是自家人,何故如此待我女儿?”这不仅仅是他心疼女儿,更是往他鄂伦的脸上抽着巴掌!
恁是婧雅如何巧舌,也没了办法,却说这时,门已推开,却见邓昌贵一行三人进来,那身后而二位,正是石猴子和佛尔果春。
彼时的石猴子像是逛园子似的悠哉的甩着外八
子似的悠哉的甩着外八字,还未待迎上来的婧雅说话,她便开了嗓:“我说侧福晋,邓公公非说有热闹看,给咱们从被窝里拽了出来,到底是嘛热闹啊?”
她这嗓门挺老大,一句话,给邓昌贵脸弄绿了,却见鄂伦紫着一张脸怒瞪着他,他忿忿的甩头,只见猴子气死人不长命呲牙朝他一笑,光洁的脑门子上书:咋,就是玩你,怎么着吧?
婧雅迎上来,万般客气:“都是自家的一些事儿,这么晚了,怎么还惊动三位贵人了。”
“咱家听说府上的窖里抬出一个人,怕有什么麻烦,便想着过来瞧瞧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
“公公客气了不是,不过是些小事,扰着您休息就不好了。”与邓昌贵说话间,婧雅有意无意看着佛尔果春与猴子,前者与她一样,淡定如常却是眉心微蹙,而后者,像是没她事儿似的,晃晃哒哒的绕到了屋子当间儿,那藤椅处。
“呀,就是这人。”小猴儿一脸‘惊诧’的扭头问周身僵硬的鄂伦,“这人谁啊?咋给大人气成这样?”
“……”
“……”
硬憋了两口气,憋的脸紫胀如蕃薯,鄂伦还是没忍住,只道:“正是小女,福茹。”
一句话,屋内霎时安静,落针可闻。
真傻的也好,装傻的也罢,这面儿一撕破,里子什么的都露在外头了,怎么着都没用了。
“我知这话我不该说,可我想我说与不说三位也早晚都会知道。”鄂伦开门见山的道:“既然先帝当初派人来与我说,小女已殁,那我也不会闹到宫里头去,也不会传到外头去,我鄂伦如今只要一个说法,这不过分吧!”
这话已经仁至义尽,认谁也说不出一个不字。
任谁都瞧得出来,鄂伦这火气不仅仅是冲的睿王府,更是冲着先帝,冲着紫禁城里的那几位根本早就知情的主子。
邓昌贵耷拉着三角眼,“石姑姑,你看呢?”
“你二品,我三品,我当然听你的。”猴子四两拨千斤的把话又推回去,心下啐着:丫既当了婊子就他妈别当王八,有事壳里一缩,俩眼一瞪就他妈知道看热闹,忒不要脸。
“好,那咱家就却之不恭了。”邓昌贵没再矫情,他只与鄂伦道:“按说咱们三个今儿来的确实不是时候,可既然赶到这儿了,大人又这般深明大义的说了,我们也不好推拒,想来也不过是一些误会,说清楚总是好的。”邓昌贵说话向来温吞,却是棉里藏针,此一番言语,便是婧雅再有心缩小事端,也再无法拒这三位于门外。
待诸人一一落座,茶虽氤氲着袅袅热气,室内气氛却是冰若寒霜。
婧雅毕竟是如今睿亲王府最大的主子,她传来讷敏,正色道:“跪下。”
彼时的讷敏早已哭成泪人,瘫跪在地,原本就病弱的身子,瞧上去风一吹便倒似的,然鄂伦并未因此收敛了怒火,甚至连椅子都坐不住,就窜了起来,言辞俱历的逼问着她——
“你这贱婢还有脸哭!枉你叫福茹一声主子,竟如此待她?谁借给你这天大的胆子!”鄂伦这话乍一听是说给讷敏的,可在坐之人谁又听不出他句句有所指?
鄂伦又不是三岁,没有谁人的默许,她不过一个陪嫁丫头,哪里能值得皇上给瞒着?
“别哭了!说!”鄂伦气急,竟抬腿剜了讷敏一记剜心脚,讷敏吃痛的闷叫了一声,瘫在地上,狼狈至极。
便是她是府中庶福晋又如何,说的好听是庶福晋,说的不好听,也不过就一媵妾,如今鄂伦有气,不冲她撒,又能冲谁?
若是只这般踢打踢打,就能撒撒气,何尝不是一件好事。
“说!”见众人皆不言语,鄂伦气急,竟又剜了一脚!
讷敏咬紧牙关,依旧只字不提。
然就在鄂伦的第三脚就要落下之时,那讷敏身后的两个丫头哭着扑了上来,一个抱着她拦着打,另一个跪地哭诉。
“大人!别打了,主子冤枉啊!若没我们主子!继福晋早就没命了!”
------题外话------
相当晚,相当少。(。。 )
第卅一回 孙悟空托生转世 天生偏偏好闹事()
“闭嘴!”
讷敏一嗓子怒喝,想要制止丫头胡说,然一切已经完了,那丫头金扣儿一开了口,便再也收不住了。
“说!”鄂伦激动,“什么叫没有她,福茹早就没命了?”
“当年要不是主子花钱买了人回来做了替罪羊,又把福晋悄悄藏起来,福晋早就做了亡魂了!”
“闭嘴!”讷敏猛地挣脱开来,一嘴巴抽在金扣儿脸上,怒斥,“我知你不忍我挨打,可也不能嘴一张就胡说!”
“我没胡说!”金扣儿捂着脸,红眼道:“就算主子打死我我也要说,奴才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主子被如此冤枉!”
“哪里来的冤枉!”讷敏又要去抽她,手没抬起,便被眉目极是阴郁的鄂伦拉开,他没有看那金扣儿,而是转过头看着那座上的四人,沉声道:“说。”
如此,有心制止也罢,无心制止也好,恁谁也不能再拦。
佛尔果春却是忽而开了口:“说吧,把你所知道的都说出来,大人不是外人,你也不用藏着。”她顿了顿,看向那金扣儿,目光依旧柔和却是难掩犀利,“可若是没有的,你要是添油加醋蒙骗咱们,咱们也定不会放过你。”
兹这一句话,金扣儿竟周身一僵,什么都说不出,而银扣儿忽然跪起挡在金扣儿身前,冷笑厉声道:“姑姑又何必吓唬我姐姐!反正过了今天,我们说什么都活不成了,又何必怕呢!”
“你——”佛尔果春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想怒却不敢言,要不是给猴子伸过来的手压住,她几要失了淡定。
猴子笑笑:“这丫头道是伶牙俐齿,想说嘛就说吧,可别憋坏了。”
邓昌贵侧目扫了猴子一眼,蹙了蹙眉,却听那银扣儿道——
“回大人,想必您不知,侧福晋当年根本不是病死的!而是把脸活活闷到炭火里头闷死的!”
鄂伦怔住,瞠目结舌,难以置信的甩头看看那座上表情并无过度惊诧的四人,连连点头:“好,好,好,合着只老夫一人不知。”
“亲家老爷——”婧雅满面为难的想要说什么,却被鄂伦横掌打断:“你不必说。”
而后转向银扣儿:“你继续。”
“便是主子是东太后娘娘当年赐给福晋的陪嫁,可毕竟是主仆一场,便是福晋待她并不好,可主子心软,还是下不了这个手去害她!若不是实在没得办法,又何故非要出了这等下策,寻了个替罪羊回来?要不是把那替罪羊的脸烫的焦烂,又怎么可能借尸还魂的把福晋藏在地窖,护了起来?!”
“胡说!”那鄂伦夫人忽然哭喊道:“护着?若是有心护着,福茹怎会这般疯疯癫癫?若是有心护着,何故不派人去找我们老爷!”
“夫人!福晋神思俱损,又怎能怪的我们主子?!我们主子一心护的福晋母子平安,可谁料她产下一个死胎,情绪崩溃,以致神思慌乱,不绑着四肢,都不自知的自伤,她这副模样,如何去寻大人?再说了,您叫我们主子如何说?在王府里,说的好听,我们主子是个庶福晋,说的难听,不过就是个没品没级的媵妾,一无背景,二无靠山,便是有心,我们主子又能做的了什么?如果可以的话,谁愿意让自己的手沾满血腥?”
“你所说之事,可是属实?”鄂伦的身子不由的颤抖,每一个字都像是自牙根里钻出来的。
银扣儿迎上他因极怒而充血的眼,忽而指着佛尔果春,“大人若是不信,可以问佛姑姑,奴才想没有人比她更清楚。”
佛尔果春失色,一直不曾作声的邓昌贵忽而怒斥道:“够了!佛姑姑是东太后的人,岂是你这丫头能编排的!”
东太后的人。
邓昌贵的话无疑在原本的冰上泼了一层凉水,更是把罪魁的矛头指向了那东太后。
可不?这又是多难想象的问题呢,讷敏是东太后当年赐的陪嫁丫头,除了她的话,还有谁能指使的动她呢?
鄂伦夫人疯了似的紧紧扯着讷敏的衣裳哭嚎:“为什么?为什么?我儿当年不过十四,还怀了七爷的骨肉,为什么要对我儿下此等毒手!为什么啊!”
“夫人——”
“闭嘴!”佛尔果春终于说话了,她看着讷敏摇摇头,只道:“已经过去的事,便不要再提了。”
说罢她起身朝鄂伦走去,微微拂身行着宫礼,不卑不亢:“大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便是翻出来也没有任何意义,若是大人心中实在有气,佛尔果春一条命,愿听凭大人处置,绝无怨言。”
一番话罢了,众人皆听的出来,佛尔果春根本不打算说那理由。
其实说不说都不重要了,只瞧那鄂伦气的直哆嗦的极怒模样,解释与不解释恐怕结局都是一样的。
知道了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这案子是先帝亲口定案的,他能做什么?
便是那罪魁再可恶,那也是堂堂东太后,他又能怎么样?
难不成真一怒之下杀了这佛尔果春?他鄂伦杀的起么?
鄂伦攥着一双拳头,许久之后咬牙说了一句:“烦请姑姑转告,我鄂伦谢太后娘娘抬爱,今日之事就当不曾发生过!”说罢又与婧雅道:“既如此,这世上也无小女福茹,老夫将她带回家照顾,也算是合情合理吧。”
婧雅一听,便知其欲与睿亲王府一刀两断的意思,她赶忙起身道:
意思,她赶忙起身道:“亲家老爷,我知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可姐姐这身子如今这般虚,哪里受的住车马颠簸,不如就先在府上住下,我这就去安排——”
“不必麻烦!”鄂伦语气冷且硬,“便是折腾的断了气,那也是她的命!她是生是死,老夫怨不上府上一句!”
“亲家老爷——”
“告辞了!”根本不再理会婧雅,鄂伦径直把藤椅上的福茹轻的纸片死的身子拦腰抱起,妻小随在身后,皆是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仇恨模样,甚至连石猴子等三位宫中贵人都不曾拜别,便极怒不已的一脚踢开了门,气冲冲的离去。
婧雅带着丫头忙追了出去,讷敏、佛尔果春也都跟了出去,一时间乱做一团。
当门‘乓’的一声阖上,风一扑扇,屋里的几盏灯火都顺着风向又飘又跳。
而后的安静,显得‘刺溜’‘刺溜’的动静儿格外明显。
小猴儿把一盏茶刺溜的只剩茶叶末后,撂下茶杯,抬眼儿瞧着那三角眼一耷拉,难掩得意的邓昌贵。
“你满意了?”
“咱家不懂姑姑在说什么。”邓昌贵不疾不徐,呵着热气,吃着茶。
“啧啧。”小猴儿咂咂嘴,“水仙不开花儿,你邓公公这大瓣儿蒜装的相当不错。”
邓昌贵也不恼,只道:“姑姑现在似乎不该把闲工夫浪费在我邓昌贵身上。”
“哦?”猴子挑眉笑笑,“公公这是提醒我,这睿亲王府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该去帮帮忙?”
“旧情总是要念的。”
小猴儿‘嗤’的一声,轻飘飘的道:“然后公公回宫的时候,好在太后娘娘跟前儿嚼嚼舌根子,说我石猴子不念皇恩,一门心思的难忘旧情?”
邓昌贵笑着吃了口茶,挑眉回道:“怎么?难道姑姑当真丝毫不念旧情?”
“这屋内只你我二人,又何必扯这样的谎。”
“谁说我要扯谎了?”小猴儿忽的直直看着邓昌贵,眼珠子亮的精光:“诶,龟儿子,你不是爱告状么,小爷儿我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这心里头装着的由始至终都是他七爷。”
“去吧,你就原话说给太后,再添点油加点醋也成,随你逼叨,满嘴冒沫子都成,你看太后信是不信。”
“你!”邓昌贵恼了,“你叫谁龟儿子!”
“谁应叫谁呗。”小猴儿贱呲呲的正说着,忽而想起什么似的拍拍脑门,“诶,不对,龟也有那玩意儿,你这种应该叫没根儿的王八,阉龟。”
“阉龟、阉龟、邓阉龟,哈哈,这名不错。”小猴儿自个儿说的乐呵,却是句句戳着邓昌贵的痛处,便是邓昌贵极力忍着不想跟她生口角,也是一万个忍不住。
啪!
邓昌贵一挥手,把那茶盏挥摔在地,他噌的窜了起身,难得站的直溜,耷拉的眼皮因愤怒瞪的格外精神。
“石猴子,你别以为我邓昌贵还是昔日那个人你欺负的人!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
小猴儿俩胳膊一张,相当大方,“来吧,你动我试试,我不还手,随你。”
那旧恨加新怨,激的邓昌贵当真扬起了手,然手没落下,就听那轻飘飘的动静儿再度飘出来。
“阉龟儿子,你打归打,可别刮破了我衣裳,我这出来的时候皇上非得给我穿上一件儿皇马褂,我这没来得及脱,你可别给我刮坏了。”
“你!”邓昌贵那空中悬挂的老抽吧手,攥成拳头,哆嗦了几下,气急的甩下,砸在桌子上,砸的小猴儿的茶盏铛铛直响。
“石猴子,花无百日红,你且嚣张着,总有一天会落在我邓昌贵的手里!”邓昌贵掐着阴阳怪气的嗓子,居高临下看着小猴儿的眼珠子恨的窜火,然,这把火,还没烧起来,就给一股子茶水给灭了。
小猴儿撂下茶杯,扫了一眼那满脸茶叶沫子的老褶子脸,‘乓!’的一声,远比他刚才更大力的猛拍了下桌子,倏的窜了起来,棱起眼神,盯着他。
那样的眼神,一如多年前,那仙人馆初见,漫不经心却满目森寒。
邓昌贵竟忘了擦去脸上的茶叶,怔怔的僵在那里,仿佛他还是昔日那跪地求饶的老坦儿,生杀大权都定在眼前的女混混儿手里。
“呵。”小猴儿冷笑一声,“邓昌贵,我是不是惯着你太多年,你当我石猴子怕你了?”
邓昌贵绝不承认,他心下漏跳了一拍。
“我告诉你,上次毛伊罕的事,我不跟你计较,不是我惹不起你,是我懒得惹你,你丫道是给脸不要脸。”小猴儿一把揪住邓昌贵的衣领子,拽过来,居高临下的钉着他,轻飘飘的道:“你要是活腻歪了,你直说,别他妈整日跟我后头捅捅咕咕,阴沟里的耗子似的,他妈招人膈应!”
邓昌贵破布条子似的给猴子扯着,忽而阴阳怪气的笑了出声:“怎么?姑姑这口气,可是替七爷出的?如果是这样,随便你。”
“咱家只告诉你,再怎么都没用了,那鄂伦同这睿亲王府的关系,已成定局。”
“是吗?”小猴儿也笑笑,“怎么?公公还有后招?”
邓昌贵讥笑,“你兹等着看好戏吧。”
“好戏?”石猴子笑笑,“却是场好戏。”
“不过这场戏,怕是要我请你看了。”
邓昌贵还没反应过来,却被石猴子猛的一推,忽的摔栽倒地,再瞧石猴子全然一副无惊无惧的模样,心下只觉不对劲儿,然未等他多琢磨,却听那猴子一嗓子厉喝——
“来人,把这龟孙子给我绑起来!”
却听这一嗓子,忽而门外窜进来七八府兵,像是一早便准备好似的,二话不说便利落的反剪了邓昌贵。
这下邓昌贵明白了,这猴子唠叨了老半天,根本就是拖着他的时间!
邓昌贵心知不好,扯脖子怒喊:“石猴子,你要干什么!”
“你别忘了!你如今是什么身分!”
“你敢——”
“把他嘴给我堵上!”小猴儿一嗓子令下,片刻,邓昌贵就只能瞪眼睛支吾。
小猴儿扬着下巴,伸手指头指着他:“邓昌贵,我告诉你,小爷儿我就是孙悟空转世,天生好闹事!”
“你不是爱瞧戏么,那爷爷我就请你看场好戏!”(。。 )
第卅二回 人嘴两张大肉皮 上下一动都是理()
驾!
鞭声划破黑夜的寂静。
两辆马车先后急促的驶出后巷,将那挂着四盏‘奠’字白灯笼的睿亲王府后门,越甩越远。
才行至转弯处,忽听七八抽刀声,兹见那黑暗中窜出七八人,身着亲王府兵服制,人人手持钢刀,月光下,那钢刀反着光,森寒森寒,惊的马夫勒了缰。
一声嘶鸣,车内的鄂伦钻了出来。
“何人拦路!”
这一嗓子怒喝还未砸到地上,却见那七八人便抽刀砍了上来,一时间众人皆是慌乱,那些下人奴才纷纷有鞭子的抄鞭子,没鞭子的抄杌子冲了上去,纷纷乱挥的挡着刀阵。
马车内的鄂伦夫人吓的面色青白,小女儿福晴更是给四肢皆瘫,滚摔的福茹压在身下,惊声尖叫。
鄂伦自垫子底下抽出刀来,护在妻小身前,眼见那府兵的胳膊上都带着孝,已是怒极!
“好个睿亲王府,好个东太后,此欺我,辱我,今还要灭我鄂伦的口不成!”
鄂伦愤然至极,扬起手中的刀,大喊了一声:“给我杀!杀出重围者,重重有赏!”
一听有赏,人人精神,管他是奴才,还是随从,各个儿像是打了鸡血,一股脑的往前冲,也不知是为那出头太过拼命,还是怎么着的,兹片刻过去,竟当真打的那些手持大刀的府兵们节节败退。
而那些个府兵根本不恋战,只虚刀乱砍了一阵,便撒腿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