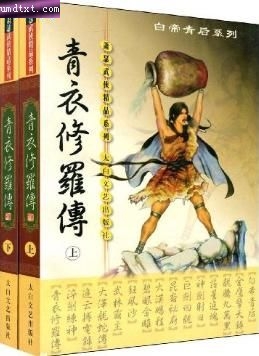痞妃传-第20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猴儿问他:“喂,你丫在外剿匪,就这么只身过来,算不算擅离职守?”
僧格岱钦低笑:“你这丫头难得求我,做一回逃兵我也认了。”看着那潮红未退,满脸布着汗珠儿的丫头,僧格岱钦想:她一定不知道现在的她,比天上的太阳还要亮!
“滚蛋,不恶心我,你丫难受是不是?”小猴儿怼他一拳,给他的肌肉块子咯的手通红,她看看拳头,撇撇
拳头,撇撇嘴,“一年不见,你丫怎么壮的跟牛似的?”
僧格岱钦爽朗大笑,回看她,“你不也是跟插上翅膀似的?我还以为要见着个病秧子呢。”
“得,你要准备好白帛,就趁早自个儿花了。”小猴儿扬扬自个儿划着横线儿的手掌,“小爷儿我命硬,你死三个来回儿,我都好好喘着气儿呢。”
僧格岱钦忽然正经起来,满眼的欣慰,“丫头,看见你这样,我就放心了。”他绝对不会说,他这一路,八个时辰不曾下马,满脑子都是她一副病殃殃的模样儿。
她承受了多少,他心中都有数。
谷子身在敌营,天养杳无音讯,孟秋才过世,种种种种,她的笑脸之下装载的是一般的男子都承受不住的压力。
是以,就算他心中有对推她出征的延珏有多少不满,也都压在了心里。
就算她坚强,他也不想再伤她。
而且,让他欣慰的是,此时此刻,她需要他。
“说说吧,那些个兵将是不是让你恨的牙痒痒。”僧格岱钦直切入题,带兵多年,他心里知道她惶惑在哪里。
果不其然,小猴儿猛个劲儿的点头,撇嘴儿,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儿,憋了半晌,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她道是诚实,话到嘴边儿,就俩字儿。
“咋整?”
僧格岱钦失笑,“我就知道,你这丫头,准一脑袋浆糊。”
“所以得找你这行内人呐,我说仙人,您就给我这尘世迷途小子指条明路吧。”小猴儿裹紧了氅子,一脸谄媚的把这顶大高帽戴在了僧格岱钦的脑袋上。
僧格岱钦不枉这一番忽悠,一语中的,“你的那一群兵,说着是兵,各个是爷儿,那一群将,叫着是将,各个儿闲散仙人,脸上写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小猴儿简直差点儿就要把脑袋点到了地上,“你说的太对了!怎么回事儿呢?我跟你说,我脑袋都想破了,也没琢磨透。”
“这有什么难琢磨的,绿营兵虽是汉人,却也都是世代承袭的兵籍,他们当中,不乏武举子,不战的时候,各个儿都是吃朝廷俸禄的,平日里,那也都是横着走惯的主儿,能服谁管?”
“那些标将就更不用说了,朝廷对汉兵向来是养着,防着,未免汉将坐大,时常掉转,待打仗时再临时调任,将与兵不相属,兵与兵不相习,彼此根本不熟悉,又如何调遣得宜?”
“又再说了,你这一路现编的那些乡勇,就算编制与绿营的弟兄们看似一样,可吃的饷,却是大大的不同,一个是终身饷,战不战,战的如何,一样吃饷,自然怠惰,一个是战时饷,有多大勇气,吃多大的饷,这是根本的不同,这样的散兵,纵有十万,不敌一万亡命徒。”
“至于你那些随军的大将们,掰着手指头算算,有几个武将?朝廷最爱派遣文臣领军,却不知,文多不知武,这是行军的大忌。”
僧格岱钦说的头头是道,小猴儿恨不能把耳朵都支过去,连连点头之后,还是那两个无赖字儿。
“咋整?”
“你真当我神仙呐?”僧格岱钦失笑,敲了敲她的脑袋瓜儿,“这样的顽疾,怎么着也得容我想想吧。”
“成,您想着,好好想着!”小猴儿拍拍拍拍胸脯,“您现在就是我亲哥,您有嘛想吃的,想要的,都包我身上,您就负责给我想明白这事儿就成!”
“嘴儿抹了蜜似的。”僧格岱钦轻嗤,“晚上明明是去人家祁大掌柜家吃白食,何来你请之说?”
“呦呵。”小猴儿楞眼儿,“晚上你也去?”
僧格岱钦点头,笑里含笑,只道:“你干什么去,我就干什么去。”
一句话,小猴儿明白了,他就说么,他僧格岱钦怎么可能甩下一众兵将,跑来干陪她耍?
合着他也是有目的的。
……
第五二回 盛情佳肴思故乡 举头明月尿慌张()
这病秧子怎么着也成不了神仙。
小猴儿这一整天委实是得瑟的狠了,天儿还没黑呢,她就俩眼珠子乏的赖歪歪的,两副药吃下了肚儿,还是不免阵阵轻咳,去归化城赴宴的路上,恁是大街依然热闹的紧,她也紧闭着帘子,始终半死不活的栽歪在方枕上,霜打的茄子似的,半点儿白日里的精神头儿都瞧不见。
“不是自个儿家门前?连这早晚凉的变脸天儿都给忘了?”僧格岱钦摘下自个儿的氅子径自给小猴儿盖上,烛火下,玄色的大氅更是衬的那白瓷儿似的脸没有丁点儿血色。
这会儿的小猴儿,谁瞧着都像纸片儿,可这主儿自个儿却是丁点儿不自觉,蔫儿是蔫儿,可该逗哏儿照样逗哏儿。
她揪起身上的氅子,撇嘴,“嗬,咱俩本来就坐一辆车,我再穿着你这层皮,恁谁不瞎,瞧咱俩都是有一腿。”
僧格岱钦没接这茬儿,猴子接着逗他,“咋,咱俩有一腿,你是高兴啊,还是高兴啊?”
“高兴。”僧格岱钦毫不转弯的一句话,给小猴儿说愣了,眼珠子瞪的老大,啧啧咂嘴,“脸皮没少厚啊,你道是直接。”
“出家人不打诳语。”
“出家人还不娶媳妇儿生孩子呢。”小猴儿损他,僧格岱钦也不恼,始终噙着笑。
小猴儿似笑非笑的道,“诶,和尚,我可先告诉你啊,我是有事儿求你,可没说以身相许哈,你要惦着如花似玉的、貌比潘安的小爷儿我,趁早快马加鞭往回走,就算我能凑合,我也没法儿告诉你丫是我儿子他爹,实在长的没丁点儿像的,骗傻子傻子都不信。”
僧格岱钦噗嗤一笑,肩头哆嗦了好半天,才弯着笑眼道:“貌比潘安是说男人的。”
小猴儿嬉皮笑脸的白他一眼,“有个叫潘安的美女,是你不知道。”
僧格岱钦失笑:“那合着是我孤陋寡闻了?”
小猴儿大方的摆摆手,“算了,算了,看在你丫给我干那么大事儿的份上,我就不笑话你了。”
僧格岱钦开怀大笑的同时,精光沉下眼底,他知道这丫头揣着什么心思,可他更能看清自己心里头熟透的心思。
……
作为大清唯一异性王的蒙古王爷,僧格岱钦在蒙古的地位绝非常人可比。
当然,虽然驻着大清的军队,行使着大清律法,也是大清极力划为内治的边贸重镇,可谁都不能不承认,这里还是蒙古。
是以当众人看清那个让小猴儿搭着手跳下车的伟岸男子是何人时,无一不惶恐的跪地行礼,那惶恐,不是来自惧怕,更多的是敬畏。
在这里,也许只有小猴儿把他身边这个俊伟的男子,当作凡人。
对于更多人来说,僧王,是神。
粮饷厅同知徐海伏地不起,说话都激动的结巴起来,“不知、不知僧王驾、驾到,有失远迎,实乃下官罪过!”
“都起来吧,本王今儿只是顺便过来看看朋友,无意声张。”僧格岱钦大手一摆,言语虽是温和如常,可无论是口气,还是言辞,都透着一股子不怒自威的风范。
小猴儿许久没见过这样的僧格岱钦了,冷不防,她都有些不习惯,她翘翘脚,附在他耳朵边儿上低语:“这官腔让你打的,还挺像回事儿的。”
僧格岱钦低低笑着,附耳回她:“彼此彼此。”
俩人说笑的开心,全然不介意这副画面在旁人看来是怎样的一副暧昧,又或者说,两人都心知肚明,只是无人戳破罢了。
可不?
谁说这样的暧昧不好呢?至少一个欢喜,一个得利。
入席后,小猴儿明显感觉,众人瞧自己的眼神儿也多了一股子敬畏。
可不?
神仙的亲戚,怎么也不是凡人,英雄的朋友,怎么也不可能是狗熊。
今儿这席子的东道主,是大盛魁的大掌柜祁晋。
小猴儿不知道这祁晋究竟有什么能耐,可能让延珏那厮写上锦囊的,绝不可能仅仅只是一个人名。
就拿今儿的晚宴来说,不得不说,他的心思是摸到她的心坎儿里了。
且不说那地点选在如今归化城并不多见的蒙古包里,只说那吃食,奶皮子,奶酥,奶酪丹,馅饼,炒米,等等小食,每一样儿都是寻常蒙古人家的日常吃食,在这归化城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吃食,却偏偏是小猴儿惦记了二十年的故乡味道。
尤其是那羊皮包着火炭的包的格烤羊,那味道还没出来,滋滋的声音就已经征服了小猴儿的胃,惹的许久吃东西没味儿的她,频频咽着唾沫。
赴宴人员大小官员将领共四十余人,除却小猴儿、僧格岱钦、石墩儿、以及本地三个级别较高的地方官员,其余通通于帐外摆席。
于主位落座之时,小猴儿扫扫那并排而列的两个位子,睨了一眼那始终忙着周旋的祁晋,心下道:看来他一早就知道僧格岱钦入城的事,不然怎么会备好两个齐平的主位?消息比地方大员还要灵通,看来这祁晋果非一般商人。
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僧格岱钦这时也附耳道:“在这西北,只有你我不知道的,绝没有他祁念乡不知道的。”
小猴儿转头看他,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哦,原来这人的表字,叫念乡。
“念乡……念乡……”小猴儿嘴里反复砸着这个名字,不知怎么,
这个名字,不知怎么,有种莫名的熟悉感,可一时又实在想不起曾经在哪里听过。
就在这时,却听次位的石墩儿一嗓子:“好香的羊肉!”
小猴儿全部思维都聚集在了鼻尖上,她深深一嗅,那股子浓浓的独有的炙烤的膻味儿,让她一瞬间便回到小时候。
曾经,每每有大宴时,她总是等不及的守在烤堆儿前,不管额娘如何耳提面命的教她‘女娃要有女娃的样子,女娃要有女娃的端庄’,她也不管不顾,反正怎么耍赖耍泼都要吃上一块儿新鲜出皮的包的格烤羊,抢久了也就抢成了习惯,甚至有一次,那炙烤的师傅手艺生疏,肉还带着血丝,她照样吃的津津有味。
阿玛笑她:“我们的小猴儿是土匪的性子,只要抢来的都是好东西!”
阿玛的笑声犹然在耳,小猴儿也不觉跟着笑了起来,一旁的僧格岱钦低声问她:“想到什么了,笑的这么开心?”
小猴儿一转头,对上僧个岱钦那和她阿玛一模一样的疤,只觉恍如隔世,物是人非。
如果当年阿玛不曾出事,会不会也这样同她并排而坐,吃着烤羊,喝着**呢?
小猴儿摇头叹笑,不想做那些没意义的白日梦,很快又复了不着调的模样,哏儿道,“你这一转头,吓我一跳,一晃儿寻思我阿玛诈尸了呢。”
僧格岱钦笑笑,嘴角却抬的牵强且吃力。
……
今儿的一切对石墩儿来说,都是新鲜的,他从未来过蒙古,更从未吃过蒙古的筵席,从摆盘,到礼节,一切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
尤其是当那个祁晋把用银碗盛的骆驼奶,依次奉上之后,他才要尝尝这从未喝过的味道,却见长姐、僧王等人用右手蘸着**,神情庄重的向天一弹,再向地一弹,最后才自己尝了一口,他好奇极了!
他悄声问身后的小狼:“小狼哥,他们这是做什么?”
小狼一头雾水,娃娃脸闪着跟他一模一样的困惑。
接下来,他们也没有立即开席,而是那个叫祁晋的喊了一声后,进来了一个穿着蒙古袍子的大汉,站在殿中间竟神情庄重的朗声唱上了,唱的八成是蒙古语,他一个字都听不懂,唱了好一会儿,待罢了,却见长姐把成着烤羊的木头盘子掉转过去,羊头朝着那大汉,那蒙古汉子从身上抽出一把蒙古剔,将羊肉割下几个小块儿放入一个银杯中,转身向天一扬,接着才回身操着熟练的刀法,把那羊肉卸成许多小块儿,接着把羊头摆好,再把木盘朝长姐掉转回去,把刀柄又递给了长姐。
这时那蒙古汉子恭恭敬敬的站立,两手聚起掌心向上,说了一句:“诸位用膳。”后,倒着退出门外。
接下来,长姐将羊头取下,这时才有仆从上来,将羊肉成在小盘子里,逐一端上席。
当那口羊肉终于吃在嘴里时,石墩儿简直觉得是他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不是那味道,而是这一口吃到嘴里,实在太漫长了!
他好奇极了,他真想张嘴问问长姐,她们刚刚那是什么仪式,可话到嘴边,又就着骆驼**咽到了肚里。
算了,他虽然不是什么聪明人,却也知道长记性。
长姐说了:拉不出香屎来,至少别放臭屁,他的任务就一个,把架子端起来,别拆了石家的台。
是以石墩儿这一个晚上,都坐的倍儿直,腰杆子挺的酸疼不已,一股子多大风都吹不倒的模样儿,想来他也算装的成功了,不只一人跟长姐夸赞他‘颇有乃父之风’,管他们是真情还是假意呢,能说的出口,至少就说明他装出了三分样子。
他看得出来,长姐今儿晚上心情十分不错,不然不可能吃了整整两大块烤羊,要知道这一路上,他可是不时伺候长姐吃喝的,什么时候也没见她吃完一整个馒头啊。
难不成,是因为那僧王在身边儿的关系?
他在京中不是没听过长姐的那些风流韵事,这僧王也是其中叫的响当当的一号人物,从前他还当说笑呢,可如今一看,嘿,别说,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
瞧瞧,僧王又跟长姐撞杯了。
那可是僧王啊,从不饮酒的僧王啊,他可是听说过,先帝在时,赐他酒都是要换成茶的啊。
石墩儿一双眼骨碌骨碌的转着,他们说的那些什么关税,粮道的,他一概听不懂,他只是故作精明的四下瞄着,冷不防对上长姐似笑非笑的眼,习惯性吓的一阵激灵,不知道是不是酒的喝多了,只觉一股子尿意往小肚子冲,他回头跟小狼耳语了一句,就悄悄的离了席。
夜晚的归化城,凉啊,月亮银亮亮的高挂在天上,像一个大冰块子似的,每过一阵风儿,都吹的石墩儿一个激灵。
几个外帐的将士也喝的脸红脖子粗的出来放放水,石墩儿想:他是要端着架子的,如厕可不能让人瞧见。
是以乌漆抹黑的,他揣着满肚子尿意,低着头不嫌麻烦的绕到了帐子的后头,寻了个不着亮儿的地儿,才放心的撩起了衣摆,着急忙慌的褪了裤子。
然才呲了一小溜儿,只觉后脖颈子一凉。
当反应出来嘛玩意儿贴在上头时,他一慌、一软,尿都洒在裤子上。
“不许叫,出一点儿动静,立马宰了你!”一嗓子清亮且不失恶狠的动静儿自身后响起,这一下,咱石墩儿嘛架子也端不住了。
就在他要吓哭之前,脖子给狠狠一砸,人软泥似的倒在自个儿的尿堆儿里。
黑暗中,两人低声问道:“天养小哥,现在怎么办?”
却听那为首的少年道:“先带走再说。”
……
第五三回 昔日发小两不认 娘俩初面提刀见()
整席都快散了,大伙儿才发现,诶,石将军人呢?
小狼说:半个时辰前如厕去了。
大伙了了,想来八成是喝醉了,栽在哪儿了睡了吧!
徐海说:多派些人去寻将军!
少时,这许多些人接二连三回来,连三倒四的摇脑袋,哪儿都找遍了,没有将军呐!
嘿,好好个活人还能不见怎么着?
小猴儿说:慌什么,没准儿小弟喝醉了,回了绥远城也说不准,要不这样,咱们先回去瞧瞧。
众人点头,唯同知徐海的脑袋低沉的看不着眼睛。
坐在他身侧的祁晋瞥了他一眼,但见他桌子底下的手攥成拳头握的红里发白,指缝儿里露出来个碴儿,瞧那模样儿,是纸张吧。
徐海好似发现有人在看他,可转过头时,祁晋早已起身,去安排车马张罗送客。
回城路非漫漫,很快众人脑子里的酒就都散的差不多了,彼时,当一拨拨的寻人将士接二连三的回禀摇头,大伙才猛然惊觉!
不得了了!
石将军不见了!
整个帐下的将士官员都懵了,还未出征,帅先丢了,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僧格岱钦面色严肃,他看了小猴儿一眼,眉眼问着:该不会吓跑了吧?
小猴儿摇头,“不可能。”那孩子胆子小归小,却还是尊重她的,就算他临阵退缩,也会先跟她哭上一番再说,退一万步讲,就算他真吓得不管不顾的跑了,总得带点儿银子细软。
回禀的将士不是说了,将军的东西都好好的,没有丁点儿动过的痕迹。
僧格岱钦沉着半晌:“看来人还是在归化城不见的。”
……
归化城大盛魁的后院子厢房中,同知徐海急的团团乱转,额头的冷汗成流的淌着,沿着落在两旁的碎白头发丝儿滴答下来都浑然不觉。
一旁的领房看不下去了,上前道:“徐大人,您再急也不是办法,要不这么着,您先回府,等扼们掌柜的醒了酒,让他去拜会您,您看成吗?”
啥子?等他醒酒?
他要是真醉了,他认等,可问题是,他祁大掌柜可是出了名的人肉酒埕,岂能谈上醉字?
他心里明白的很,他这是成心躲他,躲这不干净的事儿!
徐海真想踹开门去,耍一耍官威,可他连抬腿儿的勇气都没有,在这归化,那里头的人可是土皇帝,他这一威,怕是什么前途都没了。
没办法,他只能接着转悠,使劲儿蹋着步子,怎么动静大儿怎么折腾。
跟外头急的火烧房檐儿全然不同的里间儿,适心的很,老长工满是褶皱的手,仔细利落的焚着香,炕上盘坐着的祁晋,此时早已换上一席白衫,自案几上厚厚的一叠账本中,抽出一本,边翻边打着算盘合计,一门心思埋到里头。
直到许久许久过后,当他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