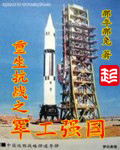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民国春归-第7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同于他的艳羡,仲清于此事上就慎重多了,虽是将人带到了客厅,但未见到陆建豪太太前,她轻易是不会走漏口风的。
陆建豪亦知空口白牙的也断然叫人难以相信,一进客厅便主动道:“夫人还有什么同在下说的吗?”
仲清让他落了座,吩咐仆人端上茶来,才道:“陆次长说昨儿有一块怀表典当到了我们家,我在这里不瞒陆次长,那怀表我倒也见过一眼,听我母亲所言,倒像是她们余家的东西,只是后来丢了。陆次长既然说是你夫人的,倒不知贵夫人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呢?”
为保险起见,她并没有说出叔云的名字,以便给自己留一个退路。
陆建豪道:“内子姓谢,双名雅娴,原同岳母住在苏州,后来赶上苏州那边打仗,岳父亡故,为避难就举家搬到上海了,我同内子正是在上海相识。”
原住苏州,迁至上海,且岳父在战争中亡故,倒都同那奶娘的身世对得上。
她又问:“可知你岳母姓什么?”
陆建豪道:“岳母姓杨。”
叔云的奶娘可不就姓杨?
仲清放在膝上的手猛然一缩,忍不住脱口问他:“那你太太如今在何处?”她几乎可以断定这一回是找对人了,真是苍天保佑,昨儿才拿到那怀表,今日就得了叔云的消息。假如母亲知道,必会高兴不已的。
她面色已然带了喜悦,********的等着陆建豪的回话。
然而陆建豪却并不如她所料的那样言明妻子的所在,只是微微低下头来,似是很为难又很落寞的样子:“不瞒太太,内子她……已经于去年过世了,所以我才说要拿回她的锦匣做个念想。”
“你说什么?”仲清冷不丁站起身来,帕子飘然跌落在地,她却一点都没有心思理会,只死死盯住陆建豪的发梢,“你说谁去世了?”她的三妹妹,她们一家找了那么多年,连面都没见过,怎么会死呢?老天不是才把她的怀表送回来么,人呢,人在哪里?
陆建豪和谭汝霖不提防她如此的不冷静,乍惊之后,谭汝霖忙起身按住仲清道:“你且听他说清楚,或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想的怎么样,我能怎么想?”仲清直觉脑子里似灌满了水,膨胀得厉害,她猛地拉起陆建豪,几乎问到他脸上去,“你同她结婚的照片呢?她长什么样子,她可……她可曾说过,她或许不姓谢?”
陆建豪让她揪住领子,人不得不随着她的力道站起来,面上仍是悲戚:“自内子去后,我因思念她太深,惹了不少乱子,家中老母实在恼恨,就将我们的结婚照都烧掉了。不过,她倒是留了读书时的照片在同学那里,太太若要看,在下倒可取来。只是,太太为何说内子不姓谢?”(。)
第一百五十六章 照片()
是啊,为什么不姓谢?她又不曾见过他太太的模样,如何就说她不姓谢了呢?
或者,或者叔云还活着。
仲清脑海里的思绪几乎搅成一团乱麻,她好不容易稳住心神,便道:“陆次长方才说贵府太太有旧日的照片留存在同学那里,因我母亲怀表丢失又寻了回来,只怕是遇着故人了。若可以,还请陆次长将你太太的照片取来,让我相看一二,我也好向母亲说明情况,将那怀表拿回来完璧归赵。”
陆建豪岂不知她心中所惑,当下也不迟疑,道一声可以,便告辞先行回去取照片去了。其实他兜里就有谢雅娴上学时的旧照,但为了表明他意外来此的诚心,故而并没有当面拿出来给仲清。他出了门尽管在外头晃悠了一会,又不知衙门今日情形,便顺路到衙门里应了卯。瞅着时辰,也足够他取照片的时间来,这才姗姗来迟一般地再次去到镇守使署。
他倒是悠闲了,可苦了仲清,如烈火烹油一般煎熬着等待他,心里又惊又怕,惊那陆家果然有干系,怕那照片来之后,她再不能欺骗自己。也许,自己那个几乎丢失十数年的妹妹,真的就要从此丢失下去了。
她如此这般的坐立不安,连带着谭汝霖和陈芳菲都一道忐忑起来,陈芳菲是不知内里详情的,还当是旧京那边又出了事,她不便于细问,只得安静地上了楼,照料俊伟去了,顺便地将翠枝替换了下来道:“你瞧瞧表嫂去,这里有我呢。”她想翠枝是仲清的心腹,仲清总方便对她说些话的。
这也是她的体贴细心之处,果然翠枝下楼来,看到仲清和谭汝霖在客厅一坐一站的,兼之谭汝霖手边的水晶烟灰缸里落满了烟蒂,便知家中是有不得了的大事了。又见仲清和谭汝霖的神色,倒不似是夫妻间失和。遂轻手轻脚走过去,依着仲清坐下道:“太太,这是怎么了?”
仲清正忧心到极处,难得有翠枝来。她二人是自小长大的,翠枝又是家中家生丫头,李家什么事是她不知道呢?她握了握翠枝的手,只当她如自己的妹妹一般,低低叹口气道:“翠枝。我心里怕得很,你知道么,咱们家三小姐有下落了。”
“三小姐有下落了?”翠枝果然惊讶,三小姐有下落那不是好事么。呀,这会子太太才走,太太知道三小姐的事吗?
她悄声问着仲清,仲清摇摇头,谈及母亲,她才觉心里更乱:“母亲还不知道三妹妹的消息。”在一切未确定之前,她不能贸贸然的就同母亲说叔云的事。母亲已经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旧京的事还那样多,一个大哥就足够让她操心的了,设若叔云有个好歹……她简直不能想象,母亲会打击成什么样子。
她一直都愧疚当初将叔云留给了杨奶娘,愧疚有多深,对叔云的思念就有多重。叔云,可千万要活着。
她鼻子里又是一阵酸涩,握住翠枝的手禁不住又紧了几分。翠枝伺候她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她这般担惊受怕的模样,可见三小姐的下落必定是不大好了。
不过。是谁送来三小姐消息的呢?
翠枝疑惑的扫一眼屋里,再三确认除了仲清夫妇,是再无旁人的了。她咬咬唇,正待要问。打外头却走来一个侍从官道:“司令,太太,陆次长回来了。”
“快让他进来。”
仲清心情更加动荡了,原先倒还坐得住,眼下一起身忙就跟着侍从官往外走。谭汝霖和翠枝也急慌慌的跟住她,直走到院子中央。恰遇着陆建豪进来。
陆建豪一见她夫妻二人,忙从兜里珍重地掏出一张照片来,两只手儿捧着,递到仲清面前道:“夫人,这就是内子。”
仲清忙伸从他手心里接过来,只在那照片上扫了一眼,整个人就仿佛断线了风筝一样,颓然向地下倒去,慌得翠枝在后头连忙抱住了她。趁着这个功夫,翠枝也在照片上看了一眼,但看那四寸大的黑白照里,一副书着陋室铭的卷轴长长悬挂在墙上,跟前侧放了一方墨色的书桌,桌子边沿俏生生倚着一个二八少女,头梳挽髻,边分刘海,一张瓜子似的脸庞白皙光亮,两弯柳叶眉微微上挑,鼻翼秀挺,樱唇半开,三两分笑意,六七分羞涩,若不是她身上稍显过时的半截袖旗衫,简直活脱脱就是李家四小姐宛春了。
仲清岂不知自家妹妹的长相?早先她还觉得陆建裙不像是李家人,这会子倒觉所料不错,她的三妹妹该当是如四妹妹一样的,一样地端庄淑雅,一样地美丽动人,就连那笑容,都只差在毫厘。
只是……只是这般可人的女孩儿,怎么会……怎么会年纪轻轻就死了呢?
她慢慢地将照片紧紧贴在了心口处,情不自禁落下两行泪来:“你且说来,我三妹妹是如何过世的?”
“三妹妹?”
陆建豪演戏演到了家,他佯装惊疑地看着仲清,片刻又直起身望向谭汝霖道:“镇守使,这……这是怎么回事?”
谭汝霖唉声叹口气,拍了拍陆建豪的肩膀,大有同情的意味:“一言难尽,英杰,咱们还是屋里说去吧。”便蹲下身,扶起了仲清,命翠枝道,“送太太回房休息去吧,今日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最好不要打扰了太太。”
翠枝听得仲清方才言语,心下已大概的猜出了事情的轮廓,她亦是伤心于三小姐的不幸的,当下便红着眼眶点点头,搀扶仲清回房去了。
这里谭汝霖同陆建豪回到了书房,既然是认定了叔云,谭汝霖自认和陆建豪就是连襟了。他起先还艳羡陆建豪的好运,这会子倒有点悲悯他起来,死就死了,陆建豪便是得了高官厚禄又如何,总比不上一个大活人的助力来得实在。况且,李家那头,实在是不好交代啊。
谭汝霖再次唉声叹气起来,陆建豪只当是不知,反倒劝谭汝霖起来:“莫不是内子真与太太是旧识?倒曾未听内子提起过,今日见太太这般伤心,镇守使还得替在下好生劝慰太太一番,内子无福,不能与太太见最后一面了,请太太节哀吧。”
“唉,你这……”谭汝霖直觉他也是倒霉催得很,都到了这儿了,还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索性他也不与他绕弯了,直白说道,“你我二人就不必分职位高低了,叫我冀望便可。英杰啊,不是我说你,你这在官场也非一日两日了,这还看不出苗头来吗?你那位夫人哪里是我家太太旧识,她分明是我家太太的嫡亲妹子,没听着我太太叫她三妹妹吗?你同她结婚那么多年,怎么一点消息都不知?”
“这……这这……这我哪里料想得到?”
陆建豪简直要受宠若惊,冀望是谭汝霖的表字,寻常也只有市长首长他们才可这般称呼。而英杰则是他的表字,同僚间倒是常常称呼,不过上级倒很少这么叫他,他听得最多也就小陆而已。
若要早知谢雅娴的这些消息,他怎么会……
不,眼下不是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紧紧握住了拳,压抑住内心的喧嚣和**,惶恐回了谭汝霖:“内子同岳母一直都住在石库门那里,靠着岳母给人家帮工来补贴家用和求学。贵府的太太那可是出身李家的二小姐,高门大户,或者连石库门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如何敢想内子会同太太有关系?且还是这般血缘关系。岳母生前虽也曾说过,内子非她亲生,但也没说她生身父母是何人,我只当内子是个孤儿罢了,倒不曾想……”
“不曾想会是北岭李家的三小姐?”
谭汝霖接过了他的话,直叹造化弄人。设若换他是陆建豪,他也会想都不敢想,自己娶得居然是百年世族的李家三小姐。
“可怜你如今正值盛年便做了鳏夫,不知你和……和三妹妹成婚几年了?”
陆建豪道:“成婚已八年了。”
八年?谭汝霖蹙一蹙眉,三妹妹才多大呀,这么早就成婚了?
“那你们可有孩子?”倘或有个孩子,岳母那边也好回话的。
“曾有过一个女儿,只是……呵,只是,去年孩子同内子一道出事故,死了。”陆建豪放缓了语气,尽量说得平静些,他纵然是个心狠手辣之人,然而毕竟事涉娇妻幼子,谈到这些未免有些心虚。
幸而谭汝霖未曾在意他的神色,只是对他所说的孩子也死了大为震惊,他还欲再问,忽听书房门外扑通一声,倏尔就响起翠枝惊呼声:“太太,太太,快来人啊,太太晕倒了。”
宛春坐在火车上倒不知镇守使署的兵荒马乱,她今晨着实是起得太早,上了车经了一阵颠簸,早有些困顿了,眼下睡意上来,少不得要躺一会子休息休息。(。)
第一百五十七章 相像()
ps。 奉上今天的更新,顺便给『起点』515粉丝节拉一下票,每个人都有8张票,投票还送起点币,跪求大家支持赞赏!
这节车厢虽不如她来时坐的特等专列宽敞,倒也舒适得很,侯升买的又是卧票,宛春躺在卧铺上,随着车轱辘哐哧哐哧的响动声,不觉就进入梦乡。她睡眠一贯轻浅,迷迷蒙蒙中,似乎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
她嘴里模模糊糊应了,想睁开眼,却不料眼皮子上仿佛坠铅一般,实在沉重得厉害,勉勉强强也只撑开了一条眼缝。一道雪白的人影就那样突兀的立在她卧铺旁,面容看不甚清晰,直觉是带了笑的,望着她道:“怎么就这样睡了,仔细着了凉。”
她想要摇头,无奈连头也动弹不得,只好听那人又笑道:“又看着书睡着的?小小年纪,倒要学这样多的东西,真是辛苦。”
咦,她并没有看书呀。来时母亲说车厢晃动,恐看书伤眼睛,早叫秀儿将书本都收起来了,哪来来的书呢?
她勉力一用劲,挣扎着要坐起身来,这下子倒是连身体都不听使唤了,双手无力的摊在床沿上,她想起秀儿是睡在下铺的,便想唤秀儿,欲张口,却又几度发不出声来,这几乎让她骇然起来。
然而床头的那个人竟然还在,她微笑着摩挲她的面庞,温凉的指尖从她的眼角眉梢划过去,嘴里还在呢喃道:“你长得可真是越来越像太太了,一样的眉眼,一样高挺的鼻梁,都是美人胚子。算下来,咱们也有十三年没见着太太了,也不知她逃出去了没有,若是逃出去了,不知她可还能记得你?你跟着我总是受苦,假如还有能见到太太的一日。真不知我要该怎么同她说起你了。”
她长得像太太?像哪个太太呢?宛春……宛春也曾受过苦么?可是,家里人都说,因了余氏夫妇的过度宠爱,四小姐是极为深居简出的。谁还敢让她受苦呢?
是谁,是谁在这里胡说八道!秀儿,秀儿……
她张大口,嗓子眼里却似塞了棉花,任她心里焦急万分。也喊不出一个字来。
那人的指尖依旧在她面庞来回,轻轻地,仿佛一个母亲抚摸着怀中稚子,怜惜又疼爱:“你本该是大富大贵的女孩儿,吃穿用度无一不好,偏生……偏生遇上我这么没用的奶母,雅娴,你以后若知晓实情,可别怨恨我呀,我实在是……找不到你的母亲了。”
雅娴?
她叫她雅娴?
她现在不该是李家的四小姐吗?为什么还会有人叫她雅娴?她的母亲……她的母亲不是死了吗。又从哪里来的奶母?不对,不是这样的,她不是谢雅娴了,她是李宛春,要快点起来,快点起来同她说清楚,她母亲余氏就在这里呢。
母亲要是知道她不是李宛春,而是谢雅娴,该会怎样的害怕和难过?
快点起来,快点啊!宛春皱紧了眉头。极力的挣扎着,想要挣脱开身上那一层无形的枷锁,可是她挣得越狠,那困着她的枷锁仿佛就越紧。耳边的人声也越来越响,眼缝中一扫而过的影响也越来越清晰。
她看到一个穿着凡士林旗袍的女孩子,快步地走进院子里,高大的梧桐树矗立在院子中央,阴凉的树荫下正坐了一个中年妇人,盘着头发做针线活。
那妇人看见女孩儿。不由就对了一脸的笑容,隔着老远就问她:“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早?”
女孩儿红唇启合,不知说了些什么,惹得那妇人脸色一僵,笑容慢慢就暗下去了,半晌才让那女孩子回屋歇一歇去。女孩儿的面色亦是僵硬苍白的,并没有听妇人的话进屋,只是蹬蹬疾走两步,跑到那妇人跟前一叠声的问着她,急迫得像是连珠炮,妇人来不及回答,将针线筐扔在地上,就把女孩儿推进房中去了,自己却靠在门外头,捂着脸呜呜咽咽低声哭起来。
她看到房中的女孩子亦是捂着脸低低哭泣着,她怔怔的看了许久,正待要上前问一问,却见那女孩儿忽的放下了手,一张巴掌大的脸霎时就出现了她面前。
啊!她蓦地就吓出了声。
那是……那是她自己的脸,是谢雅娴的脸。她记起来了,那一年她好不容易等着母亲攒够钱,送她去上了女子中学,上学没几日,身边同学莫名就开始闲话起来,都道她长得同母亲很不像。她是瓜子脸,母亲是团脸,她是柳叶眉,母亲是小山眉。她是杏眼,母亲却是丹凤眼,就连她和母亲走路的姿态都是不一样的。上中学的孩子左不过十二三岁,正是憨玩淘气的时候,女孩儿之间也免不了时常玩笑,都道她或许是抱养来的,又道或者是她母亲瞧她生得好看,拐了人家的孩子来得。
初时她还能辩争两句,后来闹得厉害了,便在一日气得从学校逃了课回来,直言不要再去上学了,又连问她母亲,她究竟是不是她的孩子?为什么她长得和她不像呢?若是不像,或者是像了父亲,可是父亲的照片呢?她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照片,也从来不知道父亲长得什么样子。那时她真是恨极了同学们的多嘴多舌,却从未想过替母亲考虑一二,青年丧父,一个人把她拉扯长大,该是多么艰难不易,她却还偏要在母亲面前一再的提起过世的父亲。
真是太不应该了!
宛春让曾经的自己羞红了脸,她偏过头又看见还在低低哭泣的母亲,很想上前去告诉她,是她说错话了,求母亲原谅她。
可是她步子还未动,身子却一晃,已然就醒了过来。
面前倒真是有个人影,但不是旁人,正是秀儿。一看她醒来,紧张地眉头才轻舒展开,笑一笑道:“四小姐梦着什么了,吓我和太太一跳。”
宛春讷讷不敢言明,试探着握紧了拳头,才发现身体终于可以动弹了。她揉一揉额头半侧着坐起身来,向下一望,恰与余氏关切的目光对个正着,便道:“妈也醒了?”
余氏点点头:“才醒,便听你叫唤了一声,只当你是磕碰着了,可我叫你两声你都不答应,便让秀儿去瞧瞧你。秀儿说你仍睡着,我便估摸着是你睡魇着,才命她唤醒你的。如今,你可好些了?”
“嗯,已经好多了。”宛春轻轻地抿唇,看一眼秀儿,“吓坏你没有?”
秀儿笑道:“没有,我胆子大着呢。这火车不比家里的床舒服,睡不好也是有的,再则,小姐脖子上那个怀表未免重了些,压着你胸口了,我听周妈妈说过,胸口上压东西要喘不过气睡不醒的,以后再要睡了,就把怀表拿下来吧。”
说着,便探手在她脖子上摸了摸,将怀表顺着颈子绕向了一旁。
宛春呼口气,怪道方才总醒不过来,原是魇着了。只是魇着的时候做的梦也未免太奇怪了,梦见旧人旧事倒还罢了,怎么好端端的母亲会说出那些话来?什么奶母不奶母,倒像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