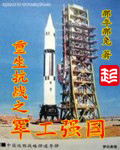重生之独宠傻瓜-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萧焱看见徐成器这般脸色笑得更加开心,当街随意地笑起来,随手就把手上的马鞭扔给了底下的侍卫,伸手拢了拢自己的头发,把头发拢到了脑后,神情反倒渐渐地缓和下来:“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可是每每看到你这幅模样,我还是会觉得简直妙不可言。看见你不高兴,我就觉得心里痛快多了。”
徐成器冷冷地看着他:“我看你就是个以他人的痛苦为乐的牲口!”
萧焱活动了一下筋骨,看着手下人牵来的马匹,瞬间踩着马镫上了马,对着徐成器粲然一笑,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薄唇微弯,看着十分的妩媚:“不错不错,骂得不错,左右痛快的是我,让你嘴上出出气也罢。算了,本想来这里找个乐子,却被人生生地败了兴致,今日我就不奉陪了。驾!”
之后萧焱看都没看被扔在一边的张瑾书,直接当街驾马扬长而去,路上行人纷纷避道而开,让他一人一马疾速奔走了。
在萧焱驾马而去之后,顾怀裕牵着薛嘉过来对着徐成器略一点头,就走了几步走到张瑾书面前,对张瑾书拂袖摆向徐成器,温言款款道:“在下和这位徐公子是一同出来的朋友,仰慕瑾书兄盛名已久。在下府邸离这里不远,如今看瑾书兄衣衫狼狈,不若前往在下府邸换洗一番,整理一下仪容。”
他可是听闻,这位张瑾书不禁文采出众,对于地方治政也是很有见地的。
第68章 共食()
大虞的科考和朔国有所不同。
大虞科考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在各城内城举行一次,在虞国是在春季举行,被称为是春闱。只有通过了童试的生员才能参加春闱,通过乡试后被称为是举人,举人中的第一被称为是解元。
会试是在乡试后第二年的秋季,在望京礼部举行,因此既被称为秋闱,也被称为礼闱。参加会试的是通过乡试的举人,通过会试的被称为贡士,贡士中的第一名被称为会元。
殿试是最终直面帝王的考试。参加殿试的是通过会试的贡士,通过后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
朔国科考与虞国类似,其与虞国不同之处就在于,朔国的乡试是在秋季,被称为是秋闱;而会试却是在春季,被称为是春闱。时间恰与虞国相反。
另外一点就是,虞国科考中有一类惯例,下放给各大城池一定的名额,择取城里最为出类拔萃的人才,可以不通过乡试直接前来望京参加会试,从地方上直接荐才到中央。各大城池名额不同,大约五到十名不等。这种制度也被称为“察举制”。朔国却是没有这种惯例的。
一般来说,能不通过乡试而直接被“保送”到望京来参加会试的人,都是各地德才兼备、极有名望之人,往往在同类学子中更为出众。而张瑾书就是淮城这次通过“察举制”推荐到望京的人才之一。
顾怀裕早就听说过这个人,对他的行为处事很有好感,最近一段时间正打算结交一下这人,没想到正好让他在街上赶上了,自然就顺势把人邀到了家中。
室外日头将落,待张瑾书换洗了一身干净衣服出来,带了淤青的脸上也敷了一层淡淡的药膏后,顾怀裕早已经在室内摆好了涮锅,与徐成器四人围着桌子席地盘腿坐成一圈,桌上配着清凉的酿酒,四个酒樽都被满上。
张瑾书过来的路上就听说了他们几人的身份,如今也没有多加推辞,直接一摆衣尾,在桌前款款坐了下来,方才在街上的气愤之色散了许多,拿起桌上的酒杯对着顾怀裕三人敬举:“没想到几位原来就是长公主的公子以及公子肖门下的景公子和卫公子,方才还要多谢徐公子的解围。只是在下不曾见过各位,如今能结识各位实在是一件幸事,在此先自饮一杯。”
说罢,张瑾书就抬起酒杯一饮而尽。
方才这人分明被萧焱踩在脚下折辱,而这一幕被他们几人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这人却没有妄自菲薄或是恼羞成怒,反倒是坦坦荡荡地提出来道谢,这份心性倒是不错。
顾怀裕笑了笑,目光里透着两分欣赏,也跟着举起酒杯道:“不错,今日我们四人相逢便是缘分,别的不说,当先浮一大白才是。”
徐成器和薛嘉笑了笑,也跟着抬手满杯而饮。
既然见张瑾书并没有避讳此事的意思,顾怀裕也就跟着说道:“不知道瑾书是否认识今日那个穿着紫色衣服的公子哥?”
张瑾书摇摇头:“之前并没见过,我只听说他好像姓萧。”
徐成器毫不客气地把盘子里的菜蔬倒进锅里,一边接话道:“瑾书不认识他也不奇怪,他就是这满望京里数一数二的纨绔,头一号的疯子,太后是他姑姑,他就是萧门里的那个萧焱。”
张瑾书脸色霍然一惊:“他就是那个打死了廷尉府少爷的萧焱?”
萧焱的名声基本上是坏到了家了,就连张瑾书这等初上望京的人都听说了萧焱几年前打死了廷尉府公子却没偿命的事情,望京里提起他简直人人恨不得避而远之。
徐成器略一颔首:“不错,就是那个萧焱。”
“萧焱这人仗着有萧老太君撑腰,在满望京里飞扬拨扈无所不为,得罪的人不在少数。只是这人横起来不要命,所以望京里人人都觉得他是个疯子。我看他精神确实也有些问题。这种人虽然一时奈何不了他,但他迟早是要遭祸的,说不定哪日就横死了也未可知。”
张瑾书知道徐成器这是在安慰他,也是向他示好的意思,于是也道:“望京里权贵众多,丞相门前尚且七品官,主街上人来送往,哪知道会得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我也知道今日惹到这人怕是有些不妥,只是实在有些看不过眼去。”
徐成器道:“哦?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惹到了瑾书,我们可有能帮扶的地方?”
张瑾书叹了口气,把自己遇上的这桩事缓缓说叙述出来,语气不无帮不到人的惆怅。
顾怀裕听他说出这件事的因果,对着张瑾书的眉目舒展开来:“如果是这件事的话,我看倒是有解决的办法。”
张瑾书顿时看向了顾怀裕:“景行有什么想法?”
顾怀裕略一颔首:“瑾书不知道,其实我认识这群玉楼的主人,这群玉楼是我一个朋友的产业,有些事情,明着不好做,暗地里想些办法还是可以的。”
徐成器睨了顾怀裕一眼,眼角微弯,眼里似笑不笑:“你这说话就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来?什么叫明着不好做,什么又叫暗地里想办法?”
顾怀裕斜斜瞥他一眼,没理会他,直接对着张瑾书道:“这件事据瑾书说,那个萧焱已经把那对姐妹买了下来,我们确实不好再插手,明着得罪这样一个行事无所顾忌的疯子并不划算。不过如果想救人的话,我倒是有个办法。”
“我和群玉楼的老板还是有几分交情的,我可以向他出这对姐妹的身价把人赎走,然后让他对萧焱诈称那对姐妹无意中食用了不该食用的食物中毒暴毙,私底下把人给换出来。之后我会替这对姐妹安排新的身份,让她们到我夫郎这两年在京郊新办的女子学堂里学些才识和手艺,日后可以过上普通人的生活。”
群玉楼的主人他的确熟悉,其实就是欧阳建。
五年前,欧阳建冬夜里替沈岸华挡了一刀,当时他就看出了这两人确实有情,纵然之前再有什么误会,这次怕是也要重归于好。后来欧阳建偶然间还对他透露出口风,说是要随沈岸华前去望京,留在云城的生意还要蒙他看顾一二。只是他没想到,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为什么,沈岸华好像并未和欧阳建商量,就撇下欧阳建自己一个人回了望京。那时他正逢薛嘉被人掳走一事,根本没心思理会他们两人之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等他找回了薛嘉,从西海上重新归来之际,欧阳建已经处理完云城这一摊事,也前赴望京了。
等他在云城的势力依靠西海上的资源站稳了脚跟,按照公子肖的意思前来望京拓展产业,才在望京和欧阳建重逢,重新联系上了这人。那时他才知道,沈岸华大约是有所顾虑,才放下了欧阳建自己回了望京。可是欧阳建为了追夫,后脚就跟着沈岸华来了望京。如今欧阳建明面上和沈岸华并没有多少联系,私底下到底如何顾怀裕也是不得而知。
至于群玉楼,是开在望京皇城直道外唯一的一家秦楼楚馆,望京头一等的风雅之地,堪称是望京的一面招牌,原本也不是欧阳建手底下的产业。也不知道欧阳建到底用了什么招数,最后竟然把这楼给盘了下来。既然群玉楼现如今在欧阳建手里头,这件事情自然就好办多了。
张瑾书沉吟片刻,脸上有些犹豫:“这个办法很好。只是,如今我囊中羞涩,没有多余的财物,出不起这对姐妹的身价。若是让景行来出,又怎么好意思呢?”
一直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的薛嘉这时眉眼微笑开口道:“瑾书若是这样想就不对了。好事天下人人可以得而做之,别的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如今眼见有两个年龄尚幼的女孩将要遭到一个心性疯狂的疯子荼毒,我们自然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重要的是要先把人救出来。既然如此,是瑾书来出钱财,还是我们来出钱财,又有什么区别?”
张瑾书虽然好读经史,可不代表他是个不通世情的人。虽然性情耿介固执,可在待人接物的礼数上,该有的他却一分都不差,不然也不会才来望京数月就有这般高的声望。他也并不是一个完全视钱财于无物的人,这事情本来是他挑起来的,人也是他要救的,自然不会觉得顾怀裕夫夫给他出钱赎人是理所应当的。
“可是此事本是与我有关,你们才会牵涉其中。我什么都没做,全仰仗你们三人帮我,实在是有些过意不去。”
薛嘉淡淡一笑,继续劝道:“钱财乃身外之物,更何况我们本是行商之家,一些钱财对我们而言本不算什么。可是天下之大,我们能同桌而食,就是一种缘分。那对姐妹的母亲对瑾书有留宿之情,有因有果,瑾书因此和她们结缘,所以想要救她们。我们既是瑾书的共食之友,出钱赎人一为帮人,二也是为了朋友,瑾书就不必将这等小事放在心上了。”
旁边徐成器朗朗一笑,一边涮了涮碗里的肉,一边跟着说道:“就是就是,钱财怎么比得上情谊重要?今日我们和瑾书相识,做好事当然也不能少了我,这钱我也出一份。”
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张瑾书自然不能再回绝。他便也放宽了心态,举起满上的酒樽对着三人敬酒:“既然这样,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今日情谊,瑾书会记在心上。”说罢,张瑾书举杯仰头一饮而尽。
顾怀裕眉毛一挑,心里暗道这张瑾书倒是有几分意思。他心念一转,随后叹了口气:“人我们倒是可以救出来,只是望京里有萧焱这等人的存在,总不免会有其他的人遭到祸事。”
张瑾书点头,话里也带上几分推心置腹的意思:“不错。我看如今的律法有些涣散,免不了一些可以钻的漏洞,也是该好好地整顿刑名了。”
顾怀裕之前只听说过张瑾书文采出众,没想到他似乎对刑律方面也有意思,语气里带着几分感叹:“原来瑾书对刑法也有所涉及,实在是涉猎广泛。”
张瑾书从锅里夹出一筷子蔬菜,摇摇头笑道:“哪里,我对刑律方面涉猎不深,只是略有所懂罢了。不过我在淮城有几个至交好友,他们都是有真材实料的人,这次也一同随我上望京来参加会考。其中有一个朋友最好研读刑律方面的书籍,对修改编写刑律最有兴趣。”
顾怀裕眸光一闪:“哦?不知道瑾书的这位友人叫什么名字?”
张瑾书道:“我那位朋友姓傅,名唤君华。”
徐成器有些惊讶:“是淮城那位有‘阡陌相逢人如玉,君华一度公子傅’之称的傅君华?”
第69章 君华()
“是淮城那位有‘阡陌相逢人如玉,君华一度公子傅’之称的傅君华?”
大抵是因着肖容敛的缘故,时下世人最为推崇的就是君子端方、温润如玉这种类型的公子。身在闺中的那些小儿女,心里往往也最为仰慕这种形象:白衣翩然,走动从容,举手投足之间风骨天成,侧面回身,面容姣好,只留下半面侧弧。
公子肖与顾怀裕同年,时年二十四岁。而傅君华如今却已是而立之年了。若说是肖容敛引发了望京乃至全大虞白衣公子的风尚,那傅君华就是风气还未起之时就已成气度的人物。
说起这号人物来,好打听奇闻异事的徐成器怕是知道的最清楚。
傅君华,淮城人士,母家寒微,身世很是有些奇特。
大虞律法不禁纳妾,但娶妻却只能娶一位。虽然民间有俗称的平妻、侧妻,地位要高于一般的妾室,但律法上却是不存在这些的。大虞的律法到了本朝只承认正妻为妻。
傅君华其父本来是淮城颇有地位的人家里的少爷,但不知道是出于何种怪癖,极爱“娶妻”。虽然名义的妻子只有一位,明明还可以再纳妾,他却偏偏在私底下捏造了许多户籍出来,编出了许多寒门身份,并蒙骗了不少小户甚至是贱籍女子,与她们“成亲”,娶了数位“正妻”,并且用不同的身份和这些“正妻”生下了不少“嫡子”。
骗一个人可能骗一世,骗一群人可能骗一时,却绝不可能骗一群人骗一世。时日一久,傅父的骗局也就被戳穿了,这人的名声最后也在淮城坏透了。
当时这件事在淮城盛极一时,传得沸沸扬扬的,甚至都传到了望京来。后来徐成器刚一听说这件奇事的时候,还为此事失笑不已。虽然从道德上来看,这个男**害了好几个良家女子,行事确实可恨,但是徐成器觉得这个男人能骗倒这么多女子来做他的“正妻”,光从骗术上来说确属一流,脑筋倒是挺聪明的,可惜就是没用到正道上去。
而傅君华,就是其父在外面骗到的一家小户女子为他生下的孩子。
傅君华母亲倒是一个很有气节的女子,虽然出身贫穷,但却不肯与人为妾。只是她没想到自己以为是嫁于人做了正妻,结果实际上自己却是做了别人的外室。后来事发,傅母极其愤慨,直接把再度上门要接走孩子的男方家人都扫地出门,立誓与傅父断绝关系,并改子为母姓,从此闭门悉心养子,再也没有嫁人。
而傅君华的那位父亲,虽然算是犯了律法,可是这种事例在开朝以来就只有这么一例,并无前例可循,也没有具体的判法。最后此事因为过于出奇闹到了淮城的刑狱司,刑狱司无法判决,只能在协商之后罚了傅父一大笔钱,并让他承担起抚养所有与骗来的女子所生之子的费用,所有被骗女子在自愿情况下都可与傅父断绝关系,此后另行嫁娶各不相干。
那些女子都以为自己嫁人为妻,可结果到最后自己只能为妾或者改嫁,一生可能就此毁掉,可实际上傅父到最后也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惩罚。
这世道对女子未免有些太不公平。
可能就是这个缘故,被傅母养大的傅君华对于律法刑名之事也格外地有兴趣些,平日里也最喜欢钻研这方面的学问。
傅君华十五岁过童试,十七岁过乡试,并一举夺得了淮城解元。之后本可奔赴望京参与秋季的会试,但因当时傅母病重没有前往。后来傅母病逝,傅君华诚心守孝三年,不知何故没有再去参加会试,一直留在了淮城。淮城城主爱慕他的才华,他因此投到淮城城主门下,受淮城城主破格聘用为城主府长史,为城主处理府内事务,并撰写诸多事务文书。
傅君华进一步没有参加科举考取功名,但是他的才能却是一日日展现于世人面前。傅君华参与过淮城好几桩出名的官司,其中最有争议性的一桩,莫属他曾为一桩官司里的犯人做辩护,写了一纸立意出奇的万言书讼状。
在淮城以前有一桩旧例,说是一家大户人家的少爷因为性情暴虐打死了发妻,被发妻家里人直接告到了淮城的刑狱司来,刑狱司最终因伤害罪判决犯人入牢七年,并赔偿了犯人正妻家里足够的补偿金。
后来傅君华就任淮城城主府长史期间,遇上了这么一桩类似的案子。说是一户大户人家的少爷因性情暴戾平时常常殴打房里人,有时也会殴打正妻,结果一次和正妻争吵后下手较重,被正妻一时奋力反抗用剪刀戳死了。此案也由淮城刑狱司受理,最后那个女犯却被判处了绞刑。女犯家里人不服判决,因此翻出之前的旧例在坊间散布流言,抨击淮城刑狱司收受了女犯夫家的贿赂,导致判案不公。
因为两案时常不过两年,很多百姓尚且记忆犹新,导致此案在淮城引发了诸多谣言,当时甚至有百姓自发组织起来跑到淮城刑狱司门口扔菜叶和臭鸡蛋来表示抗议。
这个案子和傅君华本是没什么关系的,淮城的刑法断案本不属于他管理的范畴。但他多年来潜行钻研大虞刑律,在比较两个案子之后认为案件的判决并不妥当,便在刑狱司迫于压力再次审判这个案子的时候,担任女犯的讼师为女犯辩护,并写下了那封极为出名的万言书。
整封诉讼的观点简洁明了,却入情入理。他认为,以律法来看,夫殴打致妻死是故意为之,夫殴打妻在其妻反抗之下致死却并非故意,既然前者可以以伤害罪定罪,后者又怎能定以死罪?后者判决是否失之过重?
若有人在街上行凶,直接打死了行人,尚且还要以命换命,如何夫杀妻就可以不必偿命?若是刑法一律按此,若有男子想要杀死一名女子,是否只要将她求娶回家就可任意打杀而不受重刑?反之,若是对方反抗反会受到死刑?若果真如此,嫁为人妇性命便可任人糟践,那天下所有闺阁女儿谁人还敢出嫁?
万言书中的最后一句原话最后更是流传遍了整个大虞:“若是不幸未能得遇良人,又不能得大虞例律庇护,天下何人安敢出嫁?”
这纸万言书合乎情理动人肺腑,据说当时围观百姓闻言无不纷纷落泪。
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