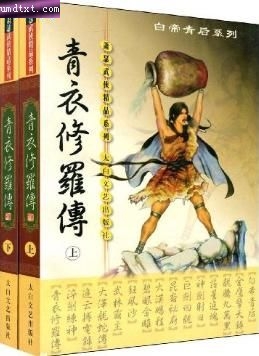大唐双龙传-第2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著痕迹、充满先知先觉霸气的狂攻猛击。
观者无不动容。
劲气交击之声响个不绝,更添此战风云险恶的形势,两道人影此进彼退,鏖战不休,人人都有看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近身搏斗下,两人是以快打快,见招拆招,在这样的情况下,席应更是吃亏。
问题在徐子陵的招数根本是毫无章法,举手投足,均是随手拈来,针对形势的创作,兼且真气变化多端,打得席应发挥不出紫气天罗五成的威力,无法扳转败局。
“轰”!
两人四掌交击,各自退后,凌厉的眼神却彼此紧锁不放。
边不负还以为席应抢回主动,大喝一声“好”。
徐子陵已从容笑道:“换日大法滋味如何呢?”
席应胸口忽地剧烈起伏,狠狼道:“你不……”徐子陵怎容他说出“你不是岳山”整句话,手结大日轮印,惊人的气劲排空切去,及时截断席应吐至唇边的下半句话。
席应厉吼一声,拚死力抗。
“砰”!
人影倏分。
徐子陵挺立原地,稳如山岳。
席应却像喝醉酒般满脸赤红,往后跌退打转,眼力高明者都瞧出他致命之伤,是给徐子陵重踢在小腹的一脚。
“砰”!
另一下响音从上传来,边不负破窗而出,就这样往院墙方向落荒逃去,安隆和尤鸟倦怎肯放过他,穿窗疾射而出,往他投去。
徐子陵一对虎目仍还叮在席应身上,丝毫不敢放松,立刻运气疗治自己体内说轻不轻的伤势。
这近乎没可能的事,终在千辛万苦干完成。
风声骤响,两道人影跃落国内,把席应所有逃路封死,显是怕他仍有力徐子陵没有转身,淡淡道:“奉盟主有何指教。”
奉振来到他旁,微笑道:“岳老客气!小弟只想知道岳老是否仍会在成都盘桓两天,若是如此,可否赏脸让小弟和范兄略尽地主之谊。”
徐子陵淡淡道:“两位好意岳某人心领啦!只是本人一向不善应酬,且另有要事,请恕失陪。”
言罢逾墙而去。
第二十五卷 第十一章 三峡之游
天明时份,避难的村民陆续回来,见到村庄安然无恙,均是兴高采烈。
那俚族小姑娘透窗看到寇仲好梦正酣,也干扰他,任他留驻梦乡。
寇仲本醒转过来,乐得在茅屋内清静白在,正思索昨夜杀死崔纪秀等人的高手是何方神圣之际,屋外一阵骚乱。
寇仲吓了一跳,提刀冲出,只见众人又开始逃亡,大惑干解,那小姑娘一脸惶恐的边随村民撤往山区,边嚷道:“贼船又来哩!”摸不著头脑之际,村氏逃得一个不剩。
寇仲暗忖难道是崔纪秀的援军来犯,照理欧阳倩的俚僚战士*仍在邻村,绝不会让林士宏的贼兵得逞,顺步往沙滩方向走去。
穿过一片树林,大海在前方漫天阳光下无限扩展,果然见有一艘船沿岸巡弋。
寇仲定神一看,怪叫一声,宜扑往沙滩去,同时发出长啸声。
赫然是天志的改装战船。
当寇仲跃上甲板时,卜天志拥他一个结实,其他人团团围著两人,欢声雷动。
寇仲大笑道:“你们没事吧?”
众人齐声应道:“没事。”
天志抓著他肩头,呵呵笑道:“虽明知那些高丽人奈何不了少帅,仍敦我们担心足两天两夜。”
寇仲笑道:“这叫天助我也,若非那场来得及时的风暴,鹿死谁手尚未可知,但现在金正宗那艘楼船至少变成半死的鹿,愿海神爷爷保佑他们。”
各人纵声狂笑,气氛炽烈。
寇仲振臂高呼道:“弟兄们!我们立即开赴岭南。”
众人轰然应偌。
徐子陵醒转过来,原来早日上三竿。经过整整四个时辰的调息,因席应而来的内伤已不翼而飞,心中一阵感触。
自离开扬州开始亡命天涯的日子,他和寇仲从两个籍籍无名的小子,到合力剌杀任少名,崭露头角,至乎现在独力在决斗中使名列邪道八大高手之一的“天君”席应饮恨断魂,其中的离奇曲折,多采多姿,恐怕十天十夜都说不完,更难以尽述。
昨夜在席应的压力下,他把所有功法融汇贯通,尤其最后的近身搏斗,起始的时候,交替使出李靖传的血战十式、屠叔谋的截脉手法、真言手印、又自创奇招,到战至酣畅时,所有招数融浑为一,意到手到,那种畅快愉美的感觉,动人至极。这无比顽强的对手,令他在武道的修行上,跨出重要的*大步。
忽然记起侯希白的约会,忙脱下岳山的面具,收起长袍,摇身变成“疤脸客”弓辰春,离开藏身的人家后院,往约定在下莲池街的酒楼寻去。
来成都过中秋的商旅游人,大多仍未离去,所以城内特别兴旺。若说洛阳是汉胡杂处的城郡,成都就是汉人和众多巴蜀各少数民族交易往来的中心,充满不同民族的风情和特色,为成都平添活泼的生机和气氛。
藏在疤脸下的徐子陵吸引力显然大幅下降,不过由於高昂挺拔的优美身型,间中也会惹来几个媚眼儿。
但徐子陵的心神只放在立即离境的思量上,赴过侯希白的约会后,他决定立即离川,然后让这几天发生的事成为日渐遥远的过去。
石青漩的似有情却无情,对他做成很大的伤害。当有压力和威胁时,他可以抛开不去想她,可是像现在心闲无事的当儿,难免触景生情,甚至怕自己会按捺不住再去寻她,可怜兮兮的看看是否会有转机。
石青漩不像师妃暄般自开始打正旗号不涉足男女之情,而今他最动心一刻,就是初抵成都时在灯下的惊鸿一瞥,那惊艳的感觉,至今仍萦绕心头。
他不想再被男女之情困扰,唯一方法就是尽快远离。
成都内有多条街道均是以河湖桥梁来命名,像他这刻走的下莲池街,还有适才途经的王家塘街、青石桥街、拱背桥街、王带桥街等等,到得街上时,会知道不久后就会跨过那同名的桥子,是很有趣的感觉。
目的地在望时,侯希白的声音从一道小巷传来道:“弓兄这边来!”
徐子陵循声入巷,见侯希白春风满脸样子,讶道:“侯兄是否在不死印法方面有突破呢?”
侯希白亲热地挽著他臂弯,往小巷另一端走过去道:“可以这么说,昨晚小弟见到妃暄,倾谈整个时辰,获益良多,心情当然不会差到那里去。”
徐子陵暗忖原来如此,看来师妃暄确对他相当不错,微笑道:“那夏要恭喜侯兄,我们不是约好在楼内见面吗?”
侯希白眉头大皱道:“小弟给范采琪那刁蛮女缠得差点没命,绝不能在公众地方露面,子陵可知席应死了?”
徐子陵装模作样的失声道:“甚么?”
侯希白长长吁出一口气道:“这可能是近年来武林最轰动的大事,重出江湖的“霸刀”岳山,昨夜在安隆和尤鸟倦的押阵下,破去席应的紫气天罗,当场击毙席应,据目击者所言岳山的换日大法当得上神乎其技这形容,不用动刀子便收拾了不可一世的席应。子陵再不用为席应伤脑筋啦!”
以徐子陵的淡泊,亦听得心中自豪,表面当然装模作样,不露痕迸,还反覆询问,最后乘机道:“小弟在成都诸事已了,想立即离开,异日有缘,再和侯兄喝酒谈天。”
侯希白愕然道:“子陵为何急著要走的样子,也不差这么一天半日吧?难得无事一身轻,不如让小弟带路往西郊的淙花溪一游,留下片美丽的回忆再走不遂。”
徐子陵摇头道:“我急著要走是因约了寇仲”侯希白截断他潇洒然笑道:“既然子陵坚持,那小弟就送你一程,你入川经由盘山栈道,离川何不改由三峡,小弟自会安排一切。”
徐子陵为之心动,大自然的美景比之甚么其他东西对他是更具吸引力,当然点头答应。
黄昏时份,帆船遇到一阵长风,速度倍增,横渡南海。
卜天志来到挺立船首的寇仲旁道:“右边远处的陆岸是合浦郡,左边的大岛就是珠崖郡,也是南海派的大本营。”
寇仲欣然道:“难怪有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又说耳闻不如目见,无论先前你们怎样去形容岭南的风光景色,都及不上现在的一目了然。
嘿!那种高达五丈的树叫甚么树?形状很古怪。”
天志答道:“那是椰树,是珠崖特产,四季常绿,且周身是宝,树干可用来建屋,果实肉丰汁多,果壳更可供制作各种器皿,甚或抗御海风。”
寇仲远眺过去,只见椰树密密麻麻的排满岛岸,树影婆娑,一片浓绿,迎风沙沙作响,与海涛拍岸的音韵互相应和,在黄昏的光线下几疑是人间仙景,世外桃源。
靠岸处十多艘渔舟正扬帆回航,只看重甸甸入水颇深的船身,便知是满载而归。
荡漾清澈的海水中隐见千姿万状,色彩缤纷的珊瑚礁,寇仲暗忖若非急著赶路,潜下去寻幽探胜必有无穷乐趣。
有感而发轻叹道:“看来仍是陵少比我聪明,天地间那么多好地方,怎都游历不完,这么辛苦去打天下干吗?”
卜天志以过来人的资格笑道:“有时志叔也会像你般生出倦怠之心,但转眼又忘得一乾二净。人是需要玩乐和休息的,少帅太累啦!”
寇仲尴尬道:“我只是随口说说!南海派我只记得一个晃公错,掌门的好像是个年青有为的人,叫甚么呢?”
卜天志道:“是梅洵,今年该是二十七、八岁的年纪,擅使金枪,乃岭南新一代最著名的高手,排名仅次於宋师道,但武功却绝不下於宋师道,只因宋缺威名太盛,连带宋师道也给看高一线。”
寇仲好奇的问道:“南海派和宋家因何交恶?”
卜天志道:“这叫一山难藏两虎,南海派对沿海的郡城尚有点影响力,深入点便是宋家的天下,你说南海派怎肯服气。”
寇仲大感兴趣道:“以宋缺的不可一世,为何不寻上珠崖,打到晃老头跪地求饶,那不是甚么都解决了吗?”
天志哑然失笑道:“少帅说这些话时,只像个天真的大孩子。击败晃公错,对宋缺或非困难,可是却会与南海派成为势不两立的死敌,於双方均无好处,所以还是和平相处上算点。”
寇仲道:“今晚我在那里上岸?”
天志道:“两个时辰后,我们会驶进钦江,少帅可在遵化登岸,北行抵郁水,渡水后就是郁林郡,宋家山城就在郁林城西郊处,我已预备好详细的路线图,少帅可毫无困难寻到宋三小姐的。”
寇仲失笑道:“连志叔也来耍我哩!”
徐子陵独坐客栈饭堂一角喝茶休息时,侯希白轻轻松松的回来,坐下欣然道:“幸不辱命,近日因下游形势紧张,客船商旅均不愿去,还好小弟尚有点面子,找上最吃得开的乌江帮,现在只有他们经营的客运船不受政治形势的影响,晚膳后小弟送子陵登船。”
徐子陵沉吟道:“是否因萧铣和朱桀桀交战正烈?”
侯希白叹道:“大概是如此吧!你该比我更清楚,三天前双方在巴东附近的江上打过一场硬仗,朱桀的水师全军覆殁,萧铣方面亦损失颇重。”
徐子陵暗忖萧铣方面的战船很可能由云玉真指挥的,想起这个女人,心中一阵烦厌,且自认对她完全不能理解。她以前的诸般行为,究竟会给她带来甚么好处。
侯希白续道:“朱桀和萧铣都有派人到巴蜀来作说客,希望至少能令巴蜀三大势力保持中立,只是李阀现时声势如日中天,说甚么恐怕终是徒劳无功。”
徐子陵苦笑道:“朱祭的说客该是朱媚吧,比起师妃暄就像太阳和萤火的分别,她可以有怎样的结果?”
侯希白唤来夥计,点好酒菜后,犹豫片刻,才道:“现在形势明显,能与李阀争天下的,论实力有王世充、窦建德和刘武周三方面,论人却只有一个。”
徐子陵愕然道:“此话怎说?”
侯希白道:“这不是我说的,而是妃暄分析出来的。李阀之所以能争得今天的有利形势,全因有李世民在主持大局,他便像天上的明月,天下群雄只是陪衬的点点星光。王世充、窦建德和刘武周三方自下实力虽足可与他抗衡,但最后会因政治和军事比不上李世民而败阵。窦建德和刘武周还好一点,前者有刘黑阖,后者有宋金刚,均是智勇双全的猛将。王世充则有名将而不懂重用,该败亡得最快最速。”
徐子陵点头道:“这个我明白,但论人只有一个指的是何人?”
侯希白定神瞧他半晌后,沉声道:“妃暄指的除了你的好兄弟寇仲尚有何人?”
徐子陵苦笑道:“师妃暄是否过份看得起那小子?”
侯希白摇头道:“妃暄是不会随便抬举任何人的,李世民兼政治军事两方面的长处於一身,豁达大度,又深懂用人之道,古今罕有,而唯一能与他争锋的人,就是寇仲。假如子陵不是无意争天下,改而全力匡助寇仲,李世民恐怕亦要饮恨收场。”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侯兄莫要高捧我们,我两个只是适逢其会吧!照现时的形势看,根本不能也不可以有甚么作为。”
侯希白笑道:“坦白说,当时我也是以类似的说话回应妃暄对寇仲的高度评价,她却笑而不语,显是深信自己的看法。”
徐子陵思索片刻,道:“可否问侯兄一个私人的问题?”
侯希白洒然道:“子陵请直言,我真是把你视作知己的。”
徐子陵迎上他的目光,缓缓道:“你身为花间派的传人,令师究竟对你有甚么期望,总不会只为酣歌妙舞、闺阁情思、樽前花下而生活吧?”
侯希白失笑道:“子陵莫要笑我。因我确实对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响慕沉迷,不过我追求的非是事物表面的美态,而是其神韵气质,才能表里一致,相得益彰。子陵这番说话,暗示对小弟用心的怀疑,以我的性格,一向都不会作出解释,但子陵问到自是例外。唉!我也不知怎么说才好。”
徐子陵淡淡道:“若是难以启齿,不说也罢。”
侯希白苦笑道:“石师对我唯一的期望,该是统一魔门的两派六道,今《天魔策》六卷重归於一,你说在如今的情况下,是否没有可能呢?”
徐子陵疑惑的道:“侯兄和曹应龙均说《天魔策》只得六卷,但师妃暄却说《天魔策》有十卷之数,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侯希白道:“《天魔策》本有十卷,但现今遗传的只馀六卷,就是如此。”
酒菜来了。
两人互敬一杯,徐子陵不解道:“侯兄既是魔门传人,为何却和其他魔门中人有这么大的分别,至少跟杨虚彦是不同的两种人。”
侯希白抓起一个馒头,递给徐子陵道:“怕是与先天和后天均有点关系。我虽是率性而为的人,但因对诸般技艺如画道等的爱好,使我对权力富贵没有甚么野心。事实上这亦是花间派的传统,追求自我完善,绝不随波逐流。”
徐子陵不解道:“那花间派为何会被视为邪魔外道?”
侯希白嘴角露出一丝无奈的笑意,平静地答:“首先是花间派的武功源自《天魔策》,此乃不争的事实,谁都没有话说。其次是因花间派的心法讲求入情后再出情,始能以超然的心态把握情的真义,对很多人来说这正是不折不扣的邪异行为。”
徐子陵点头道:“这确是很难令人接受。若侯兄摆明车马当其无情公子,旁人反没得话说。”
侯希白叹道:“敞派这心法微妙非常,难得子陵一听便明。石师之所以千方百计创出于死印法,正是要突破花间心法,否则将因碧秀心而永不能进窥魔宗至道,只得其偏,不得其全。”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侯兄无法将师妃暄绘於扇上,是否亦因能入不能出呢?”
侯希白一震道:“终给子陵看破,敝派是要徜徉群花之间,得逍遥自在之旨,有情而无情。一旦著情,会为情所蔽,为心魔所乘。所以不死印卷虽只得半截,对我却是关系重大。”
徐子陵微笑道:“时间该差不多啦!让小弟敬侯兄一杯。”
第二十五卷 第十二章 有缘相遇
抵达码头时,早有男女老幼数十人等候登船,徐子陵仍是*疤脸客*弓辰春的样貌身份,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侯希白知他不喜张扬,道:“小弟就送子陵至此为止,子陵只须向船上乌江帮的人报上名字,便不用理会其他,小弟已给足船费,一切均安排妥当。”
徐子陵顺口问道:“乌江帮为何这么大面子?”
侯希白道:“乌江帮的沙老大经营三峡客货运送生意足有十多年的历史,信誉昭著,因其与巴陵帮一向关系良好,又为萧铣负责在巴蜀买粮后付运等事宜,所以很吃得开。子陵可以放心。”
徐子陵道:“原来如此,难怪这么大的一条船,只有那么二、三十个乘客,该是以运货为主,载客只是兼营吧?”
侯希白笑道:“但真正赚钱的却是客运生意,船资看情势随时调整,由於舱房只有十五间,想弄个床铺不是有钱便办得到,我是找上沙老大说话,才为子陵办妥此事的。”
徐子陵拍拍他肩头道:“多谢侯兄的安排,小弟要起行哩!”
侯希白依依不舍地道:“若非小弟要竟地潜修,钻研不死印卷上的心法,定要陪子陵畅游三峡,子陵珍重。”
徐子陵和他握手为别,朝码头走去,乘客刚开始登船,徐子陵排在队尾,回头时侯希白已不见踪影。
自离开扬州,他尚是首次乘搭这种远程的客运船,感觉新鲜有趣。最不明白的是为何要在晚上启航,颇有点逃难的感觉。在掩映的风灯下,江水黑压压一片,只闻江水拍打船身和岸堤的声音。码头和城市被一片树林阻隔,灯火透林隐隐传来,像另外一个世界。
除乌江帮的客货帆船外,江水上游处还泊有数十艘大小风帆,此时都是乌灯黑火,偌大的码头只他们登船处活动频繁,另有数十名大汉不住把放在棚帐下的货物,送往船上。
负责点算客人士船的四名劲装大汉倒相当客气有礼,还帮客人把沉重的行李抬上船。
排在徐子陵前面的是一家三口的小家庭,男的似是个读书人,女的秀丽端庄,夫妻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带著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他们见到徐子陵的疤脸,显然有点戒心,甚至禁止小孩回头来瞧他。
其他客人大多是商旅打扮,三五成群,只有五、六个该是江湖中人。
到徐子陵登船报上名字时,乌江帮的大汉更是有礼,还大叫道:“头儿!弓爷来啦!”
前面那媳妇儿抵不住好奇的回头瞥他一眼,徐子陵点头微笑,竟吓得她慌忙垂首,匆匆走上甲板。
徐子陵混惯江湖,立时想到这一家三口定是惹上麻烦,否则不会像现下这副惊弓之乌的样子,不由暗暗留上心。
抵达甲板,一名五短身材的壮汉迎接道:“弓爷你老人家好,小人林朗,乃乌江帮梅花堂香主,沙老大吩咐下来,对弓爷的招待绝不可怠慢,请这边来。”
徐子陵很想告诉他不用特别礼待自己。但知道说出来亦不会起作用。像侯希白这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