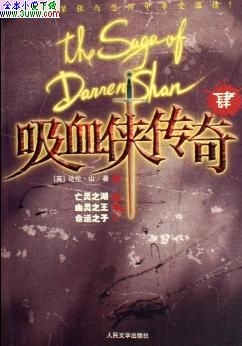吸血鬼黎斯特-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她严肃时,嘴角之间,不知不觉地就流露了刻薄之色。
此刻的她双颊微陷,窄小的脸益见消瘦,对我却美丽一如往昔。是的,母亲仍然是美丽的,我喜欢痴痴地看她。
事实上,外表我颇为像母亲,只不过我的脸庞较宽大而粗狂,嘴巴表情丰富,必要时,则相当刻薄。此外,我开朗幽默,不管多麽闷闷不乐,仍经常流露顽皮神情,更常不自禁地开怀大笑。母亲却极少笑,她冷如冰霜,若非拥有小女孩似的甜蜜,便绝对不可亲近了。
我默默注视坐在身边的母亲,不,是瞪着她。母亲以单刀直入的方式进入话题:「我知道你的感受,你恨他们,因为他们不了解你所承受的一切。他们很难想像山顶上发生了什麽事。」
对这样的话,我感到一种冷静的愉悦。我沈默地回应,母亲却完全了解我的心意。
她接着说:「这跟我首次生孩子有些相似。我足足受了十二个钟头的罪,有如陷身痛苦的罗网,唯一脱逃之道是婴儿顺利出生,或是我难产致死;痛苦终於过去,我抱你大哥在怀里,却不要任何人靠近我。并非我责怪谁,而是我所承受一小时又一小时的苦楚,似下地狱又再一次复苏的煎熬,没有身历其境的人哪能体会?我内心极安祥,就在生育的最普通境遇下,我真正了解绝对孤寂的意义。」
「你说的完全正确!」我有点吃惊地答道。
她没有回话。我一点也不觉惊讶,在说完此行想说的话後,她是不会再任意多说废话的。她只伸手摸摸我的额头,於她,这倒是罕见的举止;发现我身上犹穿着血迹斑斑的猎装时,她显然极为悲痛难忍。
母亲沈默了好一会。
我呆坐着,眼光掠过她朝向火炉,内心有一大堆的话想说,更想告诉她,我有多麽爱她。
但是我忐忑犹豫。以往每当我跟她说话时,她总是叁言两语明快截断,绝不容我有细诉的机会;所以尽管我深切爱她,怨尤之情也相对加浓。
在成长岁月当中,我只看到母亲一迳读着意大利书,跟她成长之地那不勒斯的亲友涂鸦写信,却从来不耐烦教我和哥哥认识起码的字母;从修道院回家後,事态也没有改变。我已经二十岁,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读简单的祷词;我怎能不恨她的书,不恨她只知沈湎於书里,而忽略我们的存在呢?
再进一步说,似乎也只有当我身心受到重创时,她肯多少付出母性的温情於兴趣,对此事实的模糊认知,尤让我愤愤不平。
然而除她之外,我别无救世主,我已倦於孤独,也许年轻人总是如此吧!如今,她就在眼前,她从自囿的图书室走出来,对我极表关注。
我终於确定她不会站起来走开,话语喋喋不休。我低低说道:「母亲,事情犹不止如此,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已心怀恶念——」她脸上表情不变。我继续说:「好几次我甚至梦见我杀了全家人——我的意思是说,在梦里我杀了哥哥和父亲,我一屋子一屋子捕杀他们有如杀狼一般。我感到谋杀的欲念隐埋在心底……」
「我也一样,儿子,我也一样。」她说着,脸上浮起奇特的微笑。
我弯身向着她,仔细大量她,又降低声量说:「梦中杀人时,我大声尖叫。我几乎看得见自己面貌狰狞,听得见自己咆哮怒吼,嘴巴张成完整的O 字型。」
她谅解地点头,眼里闪着亮光。
「在山上,当我於狼搏斗时,情境有些仿佛……」
「只是有一些?」她问道我点点头。
「杀狼之後,大觉自己判若两人。我甚至不知道,此刻跟你在一起的,究竟是你的儿子黎斯特,还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杀人凶手。」
她静默了一段长时间。
「不,你不是凶手,你只杀死了狼。你是猎人,是武士。你比家里的任何人强壮坚毅,这是你的悲剧根源。」
我摇了邀头。母亲的话固然不错,此际却无关紧要,再说,强壮坚毅也者,并非这回不快乐的主因,只是,我懒得解释而已。
她的视线转到别处又回到我身上。
「人的角色不止一种——」她说道:「你就扮演不同的角色,你即是杀手更是男人。不过,别只为了憎恨他们而使自己沦为杀手,也别一位只有谋杀或是疯狂,你得以解脱,得以拥有自由。你一定还有路可走。」
她最後的话重重撞击了我。她的确一言中的,话里的暗示也让我大吃一惊。
长久以来,我总认为自己不可能即跟家人搏斗,又能兼当好人;要做好人就是表示我已认输,除非我能找到更有趣的「好人」界定。
我们静静相对数刻,这是我们之间不寻常的亲密。她看着火,手在头後的园疤上轻搔。
「你猜我曾想过什麽?」她的视线再次转向我:「谋杀其实还不如背弃他们,是真正彻底的轻蔑。恨极了时,我想像自己喝得烂醉,脱光衣服,在山间小溪赤裸裸的沐浴。」
我差一点忍俊不禁。这是母亲庄严的玩笑吗?我端详着她,一时不能确定我到底有没有听对。不过她确实说了以上的话,而话还没完哩!她接着说:「然後我想像自己到了村子里的客栈,跟着任何遇见的男人上床——粗俗的,强壮的,老的,少的,我躺在床上,男人一个换过一个;斯时也,我感到一种过瘾的胜利感;一种不管你父亲,或是你们死活的绝对解脱感。在那瞬间,我纯然是我,我完全属於自己而非他人。」
母亲的话令我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对於这种说词,父亲哥哥,乃至村子里傲慢自大的商店老板,会有什麽发应呢?天呀……这简直太滑稽了!
我犹忍住不笑,可能因为想像到母亲的裸露,而不得不板脸。但是我实在憋不住而抿了抿嘴;只见她微笑点点头,又扬起眉毛,好像在表示我们互有默契一般。
我终於捧腹大笑了。我以拳捶膝,头更撞到床边的木头。母亲似乎也笑了,以她独特安静的方式在笑着。
这是古怪的刹那。我发觉某种人类残存的兽性,犹然存在母亲身上,我们的确互相了解,此时,所有对她的怨尤似也无关紧要了。
她解下发夹,头发披在肩上。
我们默默相对了一个钟头左右,不再笑也不再说话,在壁炉的火光下,享受无声胜有声的亲密。
她转头面对着火,她的侧影,细致的鼻子和嘴,美得令我百看不厌。沈思间,她猛然回头望我,坚定冷静无动於衷的说:「我绝不可能离开这里,我已来日不多。」
我整个人呆住,前面的惊吓比起来算得了什麽?
「我可以活过这个春天。」她紧接着说:「也许加上夏天,但我绝对活不过冬天。我很清楚的,肺部的疼痛太厉害了。」
我情不自禁呻吟起来,身子倾前叫着:「母亲!」
「别多说什麽话!」她答道。
我想她不喜欢被叫「母亲」,但我忍不住了。
「我非得跟一个人大声说出来不可,我完全被吓坏了,我好害怕呀!」母亲说着。
我很想抓着她的手,却知道母亲绝不允许,她讨厌被别人碰触,她从来没有用手揽抱过谁。所以我们只能一凝眸相对代替拥抱。我泪流满面。
她轻拍我的手。
「别多想。」她说:「我自己也尽量避免去想。只是当时候来到,你纵然失去我,也得设法好好活下去。唉!对你恐怕还真不容易!」
我想开口,却发不出声音来。
她离开了,一如来时无声无息。
尽管她没提及我的衣服、胡子和不忍卒睹的外表;她派了人送来乾净衣服,刮胡刀和热水,在沈默中,我享受着人的伺候於服务。
第一部:雷利欧熠熠上升3
我的身体渐渐康复,杀狼事件的记忆尽量屏除脑海,母亲说的话却铭刻心底。
我思索她所说:「完全被吓坏了」的话,我不全明白那是怎麽回事,只觉得她的话正好说出事实。如果我是垂死之人,感觉大概没什麽两样;比起来,在山上屠狼恐怕还好过一些。
不仅如此,她一迳默默承受在家里的不快乐;虽然她跟我一样的憎恶古堡里郁闷无望的生活。如今,在生了八个孩子,死了五个仅仅存活了叁个後,她却命在旦夕,一生即将宣告结束。
我决心振作起来,好让母亲开心一些,偏偏就是办不到。想到她时日无多,我简直无法忍受;只能躲在房里踱过来踱过去,关在房里吃送来的饭,却一直提不起劲儿去面对她。
那个月底,古堡突来的访客却把我拉出房间之外。
母亲进来说,村里的商家为了感谢我的杀狼壮举,特别前来拜望,我必须亲自接待。
「哎,去他妈的!」我口出粗话。
「你非下来不可。他们是来送礼,你必须一尽领主之责。」
我讨厌这一切。
勉为其难来到大厅时,发现所有来客我全认识,村里最有钱的店老板也赫然在座,所有人都盛装而来。
其中只有一个打扮浮夸的年轻人,我没有马上认识出来。
他大约和我的年纪相仿,个儿相当高,我们目光相对时,我想起他是谁了。他是尼古拉斯,布商的长子,曾经到巴黎去念书。
他还真不一样了。
身穿玫瑰红镶金的华丽织锦外套,脚趿金跟便鞋,衣领加上一曾意大利蕾丝花边。只有头发跟从前一样,乌黑卷曲,只不过系着一个丝结在背後,看上去挺孩子气的。
这正是巴黎的流行款式。而流行的快速递嬗,一如驿站车来车往。
站在他面前的我,却穿着破旧的毛衣,磨损的皮靴,污黄的蕾丝更不知修补过多少次。
由於他看上去乃镇上的代言人,我们彼此鞠躬如仪。他打开黑斜纹棉布包裹,取出一件镶毛里的腥红天鹅绒披风,多麽艳丽的衣服呀!当他注视我时,眼睛炯炯发光,让人忍不住觉得他是来觐见君王!
他诚挚地说:「爵爷,微薄之礼请您消纳。披风的毛里乃选自你所杀的最好狼皮,以後寒冬出门狩猎,穿上去即挡寒又正适合您的身分。」
他的父亲,随着送上一双黑色带毛里小羊皮长靴说:「这双也是,爵爷,打猎穿的,爵爷——」
他们的诚意深深打动了我。这些店老板的财富,我只能在梦中得以想见,他们竟对我这麽慷慨有礼,这麽客气尊敬。
我收下披风於皮靴,同时也以从未有过的礼貌,向他们深切致谢。
我的背後传来大哥?格斯丁的语声:「这下好了,他更要胆大妄为啦!」
我满脸通红,在这些来客的面前恶言相向,简直太过分了。视线瞥向尼古拉斯时,他的脸上却只见款款深情。
在离去前的轻吻时,他附在我耳边轻轻说:「爵爷,我也曾经胆大妄为!改天,请容许我再次拜访。届时,您肯告诉我如何以一挡八的经过吗?只有胆大妄为的人,能做出胆大妄为的大事呀!」
从来没有商人跟我如此说话,那瞬间,我们恍若回到少年时期,我旁若无人的大笑;他的父亲有些失措;我的两个哥哥停止窃窃私语;只有尼古拉斯,一直保持着巴黎人的从容微笑。
访客离开後,我拿着腥红天鹅绒披风和羊皮靴走进母亲房间。
她一边懒懒地轻梳头发,一边仍在看书,从窗子透进的微弱光线中,我第一次看到她头上长出的白发。我告诉她尼古拉斯所说的话。
「为什麽他自称胆大妄为?」我问道:「他的话好像别有含意。」
母亲笑了。
她说:「他当然别有含意。他曾经玷辱家门过呀!」她放下书本直直瞅我:「你知道他自小受到教育,刻意模仿贵族行为於生活。在巴黎学法律的第一学期,却疯狂爱上了小提琴。好像他听过一个意大利名师演奏,这个名师天才横溢,以致传说中,他乃出卖灵魂给魔鬼以换取才气的。尼古拉斯骤听之下,竟放弃一切跟从莫扎特学习音乐去了。他卖光所有的书,天天练琴,弄得考试也不及格。他希望成为音乐家,你能想像得到吗?」
「他的父亲一定抓狂了!」
「当然。他甚至砸碎了乐器!你是知道的,一件昂贵的货品,对布商如他意义何等重大。」
我微笑起来。
「尼古拉斯现在没小提琴了吧?」
「他还有一把,他卖了手表,迅速跑到克莱蒙郡买了另一把。他的确是胆大妄为。最糟的是他的琴还真拉得蛮好!」
「你听过?」
她对音乐懂得不少,在那不勒斯时,是跟着音乐一块长大的。不像我只听过教堂合唱,还有市集的演出。
她说:「在星期天做弥撒时曾经听过。他在布店的楼上房间演奏,谁都听得见的。他的父亲还恐吓要打断他的手呢!」
布商残酷的说法使我抽了一口冷气。我已为尼古拉斯着迷,他的执着行径,令我倾慕不已。
「可惜他绝不可能成为名家啦。」母亲接着说。
「为什麽?」
「他的年龄已过。一旦过了二十岁,你就很难再学好小提琴。不过,我又真懂得多少?他拉的琴已够神妙,何况他也许能出卖灵魂给魔鬼呢!」
我有些不自在地笑着。这听来太神奇了!
「你为什麽不到城里去,跟他做做朋友呢?」她问道。
「我干什麽要去?」我反驳着。
「黎斯特,你真是的!你哥哥会恨得半死,而老商人会欣喜若狂,他的儿子竟能和侯爵之子在一起。」
「这不成理由呀!」
「他曾去过巴黎呀!」她说着,瞅了我好一阵子,然後视线又回到书上,有一下没一下地梳起头发。
我注视着她的阅读,心里至感懊恼。我好想问她身体怎麽了,咳嗽是不是还那麽糟?可是却不敢提起这个敏感话题。
「去找他聊天,黎斯特。」她望也不望我的说。
第一部:雷利欧熠熠上升4
整整过了一星期,我下决心去探望尼古拉斯。
我穿上腥红天鹅绒披风和羊皮靴,走往通向村里客栈的蜿蜒道路。
尼古拉斯父亲拥有的布店,就在小客栈正对面。我没有看到尼古拉斯,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我的钱只够喝一杯酒,正不知怎麽办时,客栈主人出来,对我鞠躬後,端了一瓶最好的葡萄酒放在我面前。
当然,这些村民对领主之子总以礼相待。如今因为杀狼的关系,情势却有了微妙改变。奇怪的是,这更让我感到孤单於不自在。
倒了第一杯酒不久,尼古拉斯露面了;一阵亮光恍若跟着他在门边闪现。
他不像上回那麽打扮光鲜亮丽,感谢老天!不过他身上仍披挂着丝、天鹅绒和新式皮饰,在在显示了家庭的富裕。
他好像跑步过来的,一脸通红,头发因风吹而零乱,眼神充满兴奋之色。他鞠了一躬,等候我邀他入座,旋即急急问道:「於狼搏斗之情境像什麽呢?爵爷!」他双手交叠在桌上,目不转睛的望着我。
「你为什麽不告诉我,在巴黎之境况又像什麽?先生。」话出口,马上察觉我不无揶揄无利之意,连忙又说:「很抱歉,只是我真的好想知道。你真念了大学?真的和莫扎特学过琴?巴黎的人都做些什麽?他们都说些什麽?想的又是什麽?」
对着连珠炮似的问题,他莞尔不已,我也忍俊不住。我要了一个玻璃杯,又把酒瓶推到他面前。
「告诉我,你去过巴黎的剧院吗?你看过法国剧院的喜剧吗?」我问道。
「很多次。」他的回答似乎有点轻率。「听着,驿车马上就到,这里会十分嘈杂。容我请您到楼上的套房用晚餐,您的允许将是我的荣幸——」
我还来不及绅士般惺惺作态一番,他已点了酒菜,我们被带到楼上一个素而舒适的小房间。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木头小房间,然而一眼就爱上了。桌子安排妥当准备好上酒菜,火把房间烧得温暖如春,不像古堡的火炉,只听到或声呼噜作响。厚厚的玻璃窗擦得晶亮,刻意看到澄蓝的寒冬天空,於白雪覆盖的山顶。
「来吧,现在我刻意告诉您有关巴黎的种种了。」他愉快的说着,并先让我坐下。「不错,我是进过大学。」他的语气有些嘲弄,俨然那是可耻的事一般。「我的确拜莫扎特为师过,如果不是急於想收弟子,他恐怕早就斥我是无望之徒,滚远些啦!好吧!你还要我先说些什麽?巴黎的臭味?城里可憎的嘈杂?饥饿的人群四处包围你?还是每条小巷内等着割你喉咙的盗匪?」
我挥手表示对这些全无兴趣,他的微笑和他的语气截然不同,他的态度坦诚而迷人。
「一个巴黎真正大型的剧院……」我说道:「为我描述一切,它像是什麽?」
我们在房间足足四个钟头之久。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谈天。
他用湿指头,在桌上画出了剧院的细部图形。描述看过的剧目,有名的演员,大街上的小屋;他描绘了巴黎的一切,也渐渐抛却原有的愤世嫉俗意味。当他谈到西提岛、拉丁区、巴黎第四大学和罗浮宫时,我的好奇心更引发了他的狂热。
我们继续谈到有关抽象於观念的话题。诸如报纸新闻报导,他於室友聚集在咖啡厅高谈阔论;他告诉我当地人普遍浮动不安,於对君主制度的不满;他们渴望政治上的大变革,甚至从坐而谈,到了起而行的阶段;他也提到有关哲学家,狄德洛特、伏尔泰诸人。
我并不了解他所谈的全部,不过在急促时而嘲弄的口吻下,他已为我勾勒出一辐外面世界的奇妙图像。
当然,他所说诸如知识份子不相信上帝,他们对科学探讨更具兴趣;贵族引人反感,教会也不得人心等等,我倒毫不引以为异;尽管後者无关迷信破解,只是时代演变的结果。他越滔滔不绝,我越了解得多。
之後,他约略提起百科全书,那是在狄德洛特督导下最伟大的知识编辑。话题旋即转到他常去的沙龙,友朋喝酒的较量,他於演员共度的夜晚;他叙述在皇宫举行的公众舞会,在那里玛丽安东尼皇后会现身於民同乐。
他做出结论说:「我在这里跟你说的一切,听起来可比真实好太多!」
「我不相信。」我温和说道,不希望他的话叫停,希望他继续不断地谈下去。
「这是个非宗教的世纪!」酒杯注满了新换酒瓶的酒,他说:「很危 3ǔωω。cōm险呀!」
「为什麽会危 3ǔωω。cōm险?」我低语道:「一个迷信的终结?这有什麽不好?」
「你说话像个真正十八世纪的人,爵爷。」他的微笑中略显忧郁:「可是再也没人把道德价值当做一回事了。流行就是一切,连无神论也是一种流行!」
我的心灵一向是非宗教的,倒非为了什麽哲学理由。我们家中无人相信上帝的存在,表面上似乎相信,也做弥撒;但这只是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