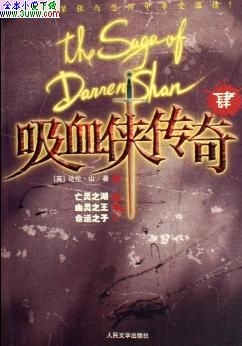吸血鬼黎斯特-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心灵一向是非宗教的,倒非为了什麽哲学理由。我们家中无人相信上帝的存在,表面上似乎相信,也做弥撒;但这只是尽职罢了。真正的宗教虔诚,老早已在我们家消逝,这种现象甚至还包括上千的贵族家庭。纵使在修道院,我也不信上帝,我只信身边虔诚的修道士。
我试着用简单而不冒犯的语言,来解释自己的看法,毕竟对他们家来说,这真是迥然有别呀!
就算他那视钱如命的可怜父亲,对宗教也无比的虔诚。
「没有信仰我们真能活下去吗?」尼古拉斯几乎悲哀地问道:「孩子没有信仰,如何面对世界呢?」
我开始了解他为什麽愤世嫉俗语带嘲讽了,他正面对古老忠诚的沦丧,而为此苦恼不已。
尽管他的嘲讽挖苦,使他颓废阴郁,然而一种抑压不住的热情於精力,仍从他身上源源益出,令我情不自禁喜爱他,想和他亲近。再多喝两杯酒下肚,我恐怕什麽仰慕的荒谬话语,都会倾囊而出啦!
「你知道我一向过着无信仰的生活。」我淡淡地说。
「我知道。」他答道:「你还记得女巫的事吗?那一次你在烧死女巫的广场,号啕大哭的事?」
「为女巫大哭?」我茫然地瞪着他。渐渐地,某些痛苦和羞辱的记忆搅动了起来——我还真有不少心境类似的回忆,为女巫大哭的往事?我说:「我记不起来了。」
「我们都还是小男孩,修士教导我们要如何祈祷,带我们去看从前烧死女巫的地点,那些古老的火刑柱,还有烧得焦黑的土地。」他提醒说。
「哦,那个地方!」我发抖了。「那个可怕的地方!」
「你又哭又叫,他们只好找人去通报侯爵夫人,因为你的保姆安抚不了你。」
「我是个讨人嫌的孩子!」我说道,试着想一笑置之。我确实已想起往事——我一路上尖叫着被带回家里,夜里还做了大火燃烧的恶梦。後来有人在我的额头擦汗说:「黎斯特,醒醒——」
好多年没再去想那恐怖景象了。每次走近那个地方——看到粗粗的火刑柱,脑海就不由自主浮现男男女女,乃至小孩活活被火烧死的惨景。
尼古拉斯细细打量着我说:「你的母亲来带你时,她说这简直太愚昧太残忍了,对修士讲这种老故事给小孩听的举措,她极不以为然而大为生气。」
我点点头。
最恐怖的真相是:这些村里早已遗忘的无辜可怜虫,他们乃死得莫名其妙。「纯然迷信的受害者!」记得母亲说道:「根本就没有什麽女不女巫的存在。」难怪我会尖叫不已。
「我母亲的故事倒截然不同。」尼古拉斯说:「女巫们是魔鬼的同盟,她们招致农作物病害,还假装野狼,杀害羊群和小孩。」
「所以,一旦没有人假借上帝之名烧死活人,世界岂非好得多?」我问道:「如果人们对上帝不再虔诚,因而人不会彼此伤害,那麽非宗教的世界,又有什麽危 3ǔωω。cōm险?起码像活活烧死人的悲惨事件不会再发生!」
他不以为然地皱皱眉头,又以恶作剧的神情,倾身向前。
「狼群在山上没伤害到你吧,是不是?」他戏谑地说道:「你没有变成狼人,对吧?爵爷,我们有没有蒙在鼓里呢?」他轻拍着仍在我肩上的天鹅绒披风。「神父曾经说过的,他们那时可烧死许多狼人哪,他们经常这样恐吓呢!」
我大笑不已。
「如果我真变成浪人——」我答道:「我刻意这麽告诉你,我绝不会留在附近杀害小孩,我会跑离这个不幸污秽小镇,这个仍然以烧死女巫来吓唬小孩的地方;我会出发前往巴黎,不见巴黎城墙誓不罢休。」
「然则,你将发现巴黎也是可悲的污秽之地。」他说道:「那里,他们在沙岸区的民众之前,公然以刑车砍断盗贼的骨头。」
「不——」我说:「我将看到一个光辉的城市,在那里,了不起的观念,孕育在一般平民脑海里,这些概念的实现,得以照亮世界最黑暗的角落。」
「唉,你是天生的梦想家呀!」他说着,神情极为愉悦,当他微笑时,他真不止是普通的俊帅呢!
「我将认识一堆如你的人——」我继续说:「他们也有你的敏捷思维和锐利辞锋。我们一起在咖啡屋喝酒,一起枪舌战热烈争论,我们将在馀生之年,快乐地高谈阔论着。」
他用手环绕我的脖子轻轻亲我。我们是如此熏染陶醉,连桌子都快受不了我们啦!
「我的领主——狼煞星!」他低语着。
当第叁瓶酒送来时,我开始谈起我的生活,做了前所未有的倾诉;我每天骑马上山,骑往远离绝对看不见古堡尖塔的山岭;驰向远离耕地以外的丛林僻野,在那里似乎鬼魂出没,阴影幢幢!
我跟他一样地侃侃而谈。我们谈到心里深处的千百种感受,彼此不同的秘密於孤寂。我们的交谈,在本质上,和我於母亲难得的交谈内容相似,我们叙述到自己的渴慕於不满足,我们屡屡相互热烈的契合作答,如:「对,对」、「绝对正确」、「我完全了解你的意思」和「是呀,所以你感到自己已不能再忍受了」等等,等等。
又叫了一瓶酒,又添了新炉火。我恳求尼古拉斯为我拉小提琴。他立刻冲回家去取琴来。
时已近黄昏,阳光斜照窗子,火烧得很旺,我们熏然欲醉,却什麽晚餐也还没点。只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躺在小床草垫上,以手支头,我看着他取出了乐器。
他把小提琴摆在肩上,一边调整弦轴一边开始拔弹。
然後他举起琴弓用力触弦,拉出第一个音符来。
我跃起身,背靠着墙紧盯住他,简直不相信是自己听见的声音。
他很快融进音乐里,小提琴的琴声音色,在他手里显得悸动而透明。他双目紧闭,下扭向一边,使得嘴看起来有些变形。最让我震撼的是,他的整个身躯似已陷进乐曲之中,他的灵魂也恍如挤进乐器里面。
我从来不知道音乐刻意如此。旋律那麽纯自然,然而强烈有力、热情洋溢的明亮音色,却从他用力锯拉的丝弦流泻而出。他演奏的是莫扎特的作品,那种轻快,飞跃,於纯然可爱的音符,也正是莫扎特创作下的音乐特色。
音乐演完时,我依然呆呆盯着他,双手抓紧我的头。
「爵爷,怎麽回事啦?」他几乎手足并措地说着。我站起来,手臂环绕着他;先亲他的面颊,又亲起小提琴来。
「别再称我爵爷。」我说道:「叫我名字!」扑向床,脸埋进双手里哭了起来。而一旦哭泣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他坐在我身边,拥抱我并问我为什麽哭?虽然我哽咽得说不出话,却刻意感受到他的不胜欣喜,因为他的演奏带给我如此强烈的影响。他的冷嘲热讽於怨恨苦涩,完全消逝无踪了。
那天晚上是他带我回家的。
翌日清晨,我站在他父亲商店那条蜿蜒石头路上,往他的窗子丢小石头。
当他伸出头时,我说:「要不要下来继续我们的聊天?」
第一部:雷利欧熠熠上升5
从此,当我不去狩猎,我的生活便是和尼古拉斯混於聊天。
春天姗姗来临,丛山层层叠翠,苹果园枝头抽芽冒绿。尼古拉斯和我形影不离。
我们在岩石斜坡上散步,携带面包於酒,坐在阳光下的草地,偶尔往南边的老修道院废墟漫游。有时我们躲在我的房间或爬上古堡城里;有时也回到小客栈温暖小房间。{炫·书·网·提·供}尤其是我们喝得太多,聊得太大声,怕吵到别人的时候。
一星期过了又一星期,我们披肝沥胆无所不谈。尼古拉斯谈到他在学校的生活,早期的失望,还有他认识於爱恋的人。
我则谈起痛苦的往事,最後更谈到随着意大利剧团离家出走的羞辱插曲。
那是在小客栈的一个晚上,我们一如往常的畅饮。每回饮到半酣,心情恍惚美妙,凡事俱皆合理,我们称之为「黄金时刻」。我们总尽量延长这段时间,然而往往不可避免的,总有一个无奈承认说:「不能再这麽聊下去了,我想黄金时刻已飞逝而去。」
在那个晚上,望着窗外照耀山间的明月,我指出但凡黄金时刻存在,纵然我们不在巴黎,不能在歌剧院或剧场等待帐幕徐徐升起,我们的日子总还差强人意。
「你和巴黎的剧院——」他对我说:「不管我们谈到什麽,你最後总不免扯到剧院於演员上面——」
他棕色的眼眸大而充满信赖,即使酒意已浓,他所穿的艳红色天鹅绒巴黎式礼服外套,也一迳整洁光鲜。
「男女演员能共同塑造魔术之境——」我说道:「在舞台上,他们虚构,他们杜撰,他们使故事栩栩如生。」
「你应该在舞台灯光强烈照明下,仔细看看他们浓妆艳抹的脸,汗水淋漓的样子。」他答道。
「哎,你又来了。」我反驳着:「你——别忘了你曾经为了演奏小提琴,放弃过一切呢!」
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眼神有点奇怪,似乎他已厌倦於自我挣扎。
「不错,事实是如此。」他承认着。
即使整个村落全都知道这场父子间的战争,尼古拉斯也不肯再回到巴黎的学校去。
「当你拉琴时,你缔造属於你的生命!」我说道:「你从无创造了有,美好的事物因你而产生;对我而言,这太有福气了。」
「我於亲缔造出音乐,而这让我感到快乐,如此而已。」他回答:「这有什麽美好於福气可言?」
当他语带嘲讽时,我总一笑置之。
「这些年来,生活在我周围的人,即无任何创造,也从不思改变。」我说:「演员和音乐家却不一样,我视他们为圣人。」
「圣人?」他望着我:「福气?美好?黎斯特,你这些用词让我好生困惑。」
我微笑着摇摇头。
「你不了解我的意思。我在谈的是人类特质,而非他们的信仰问题;我在谈的是,有些人硬是不肯接受,那种所谓人生无用论的谎言。我的意思是指那些人,宁可突破旧有的框框,他们工作,他们牺牲,他们真正在做事……」
我的话使他有些感动,我惊讶於自己的滔滔不绝,然而却也觉得他似是多少受了伤。
「这就是我所谓的福气。」我说:「这也就是神圣,不管有上帝或没有上帝,美好的事物是存在的,正如丛山在远处高耸,星星在天空闪耀一般的真实。」
他看来面容苦,受伤之色犹在。在那瞬间,我思索的却不是他。
我想的是母亲於我的谈话,深知自己不可能违抗家庭於父命,去追求我所响往的美好。如果我真相信自己刚所说的话……
仿佛他洞识了我的心念,他问道:「你真的相信这些吗?」
「也许相信,也许不信——」我愣愣回答,不忍看到他如此悲苦。
於是,我说出於演员相偕而跑的往事,我告诉他那几天的详细经过,於这件事带给我的欢乐幸福。这段往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连对母亲也绝口不提。
「瞧,这怎麽不是美好呢?」我问道:「自己即付出,同时也享受幸福快乐。我们表演之际,为小镇带来生气於生机;它是魔术,我告诉你,它真刻意治愈病人呢!」
他摇头没说话。我知道他有话想说,为了对我的尊敬,却保持沈默。
「你不了解的,对吧?」我怅然问道。
「黎斯特,罪恶总是让人感到美好。」他严肃地说:「你不明白吗?你想教会为什麽总是谴责演员?这都源自戴?尼斯,那个酒神;因为他,有剧院;在亚里斯多德所写的书里,你可以读到有关的一切。由於戴?尼斯驱使人荒淫放荡。你觉得美好所以你会沈溺——然而那实在是堕落和荒淫,是酒神於葡萄酒的作祟——你竟为此违抗你父亲——」
「不对,尼古拉斯,不,绝绝对对不正确。」
「黎斯特,我们双双是罪恶之徒——」他说着,忍不住笑了:「我们一迳是坏胚子,我们胡作非为,又声名狼藉,所以我们会变成死党呀!」
这下轮到我悲苦於感到受伤了。黄金时刻已逝,再也不可能有缓刑——除非形势有所逆转。
「来吧,去拿你的琴,我们去树林里,那里亲声再大也吵不到别人。我们且来瞧瞧,音乐本质是否有美好的存在。」我猛然做出提议。
「你是个疯子!」他说着,抓起尚未打开的酒瓶,迅速走出门外。
我紧跟在他身後。
他拿了提琴从家里走出来,开心说道:「让我们去女巫广场。瞧,半月当空,月色犹亮,我们就去於鬼为舞,於女巫之幽灵奏乐吧!」
我大笑。我一定是醉了敢这麽满不在乎。「我们将以音乐的纯净於美好,使那个地方重新神圣起来。」我坚持自己的论点说道。
有多少年我没置身在女巫广场了。
月色明亮一如他所预料,可以看到烧黑的火刑柱竖立着,看到焚烧过後已百年,仍然寸早不生的一片荒地。远处新栽的树苗依稀可见,风吹过荒野,沿着岩石斜坡而建的村庄,笼罩在黑暗之中。
一阵轻微寒?在心底泛起,那依然是当年相同的痛苦感受,一个孩子在想到有人「活活烧死」时,难以驱除的恐怖梦魔印象。
尼古拉斯的白色蕾丝鞋子,在微弱的月光下闪耀,他一边拉着琴弦,一边绕着舞步,吉普赛的歌曲旋律,旋即在月色里流窜。
我坐在烧过的树干上喝酒。乐声一起,一种心碎的凄美感觉随之而来。除了在这可怕的地方混外,我们何罪之有?很快的,我忘记罪不罪恶之念,默默无声地饮泣了起来。
虽然音乐似乎一直没停,尼古拉斯却恍若在身边安慰我。我们并肩而坐,他说这世界充满不公平,他和我在法国这个可憎的角落如囚坐牢,然而总有一天我们会破牢而出。想起古堡里的母亲,他何尝不也是在坐监待死呢?想及此,我悲伤难仰痛不欲生。尼古拉斯又演奏了,他邀我於琴声共舞,忘却一切。
是的,这就是我要让你知道的,这是罪恶吗?这是邪恶吗?我走向他旋转之处,音乐之美恍如自提琴飞跃而出,它们璀璨如黄金,亮丽得我几乎可以看见金色火花飞舞。我跟他一起旋舞,他演奏的乐曲更加迷人了,我敞开毛皮披风,抬头举目对月。音乐如烟似雾拥抱着我,女巫广场随乐声而消失,只有澄明的天空,高悬在山丛之间。
那晚之後,我们更是如胶似漆。
几天之後,不寻常的事发生了。
天色已晚,我们坐在小客栈里。在房内跺步的尼古拉斯,戏剧性地比着手势,表明出长久以来,我们脑海挥之不去的意念。
那就是说我们应该去巴黎,即使我们身无分文,也好过坐困此地;即使我们在巴黎沿街乞讨,也好过画地为牢。
此种想法我们已念兹在兹。
「当乞丐恐难避免呢!尼克。」我昵称着说:「我宁愿该死地置身地狱之中,也不愿感乡巴佬穷亲戚登豪门求助的事哩!」
「你以为我会让你如此?」他责问道:「我的意思是真正离家出走,黎斯特,唾弃每一个人,绝对不理他们!」
我甘心日复一日游手好闲下去吗?让我们的父亲诅咒我们?毕竟我们的生命在此一无意义。
当然,我们都了解这回出走的严重性,将千百倍於从前的硗家。我们不再是少不更事,我们已长大成人。对着父亲的诅咒,我们是否真能一笑置之?
何况我们已大到了解贫困的严重性。
「到了巴黎之後饿了怎麽办?杀老鼠来吃吗?」我惶惑问道。
「必要的话,我会在杜登波大道拉琴,等着过路人赏钱,你也可以去剧院讨生活!」他的话大有挑战意味。他似在表示,现在看你啦,黎斯特?「以你的容貌外表,杜登波大道上的剧院大门,会为你随时而开呢!」
我喜欢我们之间聊天话题的改变,更喜欢在他脸上,看到有志者事竟成的神情。虽然十句话当中,他往往会丢出一句:「管他的!」但是往昔的愤世嫉俗已不见。此际,好像只要我们下决心,凡事无不可能呀!
我们在这里虚掷生命,人生毫无意义的年头,开始在我们内心闷烧。
我重拾音乐於表演乃美好的话题,强调它们能赶走混乱,而混乱正是日常生活中典型的了无意义。如果我们现在面对死亡,生命除了无意义外,还留下什麽?事实上,想及母亲的将死於虚度一生,我忍不住向尼克提及母亲的话:「我完全被吓坏了,我好害怕呀!」
设若我们相处之际真有黄金时刻的话,如今它已随风而逝,不同的感受却随之来临。
对此何妨称之为黑暗时刻呢?只是室内仍然溢着奇怪的光芒,我们说话的音量也仍然高亢。我们语调急促,对了无意义的生活大声咒骂。尼古拉斯坐下来,头埋在手掌里,我痛饮着酒不醉人自醉的甘醇,在屋内一边跺方步、一边狂舞手势,一如尼克刚的举措。
我恍若听到自己在大声说话;当我们死了,也找不到为什麽要活的答案;即使自称无神论者,在死亡之前也想获得某些答案吧?我的意思是上帝究竟存在呢?还是根本没有上帝?
「偏偏悲哀的是——」我说:「弥留之际我们依然大惑不解,我们呼吸停止,生命从有而无,对人生仍一无所知。」我宛如看到宇宙运转,日出日落,银河星星闪耀,黑夜周而复始。我歇斯底里大笑起来。
「你知道吗?纵然世界末日宇宙消失,我们仍然愚昧无知。」我对尼古拉斯大吼,他坐在床上,一边喝酒一边点头。「我们将一无所知地死去。一无所知!而了无意义的人生依旧存在不变,我们意识不到,也无能为力再赋予任何意义,我们就只是死去,死去,死去,面对死亡,不知就里。」
我停止大笑,站立不动;完全明白自己在说什麽?
无最後审判之日,无终结辩解;没有过错得获矫正,惊恐得获救赎的光明那一刻。
烧死在火刑柱的女巫,不能平反报复。
没有人告诉我们事情为何如此发生。
不,那瞬间我其实根本不明白,我只是「看到」而已。我只能发出简短的音节:「哦!」我一再说着:「哦!」越来越大声的叫出「哦」这个字。酒瓶掉在地上,手放在头上,我仍然「哦」个不停,我看得到自己的嘴张开成大圆形,好像跟母亲描述的一般。「哦!哦!哦!」之声不断从我口中喃喃发出。
我像打嗝停不了似的,「哦」个没完没了。尼古拉斯抓住我,摇晃我说:「黎斯特,够了,停止吧!」
我停止不了。跑向窗前,我打开厚厚的玻璃,紧紧瞪着星星。我忍受不下去了,我忍受不了这样纯然的虚空於阒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