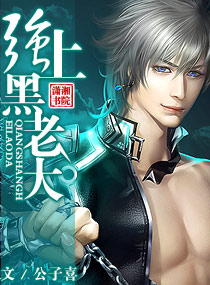船帮老大-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暮色四合,夜色渐沉……
赵法师换上青布七星袍,头戴寸缕方斗帽,左手捏“浑天应应极极空空速速得真”黄符,右手执“真水浸泡,歃血养锋,益蓄紫气”之桃木三尺剑,东、西、南、北各点燃四盏高灯,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又分燃四盏矮灯,院中正中央,摆放一桌两凳,桌上摆放香蜡黄裱灰盆,两凳上支放着童男童女硬纸图样……而后,赵法师又命众人在厨房备好柴禾,锅中放满清水,随时听候赵法师的号令,准备点火烧水……
星空之下,赵法师静静站立,倚剑于前,眼看着漫天星斗,忽然,返身一跃,直刺一剑,回环,一搅,高声叫到,“尘尘土土终归道,阴阴阳阳轮回昭……”伸手从道袍里,摸出一把朱砂,朝空中抛洒而去,趁着朱砂漫天乱飞,纷纷洒落,一把桃木三尺剑,“唰唰唰唰……”一阵利响,反转,复挑,直戳,点刺,回钩,延迎……一番剑式使毕,众人大惊——起先干簌簌的桃木剑身上,竟渗出了隐隐黑血,血珠盈聚,滚滚欲跌……
第二十八章 荐医
赵法师剑花旋舞,法袍鼓荡,闪转腾挪,袖飘襟舒,跃——刺——敛——送,招招式式,无不昭显利落遒劲!
鹏飞素来喜爱武功,见赵法师这般轻灵剑法,便悄声问身旁的郑半仙,“郑叔,赵法师这剑法,只是一种捉鬼拿妖的招式,还是确实有一定的真功夫?”郑半仙毫不犹豫,悄声道,“两者兼而有之。所谓冥武一脉,互为相支,便是这道理……”鹏飞似懂非懂地“噢”了一声……
忽然,东南处的矮灯,飘摆几下,倏然熄灭了……赵法师一个箭步上前,一剑挑起,双脚并跳,在灯盏上方,分展而开,身形呈一“大”字,左手一张黄符掷出,飘飘下落间,反手一剑削去,黄符齐齐断为两截……
“快,去点灯……”郑半仙吩咐鹏飞,“把东南处那盏灯再点燃……”鹏飞一跃上前,手执火绳,在灯盏上一撩,火星溅起,东南之灯,瞬间又被点燃了!
鹏云便问郑半仙,“郑叔,那灯为什么会灭呢?”郑半仙深吸一口气,“这是有孽鬼横穿,东南灯盏,形成域光,孽鬼见阳气刚盛,便扑身过去,以阴煞之气,将灯吹灭了……这时,法师上前以符条镇守域光,再以木剑驱鬼,迫使孽鬼原路折回,不得逃脱。所以,须将东南之灯重新点燃,形成壁垒……”
几番腾挪闪转,跃身舞剑,赵法师已是额前亮亮,汗湿面颊,忽听他喊一句——“架火,烧水——”坐在厨房灶头的满仓,便迅速将火绳,塞进干燥细柴间,灶膛内顿时火光闪耀,火舌外舔。
赵法师站在方桌之前,平神敛气,忽地将三尺桃木剑,高高直竖,擎于头顶,两眼紧闭,口中速念,“天馑欲朽万古木,良泉汩汩慰灾世,何得苍生怜此心,恶鬼从此绝其路。谶语常新愿为俗,祈颂如旧非古意,开阖阴阳断奈何,长问黄泉再鹤唳……开——”剑尖一道线,半圆扑划下,挑起黄裱一沓,疾速旋转,仿若剑身之前,盛放菊花一般。猛然一停,一抛,黄裱张张分散而开,被剑身一拨,恰遇烛火,点燃之黄裱,复又旁落,再有未燃黄裱前飘……如此更迭,轮回,续之……一时间,火光点点,熄熄燃燃,明明灭灭,乱花飞天,百鸟朝凤……直看得众人目瞪口呆!
众人正看得目瞪口呆间,赵法师将剑一收,“呼”地后退半步,回身喊,“吴氏上前,烧纸——”吴氏闻言,赶忙将备好的一沓火纸、纸钱,抱于怀中,急冲冲地迈着三寸金莲,走至供桌跟前,蹲下身子,将火纸摊开……赵法师挑起一张燃烧的黄裱,丢于火纸之上,火纸瞬间腾起火光……
这时,供桌两旁的凳子上,一对童男童女图样,竟然兀自抖动了起来,别着童男童女的竹签,弯弯折折,几欲折断,似有一双手在掰动竹签一般……
恰在此时,赵法师“嗨啊”一声大喊,从法袍中掏出一布袋,带口的细绳结,一抽便解开,转手一剑,刺入布袋之中,上下搅动,左右横贯,直将布袋口撑到了最大……
赵法师将布袋如网兜罩蝴蝶蜻蜓那般,向前一送,左下一转,遂又扯回,袋口细绳立即一圈圈速缠,绳头咬在口中,使劲一拉,将布袋牢牢系死了!
赵法师手执布袋,飞步直奔厨房,奔跑之间,众人见那布袋竟然起伏鼓胀,凸来凹去,似有无数的小老鼠在内中蹿动一般……此时,满仓早已将锅盖大开,一锅开水,正冒着珠泡,泛动不止。赵法师将布袋一下丢进沸水之中,右手桃木剑随后跟进,剑刃抵住袋口,用力下压,再下压,翻腾的沸水,转瞬将布袋淹没。起初布袋上的凹凸之状,也骤然消失……
“将火架大,烧——”赵法师长出一口气,用手擦擦汗水。满仓得了命令,将一把硬柴,在膝盖上“咔嚓”一折两半,用烧火棍在灶膛里一阵捣捅,将硬柴架入灶膛,顿时,大火熊熊,烈焰滚滚,火舌扑扑……
王铁汉几步跟来厨房,见锅中开水,扑跳溅珠,水泡迭续,而那布袋在水中,竟左右上下地翻转不停,惊得不知如何言语……
大锅被烧得极烫,锅中之水,越烧越少,至最后,只剩下不到三碗左右的水了……
众人赶来锅边,凑着去看,大惊——起先锅中倒入的是清澈的井水,而今,一番烧煮,锅中之水,黑如墨汁,油油淋淋,甚至散发出一种古怪的气息:似杨桃、米泔水、玉米须子,又似河底淤泥、鱼鳞、焦灰的混合气息……
赵法师对满仓说,“掏灰——”,满仓便操起大铁铲,伸进灶膛之中,左右一拨,上下一合,前戳,抖一抖,掏出一铲子草灰,“噗”地洒在锅中,随后,连铲三铲子,直将锅中之水,完全用草灰吸干了!
“唉……”赵法师将帽子摘下,对王铁汉说,“你派人随同吴氏,将此草灰、布袋,埋到吴氏当初进城的路上,尽量远一些……”
此时已是深夜,为了安全起见,王铁汉将所有徒弟,都派去随同吴氏。
收拾完法事道具,赵法师和王铁汉、郑半仙,来到陈叫山的房中。陈叫山此时沉沉而睡,极为安静,赵法师将一个三角形的红色纸角,塞在了陈叫山的被褥底下,并掏出一截红线,在四个床腿上,挨个绑缚了!而后,将陈叫山翻转过来,脊背朝上,伸出右手食指,在陈叫山的脊椎骨,先是蛇形绕划,而后戳点不止……
忙完这一切,赵法师长叹一口气,对王铁汉说,“王兄,你这位兄弟的冥邪,已经完全被驱,并且,我在院中各处,已布设机关,不用担心再有邪亵侵扰。另外,他的身上我也布设围障,任是诸般异象,也断不会乱他心志,王兄尽可放心……”
王铁汉、郑半仙连忙弯腰拱手,向赵法师致谢!
“不过,实不相瞒,你这位兄弟,体内已中了虚邪潜毒,而且时日已久,毒气扩散,经络皆受其害,必须寻求良医诊治!常话说,冥道医道,本为一道,我用冥道法力,将他周遭邪佞虚妄之象消尽,并布设围障护体,只能保他心志清正,不再受其虚妄。但是,他体内之毒,必须以医道诊治,方能绝而除之……如若不能,只怕……”
王铁汉起先以为,赵法师这一番法事,已然能救陈叫山,但听了这一段话,仿佛一人刚从沟坎里攀爬而出,却发现,前方却又是一百丈深涧……
“赵法师,既说是冥道医道,本为一道,还望赵法师为我们指点迷津……”郑半仙一脸迷惘与无奈,“之前请来一位老郎中,但人家却说无法诊治,要我们另请高明呢……”
赵法师看着陈叫山发青的嘴唇,转而将目光挑起,看向郑半仙,“若不猜错,你们请的一定是城南新街的史郎中吧?”王铁汉连连点头称是……
“史郎中此人,尽管年纪一大把,但实话说来,其医道学识,实是浅陋,遇见得心应手之疾,便故意拿腔作势,煞有介事,夸大病情,恐吓病者及至亲。若遇疑难杂症,自己未有信心把握,干脆不予接诊,免得名誉受损……”赵法师说到此处,唏嘘一叹,“医者仁心,岂能避祸趋福,岂能避重就轻,岂能为保名节,而处处决然,拒人于千里之外?便是我这冥道中人,也懂得这些道理,惜叹这史郎中,妄活半百啊……”
王铁汉朝赵法师略一拱手,“那依赵法师之见,乐州城里,还有哪位神医,可以诊治我兄弟之病呢?”
赵法师站了起来,背着手踱步,“以我之见,方今乐州城中,若论医术,排其第一者,当是卢家药堂的柳郎中……”
王铁汉和郑半仙,相互对视一眼,“哦”了一声……
“这位柳郎中,本为江南人士,打小跟随父亲学习岐黄之术,后来,家中遭遇变故,家道中落,便改弦易辙,做起了小买卖。再后,因生意之故,前去上海,在船上医治了一位洋人,洋人大喜,遂将柳郎中介绍于自己的医生朋友,一来二去,柳郎中的心思,又回到医术上来了,且是中医、西医并举,两相结合,医术飞升……有一年,卢家夫人去上海办事,偶遇柳郎中,见柳郎中医术精湛,却寄人篱下,无力自己开办药堂,便热情相邀,柳郎中感激不尽,便来了乐州……”
王铁汉和郑半仙,皆陷入了一阵沉思……
赵法师回身过来,看了看陈叫山的面色,将手在王铁汉的肩膀一拍,“你这位兄弟的病情,须及时诊治,不可拖延,倘若稍有迟疑,只怕是凶多吉少……我见他面色煞白,嘴唇青黑,脊背肤色亦异于常人,我虽不精通医道,但可大致判断——三日之内,若无良药救治,待到三日一过,便是华佗在世,也是无力回天了……”
第二十九章 恶疾
赵法师的一番话,令王铁汉和郑半仙愁眉深锁……
送走赵法师,两人围坐在陈叫山床前,若两尊泥像,烛影点晃,人影细长……
郑半仙想到赵法师说的那句“三日之内,若无良药救治,待到三日一过,便是华佗在世,也是无力回天了……”,便幽幽地问王铁汉,“贵楷兄弟,卢家那个柳郎中,医术到底如何?”
王铁汉叹了口气,替陈叫山拉了拉被角,“他是卢家药堂的郎中,一般是不对外接诊的……以前听德荣巷的接生婆说,卢家少奶奶一直怀不上孩子,柳郎中也几番医治,却始终不见效……”
郑半仙听了此话,又想再问,嘴刚张了一下,话又咽回去了……
“不过,如今也只能去找柳郎中了。赵法师在冥道医道,皆有人脉,他的推荐应该错不了!”王铁汉看着窗外的夜海,树叶翻卷,夜虫声弱……
吴氏和徒弟们都回来了。七庆和鹏天走在最前面,一进屋,见陈叫山睡得如此沉静,一脸欢悦。七庆说,“叔,那草灰埋到小河桥那边了,够远了吧?再走的话,都要过凌江了哩……”
王铁汉便让七庆和饶家三兄弟,到别的屋去睡觉,由他和郑半仙守着陈叫山。
天快亮时,郑半仙实在熬不住,脑袋一再地朝一侧倒去,冷不丁,一头磕在了墙上,一下灵醒,再无困意。
恰这时,大门响了两声……王铁汉感觉头昏昏沉沉,似戴着个铁帽子一般,用手扶了好几次,才不至于歪斜,正要去开门,鹏飞却领着毛蛋进来了。
毛蛋一进屋,见陈叫山沉沉睡着,便问王铁汉,“王师傅,陈哥这……到底咋了?”王铁汉拉拉床布,示意毛蛋坐下,“说是身体中了邪毒,昨个一天,难受得满床滚,啥都吃不成……赵法师禳治了一下,现在还好些,可是……”
徒弟们都起床过来了,吴氏烧了一壶水,给陈叫山倒出一碗,边走边吹热气,跨门槛时,差点摔一跤。众人都以为,经过赵法师的禳治,陈叫山的病就没有大碍了,但听了王铁汉的话,皆低头,皱眉,一屋子的人,静若深海。
“既然这样,我去把柳郎中请过来看看……”毛蛋端着吴氏递给他的茶水,一口没喝,便欲起身……身子还没完全站起,却听王铁汉说,“卢家人知道柳郎中对外接诊,会不会……?”毛蛋将茶杯,放于一侧,“哎呀,王师傅,放心好了,这都是小事儿……陈哥也不是啥外人。”
没多大工夫,毛蛋就把柳郎中请过来了,一同来的,还有禾巧和魏伙头。
柳郎中一进屋,从毛蛋背上取下诊箱,先取出一个小小细细的玻璃棒子,放在眼睛前瞄了瞄,然后用力地甩甩,对王铁汉和郑半仙说,“来,被子掀起来,把温度计放他腋下。”
在等温度计的时间里,柳郎中一边仔细观察陈叫山,一边听王铁汉描述陈叫山发病以来的症状,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都来补充,柳郎中听着频频点头……
吴氏特地为禾巧端来个凳子,要禾巧坐下,禾巧拉着吴氏的手,笑笑,示意她站着便好,将凳子让给了魏伙头,魏伙头也不坐,紧张地看着陈叫山和柳郎中,等着柳郎中说话……
柳郎中在陈叫山的膝盖处轻轻按按捏捏,又问那天比武的情况,鹏天便说,“山哥就挨了高雄彪一蹬脚,除此没啥……”柳郎中便又去查看陈叫山的胸膛,然后又从诊箱里取出个类似大弹弓的玩意儿,将弹弓叉子夹在耳朵上,弹弓裹皮上的一个圆溜溜、亮晶晶的玩意儿,放在了陈叫山的胸膛上,歪着头,闭着眼,似在仔细地听着什么动静……
柳郎中将温度计从陈叫山的腋下取出,横于眼前,看了看……而后,方才拉过陈叫山的胳膊,捏于其腕,悉心把脉……
满屋子的人,大多都看着陈叫山沉睡的样子,也有人看屋顶的椽子,看自己的脚尖,惟独禾巧静静地看着柳郎中的脸,仿佛要从他的脸上,读出些许玄机来。然而,柳郎中神情始终如一,无任何变化,把一阵,又换了一只胳膊。
柳郎中把完脉,摇了摇头……众人一见柳郎中摇头,顿时一慌,禾巧更欲走上来问话,却忽然见柳郎中,竟抬手给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呯”的一声脆响,将所有人都弄懵了……
柳郎中缓缓卷起陈叫山的裤腿,众人一看,陈叫山的右腿小腿处,有一伤疤,疤痂黑紫,早已干结,但疤痂边缘之处,斜斜的密纹,延展开来,小腿处透着一种淡淡的幽黑,仿佛山水画中的淡墨,于生宣上借水生发一般……
“我当真是失职,当真失职啊……”柳郎中拍拍前额,一脸愁结,“当初,我若及时诊治,怎会导致如今这情况?我真是……”
柳郎中说,前阵子,陈叫山被关在卢家大院西内院小屋时,夫人前去探看陈叫山,便要柳郎中来为陈叫山治伤,但陈叫山当时极为坚决,认为伤口已经结痂,并无大碍,无须治疗,而柳郎中当时也就认为并无大碍,没有坚持……
“唉……”柳郎中长叹一声,“但凡人被犬类咬伤,在第一时间进行伤口处理,并口服用药,倘若遇到的是良犬,三日之内,便可无碍了;倘若遇到的是恶犬,纵然棘手,但及时处理,中、西之医并治,虽费周折,也可痊愈。但是,所遇为恶犬,又听之任之,不做任何处理,待到恶犬之疾,完全爆发,治疗的难度便犹如登天,治愈机会,百而无一啊……”
见众人不甚理解,柳郎中进一步解释说,卢家护家犬宅虎,属于恶犬一类,体内含有邪毒,且宅虎体壮如牛,其邪毒便愈加恶重!而陈叫山当初被宅虎咬伤,完全不曾在意,未有任何治疗处理。陈叫山肌体康健,对邪毒有强劲的抵御之力,但终究是以冰阻火,只可阻一时,终究无法自愈!邪毒愈积愈重,陈叫山肌体的对抗之力,便日渐式微。最近一些时日,陈叫山定是习练武功,耗去太多体内元养,加之与小山王高雄彪比武,更是将元养损耗,反令邪毒盛旺,便由此导致了邪毒全面爆发……
柳郎中一席话,说得众人如临深渊,如坠冰窟,皆将视线投向陈叫山,每个人都想着陈叫山曾经的模样,与而今躺在床上的陈叫山之模样,两相叠合,浑浑而映……吴氏已哭出了声,禾巧将吴氏的手拉过来,安慰着她,而禾巧自己也是眸池渐盈……
柳郎中又俯身上前,查看陈叫山的嘴唇、眼睛、头发、耳朵、后颈、指节、前臂血管、肚脐……
“黄帝内经说,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深则毛发立,毛发立则淅然,故皮肤痛。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在络之时,痛于肌肉,其痛之时息,大经乃代。留而不去,传舍于经,在经之时,洒淅喜惊。留而不去,传舍于输,在输之时,六经不通,四肢则肢节痛……”柳郎中得知赵法师已通过冥道法力,为陈叫山设下围障,令心志免受邪亵虚妄,连连点头,遂而又低低叹息一声,“赵法师外驱邪亵,是将堤坝固牢,其内,心志不受虚妄,其外,异象鬼魅再难侵扰,算是大功一件……接下来,我尽力而为吧,三日之内,若无好转,只能是……”
返回卢家大院的路上,禾巧跟在柳郎中、毛蛋和魏伙头身后,走得时慢时快,嘴唇一直抿着,一抬头,见三人已稍远了些,便小跑上前,问,“柳郎中,陈叫山的病……你觉得,到底有几成把握?”魏伙头和毛蛋,也停下步子,看着柳郎中,等着柳郎中的回答。柳郎中却眼睛看向街边的一棵白杨树,仰着头,一直朝上看,直至看向树尖,而后收回视线,“半成都没有……”
毛蛋一听,急说,“那……”,只说出个“那”字,却断了话,看了看魏伙头,魏伙头明白毛蛋的意思,便说,“柳郎中,那……依你之见,还有谁能够治这种病呢?”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天下必定有治疗此病之人……”柳郎中幽幽叹息,“只是,拖延太久,发病太猛,诊治太晚,只有三天时间,三天时间了……便是去邻近的重庆、汉口等地,亦是时日仓促。更何况,此种恶疾,不宜见光,见风,不能闻听水声,如此,怎么乘船前往?”
三人听完柳郎中的话,都不再说什么,只是缓缓向前走……
毛蛋心里十分难过,魏伙头看出了他的难过,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不停地捏捏,示意毛蛋不要在大街上哭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