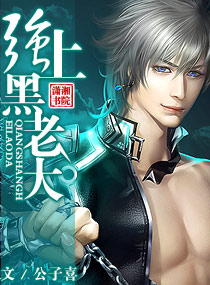船帮老大-第26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陈叫山去谭师爷住处时,谭师爷和卢恩成正在喝茶聊天,下人上前禀报,“师爷,陈帮主过来求见……”
谭师爷委实吃了一惊!
“少爷,你且先到内屋回避一下……”谭师爷起身让卢恩成进了内屋,忙又将桌上的茶碗,收拾了,这才将袖子两弹,拿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悉心阅读起来……
“谭师爷,许久未来拜访,近来可好?”陈叫山走入房中,拱手见礼……
“好,好好,陈帮主来探望老朽,老朽深感荣幸……陈帮主,请上座!”
两人简单寒暄一番,陈叫山便将卢芸香自愿入祠堂受罚一事说了出来,谭师爷心下忽地一松,遂又忽地一紧……
心弦之松,是缘于陈叫山前来,并未如谭师爷所料那般,来质问,或者探索什么。
而心弦之紧,则是因为,谭师爷觉得:宝子尽管是死了,可二小姐卢芸香在山上那么久,定然知晓许多过往之事……这些过往之事,会不会传到陈叫山耳朵里去呢?
二小姐要入祠堂受罚?这究竟是二小姐自己本人之意愿呢,还是夫人的意思,或者,是陈叫山的某种计谋所为?
在卢家大院,二小姐不入卢家祠堂,是人所共知之事!
如今怎地就要入祠堂受罚?
此事颇多蹊跷,由不得谭师爷心下疑惑,揣度,心弦一紧……
卢家历来的祠堂活动,尤其是颂愿、祈福、家规家法之梳理,公示,都少不得谭师爷参与。
可是,现下是二小姐入祠堂受罚,这是一个“眼皮上挑刺儿”的活,深不得,浅不得啊!
倘若自己将受罚程式,定的过重,二小姐心下生恨,必然会报复自己!甚至,在祠堂那种地方,二小姐当场发飙翻脸,将自己曾经设计陷害陈叫山,委派宝子进入取湫队之事,全然抖落出来,那自己的老脸,该往哪儿搁?
倘若自己一味求受罚之轻,夫人那一头,恐怕又不好过……
谭师爷思虑之间,便说,“夫人对于此事,是何态度呢?”
陈叫山此际也在不断思虑着……
在等待谭师爷接话之空时,陈叫山看见谭师爷眉头一松一紧之变化,便大许猜出了谭师爷内心之动荡……
谭师爷将话接了,反问夫人的态度,陈叫山当然不可能说,自己已然是卢家中流砥柱之类的话,便说,“夫人的意思是,谭师爷你对卢家祠堂活动熟络,卢家家规家法,也是精熟在心,让我来请教于你……”
“哦……”谭师爷默默点着头,面容上风平浪静,内心却已波涛汹涌,越发觉得此事非同一般了……
谭师爷表情之凝然,皆被陈叫山看在眼里,分析于心……
如今的陈叫山,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说话做事,仅凭一股子豪气,仅仅信奉大义为先,而不能体察人情的陈叫山了。
“此次祠堂受罚以后,二小姐便会离开卢家,远走他乡,也算是清赎了她对卢家犯下的罪孽……”陈叫山思忖之间,故意抛出这一话,看似无意,实则颇具机心……
很多事情,总是连环相套,矛盾而统一着——
假如,当初谭师爷没有设计出取湫一事,陈叫山在卢家,在乐州城,兴许也是庸庸碌碌,何能达到如今之地位?
原本是为陷害陈叫山,反倒成就了陈叫山。
假如,谭师爷当初没有安排宝子,进入取湫队伍,宝子也不过是卢家大院的家丁头目而已,不会跌落太极湾的铁索桥下,后又被瘸子李救起,成了野狼岭的二当家。
宝子如果没有成为野狼岭的二当家,卢家也就不会遭遇纵火暗袭,三太太不会因此丧命,老爷不会因此悲伤郁气,痴傻偏瘫了去……
那么,说到底,卢家如今之境况,一切之一切,其根源,是源于谭师爷的取湫之计么?
陈叫山无数回地想过这个问题——到底是谭师爷成就了自己,还是天意成就了自己?
尽管很多次,陈叫山都感知并怀疑到了谭师爷头上,怀疑到是谭师爷安排宝子进入取湫队,意欲谋害自己的……但是,宝子与瘦猴那些人,皆已失踪死亡,这样的怀疑,没有一个具体之证据……
即便陈叫山无数次想找谭师爷,质问、探索取湫之真相,可始终没有一个合适契机!
陈叫山一度想将此事,无限制地搁浅下去,但剿匪归来,又听闻到发生在唐家大院的道士装神弄鬼之事,陈叫山第一时间,便隐隐地又怀疑到了谭师爷身上……
因为,这般装神弄鬼的幽冥之计策,除了谭师爷,还有谁能筹谋得出?
现在,二小姐要入祠堂受罚一事,落到了谭师爷身上,谭师爷表现出来的种种凝虑之表情,让陈叫山隐隐觉得——这是一契机,一个解开许多旧事玄机的契机!
于是,陈叫山适时地抛出一个概念,说出“此次祠堂受罚以后,二小姐便会离开卢家,远走他乡,也算是清赎了她对卢家犯下的罪孽……”的话,这一句话,像是给谭师爷抛下的一个诱饵,又像是给谭师爷敲下的一记警钟!
谭师爷的凝虑表情,给了陈叫山一个提示:如今,二小姐卢芸香,在谭师爷的心中,犹若一个定时炸弹,一个烫手的山芋!谭师爷巴不得二小姐死,或者,巴不得二小姐早些离开卢家,走得越远越好……
陈叫山在说这句话时,特地将“清赎了她对卢家犯下的罪孽”,加重了语气,暗暗地给予谭师爷以警告——卢家遭遇的劫难,不也正是拜你谭师爷所赐么?
“哦,哦,是这样啊……”谭师爷默默点着头,以手抚着胡须,若有所思……
谭师爷尽管表现得城府似海,心迹不露于表,但在陈叫山的眼中,一切,皆已昭然……
“谭师爷,祠堂受罚之事,非同小可!老爷如今自然不能参与其中,夫人身子骨也不大好,我想,我们不如找少爷来商量商量……谭师爷以为如何?”
陈叫山明知谭师爷之七寸,却偏就猛朝七寸处击……
第611章 步步紧逼
陈叫山思接千虑,神游无极,于云淡风轻间,不着印痕地,向谭师爷之七寸猛击!
发生在唐家大院的道士装神弄鬼之事,经郑半仙一番拆解,吴先生和陈叫山皆已感觉到:少爷卢恩成行为有蹊跷之处!若非如此,绕着那太极图转圈,其余之人,皆无异常,为何单就卢恩成跌倒在地,痛苦不堪?
而当郑半仙当场揭穿那道士的伎俩时,卢恩成又突然怒不可遏,情绪激动,拔枪射击,当场将道士一枪打死……
凡此类类,皆可说明,此事非比寻常!卢恩成此人,疑点多多……
以陈叫山对卢恩成的了解,认为:卢恩成是那种没脑筋的人,看似咋咋呼呼,实则毫无城府,遍寻全身,难觅机心!那么,卢恩成之背后,必然有一位高人……
“我们不妨找少爷来商量商量……谭师爷以为如何?”
陈叫山此话一出,目光投向谭师爷的眼睛,不避不闪……
那一瞬间,四目相对,二人皆欲从对方的眼睛中,读出玄机,读出从容或怯弱,无意或机心,镇定或慌乱……
“嘎叭叭……”
两人在屋内说着话,未曾留意屋外之天气,不知何时,天空已铅云堆聚,暗暗下压,风云滚滚,随之,一声闷雷,轰然炸响
“嘎叭叭叭哄……”
时近黄昏,光线本就幽暗,再受乌云遮罩蒙蔽,室内更是黑乎乎一片……在两人对视之间,雷声出,闪电至,一道刺目的亮光,一刹里,映得两人的眸子,亮如水晶……
这,是一暗战!
恰若绝顶高手一相逢,拳风掌气,刀光剑影,不避不闪,勇然相向!
在对视时,倘若陈叫山是以一种武夫的凶顽,狠劲之目光,相对于谭师爷,谭师爷或许不会心慌自怯。'就上^^中^^文^^网'
然而是,这一刻,陈叫山的眸子中,透射出的,是一份平静、淡若、大而化之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深邃、从容……
这足令谭师爷感到恐惧、慌乱、不安、自怯了……
谭师爷从未这样惶惶过……以前,在谭师爷以为,陈叫山不管是陈队长也好,陈帮主也罢,取湫英雄也好,打败日本第一高手的所谓民族英雄也罢,都是不足为虑的!因为,至少在卢家,陈叫山没有扎实的根基。而自己,在卢家深耕细作许多年,论资历,论底蕴,论威望,陈叫山都不足以对自己形成威胁……
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陈叫山跑船途中,在瓦桥镇截获了大量金银财宝,侯今春觊觎财宝,心有不平,谭师爷怂恿撺掇卢恩成,令其去找夫人探索此事,结果,卢恩成败兴而回……
这就是一个信号!
在如今情势下的卢家,夫人已经将陈叫山推至一个新的高度上去了,对于陈叫山私藏财宝之事,不予过问。或者说,即便是夫人,也已经难以驾驭陈叫山了!
窗外电闪雷鸣,紧接着,大雨滂沱而下,唰唰唰唰的声音,反衬出屋内,那一刻的异常的寂静……
“嗯,这是理所当然的,回头我找少爷合计合计祠堂受罚的事儿……”谭师爷终究是老江湖,在片刻的惶惶后,恢复镇定之常态,并说了一句幽幽的闲话,“哎呀,好大的风雨啊……”
这一句,可以理解为谭师爷对于天气之随口感慨,但在陈叫山听来,这也是对于心智、心力之暗斗的残酷之感慨……再深一层,其弦外之音是:这么大的风雨,陈帮主你是走是留呢?
这一语成三意的话,惟谭师爷这般的老狐狸,能说得出来!
这一语有三意的话,惟陈叫山能体悟透彻,拆解清楚……
棋逢对手。
半斤八两。
“这么大的雨,我得到码头去转转,那些修补的旧船,不晓得会不会被积水压翻扣船……”陈叫山站起身来,拱手道,“谭师爷,告辞!”
“陈帮主,慢走”
谭师爷拱手还礼,目送陈叫山转过身,朝门口走去了,不禁轻吁一气,仿佛瞬间卸下了千斤负重自己真个是老了,与陈叫山这样的年轻后生,一番角逐心智、心力,时间不久,自己却已疲累不堪……
一直躲在内屋的卢恩成,听到陈叫山的告辞之语,以及谭师爷的送客之言,也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卢恩成在内屋,听见陈叫山提说祠堂受罚一事,要与自己商量之时,兀自一慌:莫非,我在唐家大院里,搜寻捕捉吴先生搞地下党工作的蛛丝马迹之事,被人发觉了?我与那道士演双簧的把戏,被人识破了?陈叫山是要借这个祠堂受罚一事,来给我好看么?
唉,这个瘟神,可算是走了,闷死我了,急死我了……
卢恩成手刚伸到门闩上,准备开门出来时,突然,手又缩了回去……
陈叫山的脊背上,仿佛长着眼睛一般:转身之后,谭师爷那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轻轻吁气的声音,全然被陈叫山捕捉……
“对了,谭师爷……”陈叫山的一只脚,已经跨过门槛了,却又迈了回来,猛地转过身来,直视谭师爷的脸,“晚辈不太懂一些规矩,请问,二小姐祠堂受罚这事儿,谭师爷觉得放在哪一天为最佳?”
倘若说,起先陈叫山与谭师爷的谈话,你来我往,角逐心智、心力,属于拳脚相对,刀剑碰撞,旗鼓相当的话,那么,陈叫山如今这猛一转身,忽地来了这么一句,便如一记飞镖,倏然掷出了……
谭师爷毫无防备,猝不及防,脸上那如释重负的释然,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凝虑,完完全全地在脸上写着呢,被陈叫山昭然而视,毫无保留,彻彻底底,清清楚楚……
陈叫山这是步步紧逼啊,完全不给自己哪怕一丁点喘息的机会!
谭师爷迅速地恢复了一种淡定神情,遂即,转为思游盘算之表情,低了头,右手的大拇指,在其余四指上来回地点压着,似在掐算日子,嘴里亦喃喃有低声,“子、丑、寅、卯……”
陈叫山就是要这般地紧逼谭师爷,令其在最短的时间里,给出答案,给出一个准确的日子!
时间短,便仓促:你谭宗砚,谭师爷,不是擅于算计设谋么?你现在好好地算计,好好地设谋吧!就在我陈叫山的眼皮子底下,就在这眨巴眼的工夫里……
谭师爷嘴巴里喃喃着天干地支,甚至眼睛都闭了起来,看似掐算日子,实则是在梳理着太多太多东西……
这是一种煎熬!
终于,谭师爷实在不愿消耗下去了,手指一停,眼睛睁开,“陈帮主,祠堂受罚这等大事,草率不得!这样吧,今儿晚上,我翻翻卢家祠堂活动事志,再查查《紫微斗数》,明儿一早,我们再合计?”
“好,辛苦谭师爷了,告辞!”陈叫山再次拱手道别,转身而去……
“奎子,奎子,给陈帮主拿蓑衣披上,这么大的雨,可别湿了衣裳……”这一回,谭师爷犹若惊弓之鸟,没有再如之前那般如释重负,便刻意喊下人,为陈叫山找蓑衣遮雨……
陈叫山接过下人送来的蓑衣,出了谭师爷住所的院门,那奎子将院门反闩好了,谭师爷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而后,用手指在桌面上一敲,冲着里屋喊,“少爷,出来吧!”
“师爷,陈叫山该不会是看出什么了吧?”卢恩成战战兢兢地出了内屋,甩甩头发,故作镇定……
谭师爷面色很难看……
卢恩成啊卢恩成,你是猪脑子啊?人家都逼到这个份上了,你还问我是不是人家看出来什么了?
谭师爷心里暗骂着卢恩成,但卢家少爷终究是卢家少爷,只可心里暗骂,怎好明着叱责?
“少爷,你刚才在内屋也都听见了……”谭师爷身子朝椅背深深地靠去,显出疲累的样子,语气也由此变得有了一种推心置腹,语重心长之味儿来,“陈叫山不是以前的陈叫山了,不是那么好对付了……唉,咱们都太想当然了,一着错手,让人家步步紧逼,狼狈不堪啊!”
“我说师爷,你未免太多虑了吧?”卢恩成用手捋了捋中分头,使得中分的缝儿,分得更清晰些,不以为然地说,“他就算觉察到了些不对劲儿,也没啥,那道士都被我打死了,他能把咱咋样啊?”
谭师爷现在恨不得扇自己一个耳光我怎么就想出了这么一个昏招?
谭师爷更想给卢恩成一个耳光我怎么就搭上了你这么个猪脑子的帮手?
“少爷啊……”谭师爷胳膊扬在了半空,似乎下了很大的勇气,要以一种激动的情绪,将很多的话,犹若开闸泄洪,一下道出,但转念之间,语气却又变了,“你就不该将那道士打死……”
“此话怎讲?”卢恩成将身子朝谭师爷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不打死他,他要是嘴巴一通乱说,咱们可不就全亮了底儿了么?”
“少爷,你想想看:你不杀他,他顶多一口咬定,就说自己是为了混到唐家,偷盗些钱物罢了,这个理由,谁能深究,谁能勘破?至于你走太极图倒地,那都是幽冥之事,他郑半仙再厉害,也寻不到实打实的把柄证据,且又顾忌你是卢家少爷的身份,能把往你风口浪尖上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郑半仙莫非不明白这个道理?”
“唉……”卢恩成似乎回过味儿了,深深一叹……
“现在可倒好,你把人杀了,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任是谁,稍微一琢磨,就能觉出了蹊跷:一个云游的道士,混骗钱财罢了,罪不至死啊!”
“师爷,那照你这么说,我们现在还拿陈叫山没办法了?”卢恩成有些急,有些慌,有些无奈……
“你没听说么?陈叫山将剿匪的功劳,全部送给了县府,送给了孙县长……孙县长是那种邀功迫切,急于升迁的官场小人,陈叫山来这么一手,算是把孙县长也收买了!”谭师爷无奈地摇摇头,“陈叫山,越来越老辣,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哈小說网
第040章 雨夜狂情
卢恩成与谭师爷聊至深夜,谭师爷左一句“陈叫山越来越老辣,实在不好对付”,右一句“你不该冲动杀人,做事要动脑子,要冷静”,听得卢恩成一肚子闷气……
卢恩成告辞,谭师爷送上雨伞,卢恩成也赌气不接,冒雨回到了自己住处。
唐慧卿在娘家住,小院只有丫鬟莲惜在。
夜深,莲惜已睡下了,卢恩成被大雨淋得一身湿透,站在院门前,发气拍门,拿脚踢……
“睡死啦?”
莲惜撑了一把小伞,急慌慌刚将门闩拉开,卢恩成便怒喝一声,猛蹬门,莲惜被门扇一打,一屁股坐在了泥地上……
莲惜认为自己开门晚,所以卢恩成才发这么大的火,一骨碌爬起来,拾起小伞,给卢恩成遮了雨,自己淋在雨中,怯怯说,“少……少爷,你不是住……”
两人回到屋里,皆是浑身湿漉漉,卢恩成拧开一瓶酒,对嘴吹唢呐,一气喝下小半瓶,“咣”地将酒瓶朝桌上一墩,哈着酒气,又“阿嚏阿嚏”连打了几个喷嚏……
“少爷,你把湿衣裳脱了,小心着凉……”莲惜给卢恩成拿来一条毛巾,让卢恩成擦干头发……
“给,你整两口,祛湿寒!”卢恩成未接毛巾,却将酒瓶子递向莲惜。
莲惜脑袋不停地摇着,湿漉漉的刘海儿,在眉上一下下晃……
莲惜着急着给卢恩成开门,穿了一件月白色薄衫子,便起了床。
经大雨一淋,薄衫子湿透了,紧紧黏粘贴身,将身子束箍得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尤其肚脐腹沟,深凹了一道窄窄细槽,薄衫子顺着那细槽抖抖闪,在灯光下亮簌簌一条线,有些别样妩媚……
卢恩成没有强塞。将酒瓶放到嘴上,一仰脖子,又猛灌了几口酒,眼睛红红,瞪着莲惜说,“你说,我在卢家。是不是屁都不顶?”
莲惜秀眉微皱,眼睛睁得大大。疑惑地看着卢恩成,不明白卢恩成怎地忽问这般的话……
“你放个响屁啊,摇她娘个什么头……”卢恩成见莲惜只摇头,不吭声,越就火大!
莲惜连摇头也不敢了,只呆着,惊惧地望着卢恩成那酱赤的面色,几欲冒火的眼睛……
“你们都看不起我了,是吧?我卢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