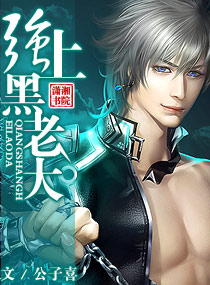船帮老大-第2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们都看不起我了,是吧?我卢恩成在卢家。就是个笑话,人人都能笑的笑话,是不是?”
“少爷,你……咋了?”
卢恩成闷闷叹一声,将剩余半瓶酒,一气喝尽,觉着浑身燥热。三两下脱了褂子,团做一团,狠劲朝地上一丢!
莲惜下蹲,要去拣褂子,卢恩成脚更快,一脚踩住了褂子。连续地踩、踏,“你这没用的卢家大少爷,我踩扁你,踩死你,我让你没用,让你没用……”
“少爷,少爷……”
莲惜被卢恩成的歇斯底里。吓得哭了起来,便蹲下去推卢恩成的脚,扯那被踩得泥水乱冒的褂子……
莲惜左争右抢,扯住了褂子一只袖管,卢恩成将其余部分,踩得死死的,两手又过来掰莲惜的手,莲惜一拽,褂子一带,便将卢恩成带倒了,一下扑到了莲惜身上,两人双双倒地……
“少爷,少爷,少……”
卢恩成爬在莲惜身上,仍旧去夺莲惜手里的褂子,一挣一夺,一拽一扯之间,莲惜身上那月白色的薄衫子,被卢恩成赤条条的身子,蹭得卷了起来,肚脐腹沟亮了出来,再往上,那一对圆鼓鼓的大蟠桃,隐隐露一截,似隐似现,乍隐乍现,且因这一番抢衣大战,气喘不止,蟠桃忽大忽小,忽扁忽圆,忽高忽低……
卢恩成觉着下面蓬勃雄武,便将那月白色薄衫子,索性更朝上卷去,脸嘴凑上,去啃咬大蟠桃……
“少爷,少……”
莲惜努力将月白色薄衫子,再朝下盖,卢恩成便就又朝上卷,两人似迂回之战,你来我往,抢夺阵地一般……
“哧——”
卢恩成又气又急,又怒又燥,双手拽紧月白色薄衫子,两手一分,将薄衫子撕扯开来……
“不——”
“少爷……少……你……你你不不能……”
“少……少……少奶奶……要……要要要知……”
卢恩成犹若骑上了飞驰的骏马,好比跳上箭速的顺风船,此际怎停得下来?
“她……她知道个屁!”
“知道又怎样?”
“不下蛋的蠢鸡……”
卢恩成喘着粗气,嘴里,鼻里,一股股的酒气,朝莲惜扑去……
“少……少少少爷……嗯嗯……”
莲惜仿佛觉得自己也醉了,醉得天旋地转,醉得浑身软如稀泥,手臂要去推卢恩成,怎地没有一丝儿气力……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剑拔弩张,怎可抵挡?
卢恩成三下五除二地消解了壁垒,雄赳赳,气昂昂地亮出军火,惊异发现:身下之人,竟闭实了双眼,完全放弃了抵抗……
卢恩成拥兵冲杀,直直冲入了城门,金戈铁马,狼烟北风,战旗猎猎,马蹄阵阵……
窗外,雷声隆隆,大雨哗哗,闪电亮亮,风刮草木,天地混沌……
屋内,花藤颤颤,花蕊艳艳,藕节动闪,藕叶扑乱,池水湍湍……
“我才是卢家真正的主人,是不是?”
“是……”
“我说什么,做什么,卢家所有人都得听着,都得办着,对不对?”
“嗯……”
“我卢恩成不是孬种,不是窝囊废,不是猪脑子,不是……”
“嗯……嗯嗯……嗯……”
万马齐喑,万箭穿心,闸道宏开,万流滚滚……
“啊——”
“嗯……”
窗外风雨依旧肆虐!
屋内风雨骤然顿歇……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大雨下了一夜,风劲吹,雷猛击,电频闪……
于一般人而言,如此夜晚,关闭门窗,裹紧被子,任由屋外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权为深眠之伴和,可睡得一好觉。
然有心事者,本易失眠,听闻树木动响,雨打檐墙,雷击浩空,闪电将窗格子上的白纸,无数回地射得雪亮,愈就辗转反侧,实难入梦了……
天明时,雨势弱了,倾盆倒斗,转为了白蚕吐丝,黄豆跳箕,转为了粉面落筛。
一整夜的闹哄哄,忽而静悄了,有人反而不适,推窗观天,见青灰天空,犹若棚幕,没有乌云压坠,反而亮白无际,便知是遭遇霖雨天了……
第041章 豪战巨浪
昨日,陈叫山向谭师爷告辞时,说了一句“这么大的雨,我得到码头去转转,那些修补的旧船,不晓得会不会被积水压翻扣船……”
实际上,陈叫山并未去碾庄码头,径直回西内院,躺倒便睡了。
岂料,陈叫山未去码头,却是一语成谶——大雨滂沱,下了一整夜,碾庄码头竟真出了不少麻烦……
一夜大雨,凌江江水暴涨,泥黄浪头,一浪扑掩着一浪,卷带着白花花的水沫,江上浮着上游漂来的木渣、树叶、草茎、破衣烂鞋、死猫死耗子,颠着晃着,浩荡而来,水浪直扑碾庄码头的出货石阶。
码头前坝,地势虽是南低北高,但坡幅终究不大,禁不住洪水的冲击!洪水一旦逾漫上码头,由南冲北,一路席卷,那些通货的土道,定然被泡得稀软,即便洪水退后,路基土层必然下陷,严重者,或可导致石墙底基不稳,从而垮塌……
船厂有几条拖运新船的滑道,以及两丈宽、六尺深的试水河,洪水一旦进入其中,顺之猛灌,船厂、仓房、工棚,尤其是临时转运囤货站,地势相对低,便皆凶险了!
码头总管冯天仁,半夜里睡不安心,戴了雨帽,到江边察看一番,以测洪标尺卡测一番,依据经验,料想天亮之前,江水不会对码头构成威胁……
谁能想到,后半夜里,凌江上游的沔州、梁州,皆由大雨转为暴雨,不到一个时辰,洪峰便形成了……
亏得冯天仁将一支短香点燃,夹于右手拇指中指间睡觉,待香火烧了手指时,急忙再到江边察看,一看,惊得跳了起来——石阶顶沿处,江水直差半寸。便要漫齐而过了。
此际,天微明,雨虽小了,但谁能晓得上游天气情况,只消再涨半寸洪水,码头便就危险了!
冯天仁飞步朝码头跑,雨帽跑掉了。也不管,飞奔回码头工棚。拼命拉铜铃,“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响,并大吼,“全都起来了,洪水要来了……”
船帮的兄弟,昨个夜里,有的回家里住了,有的串亲戚,有的逛窑子。天黑后,雨一下,好些人都未回码头住。
工棚里并没有多少兄弟……
“笙子,笙子,你快回城里喊人去,这天气不对付,还有大雨……”
“狗成。狗成,别扯懒腰了,赶紧跟我走,快啊……”
“墩娃,你赶紧领人去仓房,拾掇麻袋过来。赶紧装沙袋……你犯啥迷糊哩?再迟一阵,你****的都得让龙王爷收了……”
“老嘎呢,老嘎呢?是不是又回去整婆娘去了?”
冯天仁在工棚里喊来喊去,喊得一身汗,片刻工夫,嗓子都微微沙哑了……
笙子穿好衣裳,出了工棚。伸手一接雨,望一眼天,“冯总管,雨都快停了,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
冯天仁操起门杠,在笙子屁股上打了一下,“邪乎你奶奶个腿,赶紧回城喊人,大雨还在后头哩!”
王墩领着几个兄弟,去仓房运麻袋,刚到仓房,一看,仓房竟出了大事……
昨夜风雨凶猛,临着东边仓房的一棵大椿树,被大风懒腰折了两截,一截窜在仓房顶上,枝枝杈杈,被风吹卷,翻来滚去,将仓房房顶的青瓦,戳弄了个不像样,大雨浇击,房顶窟窿越弄越大,大雨直下仓房之中……
东面仓房里码放的是些零散木头,大雨浇灌了一夜,木头竟都漂浮了起来,在仓房里长长短短地胡乱戳撞……
仓房是外围一溜排,里间却是矮墙相隔,间门无门扇,东仓房的雨水,流到了中仓房。中仓房里码放着瓷器、陶器,因这些东西体积大、销货慢,人家买一次,得用好几年,所以没有一次性向各处货栈转运。
碗、盘、碟、杯、罐、坛、佛龛、观音像,被草绳缚了,经雨水一泡,再由些零散木头三戳两撞,货堆没了形,便垮塌下来,破碎的瓷片、陶片,满屋里漂,一片狼藉……
陈叫山寅时左右,被一梦惊醒,起床,开门,提着马灯,察看雨情,见各处并无漏雨、渗水,便又重新回屋,研了墨,依凭脑中所记忆,展卷书写着《恒我畿录》……
待笙子浑身湿漉漉地跑来喊人时,陈叫山似有一种预感,直奔屋外,冲西内院的兄弟大喊,“起床了,起床了……”
笙子将情况一说,陈叫山便又吩咐鹏天,“赶紧去城北粮仓,再多叫些兄弟……”
陈叫山与众兄弟在码头上,铲挖沙子,充装沙袋,一阵风卷过,大雨又来了……
“不行,不行,还得再加高,别歇着啊,快装沙袋……”冯天仁见许多兄弟,被大雨浇得眯了眼睛,缩手缩脚,不想下狠力干活,便大声召唤着……
“帮主,你看,上头有高浪过来,估计这水势会越来越凶,沙袋得装快哩呀!”冯天仁抹着脸上的雨水,指着上游喊……
陈叫山一咬牙,太阳穴高高凸起如岩峰,将头发朝后全然捋了去,脱掉衣裳,赤膊上阵了,铁锹飞动,连连铲挖沙子,并大喊着,“都别扎堆,散开了,各司其职,动作麻利些,别让洪水笑话我们是软骨头!”
帮主都脱了衣裳干了,弟兄们还如何再偷懒懈怠?
大雨越下越凶,哗哗哗哗哗,似倾盆倒斗,雨水冲击在精赤赤的脊背上,肩膀上,雨珠乱飞,雨线几乎迷得人睁不开眼睛……
抬运沙袋的兄弟,一步三滑,有的跌倒了,头发沾了黄泥,被雨水一冲,蛰得眼睛难以睁开,半闭着眼睛爬起来,重又抓住了沙袋袋角……
陈叫山觉着弟兄这么一声不吭地干活,不是个事儿,兄弟们胸膛中那股子豪情,没有被调动起来,这活也就干得不猛,不疯狂,没效率……
“兄弟们,船队号子整起来!断头巨浪咱都斗得过,还怕这点区区洪水,堵死它!”陈叫山脖子上青筋爆起来大喊,“水浪高过天啊——”
数十号精壮壮的汉子,一律光着脊背,在倾盆大雨中,豪情顿生,跟着吼喊起来了——
水浪高过天啊——吼吼呀嘿——龙王江中站啊!
水浪没有头啊——吼吼呀嘿——老子怕个毬呀?
桨石走得正啊——吼吼呀嘿——拖绳四股拧呀!
风打拨浪鼓啊——吼吼呀嘿——船身好借势啊!
吼吼呀嘿——吼吼呀嘿——左出龙啊——右跳虎……
吼吼呀嘿——吼吼呀嘿——能耍文啊——能玩武……
一趟跑船,很多船队兄弟们,皆觉得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仿佛自己是从阎王爷的门前溜过来了。
因而,自跑船归来,兄弟们便尽情地“享受生活”,放开吃肉,大碗喝酒,通宵打牌,睡懒觉,干女人……
仅仅是短短几天,很多人便完全没了跑船时的那股子发狠的劲儿,整日里像是晒岸的黄鱼,蔫巴了,呵欠连天,走路都腿打闪闪,稍微一动弹,鼻子像风箱,气喘连连……
而今,这久违的船队号子,又吼喊起来了!
陈叫山浑身似有冲天吸地之豪力,胸膛中跳跳荡荡着一腔滚烫热血——
是的,就是要将兄弟们的豪情调动起来,恢复那种狠劲,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无畏和大勇!
任何时候,人,总不能缺失精——气——神!
兄弟们吼欢了,干疯了,拼了命了,发了狠了!
天空一声闷雷响过,那些被丢失了的过往的豪迈恢弘的灵魂的影子,此际,全然复归于每个人的身上,眼中,口中——
吼吼呀嘿——吼吼呀嘿——左出龙啊——右跳虎……
吼吼呀嘿——吼吼呀嘿——能耍文啊——能玩武……
高高若山的沙袋,像兄弟们傲立的身影,以不屑、嘲讽、鄙夷的眼神,看着脚下那滚滚洪流……
“哈哈哈哈……”
陈叫山大笑着,仰面躺在泥地上,张开双臂,傲迎暴雨,似一只振翅搏击苍穹的雄鹰,笑得天惊地动!
第042章 连环暗斗
将码头上的事情处理妥当,陈叫山才反应过来:怎地没见侯今春呢?
一个船帮的副帮主,在码头遭遇洪水之时,在兄弟们挥汗如雨,战天斗地之时,怎就隐匿不见呢?
昨夜,侯今春去逛萃栖楼,多喝几杯花酒,歇在萃栖楼,直到今儿早上,头还晕乎着……
雨一直下,修造房屋的工匠们,自然不必去卢家大院干活,侯今春便一直在萃栖楼睡着,直到吃午饭时才起了床。
侯今春撑着一把萃栖楼的花纸伞,回到卢家大院,门房老王头一见侯今春,便说,“侯帮主,你上哪儿去了?码头上涨了水了,陈帮主四处问你呢……”
侯今春用鼻子“嗯”了一声,心里却说:就是把整个碾庄码头淹了,关我何事?
一趟跑船,侯今春起初自恃驾船技术老练,在船队之中,自有几分老江湖的资历!可是,船队遭遇断头巨浪时,遭遇龙摆尾时,跟独角龙手下的舟楫客、潜水客,在江上江下大战时,有我侯今春出力卖命的份儿,得了金银财宝,就把我侯今春拨到一边去了?
尤其是返程跑上水时,一个三旺,一个面瓜,处处掣肘着侯今春,让侯今春很没面子,却又奈何不得。
老子跑船时,你们都还他娘的不晓得在那个旮旯里呢!
那么多的金银财宝,要么交给卢家,让夫人来分配,要么,你陈叫山私底下,按照船帮兄弟跑船的功劳大小,悄悄分了……
反正,你陈叫山铺盖里放屁——独吞,就是不行!
起先,少爷卢恩成去找夫人提说过陈叫山私藏金银财宝的事儿,夫人没有搭理。
侯今春觉得:少爷又没有跑船,寸功未立。说话当然屁用不顶!
可我侯今春不一样,我就算没有大功,也有苦劳,在卢家,我是说得上话的。
侯今春撑着萃栖楼的花纸伞,朝夫人的住处走去,蒙蒙细雨中。卢家大院看见侯今春的人,便都晓得侯今春去过萃栖楼。在萃栖楼过过夜了……
来到夫人住处时,侯今春一怔:陈叫山在,谭师爷和卢恩成在,禾巧和卢芸凤也在,五个人围着夫人,像在说着什么事儿……
侯今春一瞧这架势,本想退走,夫人却喊,“今春来了啊。进来进来,进来坐……”
侯今春将萃栖楼的花纸伞,收了,斜靠在门墩旁,屋里的六个人,皆盯着他看……
“侯帮主,今儿早上。码头上都快成海了,你倒还逍遥……”卢芸凤语气淡淡地说,言语中充满了讥讽……
这话要是换作陈叫山来说,侯今春一准就顶上了,可三小姐说这话,弄得侯今春也没脾气。只得低着头,不吭声……
“侯帮主,你这样可真是要不得啊!”谭师爷也板着脸孔说,“天不见亮,陈帮主就赶到码头去抢洪,累了一早上,这才刚回来……”
陈叫山淡淡一笑。心说:谭师爷你这奉承人,拍马溜须的绝活,就不必在这时候施展了吧?
“一趟跑船,下水上水的,侯帮主操心受累,确实辛苦,多休息些时日,也好!”陈叫山正色道。
侯今春咬着牙,将脑袋偏向另一边,很不愿意听陈叫山这“假惺惺”的话……
夫人看着侯今春,将侯今春的心思,猜得透透的,嘴上却说,“今春啊,你来得正好:老帮主在世时,船帮有兄弟违反了帮规,你都参与了惩罚处理。我们现在在商量芸香祠堂受罚的事儿,你也说说想法……”
“夫人,我没啥想法……”侯今春说着话,便屁股离了椅子,准备起身走……
“那你来这儿,总该是找夫人有事吧?”禾巧语气平平地问了一句。
侯今春屁股刚抬一点点,一听禾巧的问,便又坐下了。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卢恩成白了禾巧一眼,甩甩头发,不咸不淡地说,“一个丫鬟,你操什么大心?真是笑话……”
禾巧也不与卢恩成计较,抿了下嘴,微微叹一气,却未说话……
夫人却笑了起来,“恩成,你是卢家大少爷,为卢家,你这大心倒真是没少操啊!”
屋里的气氛,顿时有些肃然、凝滞……
“少爷,你该给禾巧姑娘认个错!”谭师爷忽然变成了和事佬,“禾巧姑娘侍奉夫人这么些年,受夫人点化,聪慧异常,见解非凡啊!”
陈叫山正襟危坐,心下暗说:谭师爷这抬举人的本事,果然不一般,不抬不说,一抬,一下就把夫人和禾巧都抬举了……
谭师爷奉承了禾巧,自然不是白奉承的,铺垫完了,便亮出目的,“禾巧姑娘,关于二小姐祠堂受罚这事儿,我们方才说了那么多,未见你发表意见,你有什么好见解,说与我们分享一番?”
众人皆将目光投向禾巧……
“祠堂受罚,是二小姐的一个态度,也是卢家的一个态度……”禾巧尽管低垂眼帘,但似乎感觉得到大家的目光之聚向,眼帘一挑,“方才大家都说了很多,受罚之方式方法,将两种态度,都得以体现了!我满心钦佩,自然就无须赘言添话了……”
夫人颔首微笑,对禾巧的回答,极为满意……
陈叫山面容淡定,但心下也晓得禾巧回答得极好:禾巧完全不说话,就落了谭师爷的陷阱,谭师爷借此,可以变相地替卢恩成挽回些颜面;但是,禾巧若是不识大体,真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却就显得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了……
禾巧用“两个态度”的概念,将祠堂受罚的事儿,精准概括了,既有自我见解,又言简意赅,没有口若悬河,不识大体……
足可见,谭师爷想给禾巧下套,还是差着招呢!
果然,谭师爷听了禾巧的回答,内心十分失望,又自感尴尬,为掩饰尴尬,只得干笑着,“好,好,好好……”
“好,那祠堂受罚的事儿,就定在后天,谭师爷你就多多辛苦,捋捋家规条律……”夫人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缓缓将茶杯放下,身子朝后靠去,眼睛微微闭了,手指缩进袖管里,开始悉数念珠了……
大家都晓得:这是夫人要散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