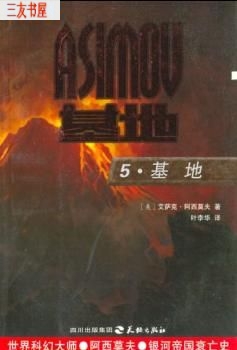云中歌(三部全)-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浓烟中,打斗的人出剑都有些歪斜,孟珏虽是满心诧异,却一面咳嗽着,一面不禁笑起来。
这拿调料做武器的人,估计世间除了他的云歌再无第二个了。
既不是毒药,自然也无药可解。若说解药,唯一的解药就是用清水漱口和冲洗眼睛。
于安因为怕还有人袭击,所以和其他太监都一面流着眼泪咳嗽,一面紧张地护着马车,不敢轻举妄动,只能旁观几个太监和孟珏他们打斗。
云歌拿湿帕子遮住了口鼻,在浓烟中爬到孟珏身旁,向正和孟珏他们打斗的太监们丢了一大捧东西,一声粗叫:“五毒蚀心粉!”
几个太监纷纷下意识地跳开,回避药粉。云歌拽着孟珏就跑,六月和八月忙跟在他们身后。
太监们随即就发现丢在身上的东西居然是茴香子、胡椒子、八角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虽然不知道别的是什么,但想来“五毒蚀心粉”怎么也不会包括茴香,深感上当受骗,大怒着追了上去。
经过云歌点燃的火堆旁,孟珏随手往里面丢了一团东西,一阵白烟腾起,扑鼻的香气替代了辛辣刺激的味道。
孟珏回头说:“奉劝各位不要再追了,这次可绝对是‘童叟无欺,如假包换’的毒药,而且我的毒药绝非一般的毒药,即使你们有解毒圣药,武功也要大打折扣。”
追来的太监虽然都竭力屏住呼吸,可还是脚步虚浮,速度大慢。果如孟珏所言,即使有解药,也有些劲力不继。
云歌指了指树林里那帮刺客留下的马,孟珏三人立即去牵马,云歌却停在了原地,孟珏翻身上马后,看云歌竟然还呆呆站在那,立即策马回身,伸手想拉云歌和他同骑一匹马。
云歌呆呆地看着孟珏,却没有伸手去握他的手。
云歌眉如远山,眼若秋水,原本写意飞扬,此时却眉间蕴着凄楚,目中透着泪意。nMkI。
孟珏惊讶不解:“云歌?”
六月和八月看到那些武功高强到变态的人快要追到,着急地催促:“公子!”
“云歌?”孟珏又叫了一遍,一面策着马向云歌靠近,俯身想直接把她强拎上马。
云歌却跳了开去,在孟珏不能相信的质问眼光中,她决绝地扭过了头,在马后臀上狠打了一下,孟珏的马冲了出去,六月和八月立即打马跟上。
云歌起先点燃的火堆被风吹得不断有火星飞出,遇到枯叶,借着风势,林子内各处都有火燃起,马儿被火惊吓,开始疯跑,孟珏根本无法勒住马,只能在颠簸的马背上,回身盯着云歌,眼中全是疑问和不能相信,云歌却看都不看他一眼。
天,墨般漆黑,地上红焰狂舞。
风在天地间盘旋怒鸣,受惊的马在火光中奔跑闪避,发出长长的嘶鸣。
一抹单薄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孟珏的视线中。
云歌拉住已经被火焰吓得乱跳的马,想要翻身上马。
一个太监眼看着人就要全跑光,气急交加,一时忘了于安说过的“留活口”,随手将手中的剑朝云歌飞掷出。
云歌的身子在刚触到马背的刹那,一阵透心的巨疼从后背传来,她低头困惑地看着自己胸前,不明白怎么会有一截剑刃从胸前冒出,手上鲜红的濡湿又是从哪里来?
她的眼前渐渐发黑,手从马鬃上无力地滑下,身子软软摔落在了地上。
马儿前蹄高高提起,仰头对着天空发出悲鸣,却唤不起主人。只有火光将它定格成了漆黑天空下一道悲凉的剪影。
林间的风呼呼吹着。
火焰随着风势越腾越高,越烧越旺,烧得整个树林都变成了火的海洋,天地间一片血红的透亮。
刘弗陵掀起帘子,走下了马车,静静看着前方熊熊燃烧的大火。
大风吹得他的袍子猎猎作响,在火光的映照下,他的面寒如水,眸沉似星。
云中歌 云中歌(二) 劫后相逢1
云歌被太监拖放到一旁。
拖动的人动作粗鲁,触动了伤口,她痛极反清醒了几分。
隐约听到一个人吩咐准备马匹用具,设法不露痕迹地把她押送到地牢,拿什么口供。
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大火,她眼前的整个世界都是红灿灿的。
在纷乱模糊的人影中,她看到一抹影子,疏离地站在一片火红的世界中。
四周滚烫纷扰,他却冷淡安静。
风吹动着他的衣袍,他的腰间。。。。。。那枚玉佩。。。。。。若隐若现。。。。。。随着火光跳跃。。。。。。飞舞而动的龙。。。。。
因为失血,云歌的脑子早就不清楚。
她只是下意识地挣扎着向那抹影子爬去。
努力地伸手,想去握住那块玉佩,血迹在地上蜿蜒开去。。。。。。
距离那么遥远,她的力量又那么渺小。
努力再努力,挣扎再挣扎。。。。。。
拼尽了全身的力量,在老天眼中不过是几寸的距离。
太监们正在检查尸身,希望可以搜查到证明刺客身份的物品,然后按照于安的命令把检查过的尸体扔到火中焚化。
于安劝了刘弗陵几次上车先行,这里留几个太监善后就行,可刘弗陵只是望着大火出神。
在通天的火焰下,于安只觉皇上看似平淡的神情下透着一股沧楚。
他无法了解皇上此时的心思,也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皇上之前要急匆匆地执意赶去长安,如今却又在这里驻足不前。以皇上的心性,如果说是被几个刺客吓唬住了,根本不可能。
再三琢磨不透,于安也不敢再吭声,只一声不发地站在刘弗陵身后。
大风吹起了他的袍角,云歌嘴里喃喃低叫:“陵。。。。。。陵。。。。。。”
她用了所有能用的力气,以为叫得很大声,可在呼呼的风声中,只是细碎的呜咽。
听到悉悉挲挲声,于安一低头,看到一个满是鲜血和泥土的黑影正伸着手,向他们爬来,似乎想握住皇上的袍角。
他大吃一惊,立即赶了几步上前,脚上用了一点巧力,将云歌踢出去,“一群混帐东西,办事如此拖拉,还不赶紧。。。。。。”
云歌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
在身子翻滚间,她终于看清了那抹影子的面容。
那双眼睛。。。。。那双眼睛。。。。。。
只觉心如被利箭所穿,竟比胸口的伤口更痛。
还未及明白自己的心为何那么痛,人就昏死了过去。
刘弗陵望着大火静站了好半晌,缓缓转身。
于安看皇上上了马车,刚想吩咐继续行路,却听到刘弗陵没有任何温度的声音:“掉头回温泉宫。”
于安怔了一下,立即吩咐:“起驾回骊山。”
可刚行了一段,刘弗陵又说:“掉头去长安。”
于安立即吩咐掉头。
结果才走了盏茶的工夫,刘弗陵敲了敲窗口,命停车。
于安静静等了好久,刘弗陵仍然没有出声,似乎有什么事情难以决断。
于安第一次见皇上如此,猜不出原因,只能试探地问:“皇上,要掉转马车回骊山吗?”
骊山猛地掀开车帘,跳下了马车。
随手点了一个身形和自己几分象的太监:“你扮做朕的样子回骊山,于安,你陪朕进长安,其余人护着马车回骊山。”
于安大惊,想开口劝戒,被刘弗陵的眼锋一扫,身子一个哆嗦,嘴巴赶忙闭上。犹豫了下,却仍然跪下,哀求刘弗陵即使要去长安,也多带几个人。
刘弗陵一面翻身上马,一面说:“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没有人会想到,朕会如此轻率。刚才的刺客应该不是冲着杀朕而来,现今的局势,你根本不必担心朕的安危,走吧!”
于安对皇上的话似懂非懂,骑马行了好一会,才猛然惊觉,皇上的反反复复竟然都是因为那个还没见面的竹公子。
皇上担心自己的反常行动会让竹公子陷入陷境,所以想回去,可又不能割舍,所以才有个刚才的失常之举。
。。。。。。。。。。。。。。
外面风吹得凶,可七里香的老板常叔睡得十分香甜。
梦到自己怀中抱着一块金砖,四周都是黄灿灿的金子,一品居的老板在给他当伙计,他正疯狂地仰天长笑,却突然被人摇醒。
以为是自己的小妾,一边不高兴地嘟哝着,一边伸手去摸,摸到的手,骨节粗大,又冷如冰块,立即一个哆嗦惊醒。
虽然塌前立着的人很可怕,可不知道为什么,常叔的注意力全放在了窗前站着的另一人身上。
只是一抹清淡的影子,可即使在暗夜中,也如明珠般让人不能忽视。
常叔本来惊怕得要叫,声音却一下就消在口中。
天下见有一种人,不言不动,已经可以让人敬畏,更可以让人心安。
来者深夜不请自到,情理上讲“非盗即匪”。可因为那个影子,常叔并不担心自己的生命。
塌前的人似乎十分不满常叔对自己的忽视,手轻轻一抖,剑刃搁在了唱叔的脖子上。
唱叔只觉一股凉意冲头,终于将视线移到了塌前的人身上。
来人斗篷遮着面目,冷冷地盯着他,“既非要钱,也非要命,我问一句,你答一句。”
常叔眨巴了下眼睛。
来人将剑移开几分,“竹公子是男是女?”
“女子,虽然外面都以为是男子,其实是个小姑娘。”
“真名叫什么?”
“云歌,白云的云,歌声的歌,她如此告诉我的,是不是真名,小的也不清楚。”
常叔似看到那个窗前的影子摇晃了一下。
拿剑逼着他的人没有再问话,屋子内一片死寂。
好久后,
一把清冷的声音响起:“她。。。。。。她。。。。。。可好?”
声音中压抑了太多东西,简单的两个字“可好”,沉重得一如人生,如度过了千百个岁月:漫长,艰辛,痛苦,渴盼,欣喜。。。。。。
早就习惯看人眼色行事的常叔这次却分辨不出这个人的感情,该往好了答还是往坏里答才能更取悦来人?
正踌躇间,塌前的人阴恻恻地说:“实话实说。”
“云歌她很好。两位大爷若要找云歌,出门后往左拐,一直走,有两家仅挨着的院子,大一点的是刘病已家,小的就是云歌家了。”
刘弗陵默默转身出了门。
于安拿剑敲了敲常叔的头,“好好睡觉,只是做了一场梦。”
常叔拼命点头。
于安撤剑的刹那,人已经飘到门外,身法迅疾如鬼魅。
常叔不能相信地揉了揉眼睛,哆嗦着缩回被子,闭着眼睛喃喃说:“噩梦,噩梦,都是噩梦。”
来时一路都是疾弛,此时人如愿寻到,刘弗陵反倒一步一步慢走着。
在皇上貌似的淡然下,透着似悲似喜。
于安本来想提醒皇上,天已快亮,他们应该抓紧时间,可感觉到皇上的异样,他选择了沉默地陪着皇上,也一步步慢走着。
“于安,老天究竟在想什么?我竟然已经吃过她做的菜,你当时还建议我召她进宫,可我。。。。。。”可我就是因为心生了知音之感,因为敬重做菜的人,所以反倒只想让她自由自在。还有甘泉宫,居然是我下令将她赶出了甘泉宫,难怪于安后来怎么查探,都查不出是谁在唱歌。
刘弗陵的语声断在口中。
于安没有想到多年后,会冷不丁再次听到皇上的“我”字,心中只觉酸涩,对皇上的问题却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当皇上还不是皇上时,私下里都是“我,我”的,一旦想搞什么鬼把戏,就一脸哀求地叫他“于哥哥”,耍着无赖地逼他一块去捣蛋。吓得他拼命磕头求“殿下,不要叫了,被人听到了,十个奴才也不够杀。”
为了让殿下不叫“哥哥,”就只能一切都答应他,
后来就。。。。。。就变成“朕”了。
一个字就让母子死别,天地顿换。
一切的温暖都消失,只余下了一把冰冷的龙椅。
虽然华贵,却一点不舒服,而且摇摇欲坠,随时会摔死人。
“她在长安已经一年多了。在公主府中,我们只是一墙一隔,甘泉宫中,我们也不过几步之遥。在这个不大却也不小的长安城里,我们究竟错过了多少次?”刘弗陵暗哑的语声与其说是质问,不如说是深深的无奈。
于安不能回答。
此时已经明白云歌就是皇上从十二岁起就在等的人。
已经知道云歌在皇上心中占据的位置。
这么多年,一日日,一月月,一年年下来,他将一切都看在眼内,没有人比他更明白皇上的等待,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皇上的坚持。
白日里,不管在上官桀,霍光处受了多大委屈,只要站在神明台上,眺望着星空时,一切都会平复。
因为降低赋税,减轻刑罚触动了豪族高门的利益,改革的推行步履维艰,可不管遇见多大的阻力,只要赏完星星,就又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因为上官桀,霍光的安排,皇上十三岁时,被逼立了不到六岁的上官小妹为皇后。
可大汉朝的天子,因为一句诺言,居然到现在还未和皇后同房,也未曾有过任何女人。
二十一岁的年纪,不要说妻妾成群,就是孩子都应该不小了。
若是平常百姓家,孩子已经放牛,割猪草;若是豪门大家,孩子已经可以射箭,骑马,甚至可以和兄弟斗心机了。
因为关系到社稷存亡,天家历来最重子裔,先皇十二岁就有第一个女人,其他皇子到了十四五岁,即使没有娶正室,也都会有侍妾,甚至庶出的儿女。
可皇上到如今竟然连侍寝的女人都没有过。
皇上无法对抗所有人,无法对抗命运,可他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诺言。
于安挤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老天这不是让皇上找到了吗?好事多磨,只要找到就好,以后一切都会好的。”
刘弗陵的唇边慢慢露出一丝笑,虽还透着苦涩,却是真正的欣喜,“你说得对,我找到她了。”
说到后一句,刘弗陵的脚步顿然加快。
于安也不禁觉步子轻快起来。
到了常叔指点的房子前,于安刚想上前拍门。
刘弗陵拦住了他,“我自己去敲门。”却在门前站了好一会,都没有动。
于安轻声笑说:“皇上若情怯了,奴才来。”
刘弗陵自嘲一笑,这才开始敲门。
云中歌 云中歌(二) 劫后相逢2
因为心中有事,许平君一个晚上只打了几个盹。
身旁的刘病已似乎也有很多心事,一直不停地翻身。
虽然很轻,可因为许平君只是装睡,他每一次的辗转,许平君都知道。
直到后半夜,刘病已才入睡。
许平君却再躺不下去,索性悄悄披衣起来,开始干活。
正在给鸡剁吃的,忽听到隔壁的敲门声。
她忙放下刀,走到院子门口细听。
敲门声并不大,似怕惊吓了屋内的人,只是让人刚能听见的声音,却一直固执地响着,时间久到即使傻子也知道屋内不可能有人,可敲门声还一直响着,似乎没有人应门,这个声音会永远响下去。
许平君瞅了眼屋内,只能拉开门,轻轻地把院门掩好后,压着声音问:“你们找谁?”
刘弗陵的拳顿在门板前,于安上前作了个揖,“夫人,我们找云歌姑娘。”
云歌在长安城内认识的人,许平君也都认识,此时却是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你们认识云歌?”
于安陪着笑说:“我家公子认识云歌,请问云歌姑娘去哪里了?”
许平君只看到刘弗陵的一个侧影,可只一个侧影也是气宇不凡,让许平君凛然生敬,遂决定实话实说:“云歌已经离开长安了。”
刘弗陵猛然转身,盯问许平君:“你说什么?”
许平君只觉对方目光如电,不怒自威,心中一惊,趔趔趄趄倒退几步,人靠在了门板上,“云歌昨日夜里离开的长安,她说想家了,所以就。。。。。。”
许平君张着嘴,说不出来话。
刚才被此人的气宇震慑,没敢细看。此时才发觉他的眼神虽和病已截然不同,可那双眼睛却。。。。。。有六七分象。
于安等着许平君的“所以”,可许平君只是瞪着皇上看,他忙走了几步,挡住许平君的视线,“云姑娘说过什么时候回来吗?”
许平君回过神来,摇摇头。
于安不甘心地又问:“夫人可知道云姑娘的家在何处?”
许平君又摇摇头,“她家的人似乎都爱游历,各处都有屋产,我只知道这次她去的是西域。”
刘弗陵一个转身就跳上马,如同飞箭一般射了出去。
于安也立即上马,紧追而去。
许平君愣愣看着刘弗陵消失的方向。
回屋时,刘病已正准备起身,一边穿衣服,一边问:“这么早就有人来?”
许平君低着头,忙着手中的活,“王家嫂子来借火绒,”
。。。。。。
从天色朦胧,一直追到天色透亮,只闻马蹄迅疾的声音。
风渐渐停了,阳光分外的好,可于安却觉得比昨夜还冷。如果是昨日就走的,现在哪里追得上?
皇上又如何不明白?
两边的树影飞一般地掠过。
一路疾弛,已经过了骊山。
日头开始西移,可刘弗陵依旧一个劲地打马。
一个老头背着柴,晃晃悠悠地从山上下来。
因为耳朵不灵光,没有听见马蹄声,自顾埋着头就走到了路中间。
等刘弗陵一个转弯间,猛然发现他,已经凶险万分。
老头吓得呆楞在当地。
幸亏刘弗陵座下是汗血宝马,最后一刹那,硬是在刘弗陵的勒令下,生生提起前蹄于安旋身将老头拽了开去。
老头子毫发未损,只背上的柴散了一地。
老头子腿软了一阵子,忙着去收拾地上的柴火。
刘弗陵跳下马帮老头整理柴火,但从没有干过,根本不能明白如何用一根麻绳,就能让大小不一,弯曲不同的柴紧紧地收拢在一起。
老头子气鼓鼓的瞪了眼刘弗陵:“看你这样子就是不会干活的人,别再给我添乱了。”
刘弗陵尴尬地停下了手脚,看向于安,于安立即半躬着身子小声地说:“自小师傅没教过这个,我也不会。”
两个人只能站在一旁,看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干活,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掉得远的柴火拣过来,递给老头。
为了少点尴尬,于安没话找话地问老头:“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要一个人出来拣